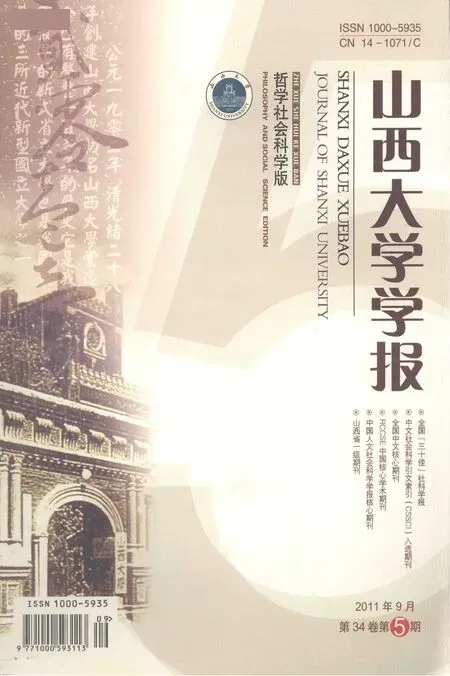制度功能与角色功能视野下的群体性事件
任 龙
(1.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2.武警上海政治学院,上海 200435)
制度功能与角色功能视野下的群体性事件
任 龙1,2
(1.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2.武警上海政治学院,上海 200435)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是,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混淆不清有着密切的关系。公众会根据制度运行的好坏及其作用的发挥来建立政治信任,执政主体也同样依靠制度的良好运行来实现价值追求,赢得公众的政治信任,从而预防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另外,我们还应看到,政治角色通常会被看做特定政治的代表或化身,所以政治角色的所作所为也同样会成为引发或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从确立制度的权威、加强问责制、完善引咎辞职制等方面入手来正确区分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
制度功能;角色功能;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大变革过程中众多矛盾和问题的一种综合反映。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源来说,笔者认为,是制度功能与角色功能的混淆不清。就制度功能而言,公众会根据制度运行的好坏及其作用的发挥程度来构建政治信任,执政主体也会依靠制度的良好运行来实现价值追求,获取公众的政治信任,预防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角色功能来讲,一般来说政治角色往往会被看做特定政治的化身,所以,政治角色自身的表现和作用,就会成为引发或预防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源头。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表现优秀的政治角色能够确立起较为广泛的政治信任,而表现失败的政治角色则易于引发或激发群体性事件。因此,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的正确区分意义重大。
一 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群体性事件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已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公安部2000年4月5日下发的《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首次使用了“群体性治安事件”一语。《规定》的第二条指出:“本规定所称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行为”。2004年,国务院委托专家完成了“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报告。2005年第一次有了“群体性事件”这种提法:7月7日,李景田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
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的,一部分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临时形成的规模性聚集的群体活动、并发生多数人之间语言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的各种事件,或表达诉求、主张,或直接争取、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事端,因而对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的大事情。从政治学角度来看,群体性事件是执政党和政府在调整阶级矛盾、利益群体矛盾、民族关系及国际关系等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历史等原因所产生的必然现象,是关系到国家稳定和执政党地位的大事。
二 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混淆不清与群体性事件频发
深入分析群体性事件,可以发现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都会影响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或升级。虽然我们在推进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力求做到帕累托改进,要求改革的设计尽量满足各方利益诉求,但实际上这是很难全面兼顾的,而会出现利益的受损者。同时,如果“一旦正常的诉求渠道在一些地方不能得到认真落实,或者使公众对这样的方式失去信心的话,那么非正式的方式和渠道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这种带有暴力倾向的非制度性表达,将会影响中国民主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1]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学,所以要想决策的全过程不出一点问题,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如果再加上政治腐败现象的存在,就可能会形成极端行为。
很显然,如果把什么都与群体性事件关联在一起,这绝不是一件好事,再不分原因、主次地去分析和解读也必然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那么,我们就面临着怎样正确看待引发群体性事件各种因素的问题和应该以什么为主来预防或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问题。
而当前的一个现实是,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混淆不清与群体性事件频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多数群体性事件是由于角色出现异化或腐败而导致的。高度的制度化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点之一。我们应该看到,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是互为补充的,但从根本上说,政治最基本的依托应当是制度。相对角色功能来讲,制度功能更能反映政治的本质。制度还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所以,公众在认识和解读制度功能的过程中会生成比较持久和巩固的政治信任;同样,政党和国家从制度功能中生成的政治信任也比较可靠和稳定,这都对预防或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角色功能则没有这样的特点,而是具有具体化和个性化的特色。与传统政治中角色大于制度不同,现代政治制度中,角色是依附于制度的。我国正处于转型期,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角色大于制度的现象,然而,这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当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达到能够将法理型权威置于最高地位时,那么对精英人物的人格崇拜及人格魅力的崇拜,即克里斯玛型权威,就会影响整个社会。角色功能运用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社会管理的成本可以大大减少。威信高的政治角色可以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在实现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他可以做到廉价、高效、顺利地达成工作任务。这种现象也将产生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制度成了角色的附属物;就会出现小平同志所批评的领导人一变化,制度也会随之而变化的糟糕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将会产生:政治角色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与一项或几项制度的存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政治角色出现了异化或腐败,那么他必然会影响到其“代表”的制度和体制。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4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2]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两次腐败高峰,一次是80年代中期部分沿海地区走私严重,一次是80年代中后期由于价格双轨制的存在造成的“官倒”现象的存在。[3]“官倒”大都是有着权力背景的人或接近权力的人,当时一度造成了社会对政治权力的质疑,政府也遭受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就是在社会主义的体系中,要想完全彻底地避免角色出现异化和腐败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毋庸怀疑,这些政治角色都代表着特定的制度或体系,如果非要把这些角色与所在的体系,比如党的体系、政府体系、人民代表大会的体系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地将角色的异化和腐败与制度的演化和腐败画上等号,必然会怀疑制度乃至得出否定制度的荒谬结论,最终还可能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一旦出现角色功能的异化,人民群众就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去看待一切,如果再从这一角度去认识和解读政治信任就会遭遇到巨大的危机,而且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就会大幅增加。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我们确确实实已经面临着这样的情况。所以,要正确解读角色功能和制度功能,构建政治信任以制度功能为主,这样才可以避免人民群众对角色功能的依赖和不当关联,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三 正确区分制度功能与角色功能
从确立制度的权威、加强问责制、完善引咎辞职制入手,正确区分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对于强化政治信任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应当作为根本大事来抓。
(一)确立制度的权威
区分制度和角色的重要前提,肯定是要确立制度权威,绝不是个人权威。制度权威实际上就是人对制度的服从关系,一般分为正式制度权威和非正式制度权威。正式制度权威基于外在的某种强制力量,通常配有较为严厉的惩罚措施,为了确保人们对制度的服从也依靠法定暴力的运用;非正式制度权威基于社会舆论和人信仰的力量,为了实现人对制度的自觉服从通常是依靠行为习惯和道德良知。“虽然道德制度不像法律制度那样明确,但却往往扎根于人们灵魂的深处,起着更为深刻的作用”。[4]确立制度的权威是依法治国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必然诉求。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实现当家做主、参政议政的基本途径,是政府依法治理,实现善治的价值诉求,更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所以,实行依法治国,既有利于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党和政府的威信,提升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和增强公民的参政意识与政治认同意识,夯实政治制度的权威基础,又有利于提高人们对国家法律与政策的认同感和服从制度的自觉性,强化制度权威的意识。实行依法治国,确立制度权威,我们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努力:一是确立法律最高权威。法律最高权威的地位实际上就是要做到“法律至上”,这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前提。它要求无论什么组织和个人都必须要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一旦触犯了法律,都必须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行政决策必须依法,力戒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官大于法、权大于法等不良思想的影响,缩小领导者自由裁量的空间,真正使制度大于角色。二是拓宽双向沟通渠道。只有积极拓展双向沟通的渠道,使政府及时获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使公民获得广泛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的机会,才能既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调动公民的参与积极性,保障公民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权利,又增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增加政治系统运行过程的透明度。三是完善法律制度的程序。重视法律行为的结果,更加需要关注法律行为的形成过程,这是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因此,法律制度的正义体现在:既要做到实体的正义,更要做到程序的正义,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为重要。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建立制度权威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制度合法化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将既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以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给这种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5]。另外,具体的法律程序是实体正义得到最终实现的重要途径,因此法律程序是确立法律制度权威,维护其公平与正义的重要保障,也是正确区分制度功能与角色功能的关键环节。
(二)建立健全问责制
在制度大于角色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政府官员的问责制,是推进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正确区分的一个重要环节。问责制不仅仅是一个人事管理的问题,其意义也远不仅仅在于客观、公正地对待干部,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清晰地界定制度功能和角色功能,凡是与制度无关的属于角色所犯的错误,一定要彻底追究角色所需要担负的责任。在制度设计这个问题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巧妙之处在于,他们实施问责制通常是把问题都归咎到政治角色身上,这样可以用追究角色所犯的错误来回避政治制度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或制度危机,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以角色的不断牺牲来换取对制度的持续支持和政治生存的空间。比如,有一项欧洲民意调查表明,即使那些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问题的国家,也“对政府的民主形式感到满意”[6]。这就说明,西方国家存在的很多问题,应该属于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大都可以从制度层面上找到真正原因。
就我国而言,目前实施行政问责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需要注意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一是问责主体要多元化。要想保证行政问责的有效,确立好问责主体是一个重要前提。在我国,行政问责的主体包括了行政系统内部和行政系统外部两个方面,行政系统内部的问责主体主要有上级行政机关,审计、监察机关;行政系统外的问责主体主要有新闻媒体、社会机构、人民群众等。问责主体只有具有多样性、广泛性、普遍性,才能保证问责结果的客观性、权威性、公正性。二是问责标准要统一。2009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界定了实施问责的7种情形,这虽然使问责比起前更具有针对性,但其弊端是无法涵盖需要问责的全部情况。所以笔者认为,为确保问责的严肃和公正,倒不如确定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标准,这样更具有操作性和有效性。三是权责范围要相一致。权责相一致的原则必须贯穿于行政问责的始终。职权与职责相一致,就是要求在进行问责时要严格划定责任对象的范围。也就是说,既不能让责任人(即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责任的那些人)逍遥法外,也不能让无辜的人受罪。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理当在多大的范围内进行问责。如果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长此以往问责便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四是要保证问责方式的权威性。保证问责方式的权威性,关键在于规范和完善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避免将问责流于形式。我们既不能将被问责官员一棍子打死,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更不能把问责的一年禁期,仅仅当作暂缓使用期,熬过一年,或官复原职,或易地易岗任职,这样就完全失去行政问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最终也必将影响公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五是要健全问责监督机制。建立系统、全面而有效的责任监督机制是实现有效问责的基础工作,也是建立责任政府的基础要件。健全问责监督机制,重要的是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和行政系统外部监督应相辅相成、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因为,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弹性较大,刚性不足,而必须依靠行政系统外部监督作为支撑和辅助,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应包含人民群众、新闻传媒、民主党派、人大代表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三)完善引咎辞职制
对于政治角色功能的认定和处置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反思。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界定角色所犯的错误,或者说,角色应充分承担自己的责任。角色在其职责范围内的责任,不论其有没有犯错误都不应被推卸掉,这不应该归咎为冤枉或个人运气不好,因为责任是客观存在的,错误也是要追究的,同时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和责任政治的要求,更是政治信任建设的重要机制。当然,如果制度或机制真的存在问题,也应该对制度和机制进行调整和完善,但实际上存在的大量情况恰恰相反,就是角色存在错误和责任。因此,完善引咎辞职制便成为应有之举。《公务员法》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于2005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这标志着把引咎辞职制度真正纳入了法治的轨道。引咎辞职制度实行的意义在于:将“责”与“权”有效相连,体现了政府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仅是从体制上体现了监督、惩罚的作用,更是从心理上警醒政府和领导干部合理、合法行使权力,同时,对于政府良好形象的塑造,政治信任的增强,提高行政权力行使的有效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目前完善我国引咎辞职制度来说,应当着重把握几个原则:一是不进行易地任职。对于引咎辞职的干部,一般应不再安排其担任领导职务,更不能以轮岗或交流的名义到易地担任领导职务,但是其可以改任非领导职务。二是倡导主动从优、被动从严。是否能够妥善安置好引咎辞职的干部,关系到引咎辞职制度能否成功、有效地实施。一般来说,考虑到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减少干部制度改革阻力,对引咎辞职的干部,应遵循“主动从优、被动从严”原则来安排其待遇。引咎辞职是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个人主动提出的,应该是个人的自辞,但实际上有时候也可能会出现组织劝辞的现象,组织劝诫在前,本人请辞在后,客观上属于被动辞职。所以,对主动辞职的领导干部,要给予鼓励,待遇上一般可以保持基本不变;对组织劝辞的干部,待遇应与主动辞职者区别开来,对那些劝辞不辞者,可以将其就地撤职或免职。三是引咎辞职应与行政追究相结合。引咎辞职是个人的一种合法权利,不属于行政处分,是一种体面的下台。那么,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是不是就意味着发生事故或问题后可以一辞了事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引咎辞职是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绝不能因此而避免党政处分或行政处罚,而是要根据辞职者在任期间所犯“咎”的程度及原因,相应给予处分。
[1]李季平.民意诉求边缘化与诽谤干部[N].现在快报,2007-05-21.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2.
[3]邵 丛.反腐 57年:从“运动”到制度[J/OL].http://view.news.qq.com,2006 -09 -08.
[4]李松玉.制度权威研究:制度规范与社会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2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104.
[6]孟庆存.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博士论文,2003:104.
(责任编辑 郭庆华)
Group Events in Perspective of System Function and Role Function
REN Long1,2
(1.Nanjing Political College of Shanghai,Shanghai200433,China;
2.The Shanghai CAPF Institute of Politics,Shanghai200435,China)
Group events are the comprehensive reflection of all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The reality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is that the frequent occurance of group events is closly related to the confusion between system function and role function.The public will generate their own political trust based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and the role it plays.The ruling subject also depends on system operation to achieve its pursuit of value and the ideological commitment to win political trust,so as to prevent or reduce group events.Besides,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political role is often viewed as a specific political embodiment.Therefore,political role performance and effect also become the important factor in triggering or preventing group events.That’s why system function and role functio should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such aspects as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al authority,enhancing fault investigation and improving blame-aking resignation system.
system function;role function;group events
D669
A
1000-5935(2011)05-0087-04
2011-06-23
任 龙(1977-),男,河北涿州人,军队政治工作学博士,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武警上海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党的建设和政治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