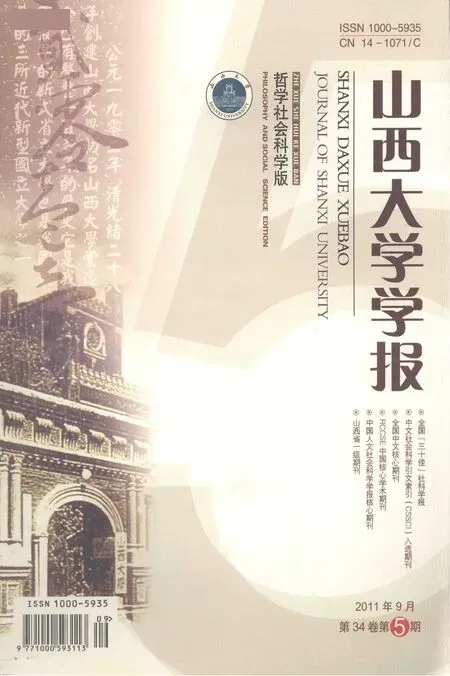中外慈善事业的政府规制比较研究
王华春,周 悦,崔 炜
(1.北京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2.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北京 100053)
中外慈善事业的政府规制比较研究
王华春1,周 悦1,崔 炜2
(1.北京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2.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北京 100053)
国外慈善事业的政府规制因制度规范、法律完善、监督全面等因素极大促进了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慈善事业的政府规制尚处于摸索阶段,需要选择性地借鉴和学习西方经验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文章首先概述了国内外慈善事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其次从管理体制、组织规制、经济规制、法律规制和监督体制上对国内外政府规制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找出差距、提出建议,最后引出我国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的规制展望。
慈善事业;政府规制;比较研究
一 国内外慈善事业的发展概况
在国外,慈善事业起步较早,发展至今日臻成熟,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文化积淀和制度积淀保障,慈善事业发展蒸蒸日上,为公众福利和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以美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为例,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慈善捐赠规模大,2009年,美国慈善捐赠占GDP的规模是2.2%;二是慈善组织发展好,2009年美国各类基金会达到75 595个,美国基金会的资产是5 834亿美元,2009年支出429亿美元;三是公众捐赠为主体,2009年美国各类慈善捐赠达到3 037亿美元,其中个人捐赠达到274亿元,基金会捐赠300多亿元,企业捐赠140多亿元。据统计75%的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款,每个家庭年均约1 000多美元;四是富人捐赠数量多,2010年8月底,已有40多名美国亿万富翁承诺至少拿出一半的身家来做慈善;五是义工制度较完善,据统计美国13岁以上人口中的50%每周平均志愿服务4个小时,美国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捐赠比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要更加平衡。[1]
在国内,中华民族的慈善事业由来已久,但真正的快速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民生的需求、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响应,慈善事业突飞猛进,逐步成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有效补充。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慈善捐赠规模较小,2009年我国社会捐赠量稳步增加,达332亿元,增长3.5%。但中国与美国、英国、巴西、印度相比,慈善捐赠规模最少,所占GDP比例最低,捐赠占GDP的比例仅为0.01%;二是慈善组织发展不成熟,全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截至2009年已达43.1万个,其中,只有1 800个基金会,中国2009年基金会的资产只有300多亿元人民币,支出440亿元;三是企业捐赠为主体,民营企业捐出总额超过54.27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额的41.35%,占境内捐赠总额的20.39%;四是相关制度欠缺,我国并没有出台相关的义工政策和规定,社会中的义工活动多为自发性行为。[2]
二 国内外慈善事业的政府规制比较
(一)国内外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体制
国外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体制总体比较成熟完善,有明确的部门分工和特定的政策法规,政府为慈善组织发展提供了比较宽容的政策环境,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不是控制和隶属关系,而是平等、合作与共赢的关系。在美国,慈善组织凸显其民间性、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在发展中遵循了自主规划、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主经营的模式。美国没有专门管理慈善组织的部门,但是管理的主体是税务部门和法律部门,较多运用了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加拿大,慈善组织已经成为并立于政府、市场的第三大组织,慈善组织接受志愿者理事会的统一管理,并与其签订了完善二者关系的“加拿大政府和志愿部门联合倡议”,规定了双方的义务和权利,有助于完善政府的行政支持体系,提升慈善组织服务公众的能力。[3]
国内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管理体制尚处于摸索阶段,各部门之间职能重叠、相关法律未成体系,慈善组织并未真正实现其民间特性和自主发展,政府在与慈善组织关系中处于领导和控制地位,慈善事业的发展受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度和法规影响较大。按照我国管理制度,慈善组织必须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而登记管理机关的审查较为严格,业务主管部门的申请门槛也比较高,使众多慈善组织游离于体制和制度之外。慈善组织在财务上需要接受政府部门的严格审计,在人事任用上往往听从政府安排,在慈善救助实施上大多遵从政府意愿,总之我国慈善组织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财务和人事上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在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平等合作中较为薄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并未普及。
(二)国内外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组织规制
在国外,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组织规制表现在准入机制和日常规制上。在美国,慈善组织的注册可以有多样化选择。慈善组织必须先向其所在州正式提出结社要求,从美国税收当局即美国联邦国税局获得慈善团体的身份,运营执照不需要政府部门批准。[4]当需要公募基金时,需要在筹款地所在州登记注册。而一些专项领域可以不需要向任何政府部门登记或由政府批准。新加坡政府在慈善组织注册方面没有严格的限制,只要是以慈善为前提、并由高等法院管辖的组织即可称为慈善组织。新加坡政府更加注重对慈善组织的日常发展和管理上的规制,施行严格的日常规章和惩罚性制度。美国学者贾纳·E·赫兹琳提出“披露—分析—发布—惩罚”的组织规制方法,强调慈善组织规制的实时化、日常化和全程化。
在国内,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组织规制表现在重准入、轻日常,重事前、轻事后,重激励、轻惩戒。业务主管部门更倾向于对慈善组织准入的审核和管理上,而忽视了日常的管理和监督,在准入制度上规定比较详细,但是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因此在准入制度上的审核往往流于形式。在慈善组织的日常活动管理上效果并不明显,尤其是对慈善资源的募集、使用和增值上,缺乏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致使近年来慈善资源违规操作的案例时有发生。在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方面,公众仍然处于被动接受角色,难以实现与慈善组织的有效互动。在慈善组织管理的惩罚机制上尚不完善,缺乏对捐赠人违约的制度约束,缺乏对慈善组织涉嫌违规的有力约束,难以从制度上予以震慑和保障。
(三)国内外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经济规制
在国外,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经济规制主要表现在税收规制上。美国制定了详细的与捐赠相关的税收政策,既有正向鼓励个人或组织捐赠的慈善捐款免税的优惠制度,也有反向促进社会资源向慈善资源倾斜的超额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双效合一的税收制度设计极大促进了西方中上收入阶层设立基金会、捐献慈善事业的主动性,提高了普通公众向慈善组织捐款的积极性。英国《遗产税法》有关免税和扣除的规定中,对慈善捐赠,国家公益事业,以土地、建筑物、艺术品等财产的捐赠免税。加拿大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在所得税额75%以内即可税前扣除。印度个人、团体捐赠可获得捐赠额50%的减免税权。中国香港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每年慈善捐款超过100港元,可在息税和利得税中扣除相等款数。
中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税收规制表现为,企业或个人的慈善捐赠免税起点较高,免税比例较低,税收优惠政策适用主体不平等。200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才规定:内外资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相比于之前的3%的扣除比例有很大进步,但较之国外的税收优惠还有一定差距。[5]在慈善捐赠税收的全额减免政策上,只对特定的教育事业、老年服务机构、青少年活动场所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红十字等基金会允许全额在税前扣除,其他慈善组织并不适用,在慈善捐赠上设置了优惠壁垒,造成慈善组织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缩小了公众的选择范围,容易在慈善组织发展上形成“马太效应”,客观上阻碍了中小民间慈善组织的运作和发展。
(四)国内外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法律规制
国外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法律规制历史悠久,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断修正完善形成一整套法律体系和标准。在英国,慈善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期有关慈善组织的法律条文散见于相关法规中,1853年,英国正式颁布《慈善法》,并在1993年进行了修改。1860年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慈善委员会”,并一直延续至今。在日本,1998年通过了《促进特定非营利活动法》(又称《非营利组织法》),2003年5月开始实施修改后的新法。[6]这部法律明确了非营利组织的设立标准,减少了政府的裁量权,取消了财产限制,缩短了审批手续,给日本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更加宽松、更加积极的环境。法国的《非营利社团法》是专门针对非营利社团的一部法律。
中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法律规制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指导性法律,而是散见于其他法律之中,在一些领域尚存在法律空白,在一些领域法律规定尚需进一步细化。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法规,但并没有一部原则性、指导性的专门法律。对于近年来慈善事业中出现的新动向、新情况、新问题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处于法律和制度空白阶段,这包括慈善组织的认定、注册、管理和监督,以及公益产权的保护、增值和转让。在慈善组织的捐赠和登记等领域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教条化和概括化,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五)国内外政府对慈善事业的行业规制
国外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监督体制是全方位、多元主体监督形式,包括政府监督、公众监督、媒体监督、第三方机构监督、行业监督和自我监督。美国的慈善机构行业协会的监督作用较为突出,全国性行业协会(社团),如“美国基金会理事会”、“独立部门”、“董事会资源”等,基金会、慈善服务机构、民间研究机构、信息公司等组织,促进会员之间的信息共享、交流合作和相互监督。[7]美国第三方机构评估也相对完善,美国“指南星公司”、“慈善导航”等是专门对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具有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进行信息公开和机构评估的公共慈善机构。加拿大注重慈善机构内部监督,制定了一整套严格、规范的管理规则,由社会选举的董事会实施管理,慈善机构聘用志愿的注册会计师进行账务处理和内部审计。[8]
在我国,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监督体制尚不完善,政府部门监督过于分散,媒体监督作用逐渐增强,第三方监督与行业监督尚属空白,公众监督与自我监督并无实效。我国政府的民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审计部门和人民银行都对慈善组织负有监督责任,在监督中容易出现相互推诿、职能重叠、相互摩擦的状况,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媒体监督虽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但是毕竟是针对某一个事件做出的报道,缺乏系统性和体系化的监督。第三方的评估部门和慈善组织行业协会在我国并未真正普及,虽然建立了《慈善民间组织评估标准》,但评估主体的缺失使得评估运作受阻。公众监督与自我监督受到信息不对称、利益相关性弊端的限制难以形成客观有效的约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慈善组织存在的问题。
三 中国慈善事业的政府规制展望
(一)明确政府定位、理顺政社关系,形成良性互动
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首要问题就是需要理顺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职能定位,构建二者平等合作的互动关系。政府应当逐步放宽对慈善组织的控制,尊重其民间性和非政府性,在慈善事业的财政和人事管理上适当放权,致力于外部监督而非内部控制,尤其在人员编制上应多多吸纳社会专业人才,并逐步形成工作人员+社会义工的慈善服务模式。[9]政府应当逐步改变双重管理体制,设立专门的单一的管理慈善事业的组织或部门,赋予慈善事业相对宽松、适宜、自主的发展环境。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职能定位应当着眼于慈善政策的制定者、慈善法律的执行者、慈善资源的监督者、慈善活动的支持者、慈善服务的购买者和慈善事业的合作者。政府应当专注于擅长的领域和范围,将部分公共服务事项通过直接拨款或公开招标的方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慈善组织)来完成,最后根据中标者所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支付服务费用。
(二)改革准入机制、完善惩罚机制,形成常态管理机制
我国对慈善事业的组织规制应当建立事前准入、事中管理与事后惩戒退出的宽严相济机制,形成常态管理和全面管理机制。在慈善组织的成立申请上应当适当放宽准入机制,对于适应公众需求、促进社会发展、符合国情和民情的慈善组织申请应当予以支持和鼓励,在注册手续上简化办理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在准入条件上适度降低准入门槛、吸纳更多优势资源。在慈善组织的管理上应当注册准入与日常监管同抓并举,尤其对于慈善组织的日常监管应当常抓不懈。尤其在慈善组织的财务审查中,应尽早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财务审查制度,执行国际通用关键指标即最低限年度支出、行政开支比重等,国际上的参考数据是,澳大利亚的最低限年度支出比例为85%,新加坡为80%,日本和韩国为50%,在慈善支出上不仅保障活动开展而且要量入为出。[10]在慈善组织的惩戒机制上,建立问责制,杜绝出现问题并未给予相应的惩处,应当做到责任落实到人、事故追查到底、惩戒从严从重。
(三)加大税收优惠、破除经济壁垒,促进公平竞争发展
我国关于慈善事业的税收政策的制定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原则,破除经济性壁垒,促进不同发展水平的慈善组织有序、合理、自由竞争。在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上,首要解决的是遗产税和赠与税的问题,应当督促相关部门抓紧制定并逐步落实,从根本上保障慈善捐赠的规模和数量。在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与慈善活动的普及,应当逐步放宽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额度,提高企业或个人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向慈善组织捐赠的组织和个人享有应缴税所得额扣除和财产税减免。[11]在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上,政府应当逐步改变目前带有指向性、特定性的优惠倾向,破除优势慈善组织与劣势慈善组织之间的经济壁垒,只要是用于公益救济性捐赠,无论捐赠人选择哪个慈善组织,都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在对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上,应当区分慈善组织直接税收形式和间接税收形式,促使慈善资金实现合理投资保值增值。
(四)完善法律规章、弥补法律缺位,形成完善法律体系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专门的慈善法律,在法律制定和完善过程中应当遵循缺位补位、越位让位、错位正位的原则,形成完善的慈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针对慈善组织的立法层次较低,缺乏专门的高位法,应当尽早出台实施《慈善事业促进法》,厘清政社关系与政府责任,明确慈善事业性质与发展方向,为慈善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基础。在慈善法律的实施中应当坚持遵循原则纲领、适度灵活变通的原则,完善慈善组织的组织结构、资产运行和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完善善款使用信息公开的规定,实现公众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双向互动信息平台,而非单向的信息查询和业务询问。在慈善法规的查遗补漏上,应当针对目前股权捐赠、网络募捐等新的捐赠形式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加以管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应当对存在争议的公益产权的保护、分配和增值进行制度约束,应当对法律较为薄弱的慈善认证体系、评价体系、监督体系进行规范化管理。
(五)改革政出多门、引入多元监督,形成全面监督体制
我国对慈善事业的监督体系应当适应我国国情,明确政府监管主体,完善媒体监管与公众监管,建立第三方监管和自我监管,形成全面监督体系。政府监管应当尽快统一各部门的职能和分工,建立专门的监督部门,制定统一的监督制度和协调制度,形成对慈善组织有效、专业的监督。在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方面,应当尊重公众意愿和公众权利,保障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有权要求相关责任部门提供全面、透明、准确的信息,提高舆论监督的力度和公众民主权利。在第三方监督方面,应当尽快出台与国际接轨的慈善组织评估标准实施细则,提高慈善组织评估的准确性、有效性、及时性,第三方监督部门应当独立于政府、慈善组织等利益相关组织之外,不受制于任何一方,任用专业的公益人才和财务人才执行,在决策和评估中保持中立和原则。[12]在慈善组织的自我监管中既包括行业协会监管也包括慈善组织内部监管,自我约束机制需要用统一、完善的行业内部自律制度保障。
[1]杨 团.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0-185.
[2]李怡心.关于国外慈善事业的研究综述[J].道德与文明,2006(2):16-19.
[3]孙 倩.美国的慈善事业[J].学会,2003(6):53 -55.
[4]田 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一个研究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04(5):88-95.
[5]许 琳.论中国当代慈善事业参与主体[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82-87.
[6]郑功成.中华慈善事业[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136-157.
[7]杨 团,葛道顺.和谐社会与慈善事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95-220.
[8]姚俭建,Janetcolhns.美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分析:一种比较视角[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11):13-19.
[9]姚俭建,黄 丹.当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战略路径探讨[J].社会科学,2003(8):75 -79.
[10]任振兴,江治强.中外慈善事业发展比较分析——兼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道路[J].学习与实践,2007(3):113-119.
[11]王 名.国内外民间组织管理的经验与启示[J].学会,2006(2):23-26.
[12]朱 力.起步中的中国慈善事业[J].南京社会科学,2000(12):37-40.
(责任编辑 李雪枫)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Philanthropy at Home and Abroard
WANG Hua - chun1,ZHOU Yue1,CUI Wei2
(1.School of Managemen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2.Social Welfare Centre of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ijing100053,China)
Foreign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philanthropy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with standardized system,sound legal system,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and other factors.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philanthropy in China is still at the exploratory stage,so we should selectively learn from western experience to promote better and faster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then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philanthropy from the management system,organizational regulation,economic regulation,legal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thus to identify the gap,offer suggestions,and produce the final development prospect for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philanthropy.
philanthropy;government regulation;comparative study
D67.36
A
1000-5935(2011)05-0073-04
2011-05-16
王华春(1976-),男,四川合江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公共参与治理、发展经济学、房地产管理研究;
周 悦(1986-),女,河北乐亭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共福利与慈善事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
崔 炜(1982-),男,内蒙古乌海人,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慈善与社会保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