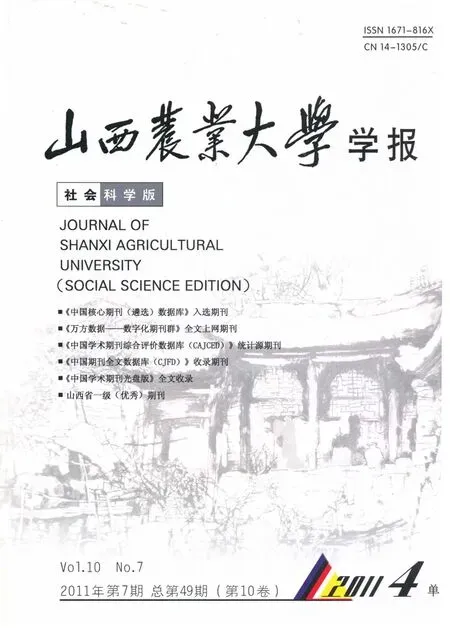清末民初华北乡村中的“好汉”群体——以山西忻州为例
潘慧生
(忻州师范学院政史系,山西忻州034000)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长期以来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将不同经济基础但生活在同一块乡村土地上的农民划开来”。[1]但仅仅强调财产占有来确定乡村社会成员的阶层属性以及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显然忽视了地缘、血缘关系。此外,韦伯主张的从经济、权力和声誉三个角度判断社会成员阶层归属的理论,在学界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共鸣。但韦伯的理论是源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其方法论特点是个人或个人主义的,且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模式有很大区别。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开始以乡村民众自身的视角与感受为基点来论述社区成员的阶层归属,如美国学者姜士彬提出:“晚清中华帝国阶层划分基于三点重要的区别:教育、法权和经济地位。中国的社会分层便按照从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特权、处于主导地位的精英到目不识丁、处于依附地位的普通人依次排列。”[2]渠桂萍、王先明的 《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将“潜藏在乡村民众分层意识中的由多种要素融化聚合而成的分层标尺归纳为 ‘乡土资源’”,[3]指出乡村正是以 “乡土资源”占有程度为区划标准,将社区成员的归属区分为 “士绅领袖”阶层、“能力型”阶层、“普通民众”阶层和 “劣势”阶层,并分析了各自的特征。作者在论述能力型阶层特征时指出:“与有一定家世、文化权威、道德威望支持的 ‘人格魅力型’士绅阶层相比,他们没有权威性社区地位,也不一定能得到乡民的尊崇与爱戴,甚至为乡民所恶,其有限支配地位主要归功于他们所特有的社会资源——‘能力’。”“在乡村普通成员的社会意识中,‘士绅领袖’的声望是超社区的,而 ‘能力型’阶层与乡村普通成员的社会距离较近。”[4]之后,渠桂萍在 《清末与民国时期华北乡村中 “能力型”阶层》一文中,站在民众视角,尝试将 “能力型”阶层分为声望型、技能型与无赖型三种。[4]以上学者的研究基本理清了近代乡村社会分层的情况。但笔者认为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2007年笔者在晋北一些县市的乡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村民常提到村中某人是 “好汉”,说这人尚武、有侠义行为、厉害等。为此,笔者于2009年在山西省忻州市部分农村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调查。在调查中,笔者感知,乡民在谈及 “好汉”时并没有将其归于传统乡村社会阶层,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评价其行为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笔者根据田野调查中所获取的有关清末到民国年间山西忻州 “好汉”的经历和传说资料,力求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系统归纳这一群体的基本类型并探究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二、“好汉”群体的类型及其特征
在乡民视野中,“好汉”群体主要指沉浮于民间,凭借 “强力”活跃在乡村的特殊社会人群。虽然在村庄的道德评价体系中他们不一定能得到乡民的尊崇与爱戴,有些甚至为乡民所鄙夷,可是他们在社区中却拥有一定的支配权,甚至有些还获取了村庄权力。他们支配力的获得主要缘于他们的 “强力”,这种 “强力”是村中一般成员无法达到的,即 “精通武功、胆识超群、无所畏惧、敢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笔者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力求站在乡民视野尝试将这一群体分为精英型、好赖型和无赖型三种类型。
(一)精英型
“精英”是 “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不是对社会结构体系中某一阶层或阶级定位的精确指称,而是基于社会控制体系中对社会成员地位的一个模糊性描述”。[5]学界在论述清末到民国年间乡村社会时,都要提及地方精英、乡村绅士等。笔者这里论及的 “精英型好汉”既非地方精英,也非乡村绅士,其突出特征是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崇尚武力,为人正义。他们与地方名流、社会精英交往较多。乡民往往用 “厉害、公正、有能力、人缘好、好人坏人都交往、有较强的号召能力,坏人怕他们、能为村中办实事”等来表述或评价他们。在乡民看来他们具有维护村庄利益的能力,因此,有很多人被村民推上村庄的权力舞台。
如清末民初忻府区奇村的邓绍禹,生于耕读家庭,一生崇尚武力,秉性放荡,交游极广,能写善画,信奉只有人服我,不能我服人。由于他本人厉害,交际广,办事公道,在1918被奇村商界和村民推为村长。①奇村邓莲溪(1915-2005)《祖先生平简历》稿本及2009年9月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邓秀明及部分村民口述。石家庄村人段景茂,“尚武、厉害、正直,敢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于1917年任村长。②2009年7月忻州市忻府区石家庄村段黄香(74岁)和段如州(54岁)口述。忻州市原平镇太平街人田梅,从小喜爱武术摔跤,一生致力于公益事业,有较高的声誉。[6]
(二)好赖型
“好汉”群体中的 “好赖型”主要是崇尚武力,以力量强人的形象活跃在乡村社会。他们体格健壮、饮酒赌博;交朋结友,仗义疏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且无法无天,信奉别人厉害,他更厉害,但从不欺压普通百姓,一般以文盲居多,属于 “红道” “黑道”的两路人。他们拥有的资源较为单一,缺乏相当的学识和财产作为支撑,对村庄事务涉足较少,在乡村社会的支配力较有限。乡民对他们又畏又敬,往往用 “好赖人”来称述他们。这一类是以活跃于晋北和内蒙古地区的 “十大野鬼”为代表,③有关十大野鬼有两种说法,其一依据2009年10月忻州市科委张六金提供的 《忻州十大野鬼小考》稿本,是赵贵根、二官金、金钱豹、罗成生、杜良喜、毛周祥、彭喇嘛、米宝泉、邢炳英、扬大汉,全部为忻州市忻府区人。其二依据2009年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马步升著的 《走西口》,是赵贵根、张占魁、赵有禄、赵喜禄、郑作霖、张永善、马有才、赵永、毛周祥,有一人不可考,其余的除三人是忻府区人外,其余无法考证其籍贯。米宝泉情况,依据2009年10月忻州市科委张六金提供的 《忻州十大野鬼小考》稿本。在忻州城乡和内蒙古地区有关他们的传说甚多。
如位居十大野鬼之首,生活在清末到民国年间的忻州东楼村的赵贵根,因其武艺高超、爱打抱不平、基本以赌博为生,人称 “仁义白花 (赌徒)”。其传奇故事在忻州以至内蒙古地区家喻户晓,流传甚广,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诸如:古庙会上整治无赖齐二;宋贵元诉说心头恨,赵贵根怒打奸佞人;瓜老头忍气吞声,赵贵根痛打官兵等,故事中赵贵根毫不费力的惩治恶人、小人,充分显示其武艺高超、爱打抱不平、胆识超群的好汉气概。[7]此外,还有忻州城北关米宝泉替人要账耍计谋、活发引 (送葬)和开饭铺路过者皆记账。①2009年10月忻州市忻府区杨庄子村部分村民口述。杨庄子村扬大汉护田 “演出曹操马践麦田以发代首”自认罚款,取得威信。②2009年7月忻州市忻府区东呼延村村民白保岚(74岁)口述。东呼延村白润四 “保田辩牛印,力战六个偷田人,穷人可拿财主粮”。合索村人张双寿以保镖为业,据传枪法很好,背着枪能打中天上飞的鸽子。③2009年7月忻州市忻府区合索村村民范贵科(90岁)口述。忻州杨家庄人杨步举 “高粱杆当大梁”勒索有钱人。④2009年9月忻州市忻府区杨家庄部分村民口述。石家庄村人段天成 “在丰镇棒打定襄人,强力让人们把忻州定襄简称由 “定忻”改为 “忻定”。⑤2009年7月忻州市忻府区石家庄村段黄香(74岁)和段如州(54岁)口述。
(三)无赖型
“无赖型”实际是民众心目中的坏人,乡民称为 “赖人”,他们横行乡里,欺压族党,其行为对民众构成严重的威胁,为民众所不齿。但他们也以 “好汉”自居,且部分乡民也称他们为“好汉”。他们和 “好赖型”一样,身体健壮,崇尚武功,也以力量强人的形象活跃在乡村社会,并与 “好赖型”有诸多的往来与冲突。正如明恩溥在 《中国乡村生活》中指出:“成为地痞的一个便利——尽管并非必备——条件是体格健壮。”[8]
在调查中乡民对这一类人一般不愿提及或只是简单提及,原因是其后人依然生活在村中,乡里相亲,出于面子,不愿说人家祖上的 “坏话”,但也能了解一二。比如忻府区合索村的范黄成,早年就在内蒙一代,此人心黑手狠;⑥2009年7月忻州市忻府区合索村村民范贵科(90岁)口述西大王庄村的岳六金,民国年间人,不为人,“好人的害,坏人的菜”,后因赌博也有说是因为女人,被孙六和邢喜堂 (原为南营人,后在下王庄落户)杀死在本村。⑦2009年7月忻州市忻府区西大王村村民李满堂(88岁)口述。孙家湾村的孙三,强盗,以偷为生,当地有 “大讨吃子”的外号。⑧2009年7月忻州市忻府区孙家湾村部分村民口述。还有团伙力量,村民不了解其真正的行为,如合索村的 “十二游神”,石家庄村的 “七十二把半片刀”,南高的 “十二英雄”、“八宝罗汉”等。
关于山西乃至华北地区村庄中的这类人,有关文献中提及较多,如 《退想斋日记》所述 “吾乡是五方杂处之地,无赖甚多,号称难理,乡中管事人等率皆萎靡不振,任无赖横行里中,虐害乡党,竟置不问。今秋父老子弟因被无赖暴虐,吁求管事人以舒积困,管事人来,请余办,以为阖村士庶共递一禀恳来一张告示,则无赖庶几散匿,不敢放火矣。岂料无赖鸱张更甚,且公行不讳,扬言于众,向村人索钱,谓与钱即不放火,不与钱则火莫能止……”[9]杨懋春 《乡村社会学》中提及:“到集镇上去作会友消遣的人,在一般村民中占少数,最喜欢作这类活动者有三类人……第二类是一些没有恒产恒业的人。他们平常以赌牌、偷窃和其他不正当方法为生。到了赶集期,就都聚到集镇上,在那里共同的或分别的做赌博或纵容的勾当。弄到一些钱之后,就一同去呼么喝六,醉酒放荡。日落钱尽,又各回到村中,过穷苦潦倒的生活。”[10]
三、“好汉”对近代乡村社会的影响
清末到民国年间华北乡村 “好汉”群体,实际是游离于乡村社会各阶层之外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我们依据田野调查和参阅有关资料,分别从精英型、好赖型、无赖型三个类别予以讨论。综合这一群体的总体特征,他们主要凭借 “强力”在乡村社会占有一席之地。与乡村社区其他阶层相比,尽管他们所拥有的资源较为单一,对于决定乡村成员社会地位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拥有度十分有限,但他们的行为对乡村社会产生着不同寻常的影响。
“精英型”好汉与以往学者所论及的乡村精英不同,在乡村中既不是文化权威,也没有累世的家财,他们声望源于自身 “厉害”、 “正直”、“交际广”,并热心于公益事业,这使他们在乡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形象,赢得乡民信赖。在维护村民利益,抑制 “劣绅”不法行为等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如石家庄村的段景茂为抵制不合理的上级派款,敢于顶撞县长,对县长说 “你是县长,我是村长。你有你的大印,我有我的戳子;你有你的公案,我有我的小桌;你有三班衙役可使用,我有两个村警来回替”。①2009年7月忻州市忻府区石家庄村村民段黄香(74岁)和段如州 (54岁)及部分村民口述。奇村邓绍禹在出任村长前,“村里大户是和、范、贾、赵四大富豪之家,掌着村里的权。邓对他们在村中行为不满,搅得他们不得安生,四大户都惧怕他”。②2009年7月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邓秀明等人口述。他们一旦被推上村庄权力舞台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村民参与村政建设,发展公益事业。如邓绍禹被奇村商界和村民推选为村长后,主持兴建了忻县第五高等小学,成立了商农社和公和局,合理解决了奇村民户和商户的摊派分成问题,并开展禁烟戒毒、植树造林等活动,不到两年时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山西省政府的嘉奖,并颁发了 “造福桑梓”大匾一块。③参阅奇村邓莲溪(1915-2005)《祖先生平简历》稿本。
“好赖型”成分相对复杂,没有出任公职的事例。他们大部分文化素质低,崇尚武力,以力量强人的形象活跃在乡村社会,以护田、保镖为业,有诸多不良嗜好,大多都参与赌博,喜好打架,甚至有一些无赖行为。但他们有自身的道德标准底线,同情弱者,维护一方利益。他们对乡村社会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作用。由于他们具有的 “强力”,在维护乡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一面。他们能够帮助乡民解决许多难于依靠正常途径或依靠正统精英无法解决的事情,如小老翁上门诉苦情,赵贵根带人去相助;兰三丑不慎丢牛款,赵贵根相助钱归主;张大财猪死要大价,赵贵根据理来解围等。特别是在访谈中乡民提起他们时,总要特别强调其护田的能力,如 “一人可以看护几个村的田”等。但是,他们的一些不良品质却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如赌博、打架、耍无赖等。可以说,这一类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很难给以恰当的定位,只能就不同的人和事作出评价。
“无赖型好汉”没有经济文化资本和道德底线,凭借其强力对民众产生威慑力,由于其行为恶劣,在乡民道德评价体系中受到极端鄙夷与憎恶,但一般人不敢招惹他们。此类人一旦攫取了村中权力,其性质是一种典型的 “横暴”权力。费孝通对 “横暴权力”描述道:“权力之所以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统治者要用暴力来维持他们的地位不能是没有目的的,而所具有的目的也很难想像不是经济的。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经济利益可得,横暴权力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之也就不易发生。”[11]在对忻州进行重点调查中村民虽没有谈及这一类人在当地攫取权力的情况,但文献中关于华北地区无赖出任村长的记述颇多,如 《中国农村惯性调查》中所记述的河北省昌黎县泥井镇长齐某、[12]寺北柴的李严林[13]以及石门村和沙井村的乡长樊宝山[14]利用公职贪污作恶的行为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群体担当公职所表现出的 “横暴权力”特征。
[1]李培林,孙立平,王铭铭,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社会学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48.
[2]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 [J].历史研究,1999(5):174-186.
[3]渠桂萍,王先明.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 [J].人文杂志,2004(6):122-129.
[4]渠桂萍.清末与民国时期华北乡村中“能力型”阶层[J].社会科学战线,2008(1):111-121.
[5]王先明.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 [J].近代史研究,2005(2):245-283.
[6]张金锁.原平跤坛风云人物[M].内部书号2000字第98号:242-243.
[7]安仁和.赵贵根传奇 [R].忻州市文联,内准印忻地行文 (93)字第5号.
[8]明恩溥著,午晴,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 [M].北京:时事出版社,1980:217.
[9]刘大棚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1895年11月13日[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49.
[10]杨懋春.乡村社会学[M].台北:正中书局,1970:125-126.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1.
[12]中国农村惯性调查(第5卷)[M].东京:岩波书店,1981:48-51.
[13]中国农村惯性调查(第3卷)[M].东京:岩波书店,1981:51.
[14]中国农村惯性调查(第1卷)[M].东京:岩波书店,1981:197-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