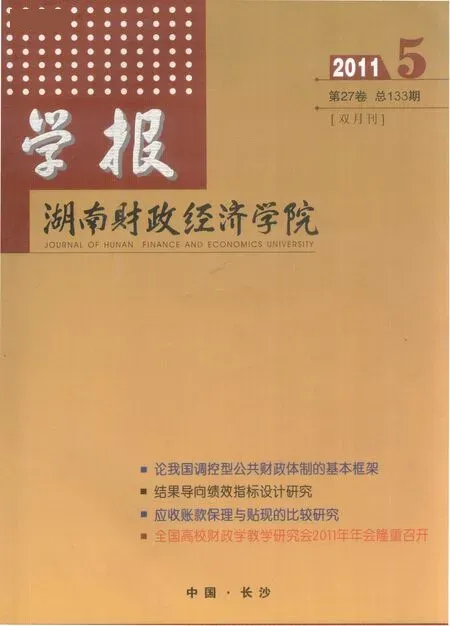论公序良俗原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指引——以合同形式为例
彭赛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公序良俗原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促进意义不仅通过其“公平”、“善良”的价值宣示而体现,而且还通过对民事法律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而实现,具体包括显失公平行为、合同行为以及遗赠行为。当这些行为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时,应当直接宣告其无效。笔者拟以合同形式为例证,探讨公序良俗原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指引,从而揭示该原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一、公共利益是公序良俗原则的内涵之一
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学者们大多认为,该条即是对公序良俗原则的立法规定,该条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德”相当于法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的公序良俗概念。可见,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德共同构成了公序良俗原则的全部内涵。
公共利益是一个使用范围极为广泛的词语,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以及民法学上都有涉及,然而,一旦论及到该词的概念,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在于公共利益一词非常抽象,没有确定的内涵,就如哈罗德·威尔逊曾在美国国会抱怨时所说:“我认为在场的每一位国会议员,都明白自己所使用的公共利益这个词的意义,并且会将其用来决断众多形形色色的问题。但我怀疑没有哪位先生,能够对自己所使用公共利益这个词的意义,给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1]。因而致使有学者感慨:“何谓公共利益,因非常抽象,可能言人人殊”[2]。公共利益概念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主体的不确定性,即“公共”一词究竟何指;其二,内容的不确定性,即“利益”一词的所指。对此,笔者未做深入考究,仅将其界定为: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利益组合而成,并最终体现于个人利益的一种共同利益。它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个人利益的集中体现;它最终体现为个人利益,但绝不是对个人利益的直接体现。
鉴于公共利益的抽象性,人们担心“如法律规定富有弹性,执法者可以自由伸缩于其间,深恐上下其手,以残害人民之自由也”[3],因此,对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一直都是学者热衷于解决的问题。笔者择要列举几种:第一,为了说明公共利益与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的价值联系,有学者将公共利益分为四个层面。一是最基础的层面,应该是共同体的生产力发展;二是公共利益就是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受益的公共物品的生产,包括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等;三是社会每个成员正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四是合理化的公共制度[4]。第二,有学者有针对性地详细列举了各国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要件,可大致概括为交通建设、公共建筑、军用目的、土地改革如耕地改造、土地重新分配、公共辅助设施以及公园、运动场、花园、体育设施和墓地的建设等六个方面[5]。第三,还有不少学者把公共利益视为“经济秩序”的代名词。比如有的认为,“公共利益就是指包括产业利益在内的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或指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有的认为是指“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秩序本身。妨碍这种经济秩序的事态,就是直接违反公共利益”[6]。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公共利益应从以下几方面来体现:一是政治秩序的和平与安宁;二是经济秩序的健康与公平;三是人类生产生活、发展进步所需要的基本公共物品的提供与保障;四是公共道德和价值体系领域内公平正义的维护与实现。有必要说明的是,公共利益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或不同的法律部门,各有侧重,也各有其不同的表现。如在劳动法和消费者法方面,社会利益侧重于指社会弱者的利益;在刑法和治安法方面社会利益的含义则是以社会秩序的和平与安全为重点[7]。
二、合同形式承载着公共利益
合同承载着多层次的功能,一方面,是当事人经济交往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纽带。因此,合同不仅涉及当事人的个人利益,同时也关涉到第三人及社会的公共利益。换言之,合同“不仅是私益交换之手段,而且还担负相应的社会使命,它是社会经济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的纽带,从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公益性。与此相适应,在消极意义上,契约自由不应与社会公益相抵触;在积极意义上,契约自由要增进社会福祉”[8]。
合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不仅通过对合同内容的法律规制而实现,合同形式同样也承载着公共利益。因为,合同的形式是内容的载体, “法律制定形式规定的目的,为了保护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提醒他不要操之过急;是着眼于双方当事人对于证据保全的利益,也许他们想得到法律方面的专业咨询;或者是为了维护某项公共利益,或维护第三人要求这类法律关系具有清晰度和公开性的利益”[9]。强制特定的合同采用法定的形式,即强制私人合意由秘密状态变为公开,是贯彻国家经济政策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及交易秩序的有效手段。合同形式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通过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地位、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来维护公共利益
现代社会民法上的“人”已实现了由“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的转变,“人”与“人”之间并非实质性地平等,“合同能力的不平衡”这个关键词触及到了当代合同法的理论界普遍、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10],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差异在经济交往中会通过合同的洽谈、缔结和履行而体现,如消费、服务、保险、劳动领域大量格式合同的运用,一方面提高了交易效率,但另一方面也给不公平交易留下了可乘之机,是“经济强者在经济弱者的同意下,所为的剥削与勒索”[11]。有学者认为,影响这些合同公正与否的是其实质性的内容而非形式,但正是法定形式的采用可以直接影响内容:第一,法定形式可以为当事人提供足够的信息与考虑的时间,如保险合同,鉴于该类合同很强的技术性,多数投保人对其并不真正了解,而书面形式中就包含了大量的重要信息,当事人在签名之前通过详细的阅读可以掌握和了解保险的具体内容以及自身的权利义务,“立法者……其目的是确保消费者在订约前或订约之际实际经由书面形式获取一定的信息”[12],这对当事人权利的维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当事人“明明白白地签订合同”。第二,法定形式能为当事人保留记载合同内容的关键证据,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只要出示书面合同就能将案情“大白于天下”,省却了取证之成本,更重要的是避免遭受因证据不全而带来的不利诉讼结果。第三,也是极为重要的,从国家监管的角度分析,合同采用特定形式还能为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这类合同提供依据,就世界范围来看,对格式合同的规制主要从立法、司法、行政以及自律等方面来进行,而这些规制的共同前提是书面格式合同的存在,我国目前在格式合同的规制和监管上尚不完善,对这类合同形式的强调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当然,也有学者对合同形式在维护弱者权利方面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如果形式强制在此之主要意义是课加相对人以提供信息等义务,则透过诚信原则以扩大先合同义务或合同义务范围之方法,或许是较佳的途径。如果立法者执意通过要式来完成该规范目的,则可能导致背离保护消费者之目的的苦果”[13]。此种看法的缘由在于:其一,形式强制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途径就是“提供信息”。但这一理解是片面的,提供信息只不过是其途径之一,此外还有证据功能以及更为重要的国家监管功能等,后者是无法通过合同先义务或义务的设定来解决的。其二,狡诈者可能借形式的欠缺否定合同的效力,由此造成背离弱者权利保护之目的。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形式强制的法律后果上,这也是我国立法含糊其词从而导致学界认识不一的地方。而且,这种干预“并不意味着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变成好心的慈悲主义,而只是建立起一些不太确定的‘公正’、‘社会正义’和‘保护弱者’的原则”[10]。
2、通过保障社会公众利益和国家重大经济利益来维护公共利益
首先,公共利益虽然不是社会公众利益的简单相加,但反映的是社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追求,是“一个相关空间内大多数人的利益,换言之,这个地域或空间就是以地区为划分,且多以国家之组织为单位。所以,地区内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就足以形成公益”[14]。据此,当合同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时,强制其采用法定形式,以促进签订者审慎之态度,并强化对合同的监督与管理,最终亦将达到对公共利益之维护。
其次,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高度融合的情形下,一方面,国家利益之实质就是市民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如国家对环境的保护、对健康竞争秩序的维系等。同理,当一些合同直接涉及到国家重大经济利益时,对其予以监管亦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从另一方面观之,尽管不少民法学者认为作为民事财产主体,国家与一般的个人或组织是“同一的”,从而反对给予国家所有权以特殊保护,[15][16][17]但国家作为利益主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一般的利益主体,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无法由具体的权利主体行使其权利,也无法直接领会利益判断错误时的痛苦、获得收益时的满足,也就无法获得最原始的激励。这样一个抽象的存在不符合包括物权法在内的私法关于权利主体的基本假设,从而导致了为私人主体量身打造的私法规则在适用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所有权时必然发生某些失灵的现象[18]。因此,应当设计一些特殊的规则以弥补这种不足,对涉及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交易要求采用严格的形式就是其中之一,进而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三、公共利益在合同形式中的演绎
基于公共利益的要求,应当要求特定的合同采用法定形式签订,即对特定的合同排除形式自由转而进行形式强制。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合同:
1、由垄断企业充当一方当事人的消费合同
利用合同形式保护公共利益主要通过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而实现。通说认为,消费群体属于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法律更多的眷顾,但合同形式的强制要求是非同于一般的法律保护措施,它是以一种权利的放弃来换取对安全与另一种权利的保障,因此,在运用时需进行利益的衡量与判断,看是否有通过形式维护公平正义之必要。在消费领域,并非所有消费类型的消费者仅享有同意与否的自由,而没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最常见的是普通商品买卖合同,如果提供该类商品的商家众多而且未形成垄断同盟,消费者其实拥有广阔的选择空间,可以货比三家,可以讨价还价,消费者的地位并不十分被动,过于强调合同的形式,不仅功效不大,反倒可能有损双方的权利。但如果商品或服务由垄断企业提供,如邮寄、电信等行业,消费者的利益就难以维系了,近年频繁出现在这些领域的纠纷即为其例,因此,通过形式干预实现国家的监管从而维护公共利益是必要的。
2、劳动合同
在劳动法律关系中,一方为企业,一方为劳动者个人,其地位的差异不言自明,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是世界共同的主题,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劳动合同需为书面形式。在我国,劳动争议案件也在逐年增加,争议的主要原因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争议的性质主要是权利争议,而且集体争议占到了争议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明劳动者所提出的权利要求不是个别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劳资力量发展不太平衡,使得我国劳动合同签订率比较低,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无合同随意用工、合同短期化、合同不规范、劳工权利不明确和劳工标准不落实、劳工权益受侵害等,所以《劳动合同法》以劳工权益保护为立法趋向,向劳动者适当倾斜,明确规定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这无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对劳动者权利的保障意义非同一般。
3、保险合同
关于保险合同的形式,存在不要式说、相对要式说和绝对要式说三种学说。与此相应,各国在保险立法中也体现了保险合同要式与否的分歧,我国《保险法》采用的是不要式主义。而笔者认为采用相对要式主义更为妥当。一方面,对投保人来讲,保险作为风险处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保障投保人的生活安全稳定,因而,对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保险活动应尽到注意义务,要求其承担保险合同的书面形式并不为过,而且形式的强制可避免非要式合同带来的种种弊端,如证据的难以确认、诉讼费用的提高等;另一方面,对保险人而言,其行为直接关系到投保人的利益能否实现,而且在缔结保险合同的过程中,保险人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基于前述原因,国家有必要加强对保险人行为的监管和保险合同的规范,对形式作出要求。不过,对保险合同的书面形式应作宽泛的理解,保险单、保险凭证、暂保书、要保单应当都属于法定形式,而且如果虽然未采用这些形式,但合同正在履行,也应当允许。
4、以提供基础设施、公用设施、公用物品等公共产品为标的的合同
公共产品的最终使用和受益者是社会大众,如道路的修筑、管网的铺设等公用设施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其质量的好坏、数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如不加强对这类合同的监管,极有可能给不法之徒留下可趁之机,最终受损的是公众的利益。我国在这方面有过一些教训与损失,因而应当加强对这类合同的监管。具体而言,包括订立时的监管和履行时的监管,前者主要是审查合同当事人的资质以及合同订立的内容,这就要求将合同书面化,而且还应当到有关部门备案和审批。
5、直接以特定的或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合同
这类合同不仅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利益,还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秩序,如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招投标行为、拍卖行为、商品房的销售、预售行为等,国家应当通过严格的缔约程序和形式来规范和调控。
6、与土地权益有关的合同
土地在财产体系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得天独厚的。土地对一国的发展和建设、对公众的生产与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与地位。不管哪个国家,都是极为重视有关土地的立法,并且对处分土地权益的合同都要求严格地采用法定的形式,如美国的《不动产租赁法》就规定:“买卖或处分土地的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德国民法典》第873条亦规定:“为转让土地所有权,为以某项权利对土地设定负担,……必须将权利的变更登记到土地登记簿中。”
7、处分国有资产以及国家投资的合同
近年来,国有资产的流失与保护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表现出来的问题,更多的是合同法、公司法、企业法以及国有资产管理法调整的范畴,而非仅靠物权法来解决,因此,在国有企业的改制、国有资产的流通中,国家通过对合同形式的强制可以将交易的信息公开化、交易的过程规范化,以此实现对这一活动的监管。
8、国家采购合同
民事领域奉行意思自治,但正如市场经济靠市场调节的同时也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一样,意思自治并不否认法律对当事人的意志自由的某方面的限制。像政府采购合同中,政府作为普通的民事主体其行为本不应该受限制。但采购资金属于财政资金,故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管理、抵制腐败等,法律对政府采购合同的形式作出了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
[1]John Bell.Public Interest:Policy or Principle[A].Roger Brownsword.Law and The Public Interest[C].German: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1993.35.
[2]陈锐雄.民法总则新论 [M].台湾:三民书局,1982.913.
[3]林纪东.行政法新论[M].台湾:三民书局,1986.42.
[4]马德普.公共利益、政治制度化与政治文明[J].教学与研究.2004,(8):77-78.
[5]程雨燕.宪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1):10-13.
[6][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 (著);谢次昌 (译).现代经济法入门[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91-92
[7]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 [J].中国法学.1995,(4):52-60.
[8]卢文道.论契约自由之流弊[J].法学.1996,(12):16-18.
[9][德]卡尔·拉伦茨 (著),王晓晔等 (译).德国民法通论 (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57.
[10][德]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法中的自由与强制——合同的订立研究[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 (第9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61-363.
[11]陈旭锋.国外对格式合同的行政监管[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7):35.
[12][德]康拉德·茨威格特,海因·克茨.合同形式[J].中外法学.2001,(1):81-91.
[13]王 洪.合同形式研究 [D].成都: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50.
[14]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 (上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4.
[15]梁慧星.民法通则对原来民法理论的突破[N].中国法制报,1986-11-07(3).
[16]王利明,郭明瑞,吴汉东.民法新论 (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157-163.
[17]王利明.国家所有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314-318.
[18]马俊驹.物权法的目标、功能与国有资产流失[EB/OL].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24962,2006-02-07,2011-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