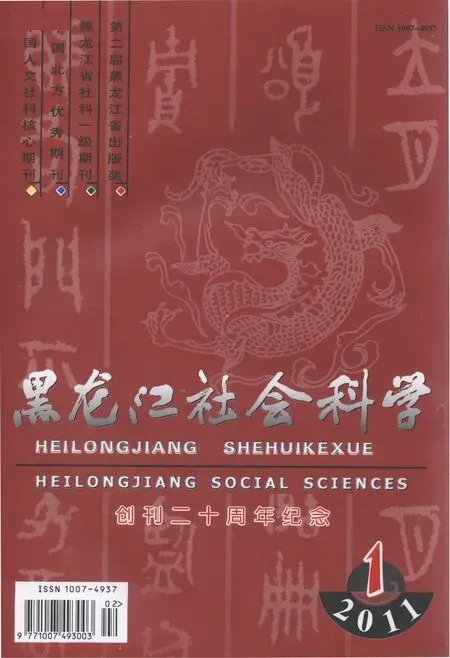“新阶级”与“特权阶层”:吉拉斯对苏联政治和社会结构演变的分析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新阶级”与“特权阶层”:吉拉斯对苏联政治和社会结构演变的分析
张建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采纳了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米洛凡·吉拉斯提出的“新阶级”理论,对苏联模式和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反思。他将社会主义建设和各国领导阶层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视为“新阶级”问题。他的理论在结构上并不严谨,但是他提出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建议却有着启发意义。
吉拉斯;新阶级;苏联;社会主义
特权阶层①俄文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有人将其音译为“诺门克拉杜拉”,原意是指“名录表”,特指那些列入官职名录表的官员。的存在是整个苏联时期,特别是上世纪勃列日涅夫执政的 60年代初至 80年代初极为突出的社会现象。然而,在苏联时代,苏联官方不承认苏联社会有特权阶层,只有对苏维埃政权持批判态度的持不同政见者 (异议思想者)以地下出版物方式进行研究和揭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肯定了苏联时期特权阶层的存在,但着重于描述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而对其产生及其影响则大多追随西方学者的观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将苏联视为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视为一个“新阶级”(New Class),②国 外 学 界 相 关 论 述 见 : ДжиласМ. Новыйкласс—Анализ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системы.New York,1957.ВосленскийМ.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классСоветскогоСоюза.London,1984.; БоффаД. ОтСССРк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неоконченногокризиса1964 —1994. Москва,1996.并且这个“新阶级”滥觞于十月革命时期,形成于斯大林时期。西方国家学者早在苏联时期即关注苏联特权阶层问题,并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中许多带有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对苏联特权阶层蓄意渲染,不能做到完全客观。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相同,大多数西方学者所指的特权阶层是指列入官职名录表的所有官员。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著名理论家米洛凡·吉拉斯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最早认识并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中特权阶层和苏联特权阶层问题的学者和政治家。他以“共产党新阶级”(Communist party—New Class)指称生活在苏联模式中的共产党特权者,因而成为 20世纪 5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种独具特色的观点。
1957年,吉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书在西方出版后,他的著作开始受到西方人的关注,并且得到了西方政府与媒体的赞赏。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他的著作却成为学者们批判的对象,理由是他扭曲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传达给了世界。自此之后,在对吉拉斯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上,东方和西方的学者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给出的结论都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一般认为吉拉斯是社会主义叛徒,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言人,其思想没有反映出社会主义的现实,是错误的;而西方国家的学者则认为吉拉斯深刻地揭露了斯大林集权主义和共产党的特权阶级。然而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大多数学者的认识都被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控制。在国内外史学界,有关对吉拉斯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虽然不是一个热点问题,但却长时间地不能得到一种排除了意识形态控制的、较为合理的评价。
一、“新阶级”理论的基本主张
米洛凡·吉拉斯 (又译为密洛凡·德热拉斯)于 1911年 6月 12日出生于南斯拉夫黑山省 (M entenegro,又译为“门地内哥罗”)。他于 1932年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此后很长时间都是铁托的得力助手和朋友。他曾多次代表南斯拉夫共产党同苏联进行会谈。在会谈中,他始终如一地与铁托站在同一立场,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战后取得合法的领导地位做出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改名为临时人民议会,吉拉斯参加了议会工作,并兼任黑山省事务部部长。在1948年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出现破裂时,他仍然以南斯拉夫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地准备经济改革方案,以抵制苏联的经济与政治封锁。
1953年初,吉拉斯出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同年末,他又出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成为南斯拉夫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然而在南斯拉夫的自治改革刚刚起步之时,吉拉斯却提出了激进的改革观点,主张取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①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于 1919年,在 1952年 11月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以下简称“南共联盟”。的领导地位和实行多党制等。他的这些观点遭到了铁托以及南共联盟其他领导人的反对。1953年夏,铁托在布里俄尼岛②布里俄尼(Brijuni):位于克罗地亚伊斯特拉半岛西海岸南部,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上层的游憩场所和铁托所喜爱的私人疗养地。主持召开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六届二中全会 (即布里俄尼全会)。这次会议引起了吉拉斯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这次全会标志着铁托结束了争取民主改革的努力。他当时就私下告诉时任联邦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爱德华·卡德尔③爱德华·卡德尔 (Kardelj,E.1910—1979):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国务活动家、理论家。:他不能支持中央现在采取的路线。④米洛凡·吉拉斯:《铁托:内幕故事》,柯雄译,新华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62页。吉拉斯认为党成了统治阶级,并产生了道德、思想退化的现象。他用尖锐的语言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批评,因而与党以及政府发生了思想上的严重冲突。从 1953年 10月到 1954年 1月,吉拉斯在《战斗报》(Borba)以及《新思想》(Nova M isao)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他的思想。⑤这些文章发表在 1959年第一次用英文汇集成册,英文书名为 Anatomy of Moral:the political essays.by Abraham Rothbert.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s,1959.中译本书名为《德热拉斯政治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吉拉斯的这些言论受到南斯拉夫国内部分公众的欢迎,甚至某些中央委员也予以盛赞。他主持的宣传部门在全国大小报纸上刊登了许多表示赞成的读者来信,有些报刊的编辑部直接予以呼应[1]。在国外,许多西方通讯社报道了吉拉斯的言论,就其观点大做文章。这些情况连同吉拉斯的政治观点本身,使南共联盟其他领导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铁托当时在外地疗养,传话要他停止发表文章,卡德尔则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长时间争论。⑥参见:《铁托选集 (1952—1960)》,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71页;米洛凡 ·吉拉斯著,柯雄译:《铁托:内幕故事》,新华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68页;丹尼森·拉西诺著,瞿霭堂译:《南斯拉夫的实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版,第114页。1954年 1月 16日,南共联盟中央召开三中全会,决定撤销吉拉斯的一切党内职务。铁托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吉拉斯的根本主张是取消南共联盟,如果不与之斗争,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导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迅速丧失。针对吉拉斯关于民主的言论,铁托说他是在宣传“抽象的民主”,“无政府状态的民主”[2]。1月 1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中央特别全会上,决定撤销吉拉斯党内外以及政府的一切职务,黑山共和国撤销了吉拉斯党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1954年 3月吉拉斯被开除出党。1955年 1月他被判处 18个月的监禁,后又多次被捕。1966年 12月吉拉斯被释放出狱,但南斯拉夫政府并没有恢复他的公民权。在南斯拉夫国内,吉拉斯既没有公开演讲的权利,文章和作品也不能刊登出版,直到 1989年吉拉斯才被允许在南斯拉夫国内发表部分作品。
退出政坛的吉拉斯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学者和作家,致力于写作和理论思考,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以及自传体的《没有权利的国家》(Land W ithout Justice)。1956年,吉拉斯在监狱中完成了《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的书稿之后,这份书稿被人辗转带到西方,并于次年以英文版的形式面世。⑦在汉语学界,《新阶级》一书最早于 1957年由台湾中央日报社编译出版。在此之后,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3年出版了由陈逸翻译的《新阶级》;1981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再次翻译出版《新阶级》。台湾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1984年出版的《吉拉斯谈话录》在附录中也刊录了《新阶级》的全文。
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包含在三部著作之中,即 1956年完成的《新阶级》、1969年完成《不完美的社会——超越新阶级》(The unperfect Society:Beyond the New Class)和《新阶级的衰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史》(Fall of the New Class:a H istory of Communism’s Self-destruction)。吉拉斯在这三本书中研究了一个历史阶段内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有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从空间上来讲,“新阶级”出现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从时间上来讲,“新阶级”存在于十月革命后至 70年代中期。
追溯“新阶级”一词的由来及发展变化时可以发现,它并不是吉拉斯原创出来的词汇。在吉拉斯之前,主要有三位思想家从政治角度论述过“新阶级”问题:马克思 (Karl M arx)、俄国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 (М.А.Бакунин)与苏联早期主要理论家布哈林 (Н.И.Бухарин)。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新阶级”一词,他认为:新阶级是相对于旧阶级存在的,它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而是存在于每一种社会形态之中。在每一个社会形态里都会有“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都“以全体社会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3]。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新阶级是相对于“旧的”阶级存在的一种“新的”阶级。巴枯宁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新阶级”这个词汇,但是他认为:有国家就意味着有统治,有统治就意味着有奴役。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将会在新的国家里上升为统治阶层[4]。布哈林则在 1922年从文化角度探讨无产阶级国家蜕化的危险时指出:工人群众文化上的落后有可能使它的先进阶层偏离阶级基础,从而导致一个“新阶级”的产生。排除这种危险的唯一办法就是取消教育垄断,源源不断地从工人群众中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去补充、更新原有的行政领导和技术人员队伍。这几种不同概念的“新阶级”中,马克思有关“新阶级”的观点同吉拉斯在 20世纪 50年代提出的“新阶级”理论关系最为密切。吉拉斯既沿用了马克思所提出的“新阶级”这一称谓[5]10,又沿用了马克思对于阶级社会中必然出现取代旧阶级的“新阶级”的判断。然而,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比,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有着自己的特点:他赋予了这个词汇一个专门的定义,具体到了专门的时代、专门的国家、专门的社会群体上。因此,无论是在吉拉斯之前还是之后,①在吉拉斯提出“新阶级”理论之后,美国学者阿尔文·古尔德纳也提出了一种观点。他在《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一书中指出:20世纪中期出现的知识分子转型现象标志着知识分子已经作为一个“新阶级”兴起了。古尔德纳把新的拥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看作历史的代言人,认为他们与旧的资产阶级斗争夺取政权,以便实行一种以知识、理性和专业技术为基础的统治。这个“新阶级”目前还没有完全成为统治阶级,它现在还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普通阶级”。西方国家还有一种“新阶级”的观点侧重的是社会性。西方的一些社会学者借用“新阶级”一词指代社会上一群因为社会经济产业结构改变而兴起的专业从业者。这些人基本从事一些与人际交往和文化传播有关的服务业。在持这种观点的社会学家看来,“新阶级”概念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文化态度和社会心态。参见: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杜维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版;范方俊《“知识分子的最后”:消失还是转型?》、《知识分子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都有学者提到过“新阶级”,只不过,他们每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理解。从 19世纪开始直到今天,“新阶级”一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出了许多种含义。它们所侧重的角度不尽相同,既有侧重政治性的,也有侧重社会性的。
吉拉斯的《新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反响,他本人也因此再度入狱。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新阶级》一书的完成就认为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也同时产生。早在 1953年底,吉拉斯在《战斗报》和《新思想》上发表文章时就已经简要地提出了他有关“新阶级”的观点:他认为,南共联盟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或者说是“新阶级”;他声称,这个阶级的成员是一批官僚主义者。他们拥有了很大的权利,在思想和道德上已经脱离或疏远了革命。这些人组成一个“闭塞的集团”,正在保护他们建立起来的官僚等级;他断言,“官僚主义这个新敌人比资本主义那个旧敌人还危险”。在题为《一个教训的研究》一文中,吉拉斯用及其尖锐的言辞讽刺南共联盟的领导人具有一种“维持既得地位的兽欲存在”。他认为这些曾经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败坏了一切伦理价值”,是自命全能的“教条主义者”[6]。
这是吉拉斯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的言论中谈到“新阶级”。同他在 1953年底、1954年初发表的这些言辞激烈的文章相比较而言,无论是在二战期间、在同苏联代表的会晤中,还是在苏南关系破裂之时,吉拉斯并没有发表过任何同铁托、同南斯拉夫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意见不同的讲话或是文章。因此,我们无法从吉拉斯以前的公开讲话中理清其“新阶级”理论发展的脉络。在研究他的思想时,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吉拉斯自 1954至 1995年撰写的近 20部著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新阶级”理论是如何产生、发展以及变化的。然而,无法否认的是,吉拉斯的这些作品多成书于 20世纪 60年代之后,而此时他的“新阶级”理论已经开始深化。因此,我们无法排除有以下这两种可能:第一,吉拉斯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新阶级”的理解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在这种前提下,如果他再回述当年的历史,就难免在真实的历史表面上涂抹上一层意识的色彩。第二,吉拉斯仅以一个人的视角,很难看清楚当时整个社会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吉拉斯及其“新阶级”理论时,有必要借助其他史料与当事人的回忆录,如《铁托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铁托自述》(达姆扬诺维奇编,达洲译,新华出版社 1984年版)、《卡德尔回忆录》(爱德华·卡德尔著,李代军等译,新华出版社 1981年版)和《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版)等。
吉拉斯“新阶级”理论的提出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对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望阶段。在这个阶段,吉拉斯产生了探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机,但并没有将这种动机转化为实践。第二个阶段是他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的失望阶段。在这个阶段,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结合了他所看到的南斯拉夫与苏联的社会现实,逐渐地形成了。
吉拉斯认为“新阶级”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显示了它与社会其他政治阶层的明显区别。
从外部特征来看,“新阶级”是一个掌握权力的集团。“新阶级”来源于官员队伍,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利用权力谋取特权,才有享受不该享受的权利的条件。但是,还应再次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属于特权阶层。
受过较高的学历教育也是“新阶级”的外部特征之一。这倒不是说凡属特权阶层的人文化水平都很高 (许多人是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取得学历的),而是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接受过高等教育是登上权力地位的重要阶梯,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极少能成为拥有权力地位的人,相应地也就很少成为特权阶层成员。此外,某种高等教育的文凭也是特权阶层借以证明自己能力和自己掌权合法性的一种手段,所以他们也利用手中既有的权力来捞取文凭,至于学到了多少文化知识对他们来说那就是次要的了[7]。但无论如何,特权阶层的绝大部分人都接受过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属于苏联社会中的知识阶层。这些人中的“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8]。他们自上而下地控制着国家权力体系。
从内部特征来看,“新阶级”内存在严格的上下等级之分。因为“新阶级”主要由党政干部组成,等级分明的行政级别同时也成为“新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标志,“这个阶层有它的生活方式,有它明确规定的社会地位,有‘主子’、‘头目’,有它的语言和思想方式”[9]。按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员享有不同的特权,越是高级的官员享受的特权越多。对“新阶级”来说,他们的级别越高、掌握的权利越大,就越有条件以权谋私,享受不应有的权利。享有特权的科学、文艺等领域的人士也是按贡献的大小被赋予不同的特权,形成了上下等级之分。如享受休假疗养和别墅的特权,级别高的人可享受高级别的疗养院和高级别墅,而级别较低的人只能住一般的疗养院和一般的别墅。戈尔巴乔夫曾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那里有许多国家级的疗养院,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高级领导人常到那里休假,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和他们接触,这为他以后的升迁提供了方便。
“新阶级”——特权阶层的等级特征也适用于他们的家属。戈尔巴乔夫回忆了在 1979年 3月 8日的一次政府招待会上,他的夫人站到了比自己高的级别的位置上,受到了毫不客气的指责,当时他的夫人“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10]。
按照吉拉斯的理论,他用“新阶级”一词指称共产党官僚阶层有两层意义:第一,“新阶级”是相对于旧阶级而言的。旧阶级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到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的各种阶级,这些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这一点上看,吉拉斯的“新阶级”可以理解为“新形成的”、“新出现的”阶级,是马克思在论述五种社会形态中从没有提到过的一个阶级。吉拉斯借此把自己划分出来的这个“新阶级”同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区别开来;第二,吉拉斯用“新阶级”一词也是出于该词使用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本身就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按照吉拉斯的话来说,毕竟这个“新阶级”诞生于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讲不应当存在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11]。
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给“新阶级”下了定义:“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是从少数职业革命家中慢慢发展出来的……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与经济优先权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12]101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吉拉斯将“新阶级”和“共产党官僚”划上了等号。而在他看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出现“新阶级”的标准是十分简单的。他认为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统治阶级是否利用特权以权谋私,是否一再追求个人额外的权利。
吉拉斯认为南斯拉夫的部分政治家们利用社会主义自治改革的成果,为自己谋求生活上的安逸,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新阶级”,而这个“新阶级”的核心就是铁托。并且强调一个突出的标志是,1953年南共联盟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并没有按照惯例在贝尔格莱德,而是在“铁托在岛上的家里去举行”,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党和国家一切重要决策都在他的孔策沃别墅的酒席和聊天中决定的相似史实。
二、从“新阶级”到苏联现实:吉拉斯对特权阶层及其危害的理论分析
吉拉斯是南共联盟的主要领袖和南斯拉夫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战后担任南斯拉夫政府副总统期间,都多次赴苏联访问或交流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 1948年 1月吉拉斯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会议,讨论对阿尔巴尼亚的相关政策。而就在一个月之后的 3月 27日,苏共中央给铁托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苏联方面在指责南斯拉夫国内正在形成一种反苏的敌对氛围的同时,又愤怒地回顾了吉拉斯在 1944年曾经说过的有损苏联红军军官名誉的话。而且,信中谈到“吉拉斯的这一反苏声明并没有遭到南共联盟中央其他成员的反对”[13]354。这里所说的“有损苏联军官名誉”讲话,是指吉拉斯曾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在解放南斯拉夫之时曾发生大量强奸南斯拉夫妇女的事件。为此,苏联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鉴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苏联军事顾问这个问题上,不是争取同苏联政府达成友好协议,而是开始辱骂苏联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名誉”[13]326,苏联方面就此决定从南斯拉夫撤回自己所有的军事顾问。在《同斯大林的谈话》(Conversation w ith Stalin)一书中,吉拉斯也承认自己在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谈话的过程中说过此事,他担心苏联红军的不正当举止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将其同英国军队相比较[14]。他的这种言论在事后遭到了南共联盟内部一些同事的批评,但是吉拉斯却认为他说出的仅是一个没有任何错误的事实。
尽管,吉拉斯的身份与上世纪 20—30年代访苏的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与 40—80年代三次访苏的以塞亚·伯林有相当大的区别,但是并不影响它对苏联社会与苏联政治做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①有关上述人士的苏联观感,请参见张建华、高龙彬《20-30年代的“访苏现象”及其对苏联的认识》,载《理论学刊 》2010年第 10期。
特权阶层原本是斯大林在 20世纪 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干部特供体制,即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 (后改称部长)、总局局长等依其级别享受程度不同的生活和供应特权。后来又改为附加工资制度,即每月根据职务领取几十卢布到几千卢布的特殊补贴,又被戏称为“斯大林钱袋”。斯大林时代,一个部长每月的补贴大约为 2000卢布。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实行干部职务轮换制改革的同时,废除了干部特供体制。勃列日涅夫继任后,出于稳定干部队伍的考虑,不仅恢复了干部特供体制,而且扩大了享受这一特权的阶层范围。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已形成自上而下的极其僵化和严重老化的干部任用制度,加上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到了 70年代,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已经形成。
这个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仅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还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做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 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
据俄罗斯学者的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 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 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这个阶层的成员凭特殊的优待证件可以买到莫斯科市场上紧缺的食品、汽车、进口电器等产品。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 2号楼的入口处有一间不太引人注目的房子,上面挂着牌子:1919年,列宁曾在这里发表过演说,看起来像是一个纪念馆,但实际上它是苏联中央委员和政府高级官员们的特供商店。在这里可以买到外国进口的各种商品,并完全是免税的:有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法国香水、德国晶体管收音机、日本的录音机等。此外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央大厦里也有特设的商店,为中央领导们服务。另外,在莫斯科还设有专门为元帅和将军们服务的廉价商品配售店,为著名学者、宇航员、企业经理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服务的专门商店,为著名作家、演员和体育明星们服务的专门商店。这类商店被莫斯科市民统称为“小白桦商店”。对于这种特权现象,老百姓们自然是极度不满的,他们戏称:“对于上层人物来说,共产主义早已经建成了。”这个阶层的人从政治立场上讲,多数趋于保守,思想僵化,迷信教条,不思变革,安于现状。他们对上级唯命是从,明哲保身,高高在上,不问群众疾苦,没有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们是一批地地道道的官僚,在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下,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凝固化,社会处在停滞状态。②以上资料参见张建华《激荡百年的俄罗斯——20世纪俄国史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机关的干部特权和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当时的领导干部,享受高于普通职工几十倍的高薪,享受名目繁多的补助,享受兼职兼薪,拥有高级别交通工具和特殊商品供应等等。特别是,领导干部搞裙带关系,结党营私,损公肥私现象相当普遍。当时,全国性的大案要案多次发生。1980年破获的“黑鱼子走私案”涉及渔业部、贸易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 300多名干部,使国家受到几百万卢布的损失。所谓“乌兹别克黑手党”案件,涉及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等一大批高级干部,他们虚报棉花产量 100万吨,从国库骗取 20多亿卢布的收购资金。有的案件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家属,如他的女儿加琳娜涉嫌“珠宝钻石走私案”,此案于 1982年 1月被破获,案由是莫斯科大马戏团出国演出时私带价值 100万美元的钻石和 50万英镑的珠宝;他的儿子尤里参与高价出售出国护照案;他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则贪污受贿 65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等等。
在吉拉斯看来,苏联“新阶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列宁时期是萌发阶段,因为列宁创立了共产党的官僚体系;斯大林时期是“新阶级”真正确立的阶段,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变成了一个只会全心全意确保他们特权的群众团体;赫鲁晓夫时期是稳固时期,“新阶级”在平庸的领导者的带领之下,实实在在地保证了自己的利益。吉拉斯在分析时引用了苏联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两种现象,以此作为自己的论据:一是政治官僚和工人阶级收入的高低悬殊,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与工业化的进程不相称;二是苏联的党员人数在短时间内激增,尤其是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的党员人数猛增了一千万。他把这两种现象结合在一起,由此得出结论:在苏联,以权谋私成为整个社会的通病,“政治成了那些想生活得豪华、食人自肥者的理想职业”;“党籍就表示党员属于一个特权阶级,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手握全权的剥削者和大老板”[12]110。
而在分析南斯拉夫时,吉拉斯认为南斯拉夫“新阶级”的出现并不像苏联那样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迅速形成的。他认为南斯拉夫在同斯大林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寡头政治。这种寡头政治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同苏联的强权相对抗才形成的。但是,当南斯拉夫已经走上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时,铁托的“个人专制”却日益明显。吉拉斯当时就向卡德尔及其他与会的南共联盟领导人反映出了自己的不满情绪,然而卡德尔等人却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同事们的这种态度,让吉拉斯认为在南共联盟中一个以铁托为首的“集团”正在形成,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官僚们利用社会主义自治改革的成果,为自己谋求生活上的安逸,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新阶级”。
吉拉斯认为“新阶级”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显示了它与其他社会政治阶层的明显区别。
首先,这个“新阶级”的形成过程同其他社会阶级不同。吉拉斯认为这一点表现在阶级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其他的社会阶级是在自己的经济基础建立之后产生的;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级则是在取得了控制社会的权利之后,才开始确立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吉拉斯认为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南共联盟,在革命胜利之前都没有自己的经济实力。而在他们取得国家政权之后,用推行国有化的方式没收私人财产,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建立起了对整个社会物质利益的独占。共产党的官僚——“新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利用、享受并且存储了国有化财产以作为他们的经济基础。
其次,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新阶级”享有政权以外的诸多特权。吉拉斯认为像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中心在中央,而斯大林、赫鲁晓夫和铁托又在政治斗争中逐渐将所有的权力控制在自己一个人手中。这种金字塔形的国家权力结构决定了上级在处理大小事务中处于决定的地位,各种任务是通过自上而下地层层下达的方式来完成。这样,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执行部门便拥有了绝对权力,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大小官员在社会中便占据了支配地位,成为拥有权势的人,而其中一些人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享受不该享受的权利,他们便成为特权者。因此,吉拉斯认为在掌权的大小官员转变为特权阶层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就转变成了“新阶级”;同时,吉拉斯认为斯大林、赫鲁晓夫和铁托在个人生活作风上日益奢侈,也给党的其他领导人乃至政府的各级官员树立不良的榜样。
第三,“新阶级”在意识上推行垄断,不允许有别于自己的思想出现。吉拉斯认为“从马克思到赫鲁晓夫,共产党的领袖以及领袖们所用的方法已历经更易。”马克思从来没有阻止其他人发表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列宁也能够容忍党内的自由讨论,只有到了斯大林时代,一切形式的党内讨论被废止。“斯大林规定……只有党中央,或者说他自己,才有权规定党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所有思想都被政府压制,自由和民主的风气已经全部丧失。因此,在吉拉斯看来,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时期是……一尊由意识形态连同某种民主而成的先锋队。”而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则“变成了对意识形态全无兴趣的群众团体”[12]111。
对于“新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问题,吉拉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做了理论上的思考。即:“共产党新阶级”必然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也必然会在社会主义国家灭亡。他在 60年代末得出的这两点认识,同他在 50年代有关“新阶级”特征的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阶级”理论体系。对于这两点认识,他给出了如下理由:
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专制性质的思想。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在 20世纪的发展成果的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对其他思想的排斥就更为明显了。马克思主义在创立之初以自然科学为依据,与自然科学之间保持一种互补的关系。但是在 20世纪科学技术有了巨大发展的情况下,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却不愿意吸收这些新的科学成果。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排斥态度上就可以发现:他们为了保证自己正统思想的地位,排斥各种与自己的理论不相容的科学理论。吉拉斯花了很长时间去阅读和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5]26-32。由此,吉拉斯认为:由于信仰这种“专制理论”,共产党不可避免地把专制主义带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中。因此,集权专制的共产党“新阶级”就注定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
第二,创建于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 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空想的思想:其思想核心是一种能够“绝对实现”的完美社会。然而从 20世纪 50到 70年代苏联、东欧的国家现实来看,吉拉斯认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先后宣布自己已经消灭了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但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就说明马克思所希望建立起的无阶级的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可能出现。由此,他得出结论: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基础是虚幻的,那么以马克思主义无阶级社会作为奋斗目标的“新阶级”自然不会在现实社会中长久地存在,人们迟早有一天会认识到“新阶级”所追求的理想是不现实的,进而人们会把它抛弃。
第三,在现实世界中,苏联、东欧乃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以及民族特点。在现实的国家建设中,政府只有将民族的理想和发展机会放在第一位,才能调动起一个国家所有的发展潜力,在世界上谋得一席之地。然而在 20世纪 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唯苏联马首是瞻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吉拉斯认为:一方面,各国的共产党“新阶级”“不顾及自己民族的特征、愿望和潜力”,在对外政策上对苏联唯命是从,在对内政策上夜郎自大、盲目发展。而另一方面,由于“新阶级”发展于未取得物质权力之前,所以它“没有在国家生活中生根”。正因如此,这个“新阶级”的想法是同国家生活脱节的。由此,吉拉斯认为这样的“新阶级”是不适应当代国家发展需要的,不论迟早,它终将被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所抛弃。
三、结语
吉拉斯一生思考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问题,而“新阶级”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他的思想始终。从“新阶级”的出现到其灭亡,吉拉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创造出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他的“新阶级”理论中,吉拉斯的许多认识在 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回味的。
他认为:在国家建设中,并没有固定的优越的模式。在《不完美的社会》一书中,吉拉斯说:“没有一个诚实的人可以相信苏维埃制度,只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便具有无条件的普遍的优越性,正如没有人可以因为美国的技术和生产领导全世界,就说美国的生活方式举世无双。”[5]113他没有畅想过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他既讽刺社会主义制度,又拒绝为资本主义辩护。诚如他一部著作的书名一样——《不完美的社会》,这就是他对现存的所有社会形态的看法。
吉拉斯细致入微地观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情况、矛盾冲突,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以此作为评价改革成功与否的依据。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冲突,即使刚刚显露出苗头也都会被吉拉斯所发现。他的这种敏锐的社会观察能力并不仅仅出现过几次,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读者都可以体会到他对社会的关注。他关心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尤其关心每一种新产生的科学技术在现实中的应用。他认为只有当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地补充到理论中时,理论才会进步。同样的道理,起源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我们今天的改革建设中不断发展也一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
然而,吉拉斯在自己作品中虽然力求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做到客观地认识苏南的特权阶层,但在他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选择的措辞用句中仍然有许多词语带有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对苏联 (包括南斯拉夫)特权阶层描述,也没有做到完全客观。例如他在文中用“荒谬绝伦”、①德文版原词:ungeremtheit(无稽之谈):德文原文:Man kann in der Geschichte des menschlichen Denkens lange suchen.bisman eine gröβere Ungereimtheit lindet als diemarxistische Leher von der Dialektik der Natur.(译文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要找到比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更荒谬的东西是不容易的。)引自 Djilas.M ilovan.Die unvolkonmene Gesellschatf Jenseits der“Neuen Klasse. ”Wien:Verlag Fritz Molden,1969..p.85.“丑怪虚伪”②德文版原词:verzerrte(歪曲变形)、unwirkliche(不真实的);德文原文:Das verzerrte und unwirkliche Antlitz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wurde zuerst im Spiegel der Naterwissenschaften,und zwar in erster Linie der theoretischen Physik,sichtbar.(译文:辩证法唯物论的虚伪丑怪的面目,首先有自然科学,主要是由理论物理学反映出来。)引自 Djilas,M ilovan,Die unvollkommene Gesellschaft:Jenseits der“Neuen Klasse.”Wien:Verlag Fritz Molden,1969..p.106.来形容马克思主义理论[5]57-73。在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中,混淆了“阶级”(class)与“阶层”(stratum)的概念。他没有辨别这两个词汇的不同含义,而直接在它们之间画上了等号。
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在影响范围上也存在局限。如前文所述,吉拉斯的多数作品都以英文版的形式面世。直到 1989年,南斯拉夫政府才允许他在国内出版部分作品和在媒体中发表讲话。这种情况的出现极大地限制了吉拉斯作品的影响力。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几乎都在西方国家里生活,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作品的抵制,他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十分低。他的“新阶级”理论只是在西方国家大受欢迎,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却鲜有人知晓。一些学者在著述中也提到了这种现象,他们认为:“只有在那些他的著作有销量以及在那些反对铁托的南斯拉夫的人群之中,吉拉斯才有他的‘市场’。在那些地方,他的‘预言’才会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东西。从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同样狂热的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吉拉斯的经历是自然而然的:像所有背弃工人阶级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一样,他缺少最基本的爱国主义精神。”[15]7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采纳了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米洛凡·吉拉斯提出的“新阶级”理论,既是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共同现象的深入思考。他将社会主义建设和各国领导阶层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视为“新阶级”问题。他的理论在结构上并不严谨,但是他提出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看法和建议,在今天看来却仍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
[1] 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M].裘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46-47.
[2] 达姆扬诺维奇.铁托自述 [M].达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350.
[3]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1卷[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
[4] БакунинМ. 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ианархия[C]//Избранныесочинение(Том.1.).,Петербург- Москва,Издотельтство’’ГолосНарод’’,1919:167.
[5] 米洛凡·吉拉斯 .不完美的社会[M].时苍,译.台北:台湾金枫出版公司,1987.
[6] 马细谱.吉拉斯思想剖析[J].世界历史,1989,(5).
[7]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M].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330.
[8] 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5.
[9] 麦德维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选译 [Z].《编译参考》编辑部,译.北京:外文出版局,1980:282.
[10] 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M].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5.
[11] 米洛凡·吉拉斯.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J].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3).
[12] 米洛凡·吉拉斯.新阶级[C].袁东,钟和夷,译.//吉拉斯谈话录 .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4.
[13] 斯蒂芬·克利索德.苏南关系 (1939—1973):文件与评注 [Z].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4] 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M].司徒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67-68.
[15] Savo Krzavac,Djilas’interviews:the blindnessof a renegade[C]//Reinhartz.Dennis,M ilovan Djilas,a revolutionary as awriter.New York: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K5:
A
1007-4937(2011)01-0141-08
2010-12-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苏联早期文化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10YJA770068)
张建华 (1962-),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国 (苏联)思想文化史、俄国汉学与中俄关系史研究。
〔责任编辑:时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