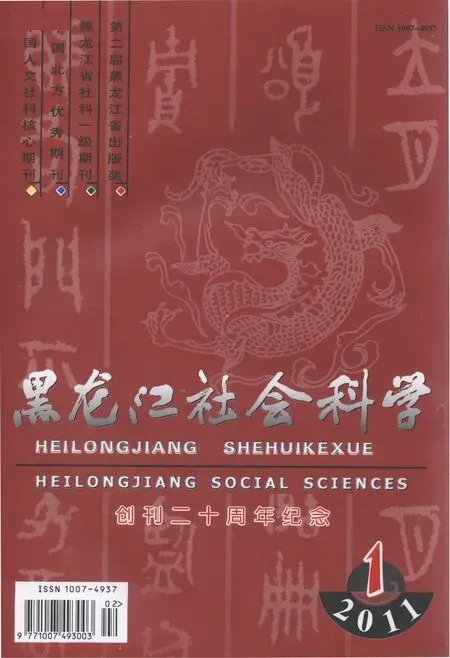祛魅现代性与重写文学史
——论以道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学谱系学
叶立文
(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祛魅现代性与重写文学史
——论以道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学谱系学
叶立文
(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就当前文学史写作对道家文化的研究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乃是文学史家在研究目标和研究手段上的本末倒置。对道家文化的文学谱系学描述这一研究手段,自 199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凌驾于祛魅现代性神话这一研究目标之上。既然历史真实在文学史家的叙述中无迹可寻,那么何妨在发扬道家文化对现代性神话的祛魅功能上大做文章?假若当今的文学史家,不再过度拘泥于对文学谱系这一类所谓“历史真实”的叙述,而是将自己投身于传统文化的精神世界,在秉承道家文化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前提下,方有可能真正实现对既往文学史神话的祛魅与重写。
现代性;道家文化;文学谱系学
自新时期以来,文学史写作始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尤其是发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重写文学史热潮,颇能折射出文学史家以现代性视野重塑新文学的叙事努力。但就文学史自身的写作实践而言,却不得不说通过对文学现象的删繁就简,1980年代的文学史家业已构筑起了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自进入 1990年代以后,经由文学史写作所建立起来的这一文学谱系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而渐趋消解。那种以文学史家自身现代性诉求为标志的文学史写作,尽管厘清和还原了新文学从启蒙到革命的现代性历史脉络,但却因其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而备受学界质疑。在此背景下,祛除1980年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启蒙现代性神话,重新发掘新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便成为 1990年代以来文学史写作中的一个新趋势。
从表面上看,这一对新文学史的重写方式,不过是学界由西入中的研究范式之转换,但潜隐其中的一个理论预设,却是对西学背景下“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神话的深刻质疑。而以传统文化的视角反观新文学,不仅有助于我们在西学视阈外重提新文学的传统价值,而且也能对现代性神话做出极具民族经验的历史反思。在这当中,道家文化以其任性逍遥、崇尚自然的文化特质而备受青睐。作为先秦诸子中最具文学气质的一种文化类型,道家文化“赐福于中国文学者甚多”[1]。即便是充满功利主义色彩的新文学,亦因道家文化的内在浸润而不失自由浪漫之品格。更为重要的是,道家文化所蕴含的自然哲学、人生哲学及社会哲学思想,尽管以其出世的面貌为入世的启蒙文学所不容,但恰恰是这种文化品格的内在反差,才使得道家文化成为知识界在 1990年代以来祛魅现代性神话的一个思想利器。有鉴于此,文学史家在反思 198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时,便格外重视新文学与道家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带来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也最终在新文学史内部催生出了一个以道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学谱系。那么,这一文学谱系究竟从何而来?它是否真如文学史家所期待的那样,能够祛除 1980年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神话?若想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从 198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说起。
1
从上个世纪 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新文学史的写作大多都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1980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新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是篡改了新文学的知识建构。换句话说,1980年代的文学史家在论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时,实际上有意无意地背离了知识学的求真原则。他们对新文学中意识形态、人道主义以及自我意识等问题的论述,无一不指向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三家,实际上已经成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温床,反传统也即意味着反封建。在“重返五四”等启蒙口号的召唤下,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自然也包括文学史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了一种绝对主义的历史迷思。在这种绝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传统文化被视为铁板一块,儒家传统伦理所滋生的迷信权威和个人崇拜等罪名,同样被嫁接于道家文化之上。颇具吊诡意味的是,道家文化对个人心性的重视、对自然之境的向往,以及对人格独立的渴慕,原本与儒家伦理的集体意识两相对立,但却在封建主义的罪名下成为儒家文化的代罪羔羊。这种对传统文化不加辨别,统一将其视为现代性对立面的做法,无疑体现了 1980年代知识分子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文学史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时所采用的现代性尺度,也表现出强烈的等级制观念:凡是不符合现代性论点的便予以嘲弄和摈弃,甚至受到严厉的谴责,直至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2]185。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传统文化在 1980年代文学史写作中的被边缘化。譬如在论及“寻根文学”时,1980年代的文学史家往往将汪曾祺的小说予以“单列”[3]。何以如此?皆因汪曾祺小说中的道家文化因素实在是太过明显,倘若将其整合进以启蒙思想为指导观念的文学史叙述,就会破坏文学史家精心构筑的现代性主脉。同样的道理,鲁迅、郭沫若、沈从文等现代文学大家也从来都被视为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至于其所受道家文化的影响,则在文学史家的现代性叙述中付之阙如。
与此同时,为防止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故鬼重来”,1980年代的文学史家还精心构筑了一个以现代性诉求为标志的文学谱系。他们认为,一种文学潮流的兴起是此前各种文学流派和思潮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它们之间彼此冲突、碰撞及融汇之后的历史合力,造就了新文学的不断演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潮流之间,始终存有一种或隐或显的连续性线索,而这种线索既是文学史家最为重视的文学史规律,也是他们构建文学谱系的逻辑起点。基于这一认识,文学史家确信任何一种文学潮流皆有其谱系学意义上的源头,“从文学到文学”的阐释框架庶足以解答某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由来。循此逻辑,五四新文学实际上成为了解释一切文学思潮及流派的历史原点。而文学史家对五四新文学启蒙本质的反复强化,无疑会构筑起这样一个文学谱系,即五四新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规约和影响了嗣后文学潮流的发展方向:1930年代的自由主义文学,1940年代的国统区文学,以及 19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皆是五四启蒙文学的流风遗绪;即便是 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 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也被解释成了启蒙文学在救亡背景下的一种历史变异。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十七年文学和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其他文学流派会在现代性的历史叙述中如此命运多舛:盖因十七年文学对政治的服膺,以及某些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皆远离了启蒙文学的国民性改造主题,故而这些文学潮流的历史地位也在文学史家的历史叙述中愈发趋于边缘。
但问题是,19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因其对文学现代性的偏执与耽溺,却与维系自身学术合法性的社会思潮之间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背离关系。就当时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而言,新启蒙运动发展至 1980年代后期,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涌入,已经出现了一股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潮流。如果抛开其中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则不难发现这股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潮流其实与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密切相关。就启蒙运动这一现代性思潮的滥觞来说,它的形成与发展,本意是要祛除欧洲中世纪宗教势力对人类价值的践踏与侮辱,但在上帝已死、人权当立的历史实践中,启蒙运动对人之主体性的高扬却渐渐演变成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进入 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越来越对自然和上帝之类的超验事物失去了敬畏之心,由此招致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及伦理危机等恶果,自然会引起人们对于现代性思潮的普遍反思。这就是说,原本祛魅宗教神话的启蒙思想,却在自身现代性诉求的不断驱使下,演化成了一个同样需要被祛魅的现代性神话。可以设想,假若中国新文学的文学史写作仍旧停留于这样一种神话学,那么就不可能真正洞察新文学自身在历史演进中所呈现的诸多复杂特征。由此可见,1990年代文学史写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其实有着借其力量祛魅现代性神话的思想取向。
2
如果从文学史写作自身的历史来看,部分学者早在 1980年代就对道家文化予以了高度关注,比如胡河清、苏丁、仲呈祥等学者,就分别从道家思想和美学趣味等层面辨析了新时期文学所受道家文化的影响[4]。但上述学者的研究并不具备自觉的文学史反思意识,他们对于道家文化的讨论,也还停留在对作家作品常见的价值判断上。不过这些颇具开创性意义的研究成果,却为 199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某些必须的个案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从 19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发掘道家文化对中国新文学的深刻影响。樊星甚至在纷繁芜杂的当代文学现象中提炼出了一条自足的文学史线索,这是一条在道家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文艺红线”:“从 80年代初的‘汪曾祺热’、‘沈从文热’到 80年代中的‘寻根文学热’、80年代末的‘伪现代派’争鸣直到 90年代初的‘国学热’,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与复兴也是随着时代精神的演进而不断显出新意的。其中,道家精神的回归与复兴又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一股大潮。”[5]在这一判断下,“新道家”成为了一股与“新儒家”并驾齐驱的文学思潮。值得重视的是,樊星对当代文学中新道家思潮的研究,本身已具备了一种自觉的谱系学意识。尽管在文章中,论者尚未明确提出对现代性神话的祛魅问题,但重申以道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却意味着在 1980年代现代性的文学史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条自足的“非现代性”文学史脉络,从汪曾祺、贾平凹、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等作家的文学传承关系上,不难一窥研究者重构文学谱系的叙事冲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樊星在讨论当代文学的“新道家”问题时,却处处受制于1980年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神话。掣肘之处首先体现为对“新道家”的命名方式:“新道家”之“新”,意在说明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下发生了一种创造性转换。在樊星看来,道家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已经具备了一种“改造国民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说,尽管有些研究者已经从 19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鉴别出了一条以道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学谱系,但这种鉴别态度的理论预设,却仍旧受困于1980年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神话。不过话说回来,这种以现代性之名反思现代性的做法,本身也是走出现代性藩篱的起步之举。
继樊星之后,杨义在《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中再度重申了新文学史上的道家文化传统。这篇文章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论者对五四新文学原点的某种价值重估。如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运动的统一性,只存在于借助外来文化以革新传统文化这个基本点上。至于在纷纭复杂的外来文化之中借助何者,对博大庞杂的本土文化如何革新,他们往往没有统一的逻辑,言人人殊,众声喧哗,未能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理论认知体系”。这与 1980年代文学史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判断显然有云霓之别,那种将五四视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起点和正宗的看法,在杨义笔下受到了尖锐挑战。按照这一论点,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学家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论者构筑道家文化之谱系的重要前提。从鲁迅、郭沫若、梁实秋、林语堂等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庶几可见道家文化如何游走于启蒙叙事的历史夹缝之间。这其中,杨义对周作人、废名及京派作家的分析尤为用心。例如周作人对新文学和晚明文学之间关系的考察,废名对老庄哲学的现代阐释,京派作家诗学趣味的道家神韵,皆成为道家文化影响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例证。由此推论,论者认为“尽管道家文化有着不少消极面,但它确实给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带来了丰富而独特的魅力,丰富了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精神素养和艺术表现形式,并以其自身文化品格的柔韧性和弹性使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熠熠生辉”。不过略感遗憾的是,论者有关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理论考察,尽管已经具备了一种明确的文学谱系学意识,但这种重构文学谱系的叙事努力,却未能实现对既往文学史神话的颠覆与消解。个中原因,显然与论者根深蒂固的辩证法思维有关,那种面面俱到式的求全之论,只能再度证明文学史写作中现代性神话的强势。因为论者的研究方式,始终立足于现代作家对道家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上,即胡适、鲁迅等人对道家文化的思考与叙述,无非是想用启蒙—理性的现代性精神去改造传统文化,而在这一前提下构筑起来的文学谱系,焉能证明自身对于现代性神话的祛魅功能?说到底,这种在文学史现代性叙事中重构道家文化谱系的研究方式,本质上是对道家文化身份合法性的谋求,即在现代性语境中,道家文化通过自身的创造性转换,业已谋得了现代性神话的合法性承诺。
就 1990年代“国学热”兴起的历史背景而言,是“海外新儒学”促成了大陆知识分子对国学的再度重视。海外新儒家以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补救现代性恶果的做法,在被大陆知识界竞相效尤的过程中却处处彰显了我们民族的某种文化自卑感,即在面对全球化的现代性热潮时,我们始终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某种创造性转换,似乎只有经过现代文化的洗礼,传统文化才能存活于世,才能真正起到补救人心的道德或伦理效用。这种文化态度无疑在体现我们文化自卑感的同时,也间接印证了现代性神话对于人类社会的魅惑功能。有论者认为,当前有关中国新文学和道家文化问题的研究已经陷入了某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即“在回答作家作品的道家精神来源这个问题时,一般认为,一是作家对道家思想文化的认同;二是个人生活对作家的影响或启示;三是作家的性格、气质与道家精神有关联。在宏观研究方面只有极少数的轮廓式描述。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还缺乏对这个问题领域的宏观、深入和广泛的研究,题域有待拓展、延伸”[6]。其实这一判断在指出种种研究困境的同时,也忽略了造成上述局面的真正原因,而这一原因即为研究者在研究目标和研究手段之间所存有的悖谬现象。
3
如果仅就研究目标而言,1990年代的文学史家和其他研究者,之所以对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文化如此重视,盖因道家文化自身的文化品格使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经验是一种以思辨方式去探索和把握宇宙本体、宇宙生成等问题的智慧体系。老子主张的“道法自然”,庄子强调“天而不人”,是一种不受人为操作、干扰和改变的性质,具有自足和封闭的内在体系。他们对自然的崇尚,恰恰与现代性所强调的工具理性相异其趣。而文学史家对道家文化的重视,正是看重了道家文化对工具理性的祛魅功能,那种通过“致虚极,守静笃”、“若昏”、“若遗”等方式达成生命尊严和实现个体价值的做法,显然能在道法自然中消解工具理性的秩序与规范。就此而言,重申新文学中的道家文化传统,就不仅仅是出于一种重写文学史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祛除现代性神话的价值诉求。但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中,1990年代的文学史家之所以陷入现代性神话的藩篱而无以自拔,皆因其反思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晦暗不彰。对他们而言,重申新文学中的道家文化谱系,本意是想借此祛除新文学的功利色彩,强调在启蒙—理性之外人与自然的融洽和谐,希望能够以道家文化为契机,走出启蒙思想在文学史叙述中所织就的现代性神话。不过事实却是,1990年代文学史家的历史叙述方式,仅仅在构筑以道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学谱系学方面,显示出了祛魅现代性的研究意图,但在具体的研究手段,即历史叙述层面却仍旧属于一种现代性叙事。
如果深入辨析 1990年代以来文学史家的历史观念,就会发现他们对于道家文化的谱系学构筑,其实来自于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本质主义相信任何事物都具有唯一性的永恒本质,现象本身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本质的途径,而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唯一本质,则是现代性神话为本质主义者所预设的一条必由之路。有鉴于此,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在对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关系的考察中便具有了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他们对于文学本质 (文学规律)的提炼,即表现为对文学史中道家文化之间内在连续性的寻求。在这种研究方式中,那些受道家文化影响的现当代作家,便被文学史家整合进了一个以道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学谱系。其中从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直到阿城和贾平凹等寻根小说诸家的连续性线索,是目前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道家文化谱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文学史家的这种历史叙述中,上述作家受道家文化影响所生成的个人心性却蜕化成了文学史家构筑文学谱系时亟需的重要论据,从个人心性的分析到文学谱系的整合,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家在其本质主义思维中深深遮蔽了道家崇尚个人修养的文化品格。而这种秩序化的文学谱系,也无疑成了现代性文学史观的一个变种。但问题在于,这种以先验的本质主义思维整合文学现象的做法,却不幸印证了反本质主义者的某种真知灼见,即“小说根据虚构的事实描写真实,历史搜集事实组合虚构”[7]。与小说家对真实的寻求不同,文学史家并不缺乏对各类史料的知识考古,但在总结和提炼规律的过程中,作为本质主义者的文学史家便会暴露出虚构文学谱系的叙述意图。关于这一点,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有具体说明,他认为在现代性神话中,“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即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历史 (文学史)写作成为历史学家 (文学史家)对文献的“组织”与“分配”。这其中自然有着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作为一个本质主义者所特有的思想迷思,也正是因为这一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家对道家文化所进行的文学谱系学叙述,已然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性神话。
就当前文学史写作对道家文化的研究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乃是文学史家在研究目标和研究手段上的本末倒置。对道家文化的文学谱系学描述这一研究手段,自 199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凌驾于祛魅现代性神话这一研究目标之上。不少论者执持于对新文学史中道家文化线索的持续叩询,却深深遗忘了这种做法究竟所为何来?倘若仅仅是还原新文学史上所受道家文化影响的文学流派与思潮,那么显然不足以警醒我们对 1980年代文学史写作中现代性神话的深入反思。更何况以道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学谱系学究竟能否成立仍有待时间检验,因为我们知道,在文学史家的历史叙述中,“当历史叙述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而自诩的时候,新历史主义使人们突然意识到,现存的历史其实是人们叙述中的历史,必然多少带有叙述者的烙印,标志着一定话语权力对写作的影响,而不可能还原于历史自身”[2]185。既然历史真实在文学史家的叙述中无迹可寻,那么何妨在发扬道家文化对现代性神话的祛魅功能上大做文章?假若当今的文学史家,不再过度拘泥于对文学谱系这一类所谓“历史真实”的叙述,而是将自己投身于传统文化的精神世界,在秉承道家文化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前提下,方有可能真正实现对既往文学史神话的祛魅与重写。
[1] 杨义.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J].中国社会科学,1997,(2).
[2] 董之林 .盈尺集 [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3] 王尧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J].江海学刊,2007,(5).
[4] 胡河清 .论阿城、马原、张炜:道家文化智慧的沿革 [J].文学评论,1989,(2);苏丁,仲呈祥 .《棋王》与道家美学[J].当代文学评论,1985,(3).
[5] 樊星 .当代新道家——“当代思想史”片断[J].文艺评论,1996,(2).
[6] 刘小平 .中国当代文学与道家文化研究综述[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7] 沟口雄三,孙歌 .关于“知识共同体”[J].开放时代,2001,(11). 〔责任编辑:王晓春〕
J1
A
1007-4937(2011)01-0115-04
2010-12-2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播史论 (1949-2000)”(07JG751012)
叶立文 (1973-),男,甘肃陇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