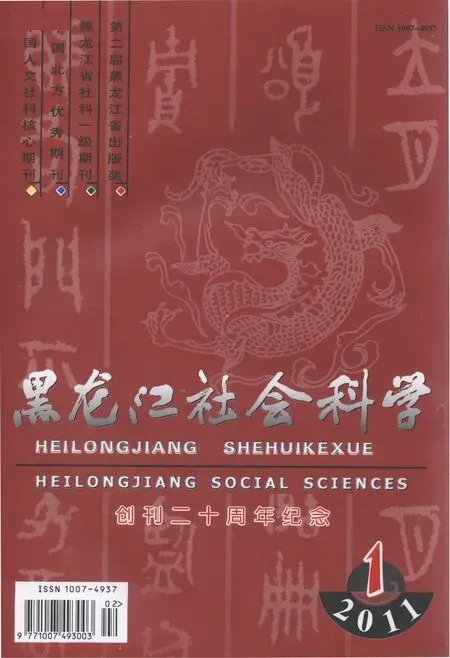酒肆与淫舍:李白维摩信仰中的取舍问题
李小荣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 350007)
酒肆与淫舍:李白维摩信仰中的取舍问题
李小荣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 350007)
在大乘佛教的人物谱系中,诗仙李白最为尊崇的是维摩诘,甚至还以之自比。但是,从其存世作品分析,则知李白的维摩信仰自有特色,即主要凸显的是《维摩诘经·方便品》“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的精神内涵,而较少谈及“入诸淫舍,示欲之过”。
李白;维摩信仰;酒肆;淫舍
众所周知,作为唐代道教诗人的杰出代表,李白一生的主导信仰自然是道教。但是,因受时代风气的熏染,诗人对佛教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比如其存世作品就涉及了西方弥陀信仰、尊胜陀罗尼信仰以及维摩诘信仰等多个层面。其中,对于大乘佛教中的经典人物,李白最为欣赏的是维摩居士,而最直接的文本证据就是诗人夫子自道式的作品《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以下简称《答湖州》),诗云:“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1]876显然,诗人于此表达出身份的自我认同,他把具有道教意义的“谪仙人”与佛教含蕴丰富的“青莲居士”、“金粟如来”(维摩诘的前身)并置,说明诗人具有仙、佛一致的思想。《答湖州》一诗,清人王琦怀疑是“长安遇贺监以后之作,故有‘谪仙人’之称”[1]1581,李白天宝元年 (742年)与贺知章相识于长安时,贺便称白是“天上谪仙人”。今人于此,则更细化,如安旗先生在《李白诗秘要》中认为当作于天宝六载 (747年)白自吴赴越过湖州时,詹锳先生则说其中的“三十春”应从“酒隐安陆”之年算起,故诗作于至德元载 (757年)左右[2]。考李白出川之后,在开元十五年 (727年)就婚于安陆的故相国许圉师之家,娶其孙女为妻。《秋于敬亭送从侄端游庐山序》回忆云:“酒隐安陆,蹉跎十年。”[1]1267其中,“酒隐”与《答湖州》的“酒肆藏名”,其义一也,所以,我们比较赞成詹先生的系年。另外,诗中“酒肆”一词,尤其值得探讨,一方面点明了酒诗是李白创作的中心题材,另一方面则揭示了“酒”是诗人道、佛信仰的契合点。具体说来,道教方面的表现是“酒仙”,佛教方面的表现则为《维摩诘经·方便品》所说“入诸酒肆,能立其志”之精神内涵。
一、《答湖州》诗的思想内容
《答湖州》一诗虽只有短短 28字,然而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兹从道、佛两方面加以分疏。
从道教方面言,李白最看重的是“谪仙人”身份。“谪仙”有多重含义,然而最重要的是指太白星精的谪世。这在当时人对李白的评价中,就已成为共识。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曰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则云:“先生得天地秀气耶?不然,何异于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贺监号为谪仙,不其然乎?”由此可见,李白的起名及其“谪仙”的由来,悉与太白星精有关。这在后世的道教传记中,还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如张天雨集《玄品录》卷五“道华”说李白“因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制青绮冠帔一副,将东归蓬莱,仍羽人驾丹丘耳。世以为太白之精,一号上清鉴逸真人”,则知李白在道教的神仙系谱中,是有仙真封号的人物。《太平广记》卷四十引《逸史》又云:“章仇兼琼尚书镇西川,常令左右搜访道术士。有一鬻酒者,酒胜其党,又不急于利,赊贷甚众。每有纱帽黎杖四人来饮酒,皆至数斗,积债十余石,即并还之。谈谐笑谑,酣畅而去……时玄宗好道,章仇公遂奏其事,诏召孙公问之,公曰:‘此太白酒星耳。仙格绝高,每游人间饮酒,处处皆至,尤乐蜀中。’”周勋初先生由此分析该传说的产生和唐时蜀中生产名酒有关[3],而李白正是在蜀中长大,年轻时即善于豪饮。既然太白星也是酒星,故当诗人荣膺“谪仙人”的封号之后,他便很自然地自称为“酒仙”,其《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文末即署名曰“酒仙翁李白辞”,杜甫《饮中八仙歌》则载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崔成甫《赠十二》又说“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此显然是把酒星与酒仙合二为一了。在道教史上,被称为谪仙者有多人,但李白认为与自己同调的只有东方朔。其自述身世之作的《玉壶吟》说:“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天宝十二载 (753年)在宣城所写《赠崔司户文昆季》说:“惟昔不自媒,担簦西入秦。攀龙九天上,忝列岁星臣。”天宝十三载作《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云:“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调笑当时人,中天谢云雨。”天宝改元所作《留别西河刘少府》又云:“闲倾鲁壶酒,笑对刘公荣。谓我是方朔,人间落岁星。白衣干万乘,何事去天庭?”其间的“岁星”,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木星,而东方朔恰恰被视为是岁星谪世于人间。如果比较一下李白、东方朔的经历,则不难发现两人有不少共同点,如:都是星君谪世,皆嗜酒如命,皆以文学才能而见遇于帝王,皆有自傲的个性和成就王业的宏伟理想。换言之,两人无论在个性、爱好与才能方面,悉具有高度的可比性和一致性。
而作为道教徒的李白,自然免不了炼丹修行之举。依据相关道典,知酒在炼丹和服丹时是不可或缺者。《太清修丹秘诀》载“采种灵砂修丹法”是:“于十二月初一日,先以美酒珍味肉食药物补助,令其气实。”《太极真人九转还丹经要诀》说“王母四童散方”的制作是:“右先熬胡麻,令香。凡六物精治分等,合捣三万杵。旦以酒饵三方,七日再服之,亦可以水服之……此返婴童之秘道者也,善填精补脑矣。”宋人张君房所编《云笈七签》卷八二记“仙人下三虫伏尸方”是:“茯苓十斤,商陆根削去上皮,但取下白者五斤,清酒麦麹各五斤,并炊,酿之。酒置盆中,封之二十日,药成。”明乎此,则不难理解李白为什么会“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赠内》)、“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了,原来饮酒是诗人修道成仙的日常功课啊!元人李鹏飞所集《三元延寿参赞书》卷三云:“神仙不禁酒,以能行气壮神,然不过饮也。”而自诩为酒仙的李白,当然不会遵守“不过饮”的戒律,因为他有饮酒而成仙的急迫心理。作于干元二年 (759年)遇赦放回南游潇湘时《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云:“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郭沫若先生解释说“李白要‘刬却君山’是从农事上着想,要扩大耕种面积。‘巴陵无限酒’不是让李白三两人来醉,而是让所有的巴陵人来醉。”[4]这可能是求解过深了。《神仙感遇传》卷五“王廓”条即云:“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州随船将过洞庭,风甚,泊舟君山下,与数人出岸,寻山径登山而行,忽闻酒香,问诸同行者,皆无。良久,香愈甚,路侧山崖间,见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余步,平石上有洼穴,中有酒,掬而饮之,味极醇美。饮可半斗余,陶然似醉,坐歇洼穴之侧,稍醒,乃归。舟中话于同侣,众人争往求之,无复所见。自此充悦无疾,渐厌五谷,乃入名山学道,去后看经云:‘君山有天酒,饮之者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据此,在唐人心目中,君山上是产天酒 (即仙酒)之地。如果刬却了君山,岂不整个洞庭湖水都变成了仙酒,如此,则真是“醉杀洞庭秋”了,即饮之者皆可成仙。
就《答湖州》一诗而言,其佛教方面的含蕴远比道教方面丰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关键词,它们都与《维摩诘所说经》有密切的关联,即青莲居士、酒肆藏名和金粟如来。
先说青莲居士。关于这一称号的由来,清人王琦首先揭橥了它和佛教经典的关系,指出:“青莲花出西域,梵语谓之优钵罗花,清净香洁,不染纤尘。太白自号,疑取此义。”[1]1574今人王新霞,则通过细检李白传世作品中“青莲”一词的实际运用,进一步补充说明了王氏观点的正确,认为:“李白取号‘青莲居士’,应是来源于佛教的内涵,表现了诗人对洁净芬芳、一尘不染的佛教境界的向往。”[5]其实,“青莲”一词,高度地展示了李白张扬的个性,是他对身、心的自我肯定。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云:“问曰:一切众生皆求智慧,云何独佛一人得一切智?答曰:佛于一切众生中第一,故独得一切智……譬如须弥山于众山中自然最第一,如四大中火最有力能照能烧,佛亦如是,于一切众生中最第一,故得一切智。问曰:佛何以故于一切众生中独最第一?答曰:如先答得一切智故,今当更说:佛自利益、亦利益他,故于众生中最第一。如一切照中日为第一,一切人中转轮圣王最第一,一切莲华中青莲华为第一,一切陆生华须曼色第一。”显而易见,此处“青莲华”有象征佛智第一之义。同人所译《维摩诘所说经》卷一《佛国品》则载长者宝积以偈颂佛曰:“目净修广如青莲,心净已度诸禅净。”其中,前一句赞颂了佛的庄严之相,吉藏《维摩经义疏》卷二解释说:“此句叹佛形也。形有五相,目为其首……世俗常云: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故头为一身之最,目为一面之标。就胜而叹。又佛以慈眼等视众生,慈为德本,故就本而叹……《智度论》云:陆生须曼为最,水生青莲第一。天竺有青莲花,其叶修而旷,青白分明,有大人眼相,故借以喻焉。”统而观之,在佛典中,青莲具有佛相庄严、佛智第一的双重象征义。李白自号“青莲居士”,当有以佛自喻的含义,此在《答湖州》诗的末句说得更加直白。
次说“酒肆藏名”。本来,酒戒是佛教的基本戒律之一,所以酒肆是出家人禁止出入之地。梁僧伽婆罗译《解脱道论》卷一即云:“云何非行处?若有比丘入于淫舍、寡妇舍、处女舍……比丘尼舍及诸酒肆,亲近国王大臣外道沙门非法伴侣,如是等辈,无信乐心,常于四众不生饶益,甚可厌患,此谓非行处。”甚至于在家居士,也应遵守不入酒肆的戒律,北凉昙无谶译《优婆塞戒经》卷三即谓:“善男子,受优婆塞戒,有五处所所不应游:屠儿、淫女、酒肆、国王、旃陀罗舍。”但是,在《维摩诘所说经》之《方便品》里,则赞扬维摩居士是“入诸酒肆,能立其志”。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此,隋智顗撰《维摩经文疏》卷九释疑云:“入酒肆,示迹也。自其志者,酒有三十六失,凡人若饮,昏神乱道,胜志皆颓。大士能自立志,亦令他立志。志者,四种菩提心志不坏,即是不可思议解脱四种净土因不退也。复次,酒是烦恼肆,是五阴凡夫饮面米酒,亦饮烦恼酒。二乘饮空无相酒,二乘不吐此酒,故于佛性生无常想,故经云:‘持空三昧瓶,醉般若无相’也。通教同二乘,别教未见中道,亦是醉无酒。举要言之,一切烦恼昏醉悉名为酒,菩萨虽复入一切烦恼而用烦恼为佛事,如饮千钟而不昏乱,故云能立其志。”据此,智顗是从本、迹范畴来看待维摩诘出入酒肆之举的,由烦恼即菩提的思想高度加以解释,指出大乘佛教的精髓在于不舍凡夫事而入佛法 (涅槃),“酒肆”只是烦恼的比喻而已。或者说,维摩诘虽然入诸酒肆,但志不在酒,而是借酒说法悟道。
如果我们综合分析“青莲”、“酒肆”之寓意,则知在《答湖州》中,李白自称的“青莲居士”,它和“酒肆藏名”所指的维摩诘居士,含义相同。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二三云:“犹如青莲华,红赤白莲花,水生水长,出水上,不着水。如是如来世间生,世间长,出世间行,不着世间法。”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共译《长阿含经》卷一也说:“譬如优钵罗花、钵头摩华、鸠勿头华、分陀利华,或有始出污泥未至水者,或有已出与水平者,或有出水未敷开者,然皆不为水所染着,易可开敷。世界众生,亦复如是。”“优钵罗”即“青莲”,它与其他颜色的莲花一样,皆可譬喻佛性,即虽处世间烦恼法中,却不为烦恼所束缚,这恰与维摩诘“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的精神实质毫无二致。此外,晚唐五代诗人贯休《迎真身》诗云:“可怜优钵罗花树,三十年来一度春。”《道情偈三首》则云:“优钵罗花万劫春。”据北凉昙无谶译《悲华经》卷五说:“未来之世过一恒河沙等阿僧祇劫,入第二恒河沙等阿僧祇劫,是时有劫名曰遍敷优钵罗华,此佛世界当名愿爱,是时人民寿八万岁。”则知《道情偈》的用典契合佛典本义,而《迎真身》之“三十年”说,与李白《答湖州》相同,当是受中国本土文化中“三十年”为一世观念的影响。
从《答湖州》诗看,李白也深受佛教三世观念的熏染。比如“青莲居士”、“酒肆藏名”讲的是今世(现实人生),“谪仙人”虽着眼于今世,重点却在交代前世因缘,即李白的前身是仙人,最后一句则讲未来世,意即李白的理想是成为金粟如来。
关于金粟如来的出处,主要见于隋唐时代的典籍。智顗撰《维摩经文疏》卷九云:“维摩义前具翻释,长者义今当略解。原其本地,旧云金粟如来,即是法身长者。故《法华经》云:大富长者即是如来,语其迹也。位居法云,或云等觉,望佛为菩萨,即是长者子,望下地菩萨名等觉,佛即是长者也。”“今净名或云是金粟如来,已得上寂灭忍。或云位居等觉,得中品寂灭忍;或云位在法云,得下寂灭忍。若中下无明已断,但有微习不能牵生,名无生忍,即高位也。所以不受寂灭忍名者,正为让佛,但受无生法忍也。”卷二十八又云:“寻末取本者,明大士是金粟如来所得法身与今释迦法身不异。吉藏撰《维摩经义疏》卷一说:“有人言:文殊师利本是龙种上尊佛,净名即是金栗如来。相传云:金粟如来出《思惟三昧经》,今未见本。”《净名玄论》卷二则说:“净名文殊,皆往古如来,现为菩萨。如《首楞严》云文殊为龙种尊佛,《发迹经》云净名即金粟如来。”综而论之,则知维摩诘 (又译“净名”)居士的前世已得佛的果位 (本),但为教化人间,于今世现身为菩萨 (迹),故有“让佛”之称。这与文殊菩萨的情况相同,因为后者其实也早得佛果,号龙种尊佛。
至此,我们会发现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虽说李白《答湖州》诗是仙佛并置,然而仙、佛的时空意识并不相同:从仙的这一层面讲,李白认为自己是谪降,即前身 (太白星精、酒仙,天上)→今世 (酒肆藏名者,凡尘);从佛的方面讲则是涅槃,即今世 (青莲居士)→后身 (金粟如来)。当然,后一层面恰与佛典本义相反,可视作李白的创新之一。
二、李白对维摩信仰的取舍
宋僧释惠洪《冷斋夜话》“舒王编四家诗”条载王安石语:“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从创作题材言,荆公的评判确为有见。更值得注意的是,就《维摩诘所说经》来说,其《方便品》也涉及了酒与女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女性,是颇受正统人士诟病的淫女。经云维摩诘长者:“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离。资财无量,摄诸贫民……虽乐世典,常乐佛法……一切治生谐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诸四衢,饶益众生;入治政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诱开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长者,长者中尊,为说胜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断其贪着……长者维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由此可见,至少在身份上,李白与维摩诘居士有相似之处,比如李白也出生于富商家庭,好乐散施;在爱好上,两人都兼通世典与佛典,都喜欢谈论政治、有治国安邦的理想;都好“游”,只是维摩诘重点在游化芸芸众生,而李白重在干谒权贵和山水之游,等等,不一而足。
一般说来,古代文人在接受维摩信仰时,常打着不舍凡夫事的旗号来行声色之好。最突出的表现有二,即酒与女性 (歌妓、艺妓)。唐代另一大诗人白居易《酒筵上答张居士》即说:“要知前尘灭,无妨外相同。虽过酒肆上,不离道场中。弦管声非实,花钿色是空。何人知此义,唯有净名翁。”乐天于此,不但公开宣称酒肆即道场的思想,同时也指明声色之本性在空。当然,这也有内典依据。
隋智顗所说《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三云:“菩萨具持两种,故名大乘戒。不退者,行于非道善巧方便,淫舍酒家非法之处辄以度人,而于禁戒无有退失,如医疗病不为病所污,故名不退。随顺者,随物机宜随顺道理,故名随顺戒。”灌顶撰《大般涅槃经疏》卷二又云:“举足下足皆具佛法,淫舍酒肆无非正道,住佛威仪乃名具足。当知五戒与威仪有本有迹,能于本不动普现众迹,是名具足戒威仪。”这师徒两人的解释,虽然皆着眼于戒律,却也可以用来解释处于菩萨位的维摩居士出入酒肆、淫舍来化度众生的成因。《注维摩诘所说经》卷二在“入诸淫舍,示欲之过”之句下有注云:“什曰:外国有一女人,身体金色。有长者子,名达暮多罗,以千两金要入竹林,同载而去。文殊师利于中道变身为白衣,身着宝衣,衣甚严好。女人见之,贪心内发。文殊言:‘汝欲得衣者,当发菩提心。’女曰:‘何等为菩提心?’答曰:‘汝身是也。’问曰:‘云何是?’答曰:‘菩提性空,汝身亦空。’以此故,是此女曾于迦叶佛所宿殖善本,修智慧,闻是说,即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已,将示欲之过。还与长者子入竹林,入林中已,自现身死,膖胀臭烂。长者子见已,甚大怖畏,往诣佛所。佛为说法,亦得法忍。示欲之过,有如是利益也。肇曰:外国淫人别立聚落,凡豫士之流,目不暂顾,而大士同其欲,然后示其过也。”“什”即鸠摩罗什,“肇”即罗什高弟僧肇。其中,什法师的注解引用了一个故事,具体说明“入诸淫舍”的目的在于“示欲之过”。僧肇则说明了印度的一个习俗,即建立专门的馆舍来从事色情服务,但维摩出入其间,并非是嗜淫,而是彰显淫欲之过。正如《维摩诘所说经》卷二《佛道品》所云:“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道。”原来,“淫女”、“淫舍”都只是维摩教化众生的一种方便。另外,大乘空宗经典则从中道的角度来解释“淫欲”与“菩提”的关系,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六有云:“淫欲即是道,恚痴亦如是。如此三事中,有无量佛道。若有人分别,淫怒痴及道,是人去佛远,譬如天与地。道及淫怒痴,是一法平等。”宋人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五则说:“淫欲即是道,恚痴亦复然。如此三事中,无量诸佛道。今问淫事秽污佛道清净,安指秽事名为净道?答:观淫怒痴相同水月,了染净体,性如虚空,遇顺无著,逢违不瞋。于恶境界,得解脱门,乃行非道,通达佛道,是名无碍人。”此从体相、净染之范畴给出了“淫欲即是道”的成因解释。
回过头来看看李白的诗文创作,虽然女性题材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诗人根本就不像《维摩诘经》一样,有“入诸淫舍,示欲之过”的思想主题之表现。确实,李白是很喜欢美女,在各种酒筵上也遇见过各色女性,甚至于青楼女子,却几乎找不出诗人有淫乱之举[6]。诗人更欣赏的是酒会上女性的可爱醉态和多才多艺。如《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一)云:“落花纷纷稍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酡。”其二云:“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白纻辞三首》(其三)云:“明妆丽服夺春晖,扬眉转袖若雪飞……《激楚》《结风》醉忘归。”《东山吟》谓:“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浇君同所欢。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书情赠蔡舍人雄》云:“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金陵酒肆留别》云:“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云:“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园东。”《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云:“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行云且莫去,留醉楚王宫。”《忆东山二首》(其二)云:“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赠段七娘》云:“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无论胡姬、吴姬、段七娘,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青楼女,她们都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多又能歌善舞,具有较高的艺术才能,特别是谢 (谢安)妓,更成了李白政治风流的象征,寄托了其远大的理想和信念。
再说李白的酒诗,则多表现出《维摩诘所说经》“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的思想信念。这点除了前面所引谢妓 (东山妓)诸诗外,当还有多种情况。对此,台湾的林梧卫先生做过详细的梳理,他从多方面分析了李白的酒诗,如表达社交功能之赠答类,其主旨有发牢骚、思亲情、戏谑语、言隐遁、报国心等;而内在抒发功能类,其主旨则有恃才傲物纵酒歌、怀才不遇酒解忧和诗才零落悟道游[1]46-71。但无论哪一类,不管其主旨如何,都可以归入佛典所说的“烦恼酒”。
前引《维摩经文疏》卷九,智者大师已经从本迹范畴的层面分析了维摩诘居士“入诸酒肆”的精神实质,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一切烦恼昏醉悉名为酒,菩萨虽复入一切烦恼而用烦恼为佛事,如饮千钟而不昏乱,故云能立其志”。其中,饮千钟而不昏乱之喻,表现了维摩诘居士愈饮愈醒的豪饮,而李白的饮酒,恰好也呈现了这一特点[7]85-89。
李白的酒诗,表现了极其丰富的内心情感和理想信念,喜怒哀乐,一一毕现其中。为加深读者印象,兹举出一些具体的诗句。如《行路难》(其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千载身后名”,表达了诗人旷达的情怀;《门有车马客行》之“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叹我万里游,飘飖三十春。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慨叹的是理想的破灭和怀才不遇的悲凉;《悲歌行》之“悲来不吟还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抒发了壮志难酬和知音不赏的苦闷;《流夜郎赠辛判官》之“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表现了平交王侯的气概;《赠钱征君少阳》之“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抒写了极度的自信;《广陵赠别》“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表现了真挚的朋友之情;《五松山送殷淑》之“抚酒惜此月,流光畏蹉跎”,悲叹的是青春永逝和生命的无常。诸如此类,无不是诗人对现实生活 (即佛教所说的烦恼世界)情感的真实表现。当然,李白一生爱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前文所揭示的修仙炼丹之外,也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太平广记》卷二○一引《本事诗》即云:“白自幼好酒,于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显然,诗人自建酒楼,表明他与维摩诘一样,皆有从商的经历。此外,这也为其出入酒肆提供了方便之门。
初唐窥基《说无垢经疏》卷三对经文“入诸淫舍”至“游诸伎乐”之赞曰:“此有二句:一处欲劝超染,二游偶令念知,令彼正念正知,不因伎乐业妄忆邪解故。旧云‘入诸酒肆,能立其志。’酒肆多有弦歌,立志令正知念也。文虽有异,意会可知。”据此,则知酒肆常与伎乐相联,而伎乐的表演者多是艺妓 (如歌妓、舞妓或青楼女子)。而李白的酒诗,正好也呈现了这一特点,即常常把酒、女性和音乐融为一体。但是,诗人的主旨,若与《维摩诘经》比较,仅仅重在表现“入诸酒肆,能立其志”,而较少谈及“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原因何在?
考诸印度文化,其对女性较为轻视,这在佛典中也有所表现。如《正法念处经》卷十六说“女人之性,心多妒嫉”,卷二十五又说“女人之性,三种放逸。何等为三?一者自恃身色而生放逸,二者自恃丈夫而生放逸,三者憍慢而生放逸”。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三则说:“女人之性,欲心猛利。”唐般若译《大乘理趣六般若蜜多经》卷五又云:“女性妖媚幻惑人,如怨诈亲不可近。贪欲迷荒坏清净,如水瀑流摧石壁。女人之性多谄曲,如水随流性不定,恒怀异志背其夫,智者谛思应远离。”总之,女性是罪恶之源,修行者应当远离她们。
但是,李白对女性比较尊重,其性别观基本上是平等的。尤其对酒宴上相识的青楼女子,他还有赞颂之词。《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云:“出舞两美人,飘飖若云仙。”此即把青楼之妓比作仙女,溢美之情表露无遗。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诗人内心根深蒂固的道教信仰,特别是作为一个上清派的道士,李白对女性尤其女仙是无比尊崇的。女仙常常是诗人存思的对象,而且是诗人进入仙境的引路人,《游泰山六首》(其一)即说:“玉女四五人,飘飖下九垓。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玉女,即女仙,她们还赠诗人以仙酒。或许出于爱屋及乌的人之常情,故诗人对妓女并无轻视之意。
最后,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历史上也出现过酒肆藏名的释家人物,比如《景德传灯录》卷三载禅宗东土二祖慧可是:“韬光混迹,变易仪相:或入诸酒肆,或过于屠门,或习街谈,或随厮役。人问之曰:‘师是道人,何故如是?’师曰:‘我自调心,何关汝事?’”其行为正体现了维摩诘“入诸酒肆,能立其志”的精神。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宋时期的杯度法师,他虽然“饮酒啖肉”,竟然也与李白一样,有着“谪仙”之称。释道并尊既然可以安于释家人物杯度身上,当然也可用于道教人物李白。从现实的角度,特别是李白自己对佛、道的态度看,他更看重的是两教思想的相通之处,经常有仙佛一致的主张,而《答湖州》诗中“酒”字,正是二者相通的契合点之一。再则,从李白涉及僧人与佛教题材的作品看,“酒”并非是禁绝的用字,如《赠僧行融》云:“赋诗旃檀阁,纵酒鹦鹉洲。”《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云:“天乐流香阁,莲舟飏晚风。恭陪竹林宴,留醉与陶公。”《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云:“了见水中月,青莲出尘埃。虽游道林室,亦举陶潜杯。”可见与李白交往的僧人,似乎不忌讳诗人在佛门圣地用酒,此亦是《维摩诘所说经》之方便观的体现吧。
[1] 李太白全集 [M].王琦,注 .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詹锳 .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2633.
[3] 周勋初 .诗仙李白之谜[C]//周勋初文集:第 4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210.
[4] 郭沫若 .李白与杜甫[M].西安: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130.
[5] 王新霞 .“青莲居士”由来考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2).
[6] 参氏 .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12.
[7] 林梧卫 .李白诗歌酒意象之研究[D].玄奘人文社会学院中国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J2
A
1007-4937(2011)01-0122-05
2010-12-25
高校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1016)
李小荣 (1969-),男,江西宁都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宗教文学与敦煌文献研究。
〔责任编辑:王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