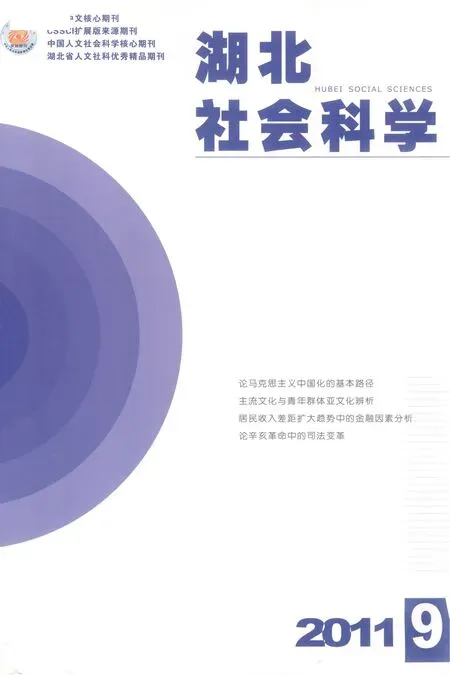论多丽丝·莱辛“妇女政治主题”小说
王 群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论多丽丝·莱辛“妇女政治主题”小说
王 群
(华中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在多丽丝·莱辛的创作中,“政治主题”和“妇女主题”是两大重要主题。莱辛重要的“政治主题”小说往往以女性为主人公,在对种族、歧视、战争、暴力等社会政治问题等进行批判和揭露时,能引起对主人公作为女性的同情和关切。同时,她最杰出的“妇女主题”小说在对妇女的境遇进行探析时,却往往又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把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与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紧密相连,折射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众多的政治问题。这些小说是“政治主题”和“妇女主题”的精湛结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多丽丝·莱辛;政治主题;妇女主题
多丽丝·莱辛 (Doris Lessing,1919— )是公认的英国当代最优秀的女作家,她创作丰富深邃、视野广阔超越、风格独特多变,长期以卓越的艺术成就蜚声于战后的英国文坛。自处女作《野草在歌唱》1950年问世以来,莱辛共发表了50多部作品,包括长篇、中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自传、诗歌、剧本、散文、文论和其他纪实文学,并于2007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学者李福祥曾发表文章总结多丽丝·莱辛的创作,把她的作品归类为“政治主题”和“妇女主题”,并分别进行详细的探讨,指出“政治主题和妇女的人生探索及命运主题始终是莱辛关注的焦点”,他的精辟分析为中国学界研究莱辛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益。[1](P40)本文认为,莱辛的许多作品是“政治主题”与“妇女主题”的艺术融合。她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主题”小说往往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如《野草在歌唱》、《暴力的孩子们》,这些作品在对种族、歧视、战争、暴力等社会丑恶、时代弊端等进行最无情的批判和揭露时,能引起对主人公作为女性同情和关切,兼有“妇女主题”小说的特点。另一方面,莱辛最杰出的“妇女主题”小说,如《金色笔记》,在对妇女的境遇进行了探析的同时,却又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把对妇女问题的深思与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紧密相连,折射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众多的政治问题,具有“政治主题”小说的特质。这些小说是“政治主题”和“妇女主题”的精湛结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本文将结合莱辛的几部重要小说对此进行详细论证。
一
《野草在歌唱》是莱辛的处女作,发表于1950年,被认为是“莱辛早期文学创作中的一部颇具代表意义的政治主题作品小说,是莱辛声讨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战斗檄文”。[1](p40)小说采用倒叙的方式,循着玛丽在非洲殖民地的生命历程,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展示了种族歧视制度下的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和这片土地上的被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扭曲了的人性,揭露了殖民社会和种族歧视制度的罪恶。《野草在歌唱》出版之时,正值二战后世界各地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帝国殖民主义大厦也摇摇欲坠,这部以反对殖民主义为主题的小说在当时的确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一经问世,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者用犀利的笔触无情地揭露了殖民社会和种族歧视制度下人性扭曲的悲剧,让读者听到了一曲刺耳的西方殖民主义的悲歌。
同时,《野草在歌唱》也是探索女性生存和社会存在的一部优秀小说,白人妇女玛丽最终走向疯癫与崩溃的悲剧人生给我们留下极大的震撼,引起了对其生存状况、生存悲剧深深的思考。玛丽的一直在逃亡、在追寻。她逃亡贫困的童年和冷酷的父母,靠自食其力追求自我,却迫于世俗压力不得不仓促结婚;她逃亡令人绝望的婚姻,希望在社会中立足,却不为男权社会所容,最终无奈回到闭塞潦倒的农场和令人窒息的热铁皮屋。富白人的歧视疏离,丈夫的冷漠隔阂,对土著黑人仇视与恐惧,玛丽生活在的孤寂绝望之中,任凭时光生命的徒然耗逝,直到黑仆摩西的到来。摩西善良体贴,素养有度,玛丽身心倍感温暖,摩西高大健壮,玛丽也无法抗拒本能,开始与摩西发展并保持着一种暧昧关系,显出了活生的气息。然而在当时的非洲殖民社会,这是严重的“道德沦丧”和“伦理越轨”,被其他白人觉察后时立即遭到警告和痛斥,自小就认同殖民和种族观念的玛丽自己也深感负罪,生活在灵与肉的撕裂之中,莫名的恐惧、乱梦萦绕的长夜和无法摆脱的妄念折磨得她近乎疯癫。她最终屈服于自己的种族,冷酷无情地呵斥曾给她许多温暖和慰藉的摩西,之后却感到了更大的绝望和崩溃,而此时,摩西已向她举起了仇恨的钢刀。小说在探索种族和殖民同时,还融入了对阶级、性别等重大主题的思考,深刻揭示出殖民统治下的白人与白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的本质关系,莱辛让女性个体在经受物质匮乏、性别歧视、种族偏见的积压、内心世界在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失衡最后走向疯癫与崩溃,尤其引发了人们对殖民主义背景下女性问题的严肃思考。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结合妇女存在问题来反映殖民、种族、歧视等重大政治主题的小说。
二
五部曲系列小说《暴力的孩子们》历时十七年完成,描述的是一名从南非殖民地走出的白人妇女探索人生、寻求自我的经历。李福祥先生认为“在这部宏著中,政治主题表现得更为集中、鲜明、形象、深刻和成熟。”[1](p43)莱辛把玛莎的人生探索置于严峻的环境中,大胆地让她触及殖民、歧视、战争、核恐怖等,从中透视出一个充满暴力、歧视、恐怖、灾难等等丑恶的时代,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政治内涵。
同时,这五部小说从玛莎少年到成年再到老年,贯穿始终的是玛莎作为女性的觉醒、对婚姻家庭的困惑、对自由的向往,对独立人格的渴望。如果说《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还只是在做生存意义上抗争,那么《暴力的孩子们》中的玛莎却是要决意要逃离“似乎男人按下开关,就指望你为了他们取乐而变成什么别的东西”宠物般的境地,决意在男人统治着的世界里去探索人生、实现自我、确立某种新的女性人格和价值观。[2](p82)《暴力的孩子们》是代表了莱辛在妇女主题方面已经从女性社会生存的探索上升到了社会自我价值实现的探索。小说第一部《玛莎·奎斯特》从玛莎少年写到她第一次结婚,生活在40年代非洲的玛莎为种族、阶级和性别等问题所困扰,积极地投身于左翼政治团体的活动,想寻求一个“没有仇恨和暴力”的“高尚的城市”。在第二部小说《恰当的婚姻》中,玛莎陷入到婚姻、母爱、家庭主妇的圈子中,感到生活像一潭死水,渴望逃离和自由。小说结束时她的婚姻破裂,她又回到了左翼政治团体中间。第三部小说《暴风雨掀起的涟漪》主要描写了玛莎的幻灭感。她所参加的左翼政治团体孤立于黑人之外,在面对非洲的种族、政治、社会问题时逐渐产生了严重分裂,玛莎的再次婚姻也逐渐破裂。在第四部小说《被陆地包围》中,玛莎的婚姻完全破裂,她感到自己像战后罗得西亚的殖民社会一样被“包围”了起来,最后决定去英国实现人生价值。第五部《四门城》描写了五六十年代玛莎回到英国后在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她困惑迷乱、几近疯狂。
在这五部小说中,莱辛成功的将妇女主题与政治主题结合起来,真实而深刻地挖掘了各种社会异化力量对于妇女的种种困扰、束缚和扼杀,同时展示了暴力与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表达了鲜明的反暴力、反战争的政治倾向。最后一部小说《四门城》用象征手法预言了人类文明的末日,描绘人在科学物质文明中的异化,真实表现了20世纪西方世界所普遍存在的虚无感和幻灭感,同时深刻揭露核战争的罪恶与恐怖,表达了作家对未来世界的深深的忧虑。
三
《金色笔记》是莱辛的代表作,于1962年面世,小说因其对女性独立意识及困境的率真描写而常被誉为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波伏瓦的《第二性》的姊妹篇。50年代末的伦敦,女作家安娜由于婚姻情感挫伤、政治理想破灭以及对自己写作意图的质疑而焦虑不安,精神接近崩溃。她求助心理医生,但收效甚微。就在她疯狂混乱、写作难以继续时,她家里住进了新房客——来自美国的流亡作家索尔·格林。从相似的经历及相仿的精神状态中,他们彼此看到了分裂自我的投射,在痛苦的磨合中,他们共同经历了从分裂到整合的心理过程,获得了精神再生。
安娜与《暴力的孩子们》中的玛莎一样,渴望独立人格、渴望自我发展,但莱辛并没有机械地重复,而是用一种更为成熟的女性意识审视了妇女与社会的关系。女主人公安娜热情而敏感,独立而有思想,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妇女处在男权社会中的种种困惑与矛盾冲突,表达了作家对妇女命运的深沉哲学思考。莱辛自己概括说:“有时候.安娜看起来像一个中年玛莎·奎斯特:具有相同的历史,相同的关注和兴趣,都同样因自我分析、因生活在男人世界里的妇女的自由、因渴望献身于某种持久的令人满足的存在理由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烦恼。推测起来,安娜是一个‘自由妇女’的代表。……由于对人类的愿望和动机的高度理智和敏锐,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安娜明白了她究竟该做什么样的人,并以鲜明的自尊去开创她自己的生活”。[3](p49)这是莱辛多年探索后在妇女人生价值发展取向上的一次更成熟的思考,更加深刻和富于启迪性,安娜的女性形象有更鲜明、更饱满的特征,是妇女的自我实现和发展的崎岖道路上的一个新路标。《金色笔记》是莱辛从独特审美视角去拓展妇女主题的一次成功尝试。
然而,《金色笔记》的主题已远远超出了女性意识和妇女解放的范畴,小说通过讲述安娜从心理分裂走向心灵整合的故事,探讨了个人、集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以及个体在分崩离析的社会如何保持精神的健全与人格的完整。《金色笔记》的主体是一部《自由女性》的小说,但穿插其中的是黑、黄、红、蓝四色笔记使全书反复交叉、支离破碎。这种标新立异的结构以及蕴藏其间的颜色象征的妙用,赋予了小说强烈深刻的政治主题内涵。小说结构上的支离破碎象征着安娜人生的支离破碎,而安娜人生的支离破碎正是时代的碎裂所致,用莱辛自己的话说就是:“自从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后,世界就开始四分五裂了。……我感到原子弹在我的体内爆炸了,在我周围人的体内爆炸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碎裂的意思。好像从里面敲击人们的心灵,正在发生着什么可怕的事情”。安娜苦涩的人生探索既平凡又琐碎,却强烈地映射出作家对时代和世界的总看法。安娜的内心世界与心理困扰:对时代的感受、对信仰的幻灭、对文学创作的质疑、对男女关系的困惑、对自由独立的企盼与追求,折射出整个时代的精神和道德气候。在最后一部分“自由女性”之前,四本笔记合而为一成为“金色笔记”,记述了安娜最后从分裂走向整合、实现完整自我的心灵过程,从结构上完美地完成了作家关于“分裂与整合”的创作意图。《金色笔记》以最严谨的形式、最独特的方式描绘了整整一代人的经历,体现了莱辛的世界观和美学观。
四
《最甜的梦》发表于2001年,描写了60年代一个“问题家庭”中的三位女性生活经历。朱莉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她少女时代的幸福安宁一去不复返,家庭残缺不全,爱情也伤痕累累,年老的朱莉亚生活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最后在痛苦的记忆中死去。小说通过朱莉亚的生活从侧面反映了战争的残酷、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对人们心灵产生的持续影响。法兰西丝是一位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女性,更是一位回归传统女性角色、胸怀宽广慈爱的母亲。为了抚养两个缺少父爱的儿子、支撑一个残缺的家,她远离了“红色革命”的热潮和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理想,以极大的坚毅和忍耐,承担起家庭的重任,还像母亲一样宽容慈爱地对待那些无家可归的“问题”青年。法兰西丝的经历折射出的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困惑,体现了莱辛对激进思潮运动的反思和当时西方社会某些现象的讽喻。西尔维亚是莱辛小说中新一代的女性形象。她勤奋刻苦,毅力坚强,立志做一名好医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西尔维亚带着梦想来到非洲,全力投入到帮助贫困人们的工作,最后不幸感染艾滋病,离开了人世。通过西尔维亚的视角和生活经历,莱辛让人们看到了前殖民地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政府腐败无能、人们生活贫困、疾病肆掠蔓延、艾滋病吞噬生命、媒体虚假报道、友善不被理解……
《最甜的梦》用冷静睿智的目光审视了20世纪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表达了作家对战争的谴责和批判,对当代社会的家庭问题、青年问题以及女性问题的关注,对殖民历史的深刻反思、对前殖民地国家现状的忧虑。与前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相比,这部小说有很大的不同。通过法兰西丝这位普通却又不寻常的女性和母亲的宽广无私的爱的描写,我们感受到了莱辛作品中“强烈的乐观主义”,感受到了她对整个世界和年轻人的未来的美好希望和梦想。透过西尔维亚的形象,她的宽广博大的心怀、她对穷苦人们伟大的奉献,我们感受到莱辛作为小说家一贯所坚持的人道主义传统,那种热爱人民、给被压迫者以同情和温暖的博爱的光芒。《最甜的梦》是莱辛重返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妇女政治主题小说。
综上所述,莱辛敏锐地探索了当代政治和妇女这两大社会问题,并使这两类主题在许多作品中紧密结合,交相辉映,表现了卓越的艺术创新力。莱辛是一位坦城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当代政治始终是她关注的重点,她对女性问题的探索常常放在了整个社会大环境中进行宏观而辩证的思考,这使得她的妇女主题有着与众不同的广度与深度;同时,莱辛又是一个敏锐犀利的女性作家,她对现代社会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地思考常因有女性视角的切入和女性体验的糅合而显得别具一格,也正因为如此,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莱辛“书写了史诗般的女性经历”,展现了“一个分裂的文明”。莱辛的创作主题丰富深刻,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和感召力,她的手法不断变化,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实、到锐意革新的现代主义实验、到充满理性忧思的神奇科幻。莱辛“一直在探索、在否定、在超越”,[4](p96)体现了一位真诚的人文主义作家的不懈努力和执著探索以及对人类的永不枯竭的高度责任感。
[1]李福祥.多丽丝·莱辛笔下的政治与妇女主题[J].外国文学评论,1993, (4).
[2]王家湘.多丽丝·莱辛[J].外国文学,1987, (5).
[3]Schlueter.Doris Lessing:The Free Woman’s Commitment[A].In Charles Shapiro(eds.).Contemporary British Novelists[C].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5.
[4]朱振武,张秀丽.多丽丝·莱辛[J].当代外国文学,2008,(2).
I106.4
A
1003-8477(2011)09-0141-03
王群(1972—),女,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诺贝尔文学精神与多丽丝·莱辛的文学创作”(项目编号2009b040);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多丽丝·莱辛小说叙事伦理研究”(2010-2011年度人文社科)。
责任编辑 邓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