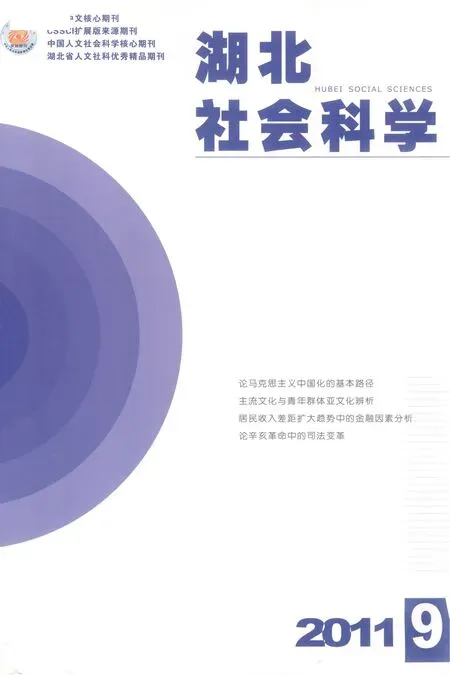徘徊在忙与闲之间
——对威廉·亨利·戴维斯名作《闲暇》一诗的社会学分析
付 静
(武警警种指挥学院 语言教研室,北京 102202)
徘徊在忙与闲之间
——对威廉·亨利·戴维斯名作《闲暇》一诗的社会学分析
付 静
(武警警种指挥学院 语言教研室,北京 102202)
闲暇是休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闲暇的稀缺造成了生活的单调和人生意义的缺失,不利于人的生存发展。对闲暇稀缺的忧虑、对闲暇价值的张扬是戴维斯《闲暇》(Leisure)一诗的主题。时间饥渴症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相信金钱万能的人必然患上时间饥渴症。诗人在该诗中反复吟诵“没有时间”,就是要告诉人们,当时的人已经患上了时间饥渴症,当时的社会已经是病态社会。在当今中国,正确认识“闲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戴维斯;闲暇;价值;稀缺
英国著名诗人威廉·亨利·戴维斯(William Henry Davis)的诗短小精悍,隽永质朴,富于人文关怀,在简洁朴实中包含着深刻哲理。《闲暇》是他著名的诗篇。该诗描写了人们整日忙碌,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停下来关注自然,品味人生,享用自然和生活之美,在对缺失闲暇的忧虑中承载着对自由的向往,对大自然的依恋和对生活的热爱。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闲暇》一诗如何揭示上述主题。
一、对闲暇稀缺的忧虑
N.J.帕里(Parry,N&J)《文化与休闲》一文指出,英语的闲暇(Leisure)一词源于古法语“Leisir”,意指人们摆脱生产劳动后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活动,该法语词汇又出自拉丁语“licere”,意为合法的或被允许的,泛指在劳动之余被获许可的活动。A.J.Weal编著的《休闲与旅游研究方法》一书则认为,休闲一词最早出现于希腊文,希腊语“schole”一词意指闲暇、休息以及教育活动,其反义语“a—schole”一词则指处于劳动或被奴役状况。拥有闲暇之所以是人类的不懈追求,就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劳作时间的减少和闲暇时间的增加都是富裕的标志,生活质量的提高总是伴随着休闲的心情和更大的自由。
对闲暇缺失的忧虑正是戴维斯《闲暇》(Leisure)一诗的主题。该诗由七个诗节组成。在第一节中诗人使用了反问句,对现代人繁忙而单调的生活发出了“这生活算什么”的叹息和疑虑。从第二节到第六节,诗人用他那善于发现美和欣赏美的眼睛,勾画出大自然和生活中一系列美好事物的意象,通过描绘一幕幕人们因忙碌而无法稍作停留享受这些美好事物的情景,表达他对现代人缺乏闲暇的忧虑。
该诗分别用两组意象象征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在讴歌自然之美方面,诗人通过将“sheep”、“cows”、“squirrels”等指称动物的词汇和“stare”、“pass”、“hide”等表达行为的词汇相互搭配,将“daylight”、“stars”、“streams”、“skies”、“night”等代表天空和大地的的词汇和“broad”、“full”、“like”等表达状态的词汇相互搭配,构成“凝视的牛羊”、“草丛中藏食的松鼠”、“明朗的日光”、“盛满星星的溪水”、“夜晚的天空”等各种大小尺度的鲜活意象,将大自然的静态美和动态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讴歌生活之美方面,诗人通过“beauty”、“glance”、“feet”、“mouth”、“eyes”等描写人物形体的词汇和“turn at”、“smile”、“watch”、“dance”、“wait”、“enrich”、“began” 等刻画人物动作的词汇相互搭配,构成“回顾美人的明眸”、“注视她的双脚”、“观赏她曼妙的舞姿”、“等待她的小嘴给眼角漾起的微笑增添妩媚”等意象,展现女人身体之美;将“boughs”、“woods”、“grass”等表现自然景色的词汇和“stand”、“stare”、“see”、“pass”等表达人的动作的词汇相互搭配,描绘人们“伫立在树林下面”、“良久的凝视”、“从树林边走过”等种种行为,勾画出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在诗中,诗人通过赞美大自然、赞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万物息息相通,只要满怀爱心,去倾听去凝视,就会发现其中的美丽、神奇与灵性。热爱自然的人心中充满着好奇与虔诚,这种审美行为是懂得生命真谛的人的必然选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闲暇的稀缺,人们却没有时间或心情去亲近大自然,享受如此美好的事物。在诗中,诗人通过把女人的身体作为审美对象,赞美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赞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诗人把人的身体作为审美对象,是因为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物存在,更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女性的身体从来就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男性视野中的重要审美对象。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苏珊?鲍德所说:身体决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实体,它还包含或体现着文化、知识和社会信息,不同的身体处于不同的位置,表示的是不同的文化符号,作为文化文本而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相关联。[1]社会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当然不局限于女人的身体。不过,连对女人的身体都缺乏欣赏的情趣,却画龙点睛地凸现出现代人缺乏闲暇。
上述两组意象承载着诗人的审美体验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些意象,也是诗人追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理想境界的形象表达。从哲学角度看,人的“体验”不仅包含着他的“原始经历”,还包含着他与生命的内在联系。每一种体验都是在自身生活的延续中产生,并与其自身的生命整体相连。由于体验存在于生命整体中,生命整体也因此存在于体验之中。[2](p153)审美体验是满足人高级需要的活动,通过审美体验,可以增加人的幸福感,拓展人生意义的广度和深度。
拥有闲暇能使人摆脱生活中种种不愉快的羁绊,在放松和沉思中获得自由、宁静与幸福。该诗最突出的语篇特征,是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反复使用动词短语 “No time to…”如“No time to stand”、“No time to see”、“No time to turn at”、“No time to wait”等,以形式整齐匀称、内容联系紧密、声调铿锵有力的排比结构,创造了一种均衡美,表达了强烈的感情。这种反复(Rhetorical repetition)辞格的使用,强调了感受,宣泄了感情,带有强烈的主体性投射色彩。人在因某种感受而叹息时,就会情不自禁地采用反复辞格,所谓“一咏三叹”正是指此。该诗的题目是“闲暇”,诗人反复吟诵的“没有时间”,从反面给人们留下了强烈印象。诗人在诗中强调,如果人们内心“充满了忧虑”,就无暇顾及和体验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也就显得“没有时间”。现实生活中的“忙”与理想状态中的“闲”形成了鲜明对照。上述排比结构所强调的“没有时间”实际上是一种夸张,要突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人缺乏闲暇是由于缺乏休闲心情。本来,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使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然而,现代人却变得更加忙碌了。本来,自由的时间的增多意味着应当放慢生活节奏,使生活变得更加宁静和舒适,可是,对很多人来说,生活节奏的加快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们的神经越蹦越紧,以至于没有时间伫足和凝视,难以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闲暇。在诗歌的最后一节,诗人使用了贬义词“poor”(这里,“poor” 的含义是“deserving or causing pity;unlucky”,即可怜,不幸)来评价充满忧虑、缺乏闲暇的生活,认为这样的生活与人们追求自由、快乐和幸福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没有多大价值。闲暇的稀缺造成了生活的单调和人生意义的缺失,生活的意义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就好船像在没有航标的河流里随波逐流。美国学者杰弗瑞?戈比在《你生命中的休闲》一书中曾指出:正如古雅典哲学家们所注意到的那样,“由时间造成的饥渴会使人的生命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总会有下面的事在等着去做。那种任由事情自然发展的近乎奢侈的闲适心态——相信世界会展现为它应该展现的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幸福问题专家都确信,生活压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最大杀手。”[3](p68)缺乏闲暇的生活必然是不幸的生活。
戴维斯对闲暇稀缺的忧虑也是对当时西方社会状况的忧虑。宗教改革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崇尚休闲转变为推崇工作,于是,从前那种闲适自在的生活方式便让位于勤俭节约和追求发家致富。这种有关个人在世上必须勤奋工作、节俭和讲究效率的价值观,被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称之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也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深入探讨了市场经济如何导致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变化。[4]他在书中所描述的经济制度的转型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也就是戴维斯创作《闲暇》一诗的年代。那时,近代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闲暇时间的增多提供了可能,人们在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开始向往丰富的精神生活。可是,实际情况却是,竞争的压力和发财致富的愿望,使几乎所有人都失去了闲暇时间和心情。生存的压力与闲暇的稀缺使人性和人的发展遭到空前压抑,徘徊在“忙”与“闲”之间成了人们难以摆脱的困境。
戴维斯对闲暇稀缺的忧虑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工作是造就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相反。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人的工作与休闲必须保持平衡。主动在“忙”与“闲”之间寻求一种和谐,创造一种平衡,是现代人必备的素质。
二、对闲暇价值的张扬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悠闲颂》中说,“没有相当大量的闲暇,一个人就和许多最美好的事物绝缘”。[5](p142)杰弗瑞?戈比在《你生命中的休闲》一书中也说:“拥有闲暇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从无休止的劳作中摆脱出来;随心所欲,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于各种社会境遇随遇而安;独立于自然以及他人的束缚;以优雅的姿态,自由自在地存在。西方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3](p1)在一切社会中,闲暇对每一个人的生存发展都极其重要。可以说,它是生活意义的重要载体和生活质量的理想境界。这是因为,无论古往今来,所有人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终极目标来追求的,闲暇意味着不用为生存而奔波劳碌,可以无忧无虑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专心致志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与这一终极目标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对闲暇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不仅认为,在“闲暇”、“好奇心”、“思想自由”这三大“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中,闲暇是首要条件,而且强调“闲暇是一切事物围绕的中心”,“只有拥有闲暇的人才是幸福的”。他的上述观点至今仍在影响着西方学术界。马克思也非常看重闲暇时间及其价值。他在1862年完成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强调:“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的广阔天地,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6](p281)
正确认识“闲暇”对个人和社会都具重要意义。闲暇不仅可以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而且可以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幸福的生活。这需要通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实现。不过,所有人都不应该把幸福托付给遥远的未来,也不应该像基督教徒那样,把幸福托付给彼岸世界。在现实生活中,要获得幸福,促进自己的全面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敢面对生存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的现实,弄清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善于调整心态,正确处理忙闲之道,把忙和闲结合起来,能够在忙中保持一点闲的心情,能够调剂出时间进行“休闲”,欣赏人生路途上的风景,做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要充分认识到,闲暇是人生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闲暇的基本功能,除了便于恢复疲劳,使人们能够精力充沛地再次投入工作中,就是它本身就是幸福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闲暇时间的增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一方面,闲暇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闲暇时间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富裕的真正标志是劳动时间的减少,闲暇时间的增多。另一方面,人们在闲暇时间中得到了休息,发展了个性,会反过来又促进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总之,闲暇作为一种以时间形态存在的人类财富,根本价值就在于它对个人的发展、社会进步具有促进作用。
对现代人来说,假如生活的节奏能减慢下来,假如可以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们将会感到更幸福。现实却是:尽管我们可以证明,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当今劳动时间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可以大大减少,但在我们的意识中,闲暇却变得越来越稀缺,时间的稀缺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无形的杀手,时间饥渴症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被时钟测量的线形时间很快成为奴役人类的新形式。”[7](p151)当今人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如何才能摆脱时间的奴役,使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去过一种宁静的、惬意的美好生活。这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严肃对待生活并希望提高生活质量的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明白,闲暇是人们完全凭个人意愿所度过的时间,它不仅是一个客观的时间概念,也是一个心理概念。在闲暇中,人们更多地依据心理时间(而不是钟表时间)而生活,接受主观意愿引导,自由地支配自己,尽可能地去过一种内容充实又形式多样的生活,这种内在时间感就会使我们不知不觉中忘却钟表时间对我们的束缚。也就是说,医治现代社会的各种顽症,闲暇有特殊的功效用。闲暇可以提供一条返璞归真之路,即返回到人自由向上的天性,返回到拥有从容宁静的心态。这种天性和心态有助于增进人的幸福,促进人的发展。
时间饥渴症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把衡量幸福的标准建立在拥有财富的多少上。相信金钱万能的人必然患上时间饥渴症。诗人在该诗中反复吟诵“没有时间”,就是要告诉人们,当时的人已经患上了时间饥渴症,当时的社会已经是病态社会。要医治这类病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破除金钱万能,张扬闲暇的价值,缓解对金钱的忧思带给人们的心理压力。所以,诗人在该诗的第一节用反问句发出“这生活算什么,如果充满了忧思,我们没有时间伫立和凝视”的叹息后,从第二节到第六节用一系列意象描绘人们因忧思而无法享用大自然和生活中美好事物,烘托缺乏闲暇对人所造成的损害,张扬他对闲暇缺失的忧虑,从反面强调闲暇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诗的最后一节,诗人明确给出答案:缺乏闲暇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是仅仅在活着而不是真正在生活。所以他才说,“这生活真可怜,假如充满忧思,我们没有时间伫立和凝视”。这种自问自答、前后照应的结构,突出了该诗的主题。
戴维斯《闲暇》一诗对休闲的赞美和向往,对当时西方社会缺乏闲暇的深刻反思,曾在美国引起强烈共鸣。美国著名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写道:“大多数人……被人为的生活忧虑和不必要的艰苦劳作所控制,而不能采摘生活中的美果……一天又一天,没有一点闲暇来使得自己真正完善……没有时间使自己变得不只是一架机器。”[8](p5)作为一种警示和启迪,这首诗还被载入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广告词中,用于提醒人们,正确处理忙与闲的关系,保留一份闲暇,去接近自然,体验自然之美,去感悟人生,充分享受生活之美。
[1]Bordo,Susan.Unbearable Weight:Feminism,Western Culture,and the Body[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2]李仲广,卢昌崇.基础休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美]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4][德]齐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5][英]罗素.罗素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美]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8][美]梭罗.瓦尔登湖[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H0
A
1003-8477(2011)09-0134-03
付静(1970—),女,法学博士,武警警种指挥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