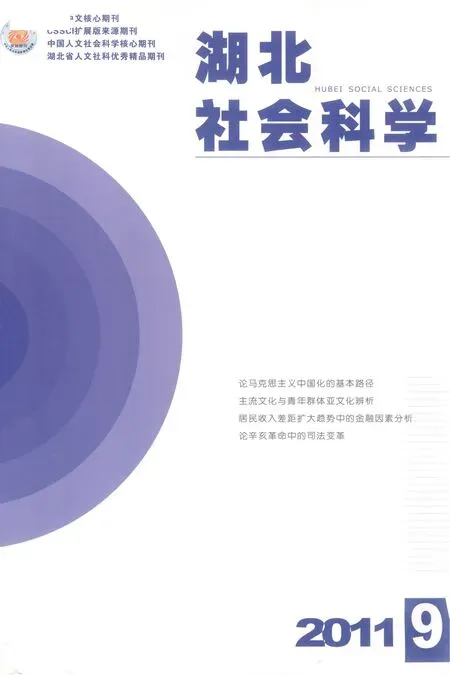非诗意的语言与诗意的语言
——海德格尔晚期语言批判思想再研究
王 俊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非诗意的语言与诗意的语言
——海德格尔晚期语言批判思想再研究
王 俊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思考体现在世界的世界性和历史的历史性中,但在晚期更凸显出其语言思想的批判性。晚期海德格尔通过对非诗意的语言即日常语言、形而上学的语言以及技术语言的批判,努力克服了语言的不纯粹性及工具性的理解,为语言的本性即诗意语言的显现开辟了道路:作为纯粹语言的诗意语言自身言说,其言说的方式是沉默的道说,在沉默的道说中,诗意语言言说并聚集了天地人神四元的世界。
海德格尔;语言;非诗意;诗意
当海德格尔在思索世界的世界性和历史的历史性时,语言的语言性已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明的:“因为关于语言和存在的思索从一开始就规定了我的思想道路,所以,此一讨论尽可能地处于背景之中。”[1](p7)在早期的《存在与时间》里,言谈和闲谈在不同层面显现为语言;在中期的《艺术作品的本源》里,真理是由语言而创立的;然而,直到晚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才真正转向了语言。因此,在世界的世界性和历史的历史性被揭示之后,语言的语言性在此也必须显现出来。由此,海德格尔踏上了一条沉思语言的道路。但此沉思,首先不再是追问,而是对纯粹语言的倾听。而纯粹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诗意语言。[2](p194)但海德格尔对诗意语言的思考,首先是从语言的去蔽开始,即对非诗意的语言的清理。清理就是在开辟一条道路。
一
海德格尔对非诗意的语言的清理是从抛弃关于语言的流俗和形而上学的看法开始的,也是从对技术语言的批判开始的。这体现在对日常语言、形而上学的语言以及技术时代的信息语言的批判。人们通常认为,语言是人的言说,是人交流表达的工具和概念,在技术时代就是信息。这些看法好像是明确的,但对海德格尔而言,却只是明确的迷雾而已,它们都非语言的本然样态。“……因为语言的领域实际上是一个幽暗的王国。这种幽暗不在于没有光明,而在于它的自明,亦即人们用语言谈论一切的时候,无需谈论自身,这使语言的本性一直遮而不露。”[3](p44)因此对海德格尔而言,走上一条语言的道路,首先就是与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作斗争。
首先是对日常语言的批判。人们一般认为,语言是人的某种属性,人拥有语言,就像人拥有某种品格或许多其他东西一样。但拥有语言首先把语言表达为一个东西,不管它是抽象还是具象的。同时拥有也意指此物可有可无,或至少不是本源的。因此在日常语言中,语言就被理解为人的言说。汉字中,“语、言、话、说”四字的意义在《说文解字》中被释为:语……言也……;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话,合会善言也……说,说释也……[4](p51-53)四者均被解释为人的言说或言说方式。在拼音文字如英语中,语言(Language)被定义为:人类需要后天学习的一种通过声音系统和语音符号进行思想、情感、意愿交流的方法。这个定义除了仍然突出人的言说之外,强调了语言作为一种表达、交流、计算的工具和概念语言,但也因此更加成为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对象。日常语言之所以是非诗意的,在于人可能言说真理,也可能不言说真理,尤其是当人把语言作为工具来言说欲望或愚蠢的时候,日常语言往往就变成了沉沦的语言。对于日常语言与诗意语言的关系,海德格尔说:“诗意语言绝不是日常语言的高级形态。毋宁说:日常语言是一种被遗忘、被耗尽的诗歌,由此不再享有任何呼唤。”[2](p208)
其次是对理论语言即形而上学的语言的批判。“为了向语言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明确地告别,海德格尔的语言性经验首先要求这样一种区分:谁在说话?既非神,也非人,而是在诗意意义上的语言在说话。”[3](p181-182)形而上学的本性就是追问存在者的整体,同时追问其存在的根据。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坚守一个原则:即为事物的存在寻找一个最终原则。然而根据、原则总是外在于事物的,而根据的根据、原则的原则离事物的本性越来越远,因此形而上学造成了对事物的遮蔽。在古希腊原初意义上,语言即逻各斯与自然、存在是统一的,此时的逻各斯并非概念。但后来随着逻各斯发展为世界的尺度(古希腊)、上帝的话语(中世纪)和人类的理性(近代),语言在遗弃自身的同时其本性也被遗忘了,语言由存在变成了存在者。尤其在对洪堡特的本体论的语言观的批判中,海德格尔认为,“洪堡特把语言当作在人类主体性中制定出来的世界观的一种方式和形式而带向语言”,[1](p119)从而遮蔽了语言的本性。如上所述,人们通常认为,说是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的活动,是有声的表达和人类心灵运动的传达。这样就必然导致这样的看法,即语言是工具,人说话是在使用这种工具等。实际理论情况正是如此。在形而上学看来,语言总表现为言谈,它是人的器官口舌和声带等的运动,并因此是人的言说,是人心的活动。因此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而思想也总是存在着的人的思想。这样情况就是,存在决定思想,思想又决定语言,人们有什么样的思想就用什么样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语言就成为了工具和概念。这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识和理论思维,因为语言正如符号,表明了存在和真理。但问题是,常识仅仅是常识而已,常识只是表象,它往往是盲目和意见,我们需要的却是洞见。显而易见,语言的理论形态实际上是语言的日常形态的纯粹化,因此它保留了日常语言的核心,即它仍然是人的言说,同时又进一步变为工具和概念,从而由感性上升为知性和理性。同存在、真理本性的被遗忘一起,语言成为了形而上学中逻各斯的语言,即陈述、概念、工具的语言。虽然语言不从属于存在者甚至也不从属于存在,语言只是自身言说,它如其所是并是其所是,但在日常语言中,诗意语言被遗忘了,而在形而上学的语言中,这种遗忘也被遗忘了。因此,对海德格尔而言,深思诗意语言,就要求双重去蔽。
最后是技术语言。“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陈述的最后形态不是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判断,而是理解为技术当代的信息,此信息已不再可能道说那不道说。”[3](p182)形而上学的历史表明为存在遗忘的历史,它的发展经历了本体论(古希腊)—神学(中世纪)—逻辑学(近代)三个形态。形而上学致力于为事情寻找根据,致力于设立。在形而上学的影响下,技术的本性即去蔽被遮蔽了。技术的现当代形态更表现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也就是说它成为了一种极端性的技术构架。在技术构架的时代语言就变成了技术语言或信息语言,同时技术也变成了语言技术或信息技术,即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此时的语言就变成了信息。在这样的时代,语言的技术化如信息语言、技术的语言化如信息技术遮蔽了语言也遮蔽了技术自身。这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遗忘:在古希腊,存在和思想本源的统一表明为自然和逻各斯的统一,此时自然是涌现,逻各斯是聚集。然而,在形而上学本体论—神学—逻辑学的样式中,存在和思想发生了分离和对立,此时自然变成了观念,逻各斯由聚集、言说变成了陈述,真理由作为存在的无蔽的去蔽变成了思想和存在的符合。同样,技术的本性也由去蔽变成了人类学和工具学意义上的目的和工具,而现代技术更发展为挑战和采掘,其本性更极端化为构架,它表明自身为设定、支配和控制。[5](p141-149)“但语言的技术化并不只是产生于技术的发展,而是产生于语言本性之中。因为语言自身沉默,所以它在现代的世界中萎缩为信息。”[5](p151)系统论将语言纳入技术之网,控制论设定了语言的设定地位即工具性,信息论使语言信息化即符号化和形式化了。这样一来,语言的自然性变成了非自然性,从而激动不再;语言的诗意更变成了非诗意,其本性遭到侵犯和遗忘。由此而来,人也不能诗意而只能技术性地居住。
技术语言在当代的极端形态是网络语言。这是海德格尔个人无法体验的,因为它所处的时代技术还没有如此发达;但却是他的语言之思所能经验的,因为海德格尔深思了技术的本性,对技术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网络中,我们当然会有审美的体验。我们可以到“榕树下”文学网站中寻找诗意,到新浪博客或微博中建一个“家园”,甚至可以凭借虚拟手段“看中并爱上”一个“人”。然而这一切却遮蔽了人的本性甚至人本身,它使人遗忘了真实和虚幻的边界。那些看似真的往往是假的,而那假的却往往逼近真实甚至超过真实。因此在网络里人们遗忘了真实的存在,这表现为网络依赖症,这也是人们遗忘了语言的本性的表现。当然,当技术越过它自身的边界时它也预示着一种拯救的可能,比如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也有向诗意语言转化的可能。因此正如海德格尔一样,我们既不是技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技术乐观主义者,我们只是要深思语言的本性。
二
海德格尔是通过对于语言的去蔽即对非诗意的语言的清理而踏上通往诗意语言之途的。但何谓“诗意语言”?这要从语言和诗意两个方面来思考。首先,此语言已区分于日常语言、形而上学的语言以及技术语言,因此语言的本性不是作为人的言谈,也不是形而上学理解的工具、概念或技术时代的信息,这样语言的本性最后只是作为沉默的道说即诗意语言。其次,此诗意区分于日常语言所理解的想象、激情、浪漫等等语义,也区分于古希腊和近代诗意理性——给予尺度意义上的诗意。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听到“诗意”的时候,我们首先和大多所想到的可能是一种感情的表达,如诗情画意的味道与激情、浪漫的情调,如同诗人的诗篇所描写的一样;或者意味着我们居住在一个临近山水的别墅里。但这些都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诗意”。在中国的诗论、文论、画论等里面,诗意是指像诗里所表达的那样能够给人以美感的意境,这也不是海德格尔所讲的诗意。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的理性分为三个方面: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诗意理性。诗意理性是指创造理性,但它被理论理性所规定;中世纪,诗学作为神学的附庸,本身也没有独立的意义;“只是在近代伴随着‘感觉学’亦即美学的建立,诗意的创造才获得了独立的意义。所谓的感觉就是‘我感觉对象’,这里已经构成了我和对象、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关系。至于感觉自身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创造的,也就是德意志唯心主义所说的‘设立’。这种意义的设立不仅规定了近代美学,而且也规定了近代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 (如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6](p12-13)但不管是在古希腊、中世纪,还是近代,西方传统上的诗意作为创造都是给予尺度,亦即人给予世界一个尺度或理性给予存在一个尺度。这种诗意,是一种规定世界的意愿,随之而来就出现了主体主义、主观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人对自然的奴役,人对自然的奴役又扩大为人对人的奴役。思想和现实中的暴力色彩与暴力言行由此产生。
与此相反,在海德格尔这里,诗意作为倾听是接受尺度,亦即思想接受存在所给予的尺度。诗意在根本上是人居住在大地上的方式,是在天地人神的四元中对于尺度的接受。最后从一般的语言意义上来看,诗意作为名词是指诗的意蕴,作为形容词是指蕴含着这种意蕴的。但这里却出现了相互关联的三方:即诗、诗人、诗意,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艺术作品、艺术家和艺术的关系一样,因此诗与诗人互为本源,同时诗意又是诗与诗人的本源。但在词源学上,西语的诗、诗人、诗意均与“制造、制作、创造、创作”即“make”一词相关,也即与尺度相关,只不过在海德格尔这里是由给予尺度变为接受尺度。以诗为例,我们追问:何谓诗?诗并非仅指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是指本性的语言。这样,对海德格尔而言,语言就是诗,是诗意或诗意的,诗、诗意或诗意的就是语言或语言的本性。所以海德格尔的语言就是诗意语言,在“诗意语言”中,准确地讲,诗意是语言的本性,而不仅是语言的规定或限定。
海德格尔思想的道路是“存在”从世界到历史并到语言,他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对语言做出了深入的思考。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说,“……在思想中存在来到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住在语言之家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只要这些看护者通过他们的道说把存在之敞开状态带向语言并且保持在语言中,则他们的看护就是对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完成。”[7](p193)晚期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乃是走向语言之途,“然而,通向语言的道路,并不在语言之外,而是语言自身。”[8](p188)语言自身是自身言说的语言,即纯粹、诗意的语言,对于海德格尔,这指向了“语言的神秘:它唯有与自身言说”。[1](p111)
针对语言本性的遗忘,海德格尔认为:“它们全然忽视了语言的最古老的本性。因此,尽管这些观念是古老的和明确的,但它们却绝不能把我们带向语言本身。”[2](p193)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既非神言,也非圣言和人言,而是语言自身言说。语言乃自身言说,那自身言说的语言是纯粹的,因为其克服了其非纯粹性以及工具性的理解。但正如存在的显现要找到一个特殊的存在者——此在,即通过对此在的存在论状态的分析,存在的意义才得以显现一样,语言言说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人言才能说出,这种特殊的人言便是倾听之后的跟着说,但它仍是语言自身的言说即道说。这里语言与人的关系的启示在于,人要理解自己只是人,而不是主人更不是神或上帝。人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要学会倾听而不是发号施令。“作为能死者的言说,人的言说并非自身固有的。能死者的言说依赖于语言自身的言说。”[2](p208)作为如此,人不仅要学会学习,而且还要学会放弃,唯有真放弃,才能真正成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泰然让之的人。泰然让之作为放弃的样式,不是其他什么,而只是给予。“对万物的泰然让之是完全不同于作为万物的设定和控制的另外一种思想方式。”[5](p172)泰然让之,正如庄子讲的“坐忘”,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唯其如此,才能“同于大道”。一个泰然让之的人,便如庄子所讲的至人、神人与圣人,因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9](p287、14)这样,泰然让之便开启了人的自由境界,也开启了倾听语言的心耳与气耳。但自身言说的诗意语言如何言说?又言说了什么?
三
在沉思语言的本性时,海德格尔用了这样的引导词:“语言的本性:本性的语言。”[1](p94)但当海德格尔如此标示时,他并非在给语言下定义,而只是引导我们经验语言的本性:即语言的本性并不是一个在符号意义上的存在者,并不是存在者意义上的本质,而是存在意义上的发生即语言本性化起来。因此,“在此我们要斗胆一试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并用以下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把语言作为语言带向语言。”[1](p112)那么,何谓“把语言作为语言带向语言”?这里要求对三个“语言”进行解释:第一个“语言”是道说,第二个“语言”是语言的本性,第三个“语言”是人的言说。因此,“把语言作为语言带向语言”根本上是:把语言的本性揭示出来,即让语言自身显现出来。而语言自身乃是纯粹语言,因为它不是其他的什么。纯粹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即诗意语言,而不是非诗意的语言如日常语言、理论语言或技术语言。
“语言之本性现身乃是作为显示的道说。”但是,何谓道说?“道说叫做:指示,显现,让看和让听。”[1](p123、122)语言的本性在于道说,道说乃是让显现和让闪亮意义上的显示。只是在语词的道说中,物才被赋予了存在。格奥尔格诗云:“语词缺失处,将无物存在。”[1](p60)“语词缺失处,将无物存在”实际上道说着:一、从必然性上看,语词存在,物存在。二、从可能性上看,语词允许物存在,语词缺失将不允许物存在。三、从现实性上看,思想遗忘了这一点:即语词让物存在也意味着让物不存在,但这种遗忘在根本上源于语言自身的沉默。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词才让物存在。”[1](p148)由此,道说乃道路,而道路即开辟道路,语词是通向物存在的道路和让物存在的道路。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本性就是自然语言,自然的语言就是道说,即显现。人的身躯和口是大地的涌动和生长,因此语言是大地上开出的花朵。此正如荷尔德林所谓 “词语如花”。[1](p100)但自然语言的道说并不是显现为自然万物,而是通过自然万物显现出来,这正如中国哲学美学中道的显现。但道不仅显现,而且遮蔽,并且首先遮蔽。同样,语言的道说也就是语言的沉默,也即“语言言说为宁静的排钟。”[2](p207)“不同于陈述,道说是语言的本性,此本性理解为宁静的排钟,而且对于语言中的无之无化是本己的。语言以此方式聚集了天地人神,亦即四元。但是陈述却并不认识宁静的排钟,而是遮盖和阻挡了它。”[3](p182)此沉默或宁静却是无声的说,也就是“大音希声”。首先,“大音希声”的“大音”并非无声,相反是普通可闻声音的源泉,但它自身标明为一屏蔽的声音即无声,这是道的遮蔽;其次,“大音无声”虽然不是道本身,但与“大象无形”一样却是道的喻相,是道的显现,只是道不显现为具体的声音或形象,而是显现为“大音”和“大象”。再次,“大音希声”也是“天籁”。“天籁则是无为,虽然它‘吹万不同’,但都是自己发出来的声音,也就是‘自生’、‘自化’。天籁也可能无声,但无声也是道的存在方式,所谓 ‘大音希声’、‘希言自然’。”[10](p77)同样,宁静不是无声或者声音的静止,而是安宁,即使宁静。“如果我们深思的话,作为寂静的寂静化,安宁比一切运动更为丰富,比任何行动更要动感。 ”[2](p206-207)作为如此,“宁静的排钟”既宁静也奏鸣,且宁静即是奏鸣。这样,语言的显现即是语言的遮蔽,语言的沉默即道说。
道说不同于我们日常的言说,而是一种本真的说,是言说的本源。如果言说是陈述,那么它只是道说的衍生样式。“道说和言说不是同一的。一个人可能言说,且无休止地言说,但是一切却没有被道说出。相反,有人沉默,他没有言说,但是在没有言说中道说许多。”[1](p122)如果言说不只是陈述,而首先将言说中尚未言说的带向语言,那么言说也就是道说。语言的道说即语言的沉默,对于思想的事情的规定而言,“语言性的阐明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根本上是语言的声音……它道说,凭借于它的沉默。”[5](p4)沉默道说,凭借于它将那不可道说的带向语言。人只有倾听语言的道说与沉默,人的言说才具有生成性。在海德格尔这里,语言具有早期世界的世界化以及世界的自身拒绝性,具有中期世界的敞开性以及大地的遮蔽性,但语言最终仍表明了存在作为虚无,凭借于其沉默的道说。
语言是自身言说,其言说的方式是沉默的道说,但语言言说了什么?按照海德格尔,语言言说出了天地人神四元的世界。语言言说了世界,也即语言让世界显现出来,诗意语言所言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语言世界。
“那已被命名的万物,因此也是已被呼唤的,聚集于自身亦即于天地人神。此四者是一本源的统一的相互。万物让四元逗留于自身。此聚集让逗留是物的物化。我们称在物之物化和天地人神的逗留的统一的四元为世界。”[2](p199)语言召唤出四元,四元即天地人神。四元的世界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天地人的世界,中国传统的天地人的世界是一个自然与历史的世界,同时,中国传统的世界是现实的生活世界,即在中国的天地人的世界里面,没有神的维度;这个四元也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天地人神的世界,即它不是古希腊的在场者的整体,不是中世纪上帝的创造物,也不是近代作为自然和历史的宇宙。这里四元的世界已经告别了西方形而上学历史所理解的概念,“它所称谓的既非世俗化所设想的自然和历史的宇宙,亦非神学所设想的创造物,亦非自身在场者的整体。”[2](p201)于是,“海德格尔思想中作为四元的世界却不再意味着存在者,也不意味着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存在自身,因此是出于虚无中的虚无化。”[5](p135)因此,天地人神四元是海德格尔独特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海德格尔的四元不仅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世界,同样不同于其早期和中期的世界,即四元区分于“在世存在”中的世界与在“大地和世界”意义上的世界。这在于,虽然从早期到晚期,海德格尔的思想始终没有离开世界,但在思想的不同阶段,却经验了世界的不同维度。早期,世界是此在的世界,“在世存在”的世界在它那方面而言是世界性的,只要它是此在的世界的话。中期“大地和世界”的世界是历史性的,因为它与大地的争端在本性上是存在历史的真理的本源。但是晚期天地人神却是一语言的世界,凭借于它被语言所指引并道说出。
[1]Martin Heidegger.On theWay to Language[M].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s,1982.
[2]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Thought[M].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3]彭富春.哲学与美学问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许慎.说文解字[K].北京:中华书局,1963.
[5]彭富春.无之无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6]彭富春.哲学美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7]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s[M].New York,Harper&Row Publishers,1977.
[8]张贤根.存在·真理·语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9]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0]陈望衡.中国美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B516.54
A
1003-8477(2011)09-0114-04
王俊(1971—),男,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本文为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项目编号:20110330
责任编辑 高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