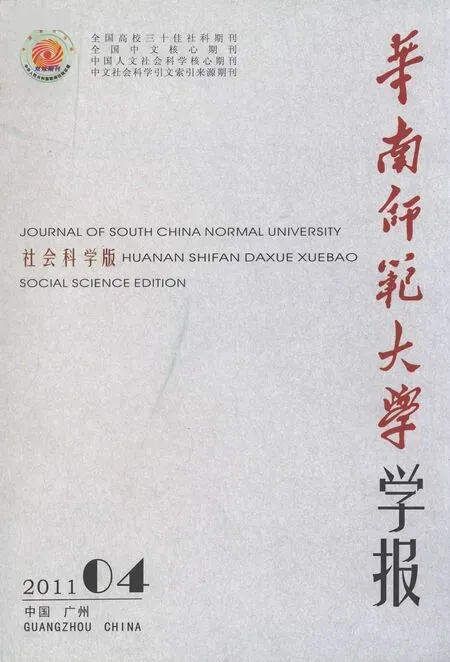1922年湖南省宪法五辨——基于英美宪政经验的解读
王涛
(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1922年湖南省宪法五辨
——基于英美宪政经验的解读
王涛
(华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1922年《湖南省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制定且实施的宪法。根据比较英美宪政提供的例证,与该宪法相关的五个重要问题可以重新定位:军阀政治可以是近代宪政的基础;地方割据对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可以产生推动作因;制宪过程中不应当排除对私利或社会集团利益的考虑;联邦制与单一制不仅都是地方与中央力量平衡的结果,而且都以中央集权为目的;史上不存在无缺陷的宪法。
联省自治 联邦制 宪法 宪政
1922年元旦《湖南省宪法》颁布,湖南人民报之冷淡,以“迎神”、“赛会”、“看会”等作庆祝①宋斐夫:《湖南通史 现代卷》,第7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一年是民国十一年。民元之后,湖南是南北战争中兵家必争之地,身受战火洗劫最为浩大,1918年,属于皖系的张敬尧督湘,“湘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②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一册,第50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1920年7月,湖南省军人和民众驱张,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湖南自治宗旨。赵恒惕接任后,主持湖南省宪法的起草、审查和公民总投票。湘省宪法颁布后,省政府根据该宪法于1922年12月成立。1925年,在吴佩孚武力统一的压力下,《修正湖南省宪法》颁布。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宣布誓师北伐,14日,代理湖南省长唐生智宣布废除湖南省宪法,解散省议会。之后,联省自治主张无人再提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联省自治”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1922年湖南省宪不但是联省自治运动中第一个制定成功而且被实行的省宪,也是我国破天荒的第一部被使用的宪法④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2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它曾被认为是“省治制宪的新纪元”⑤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23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
一、军阀政治可以是近代宪政的基础
上述张敬尧、谭延闿、赵恒惕、吴佩孚、蒋介石、唐生智之流都是军人。他们都与1922年《湖南省宪法》有密切联系。每每谈及此事,必然有人说“军人干政”。引用当时评论者的话,湖南省宪是“军阀烂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是“军阀烂政客争权争利的保障”⑥毛泽东:《省宪经与赵恒惕》,载《向导》1923年第36期。,而联省自治的结果是“使小军阀各占一省,自谋利益,以与中央政府之大军阀相安无事而已”⑦广宇:《东方巨人孙中山》,下卷,第195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现代学者也认为中国省宪运动的兴起,是军阀、政客为各自目的相互呼应的结果⑧李秀清:《近代中国联邦制的理论和实践》,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冬季号。,“徒以供军阀之利用。”⑨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15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宪法从策划到提倡、制定、实施、废止,无一不与军阀有关。因此,评价这部宪法时,由于军阀因素的强烈特征,它在史家心中的形象大为贬损,论者一般认为军阀与近代宪政无缘。
军阀的军队与拥护宪政状态的军队有本质区别,史学家蒋廷黻如是界定军阀:军阀的军队是私人的,军人“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①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86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王尔敏在《淮军志》中对军阀特征作出如下概括:“一、对于中央政府有极大的离心力;二、据地自雄;三、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而非中央利益。”②王尔敏:《淮军志》,第377-378页,中华书局1987版。
在世界宪政史上,军阀在很多场合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英国为例,按以上标准衡量,与英国国王中央集团相对抗的近代英国贵族大多都是军阀,他们对国王的政治斗争与军事征讨是英国近代宪政事业的重要内容。将1215年《大宪章》的形成过程与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宪政相比较,在军阀的问题上可归纳出如下三点共同点。
第一,作为近代宪政基础的私人武装制度的存在。近代英国宪政形成的过程中,如果贵族的私人武装(或其联合)不能与国王的军队抗衡,就不可能有地方分权制度的实现。私人武装制度在英国历史渊远源长。早在11世纪的“危险年代”里,“国王和贵族一样依靠着一帮士兵巩固自己的家室,士兵通过保护主人以取得自己的报酬,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从事抢劫。这些士兵身披盔甲,跨坐战马,这些是领主为他们提供的装备”③[美]时代-生活图书公司:《骑士时代—中世纪的欧洲》,第52页,侯树栋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这些传统背后隐藏的思想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罗马人就是古代民族的榜样④[美]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第172页,傅景川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私人武装对私人的效忠。狭义的贵族-骑士制度专指作为领受土地条件的军役-骑兵兵役制度,这是一种上下级之间的契约关系,其着眼点是对付动乱年代的战争。领主把作为财产的土地分给封臣,封臣就对领主有服从、效忠和尊重的义务,在英国,征服者威廉就在英格兰推行法兰克的骑士占有制,而该类效忠不是对民族国家的效忠,而完全是蒋廷黻上述所论之“小忠”,用欧洲的语言来说,就是“我的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这种契约的关系体现为一种以军事服役为交换条件的土地分封的经济制度,其最外在的表现,则是多层次的等级身份制社会结构。这种社会所包含的契约关系尽管是人格化的和不平等的,却形成后来的《大宪章》、议会政治和习惯法体系的起源基础⑤A.G.Eyre,M.A:An Outline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Longman Group Ltd,1981:23.。
第三,地方割据的存在。英国的地方贵族们拥有可观的私人武装,因此贵族们与国王之间的关系由于力量上的均衡而有条件形成相互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关系,此类关系不见得体现在成文法律中,但在习惯中拥有正义基础,任何一方不履行义务,对方就可以诉诸武力。因此,地方贵族们经常能够从先例里理直气壮地找到“反叛”中央政府的理论根据,在英国历史上,“地方”贵族以各种方式与“中央”君主抗衡的事例绝非一二,只是1215年贵族反叛因其具有武装反抗的性质,并联合市民阶层促成《大宪章》的形成而具有典型性。这部对英国宪法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最早的宪法性文件⑥由嵘:《外国法制史》,第4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实是一个停战条约,是一个“集封建权利和义务之大全的彻头彻尾的封建文件”⑦钱乘旦等:《英国通史》,第4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贵族们采取为个人目的而非中央利益的军事行动,或据地自雄,连绵不断地向“中央”的国王造反,之后导致一系列的宪法性文件的签定,就是这些事件组成早期的英国宪政史。
二、地方割据对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可以产生推动作用
1922年《湖南省宪法》制定实施前后的所有过程中,“湘人治湘”、“湘人自治”、“湖南自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决之”⑧中共湖南省党史委:《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50-52页,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等口号一直都在坚持,这些主张经过省长赵恒惕在1924年护宪活动时期的表述,直接变成“门罗主义”⑨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七册,第29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现代论者一般认为,这些口号都是借口和招牌,实质都是地方势力割据分治,不受北京政府的管辖,不是联省自治,而是“联督割据”⑩谢俊美:《略论联邦制和联省自治运动》,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赵的门罗主义在当时的目的是为对抗广州政府,对此,广州政府认为其“不过分裂中国”、“何自治之足云”,而“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各省真正自治之实现,必在全国革命胜利之后”⑪广宇:《东方巨人孙中山》,下卷,第1954页。。由于该评价的历史权威性,以省宪法为依托的湖南自治足以定性为地方割据,似不是现代宪政行为。
与东方春秋一统的历史愿望不同,西方宪政学者多数认为强势的大国不利于政治自由。为避免中央集权带来的危害,就或者必须抑制国家规模的扩张,或者必须保持地方拥有足够的实力。托克维尔曾经断言:“小国历来是政治自由的摇篮”,并且“大部分小国有时随着自身强大起来而丢失这种自由”①[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179页,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追溯到西方宪政思想源头的古希腊时我们可以发现希腊人在心理上就有一种把城邦作为国家的最终形式的成见②[英]韦尔斯:《世界史纲》,第288页,吴文藻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希腊公民们认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这很像是处于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地位”③[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25页,盛葵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因此,柏拉图认为一个完善的城邦的公民人数不宜太多。这虽然是一种狭隘的城邦主义,但这种观念一直在欧洲延伸,以至于欧洲自罗马帝国沦亡后就再也没有提供过一个长期统一的大共和国的例子。
近代欧洲的地方割据,就是在中央极权消失、社会出现动荡危机的时候,为一种各地方力量相互保障安全的目的而产生的制度。大大小小的采邑遍布于英国土地上,形成一种松散的社会联合体,其间带有极多的地方性或个人色彩,领主下土地的持有者为封臣,封臣所持有的土地或其他财产称为采邑或称封土,而这正是“封建”制度名词来源。每一个采邑和庄园不仅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单位,还是一个政治、军事社会实体。地方割据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强有力中央政府的目标长期不能实现,贵族政治得以推进,阶级特权得以形成,地方势力拥有当然的正义感,用来限制国王的权力,或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集权。
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利益的做法并不符合宪政史上的正义标准,“地方的郡和百户法院管辖权的逐步丧失终于引起英国贵族们的反抗,他们伙同一群同样感到愤愤不平的官吏迫使约翰王在1215年签署一项文件,”④[美]格伦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第97页,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是《大宪章》。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中论述大宪章和地方权利的直接关系时认为,作为割据势力存在的封臣与领主之间的契约关系,形成从古老的加洛林王朝的教会法令集到作为英国人自由的古典基础的《大宪章》,而这些都是欧洲封建习惯最丰富的渊源之一⑤[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第372页,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在欧洲,地方割据与“封建”这一概念密切联系,而这是地方自治、权力分立等民主、自由观念的社会基础。“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远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漆黑一团的、魔鬼横行的野蛮时代”⑥[意]卢多维科:《中世纪》,第134页,夏方林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世纪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它因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很多变化和创造而著称”⑦[美]时代-生活图书公司:《骑士时代—中世纪的欧洲》,第11页。。在宪政方面,王世杰在《比较宪法》中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代宪法观念萌芽的时代”⑧王世杰等:《比较宪法》,第1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地方割据与地方自治一个是实施宪政之前,一个是实施宪政之后,二者的区别固然明显,然而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倾向上二者却存在着根本逻辑结构一致性,都强调以地方来管理地方,对地方的事务说了算而排斥中央的集权意志,二者与中国传统思想史上自古就占主流的“合”的思想甚为异质,其“分”的思想很难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同。此时湖南制宪以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为社会基础、以西方宪政理念为正义论证来追求舆论上的地方自治,可以说,此时的湖南若无地方割据,根本就无法开辟出此一道路。对此,有外国学者注意到当时中国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些的事实:包括湖南在内的近代中国地方自治运动中,各省的商人、知识分子等力图利用这一运动实现它那政治自由与社会秩序的愿望,通过推动各省起草宪法,恢复地方政府的机能,在缺乏强有力国家政权干预的情况下,不同社会集团从不同侧面发挥各自创造的精神,而“地方精英是这次运动的最先得利者,而其中商人阶级实际上充当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⑨[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241页,张富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史学家蒋廷黻也说:“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作官的机会就愈多⑩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86页。。
三、联邦制与单一制都是以集权为目标的地方与中央力量平衡
史学论者都已经确定,1922年《湖南省宪法》制定和实施是联邦制在中国的实践。由于有的联邦制是只做不说,因此判断一个国家体制是否联邦制的形式标准之一就是检视成员单位是否拥有自己的宪法。《湖南省宪法》在附则中规定:“省法律未公布以前,中华民国现行法律及基于法律之命令与本法不相抵触者,仍得适用于本省。国宪未实施以前,应归于国之事权,得由省议会议决执行之。”“联省自治”之新名称是中国人的创造,据说是章太炎的神来之笔①喻希来:《中国地方自治论》,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湖南自治运动中的一个激进人士在1920年10月10日的文章中写道:“二十二个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毛泽东也曾在一篇名为《反对统一》的文章中说:“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思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②毛泽东:《反对统一》,载《时事新报》(上海),1920年10月10日。将全国分为“二十七个国”,将湖南建设为其中之一的“湖南共和国”,这些话语已经昭示联邦制的政治主张。
我们应当注意在此问题上的双重误读。
第一重误读,当年的湖南制宪者们认为可借联邦制宪法来实现地方自治;第二重误读,史学论者认为湖南省宪的联邦制改革本身是“闹分裂”,与传统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单一制背道而驰。前者是当年的湖南制宪者被联邦制宪法话语的假象迷惑,后者,后代史家以省宪作为政治分裂的象征或标签,则也欠妥帖。
联邦制和单一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发展轨道不是分道扬镳,而是趋同。作为民国宪政设计人的孙中山在谈到联邦制时论述道:“美国当独立之后为什么要联邦呢?是因为那十三邦向来完全分裂,不相统属,所以不能不联合起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③《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3、30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中国则因长期的集权传统而可直接采用单一制结构,“中国原来既是统一的,便不应该把各省再来分开”,“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④《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03、30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通常而言,联邦制的目的不是从统一走向分裂,而是从分散走向联合。在美国,联邦制是为解决各州“不能联合时的不和与敌对”而设计,⑤[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第28页,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凡是要结成联邦的成员国家,它们都必须努力地、想方设法地寻找原先有过的一些共同元素,这些共同元素就形成它们联合的精神纽带,否则就不能形成政治力量的联合。正是因为各州“不仅有大致相同的利益、相同的起源和语言,而且处于相同的文明水平。这便使它们的联合几乎永远成为容易的事情”⑥[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189页。,美国先贤们也才能够成就联邦制的大业。演进到20世纪时,新联邦主义又已经取代联邦主义,根据这种新的处理方法,不存在任何各州专有的可以用来限制联邦采取行动的权力,联邦优先的原则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宪法主题。而且,“这一发展是本世纪权力不断向政治结构中心集中的整个世界趋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⑦[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第187页,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联邦制的历史是国家权力由分散而走向中央与地方分权而达到的平衡历史,现代单一制的历史是国家权力由集权而走向中央与地方分权而达到的平衡历史。平衡是核心,联邦制国家权力分配是地方权力优势前提下地方向中央给予权力的最大化,单一制国家权力分配是中央权力优势前提下中央向地方给予权力的最小化,二者都是中央与地方权力较量的结果,大趋势则都是联合与集权。因此,无论是当年的湖南制宪者还是后代史家,无论是评论1922年湖南制宪事件,还是总结联邦制的历史规律,应当承认,强大的地方势力是造就联邦制的基础,而在地方势力未达到规定性程度时,希冀依靠一部废除单一制而采用联邦制的成文宪法来造就地方自治,多属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未理解联邦制本身的集权实质,也未理解西方联邦制历史事实与中国的迥然相异之处。
四、制宪过程中不应当排除对集团私利的考虑
西方宪政史上从来就不排除私利的正当性。在近代,英国议会和国王的斗争是西方民主与分权的主要象征,私利的争夺却是其中不能否认的决定性动力来源。僧俗贵族们“堂而皇之地成为御前会议、贵族会议以及议会等各种政治会议的当然成员”,议会在获得赋税批准权和立法权之后,又为自己披上“国民代表”和“法治化身”这“两件绚烂的外衣”,“将最龌龊无耻的权力之争遮掩在这两件外衣之下”,而示人以“为民请命”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表象①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第109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9世纪以来英美两党制的运作时时刻刻充满着党派利益之争,而且并不是时时刻刻都遵守宪法的规定②有学者指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1803年)是一个近代宪政国家党派利益之争的典型事件。杰弗逊命令麦迪逊扣留马伯里的委任状的行为纯属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目的无非是一党私利,而马歇尔又完全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违背司法常规作出被称为“伟大的篡权”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党派斗争需要的这一判决,终于成为美国宪政历史的一个里程碑”,“自私的动机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任东来:《美国司法审查权的确立: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见http://www.cc.org.cn/(《世纪中国》)。。20世纪初,把那些与当权者利益不相容的人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的主要手段是对选举权的限制。将他们“过滤出”政治过程的方式很多,英美宪政史上的经典的方式就是“选举权和拥有官职的权利相应地限于拥有财产的人或受过教育的人”③[美]贾恩弗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第120页,沈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论者在研究1922年《湖南省宪法》时比较容易地将注意力集中到其中一些涉及集团私利的条款以及与之相关的勾心斗角的系列事件,因此大多持负面评价,认为该宪法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是似民意而非民意的特殊势力侵入制宪机关的结果,是“中了政客的毒”。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省议员名额分配条款。《湖南省宪法》草案原文纯采人口比例代表主义,将地方代表主义作暂行的办法,而修正案则采人口比例代表主义,又不抛弃地方主义,又以金钱代表主义为暂行办法,时人叹息道:“前所未闻”④宋斐夫:《湖南通史 现代卷》,第7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其实这只是人类宪政史上集团私利争斗的又一次表现而已,它无非是当时湖南“路界”势力划分的结果。清末湖南开办三路师范学校后,湖南就有所谓中、西、南三路界限的划分,为防止三路界限的冲突,赵恒惕在制宪时就已不得不将“湖南制定省宪法筹备会”分设湘中、湘西、湘南三路,分由原任湘省议会议长彭兆璜、原任国会议员吴景鸿、原任国会议员钟才宏负责⑤张朋圆:《湖南省宪之制定与运作》,《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二集,第529页,台湾正中书局1982年版。。可是在审查会中,部分人基于三路路界的感情,或者是为自己将来的活动打算,一再提出修正案,使得审查意见愈来愈分歧,其中特别是关于省议员的分配问题,使审查会拖延3个月也弄不出个头绪来,会议几乎开不成⑥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第56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路大县多,人口多,西、南两路小县多,人口少,人口比例和地方比例的选择显然给政客当议员的机会带来巨大差别,所以,宪法文本的最后结果“是三路政客的饭碗平均”⑦李秀清:《近代中国联邦制的理论和实践》,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冬季号。。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宪政史不过是步西方宪政史后尘。在西方,从普罗泰哥拉以“人是万物的尺度”来论证利益与政治的关系,到古典自然法学派以自然权利、财产、契约来论证近代宪法的合理性,到边沁的功利主义,到现代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人性中的私利要求都是法律的正义的基础,何以见得,在西方宪政史上可以容忍公民个体利益、军阀利益、党派利益对宪法的决定性影响,以至于正面承认其正当性,而在中国就不可以考虑集团私利的宪政诉求?我们是否要求过于苛刻,抑或存在不应有的偏见?
五、缺陷可以充斥于宪政历史
作为英美宪政思想的重要哲学来源,休谟的怀疑论和经验论特别关注人类理性的局限。没有人是至善的,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的人民所能期待的“只能是一个可以容忍的、有序的、自由的社会”⑧刘军宁:《保守主义》,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这样的社会中,难免会存在着某些罪恶和弊害。以此为思想传统,在宪政上,英美思想家认为宪政制度与人类的其他文明现象一样,并不来源于人的抽象的理性能力,而是自生、自发、演变、成长的产物,缺陷必不可少。
1922年《湖南省宪法》缺陷林林总总。
比如,时论者质问:由谁来培育宪法?湘省宪法操纵于少数特权人士手中,民众并未真正参加,这是它的“先天性的不足”,这已决定省宪内容必然受制于各派利益而不能真正反映民意,所以省宪运动也不可能真正发挥推进中国宪政发展的作用。对此,舆论界大有抨击①胡昭鎔:《湖南革命出版史》,第48-4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又比如,该制宪程序设计是否合理,是否体现民主?这也极不尽人意。省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李剑农在制宪过程中痛感制宪程序的缺陷,早就断言:“湖南的省宪,一定不会好的”。他所批评的特指在制宪过程中,既然相信专家,聘请专家学者们来草拟一个完善而有系统的宪法,就不应再采用一种人数众多的审查会去修改它,特别是在选民知识缺乏宪法知识背景,无法判断宪法良否的情况下②李剑农:《由湖南制宪所得之教训》,载《四川筹备省宪周刊》第二号,转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1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而其矛盾在于,如果赵恒惕省略各县市推选代表对省宪加以审查的手续,则又是一部民国的钦定宪法大纲,所以只好妥协。
这部宪法严重缺乏操作性,以至有人描写说,这部宪法“不切实际”,“非公布之后,束之高阁,以待子孙施行者也”。③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752页,商务印书馆(上海)1935年版。省宪规定“收束军队”,“将军费减至省预算案岁出二分之一”,但当省议会要求政府将军费开支按岁收三分之一编制预算案时,赵恒惕却不仅推脱说“万难实行”,还预征1923年的田赋。对这类事件,评论者多持讽刺态度,说“《湖南省宪法》实际上是一纸空文”,人们获得的“只是医治自己幼稚病的一服清凉剂”④宋斐夫:《湖南通史现代卷》,第74页。,并推论说“只有革命造成宪法,没有宪法造成革命”,等。⑤但是,很少有人看到,“此一结果正是促使湖南省长赵恒惕,日后不得不正视裁军问题的原因”。参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再例如“主义”或信仰缺失问题。由于“主义”或信仰的缺失,培育省宪的湖南军人、政客、知识分子和芸芸众生们在宪政问题上两面派、是非不明、首鼠两端、敌我不分,立场不坚,论者不免咄咄逼问:湖南省依据什么“主义”或信仰来制定宪法?要否坚持、是否坚持、又如何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依靠什么政治口号来维护自己的宪法?广州革命政府是三民主义的,刚成立不久还未建立政府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当时湖南政府是什么主义的?
宪政的缺陷无非分为两部分:尚未意识到的缺陷和已经意识到的缺陷。对于前者,我们应承认“每个时代都有许多随后的时代不仅视为伪误而且视为荒谬的东西”,⑥王涛:《中国近代法律的变迁》,第6页,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英美先进宪政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的缺陷还非常多”。⑦[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10页,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对于后者,我们必须承认,英美宪政史上存在着这样的大量的现实,即人们虽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宪法的众多缺陷,却仍然制定、实施、遵守它们。
在英语国家宪法学者看来,人的理性难免有一些缺陷。由于理性自身的不完善,宪政制度就不可能完善,理想的乌托邦的追求努力总难免失败,近代宪政的进程中有大量的事件需要人们以保守的态度来对待,并且只有正视妥协,将妥协作为一种政治艺术,认真思考政治妥协的方法,让它尽可能地不失原则、有品位,将妥协艺术升华为不可或缺的宪政精髓,才会有伟大的成就。任何宪法的诞生,总不能避免保守与折衷。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结果,宪法外表光鲜艳丽,但政治斗争可能会有种种令人憎恶的现象,英美宪法如此,革命的中国宪法如此⑧孙中山在广州军政府以三民主义为号召社会的主义,自己却既没有具体实施《临时约法》,也没有建立《临时约法》所确定的权力制衡机制,以至于本政府的海军总长、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联名要求改组军政府,废除个人专权制度。参见朱勇:《论民国初期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1922年湖南省宪法由于战争、政治等原因而存在林林总总的缺陷,似也符合历史规律,不足为奇。但如果因为这些缺点而将湖南宪政历史负面标签化、本质化,后人在阅读1922年《湖南省宪法》时,就会被这些“问题”纠缠而占据几乎全部研究精力,这必然导致很多值得研究的湖南近代宪政问题不能出场、不能言说,所谓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对思维方式的压制,因而应当加以消解⑨杜宴林等:《后现代方法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向》,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王涛(1970—),男,湖南长沙人,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1-02-16
K26;D909.92
A
1000-5455(2011)04-0074-06
【责任编辑:王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