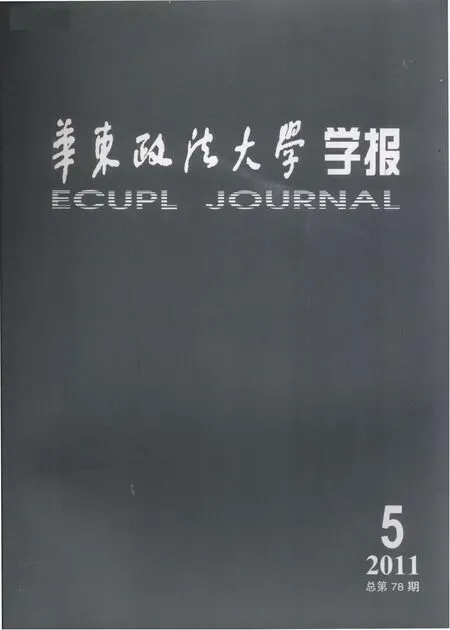英国宪政革命中的辉格党律师
李 栋
英国宪政革命中的辉格党律师
李 栋*
英国宪政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过往法史学界大都将阐释的视角放在政治制度领域,法学界虽然有学者从司法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但这些解释大都将着力点放在了法官,而忽略了普通法律师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1678年至1689年间,以辉格党律师为代表的英国法律职业者在英国宪政革命中运用法律同专制王权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借助一系列事件和案件的处理,推动了英国宪政的进程。
宪政革命 辉格党律师 法律职业者 普通法 专制王权
一、英国宪政革命中被忽略的法律职业者
谈及“英国宪政革命”〔1〕这里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教科书,将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称之为“宪政革命”是因为这场革命的斗争焦点是围绕着国家政治统治权的归属之争展开的。参见程汉大:《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的博弈分析》,载《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成功的原因,就国内研究状况而言,已有成果大多从政治制度史的视角出发,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的作用上,诸如城市与经济的发展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国王与贵族的关系、议会与王权的斗争等。所有这些因素,尤其是议会制度的较早建立,对于英国宪政的积极推进作用,毫无疑问是巨大的。
但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却被国内学者所长期忽视,这就是司法对于英国宪政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近年来已有国内学者从司法的角度研究英国宪政问题,〔2〕如国内学者程汉大、李培锋、李红海、陈绪刚、于明在各自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已经作出了一定的研究,具体参见程汉大、李培锋:《英国司法制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程汉大:《不同寻常的英国司法》,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春季号;李红海:《普通法的历史解读——从梅特兰开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绪刚:《法律职业与法治——以英国为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于明:《法律传统、国家形态与法理学谱系——重读柯克法官与詹姆斯国王的故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2期。但这些研究大都着力于法官与17世纪专制王权的斗争,尤其是科克法官与詹姆斯一世的对抗,鲜有人从英国律师角度论述其与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英国法律职业共同体〔3〕中世纪英国,由于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学者在出身、学识背景、价值观念和职业伦理等许多方面存在很强的同质性与同源性,因而,笔者在本文中将这样一群法律人统称为“英格兰法律职业共同体或普通法法律职业共同体”。参见李栋:《试论中世纪英格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另一支的法律职业者(律师),〔4〕一般而言,在英国普通法中,法律职业者(legal profession)仅指职业律师。所以,本文中的“legal profession”仅指英国职业律师阶层,具体包括早期的法律代理人(attorneys)和法律代诉人(narratores)以及后来的事务律师(solicitor)和出庭律师(barrister)。See Paul Brand,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Legal Profession,Blackwell Publishers,1992.在1678年“排斥危机”后不仅从英国法官手中成功地接过与专制王权斗争的大旗,而且用实际行动直接推动着英国宪政革命的胜利。
二、日渐式微的普通法法官和不断崛起的辉格党律师
1642年以后英国政坛风云变幻,查理一世被处死,君主制和议会上院被废除,一院制的共和国宣告成立。人们原以为专制王权的摧毁,会有利于自由与权利的保障。但事实上,人们发现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都被克伦威尔一人控制,他根本不关心法律,而且总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科克时期所取得一些司法成就被破坏。首席法官罗利及其同僚因受理了一宗涉及税收的案件,被克伦威尔用下流的语言当面痛骂一顿,并因此被解职。律师梅纳德和普林因抗议强行征税,结果前者被关进伦敦塔,后者被处以罚款和监禁。〔5〕程汉大:《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58页。一时间司法仿佛回到了斯图亚特初期,那个被专制王权侵渔的时代。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一个极为朴素而又深刻的宪政原理:国王并不是专制的最终根源,真正可怕的是不受限制的权力。
1660年的“复辟解决”,查理二世(1660-1685年)重登王位,“政府应该由国王、上院和下院组成”的古老政治原则似乎又回来了。然而,复辟初年的和谐局面只是一种虚浮的暂时现象,〔6〕从本质上讲,复辟初年短暂的和谐局面是国王与议会、王权与法律之间的一次政治妥协。然而,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复辟解决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彼此之间的冲突,因为它回避了冲突的根源性问题,即国家主权究竟由谁所有。复辟解决只是片面地吸取了革命年代的教训,将王权和议会重新纳入到“国王在议会中”的传统外壳中,并没有从制度上对二者的权力关系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调整。一旦两个权力主体彼此之间就主权归属问题发生冲突,和谐局面必将破坏。1668年政坛冲突风云再起,特别是在1678年“排斥危机”后,随着两党制(辉格党和托利党)萌芽的产生,政治斗争空前激化。
与先辈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一样,查理二世认识到控制司法是战胜政治反对派,维护王权的重要手段,于是,他开始利用王权干预司法。如查理二世执政后期先后将11名法官免职。1678年,他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强行免去首席法官雷恩斯福德(Rainsford),任命了自己的宠臣斯科罗格斯(Scroggs)。1679年,他又因政治原因将几名法官免职。〔7〕See J.H.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Butterworths & Co.Ltd,1979,p.192.
较之于查理二世,1685年继位的詹姆斯二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短短四年间就将12名拒绝执行其法令的法官免职。伦敦记录法官(recorder of London)豪特因拒绝判处擅自离守的士兵死刑而遭解职。1686年,琼尼斯与男爵蒙泰古、尼维尔因倾向于赦免伊丽莎白吉奥特(Elizabeth Gaunt)和科尼什(Cornish)而被免职。彻斯特首席法官鲍勃·查尔顿(Job Charlton)在调任普通诉讼法院首席法官不久,就收到调回彻斯特的命令,原因是为了给国王宠臣杰弗瑞斯腾位置。法官利文(Levins)也因拒绝按照国王旨意给擅离职守的士兵判刑而遭解职。法官约翰·鲍威尔和理查德·豪洛威也因在“七主教案”中坚持自己的观点被解职。〔8〕See W.S.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l.6,Methuen,1956,p.510.
科克时代法官任职缺乏制度化保障的弊端在此刻充分地暴露出来。普通法法官虽不乏上述与国王权力据理力争者,但许多法官在“丢官罢职”的现实压力下,很难形成合力对抗专制王权。顷刻间,法官的权威、道德水准一落千丈。“他们成为全国民众鄙视的目标”。瑞斯比(Reresby)曾记述:“詹姆斯二世时期天主教徒法官(Roma Catholic judges)阿利伯恩(Allibone)因遭民众鄙视,在一次巡回审中竟没有人愿意向其投诉。”拉特瑞尔(Luttrell)在1686年日记中写道:“由于受到国王赦免权(king’s dispensing power)的影响,往日人们流行的那种对法官的敬畏之情已经荡然无存。”〔9〕W.S.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l.6,Methuen,1956,p.510.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富有正义感的法官开始逐渐离开法院,重回辩护席,聚集在律师界(the Bar)。如“七主教案”中七主教的辩护律师彭姆伯顿(Pemberton)、利文(Levinz)等人都曾经是普通法法院的法官。〔10〕See W.S.Holdsworth,A History of English Law,Vol.6,Methuen,1956,p.511.他们与专制王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他们接过了司法界(the Bench)的大旗,在另外的舞台上推动着英国宪政的进程。
与日渐式微的普通法法官不同的是,英国普通法律师的地位却不断崛起。随着封建制的衰落,16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与之相应,商业发展所引发的利益冲突,使得各种纠纷日益增多,王室法院陷入“诉讼洪流”之中。此外,丰厚的收入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于法律职业。据学者普雷斯特统计,从1610年到1639年四大律师公会共培养了1466名普通法律师。短短三十年间培养的律师总数,与这之前一百年里四大律师公会培养的律师数量大致持平。〔11〕See Wilfrid R.Prest,The Rise of the Barristers:A Societ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ar 1590-1640,Clarendon Press,1986,p.7.由于普通法律师大都出身于拥有土地的上层社会,为了维护切身利益,他们大都关心政治、参与政治,于是,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普通法律师数量的增多以及政治地位的提升使得他们在英国宪政革命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学者麦克·伦敦指出:“17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莫过于宪政革命,许多普通法律师都参加了1603-1689年的政治论战,其中绝大部分的普通法律师都站在反对王权的一边。”〔12〕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p.24-25.他将这些坚持法律至上,坚持议会权利的普通法律师称为辉格党律师(the Whig Lawyers)。
1678年至1681年,辉格党在沙夫茨伯里伯爵领导下控制了议会,并成功阻止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继承王位。辉格党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然而,1682年,由于辉格党骨干分子图谋暗杀国王,许多辉格党领袖因此被判刑或流亡海外。由于1686年至1688年间詹姆斯二世的倒行逆施,破坏了与托利党(Toty)的良好关系。于是,托利党绅士们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转而与蛰伏数年的辉格党一起发动了“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在这段历史中,辉格党的罗伯特·阿特金斯(Robert Atkyns)、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约翰·梅纳德(John Maynard)、亨利·波莱克斯芬(Henry Pollexfen)、乔治·泰比(George Treby)、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Williams)和弗朗西丝·温宁顿(Francis Winnington)等七位普通法律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杰出的辉格党律师也是需要我们铭记的,如亨利·波勒、约翰·萨默尔、理查德·沃勒普以及约翰·豪特等。其中萨默尔不仅写过多本宣传辉格党的小册子,而且在“七主教案”中做过出庭律师、担任过议会的法律顾问。〔13〕这里之所以只强调其中的七位辉格党律师,是因为在学者麦克·伦敦看来:“这七位辉格党律师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See 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p.43-44.
这些辉格党律师大都是律师的后代,都曾在四大律师会馆学习过法律,后不约而同地由律师界转入政界,在议会中从事反对专制王权的斗争。例如,约翰·梅纳德〔14〕约翰·梅纳德(1602-1690年)是德文郡土地拥有者的后代,其父阿莱夏德·梅纳德曾经是一名出庭律师。梅纳德毕业于牛津郡的埃塞特学院,1621年进入中殿律师会馆,1626年11月进入律师界。虽然在1631-1634年间担任过查理一世的总检察长,但1641年以后,他开始同议会反对派一起对抗王权。他曾在领导议会下院弹劾斯垂福德郡伯爵时,表达过法律至上的观点,他说:“叛逆国王的臣民是一种很严重的犯罪,但是最严重的仍是背叛整个国家和法律。……法官本应该以法律为生命,但是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却认为国王的意志是最重要的。”〔15〕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46.
此外,亨利·波莱克斯芬、乔治·泰比、威廉·威廉姆斯和弗朗西丝·温宁顿都曾在议会下院反对过国王。
尽管上述辉格党律师都不同程度地给国王制造过麻烦,但是,从总体看来“这些杰出的律师在1678年以前仍处在中立状态——置身于法院与国家、托利党与辉格党的斗争之外”,〔16〕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61.不仅没有主动地向国王进行挑战,而且也没有通过制度化的法律,限制国王的特权,处于隐而不彰的蛰伏状态。
三、辉格党律师与专制王权的斗争过程及其成果
(一)1678年“天主教徒阴谋事件”中对国王在弹劾案件中行使赦免特权的否定
辉格党律师在政治生活中的中立状态,在1678年被泰特斯·奥茨(Titus Oatea)所引发的“天主教阴谋事件”(Popish Plot)打破。〔17〕1678年4月背叛自己信仰的奥茨,成为新教的一员。他手中掌握了英国天主教徒和耶稣会教徒写给圣奥梅尔和法国其他天主教中心教友的信件。根据这些信件,他指控约克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私人秘书科尔曼(Coleman)阴谋杀害查理二世,招引法国人入侵,企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1678年10月地方法官埃德蒙德·贝里·戈弗雷对科尔曼进行了审讯,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在审理期间戈弗雷法官被谋杀了。这一事实迅速引起了国教徒与清教徒的不满,他们相信这些都是天主教所为,于是国内反天主教情绪被激起。这场真假难辨的“天主教阴谋事件”迅速被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伯爵所利用,他利用托利党领袖丹比(Danby)伯爵曾经支持国王同英国死敌路易十四签订《多佛尔密约》的“把柄”,提出了对国王宠臣丹比伯爵的弹劾。弹劾的理由是丹比在担任国王首席大臣和财政部长期间,违背议会意愿,不仅在政府内大量培植天主教势力,而且坚持亲法外交,伺机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以换取法王路易十四财政津贴的许诺,并最终试图摆脱议会的控制。在这场弹劾案中,辉格党律师发挥了重要作用。
威廉·威廉姆斯和约翰·梅纳德首先将本案注意力从科尔曼的审判转移到对丹比爵士的弹劾中。他在给彻斯特市长威廉·哈维的信中暗示,戈弗雷法官之死是支持天主教的阴谋。梅纳德在议会下院也明确宣布,根据多年的法律经验,奥茨不是一个说谎者。接着,威廉姆斯明确说道:“如果丹比爵士真的同法王路易十四写过这些信件,那么,他就应定叛国罪。因为我们的宗教和财产受到了危险,我们的法律受到了他的蔑视。不管他是否以国王的名义行使此事。”〔18〕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p.69-70.
然而,“查理二世希望暂缓进行这种会把他的大臣置于死地的诉讼程序。这次控告有不公之处,何况丹比是为了博得国王的欢心而采取如今受到控告的那些行动。”〔19〕[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民族史略》(第1卷),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页。于是,威廉姆斯因为弹劾丹比被国王解职了。
幸运的是威廉·琼斯和总检察长温宁顿接过了威廉姆斯斗争的旗帜,继续弹劾丹比。前已述及,国王赦免丹比的理由是,丹比是依据国王的命令行事。针对国王的这种说法,琼斯在理论上反驳道:“国王应仅以他的枢密院提出的建议行事,这样才能使‘深思和谴责’(reflection and censures)仅仅降临至大臣们身上,而王权本身则应保持较高的普遍尊重和热爱。这一点对于国家的稳定性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大臣可以以‘带有国王的命令色彩’的借口去违背法律,因为所有与法律相违背的命令都是无效的。”〔20〕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70.总检察长温宁顿在议会下院为了重新启动对丹比的弹劾,他动情地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应该发表我的观点,否则将没有人能够生存,人们将处处受挫。这是一个破坏议会和王国基本法律的阴谋,议会下院应发挥它固有的司法职能,并宣布这些活动是叛国的。丹比爵士应当受到弹劾。”〔21〕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p.70-71.
在琼斯和温宁顿的努力下,议会下院以179票对116票重新提出了对丹比爵士的弹劾,议会下院指定包括威廉姆斯、温宁顿和梅纳德在内的委员会专门拟定弹劾报告。1678年12月21日议会上院同意了弹劾报告中对丹比伯爵的六项指控。正当丹比将要被投入伦敦塔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查理二世意识到,他丧失了对于议会上院自复辟以来应有的控制,因此,1679年1月24日,他解散了议会,弹劾程序戛然而止。温宁顿等一批在弹劾案中表现积极的辉格党律师也因此被解职。
1679年3月,由于查理二世并没有获得法王路易十四新的补助金,于是不得不重新组织新一届议会。辉格党律师泰比、梅纳德、温宁顿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启动了对丹比的弹劾。处在危机之中的丹比伯爵坚持认为,没有任何普通法、制定法能够阻止国王利用特权赦免被弹劾之人。温宁顿立刻反对道:“国王的特权是有限度的,国王不能赦免叛国罪……因为国王应是臣民的庇护者,而不应是臣民敌人的避难所。”〔22〕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78.另一位辉格党律师亨利·波莱克斯同样坚决反对国王的这种赦免权,他指出:“即使丹比伯爵没有同法王路易十四写过这些信件,丹比请求国王动用赦免权本身,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丹比的罪行。”〔23〕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79.迫于压力,查理二世于1679年3月26日解除了丹比财务大臣的职务。然而,议会并不同意国王的意见,他们坚持认为,丹比应当关入伦敦塔受刑5年。结果,国王屈从了议会的最终意见。
丹比伯爵的受刑说明辉格党律师在议会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通过这一事件,辉格党律师实际上否定了国王在弹劾案件中行使赦免权的特权,并且在理论上否定了被弹劾人惯用的辩护理由,即他们的政治活动和行为,都是依照国王命令行事,不能认为是有罪。从此,议会弹劾权再也不受王权的干涉,两院可以挥洒自如地行使弹劾权。该事件的胜利为日后英国宪政确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该场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国家最高主权属于国王还是议会,政府大臣是依法行政还是唯王命是从等最基本的宪法问题。
(二)《排斥法案》中辉格党律师运用法律同国王进行角力
“天主教阴谋事件”后,辉格党律师不仅控制了议会下院,而且还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国王的枢密院(King’s Council),王权成为他们斗争的下一个目标。
引发双方斗争的“导火索”是王位继承问题。因年近半百的查理二世膝下无子,他准备指定自己的弟弟,天主教徒约克大公为王位继承人。这一举措迅速引起了议会的反对,因为他们不能容忍一名天主教徒作为国家的主人。为了制止国王的行为,沙夫茨伯里伯爵与其他议会辉格党成员于1679年4月提出了旨在取消约克大公继承权的《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l)。由于泰比和威廉姆斯等人的努力,《排斥法案》在议会下院以207票对128票获得通过。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国王此时宣布闭会,《排斥法案》被搁置。
1680年11月3日琼斯重返议会,他与温宁顿联合起来成为《排斥法案》的主要提议者。温宁顿不仅极力反对詹姆斯(约克大公)继承王位,而且明确指出,如果詹姆斯在1680年11月5日后返回英格兰就是严重的叛国行为。同时,琼斯与温宁顿于11月11日共同指出:“高级法(supreme law)应当体现公众的评价标准,《排斥法案》正是符合了这一点,因此,它与‘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原则是一致的。”〔24〕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91.琼斯接着说道:“《排斥法案》并不是只针对约克大公,而是为了每个英格兰民众自身的安危。自然正义和宗教原则的基础就是为了保护王权与王国,并防止对任何个体利益的损害。”〔25〕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91.尽管《排斥法案》11月11日在议会下院第二次获得通过,但是由于国王的反对,它在议会上院以63票对30票未获通过。
1681年1月,没有放弃努力的辉格党律师又一次拿起《排斥法案》反对英国的罗马天主教徒。在琼斯、温宁顿和其他三位辉格党律师起草的文本中,他们主张禁止天主教徒在伦敦周边的活动,并且严禁他们在王国内骑马或手挽着手并排行走。温宁顿还特别指出,应禁止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来到英国。此外,他们还援引了1593年法令,反对那些不信国教的人(Dissenters),以便使《排斥法案》在议会两院获得通过。然而,愤怒的查理二世于1月10日宣布闭会,并于10天后解散了这届议会。
新一届议会在1681年3月的第三个星期在牛津召开。议会重启伊始,琼斯和温宁顿就立即提出,这届议会应将注意力放在上届议会没有完成的事情上,即讨论、通过《排斥法案》。新的法案应一如既往地保护国教徒的利益,驱逐天主教徒。面对议会下院辉格党律师的压力,查理二世接受大臣海利法斯(Halifax)的意见,拟定了旨在与《排斥法案》相妥协的意见:在查理二世有生之年,约克大公不得返回英格兰;如果查理去世,大公的女儿玛丽继承王位,如果玛丽去世且没有继承人,则由大公的另一个女儿安妮继承王位;但是如果大公在有生之年生有一个信奉国教的儿子,当他成年后可以继承王位并优先于玛丽和安妮。然而,法王路易十四的决定改变了查理二世的妥协意见,因为查理得到了法王一笔丰厚的补助金。由于没有财政上的压力,查理二世摆脱了对议会的财政依赖。于是,他于1681年3月28日下令解散了议会,此后4年他也未再召开议会,《排斥法案》也因此遭到再一次的搁置,其通过终成泡影。
虽然《排斥法案》最终未能通过,但是,辉格党律师在议会与王权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用朗顿的话说:“在议会反对派与王权的斗争中,‘辉格党’律师用他们的宪政和法律知识,支持了议会反对派。”〔26〕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99.
(三)1681-1685年政治审判中辉格党律师通过法律限制王权
1701年以前,由于不存在保障法官职位免受王权干扰的制度,从1679年开始,许多普通法法官由于政治原因被解职。查理二世趁机任命了大量亲信,控制了有关政治案件的司法审判。对于国王的这一行径,辉格党律师在1681年至1685年间有关政治案件的审判中反对国王,极力维持国王、议会上院和议会下院三方力量的平衡。
这一时期第一个涉及政治的审判案件是关于爱德华·菲特扎瑞斯(Edward Fitzharris)的。1681年3月25日罗伯特·卡雷顿、乔治·泰比向议会下院举报说,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菲特扎瑞斯在两个星期前提供了有关“天主教阴谋事件”的诸多细节,证实了先前辉格党人的观点,并指证约克大公和丹比伯爵共谋意图杀害查理二世。由于查理二世认为这只是辉格党人的阴谋,并决心将王位传给约克大公,因而,于3月26日命令总检察长索耶控告这个来自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辉格党律师很快就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认为国王的这种做法是违背普通法的。因为从爱德华三世开始,对于普通人的诉讼控告应由大法官提起,国王这样做会使普通民众的自由变得名存实亡。琼斯呼吁议会上院反对国王的这种做法。温宁顿认为,如果没有法定的程序,任何控告都是鲁莽的。在温宁顿的帮助下,菲特扎瑞斯于4月27日得到了人身保护令状依照普通法的程序接受调查。
1682年5月流亡海外的约克大公回到英国。一直反对约克大公继位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因谋害约克大公和国王查理二世的阴谋被暴露,于是逃往海外。许多受到牵连的辉格党人被陆续传唤至法院,接受审判。第一个接受审判的辉格党人是拉塞尔勋爵威廉,审判于1683年7月13日在普通诉讼法院由首席法官派姆伯顿主持。普通法律师罗伯特·阿特金斯担任他的辩护人。事实查明,拉塞尔虽然没有图谋杀害国王,但他参与了政变的策划工作,陪审团一致认定其有罪,法院最终判处其死刑。阿特金斯立刻对判决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此案中陪审团的组成是不合法的。因为该陪审团成员中只有少数自由土地保有人的财产超过了40先令,而根据《戴尔报告》(Dyer’s Reports)中的权威先例,对于重罪的审判,陪审员必须是拥有40先令以上的自由土地保有人或拥有100英镑以上财产的人。
另外,阿特金斯还指出,将拉塞尔定为叛国罪有失公允,因为许多策划或密谋的叛国行为并不都会被定为叛国罪。在阿特金斯的帮助下,“拉塞尔案”得到了重审的机会。在重新开始的审判中,阿特金斯坚持认为,前案中拉塞尔被指控为叛国罪的依据,是爱德华三世时期制定法对于叛国罪的规定,即任何图谋害死国王的行为。但是,查理二世时期的第13号法令修正了它,只有那些废黜国王或发动战争的叛乱行为才应被认为是叛国罪。如果任何没有付诸于实践的图谋和策划行为都被认为是叛国行为,那么查理二世没有必要修改爱德华三世的制定法。因为图谋和策划杀害国王与发动战争,反对国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7〕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p.165-166.况且,事实证明拉塞尔并没有与他人共谋夺取国王的军队,威胁国王的生命。因而,拉塞尔不应当被判处叛国罪。最终,法院接受了阿特金斯的观点。
在此事件中另一接受审判的人是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1683年11月他同样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理由是他不仅参与了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阴谋,而且在著作中为抵制王权的做法进行了辩护。威廉姆斯、波莱克斯芬和其他三位辉格党律师成为他的辩护人。威廉姆斯在庭审过程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国王的特权只是议会中三种权力中的一种,此外还有议会上院和议会下院所享有的权力,国王不能离开后两者在议会中任意行事。”〔28〕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168.此后,威廉姆斯又出现在王座法院陆续为辉格党的约翰·汉普登(John Hampden)、劳伦斯·布雷顿(Lawrence Braddon)和休格·斯派克(Hugh Speke)进行辩护,维护他们的权利。
从上述1681年至1685年辉格党律师在政治审判中的表现,我们发现除威廉姆斯在“西德尼案”中的辩护观点偏向议会外,其他辉格党律师在审判过程中都是以法律和正义作为基本准则,而不是将法律之外的政治观点作为辩护依据。辉格党律师正是在坚持法律的基础上,保卫着整个王国的安全,通过手中的法律限制着任何可能破坏王国安全的因素——哪怕是代表最高特权的王权。对此,学者朗顿总结道:“在1681-1685年里,是‘辉格党’手中的法律而不是议会起到了更为绝对和决定性(absolute and decisive)的作用。”〔29〕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179.
(四)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对国王赦免特权、中止特权的否定
1682年2月6日,查理二世逝世,约克大公继承王位,史称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利用托利党的支持,在5月召开的议会中获得了大量的税款。据统计,此时国王每年的固定岁入达到200万英镑。此外,他还得到法国相当数量的秘密津贴。詹姆斯二世借助雄厚的财政基础,建立起一支3万人的常备军。权力急速膨胀的结果导致议会被关闭,许多先前反对其继位的政府官员被解职,王权再一次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当时欧洲最专制的法王路易十四都以羡慕的口吻说:“没有一个英国君主的权威超过现任国王。”〔30〕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在这样的恶劣政治环境里,辉格党律师仍然坚持着法律的立场,同专制权力进行抗争。
据学者朗顿考证,在詹姆斯二世时期辉格党律师最具宪政意义的两次抗争分别是1686年的“戈登诉黑尔斯案”(Godden v.Hales)和1688年的“七主教案”(Seven Bishop)。
黑尔斯是一位天主教徒,1685年11月被詹姆斯二世任命为团长(regiment)。詹姆斯的这一行为违背了1673年的《忠诚宣誓法》(the Test Act),〔31〕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说法,《忠诚宣誓法》是1672年制定的,其内容主要是规定,所有接受民事或军事官职的人以及接受王室信托下的某一地产者,应宣誓效忠和承认王室的最高地位,并签署声明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说(transubstantiation),并按照英格兰国教的惯例接受圣餐。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8页。因为黑尔斯没有按照该法律的要求,宣誓效忠和承认王室的最高地位,并在3个月内签署圣餐变体说。据此,黑尔斯的仆人戈登控告黑尔斯违背了《忠诚宣誓法》。1686年3月29日,法院认为黑尔斯的行为违反《忠诚宣誓法》,应罚款500英镑。黑尔斯拒绝交付罚金,并认为是国王赋予他免于宣誓并履行该法案其他条款的特权,因而,不应受到任何处罚。辉格党律师泰比、温宁顿都曾被命令代表黑尔斯出庭辩护,但他们最终都拒绝了该命令。不仅所有的辉格党律师不愿意为黑尔斯辩护,就连一向支持国王的托利党律师也反对为其辩护。托利党律师菲茨甚至宁愿辞去副总检察长一职,也不愿参与该案。最终,菲茨的继任者普维斯(Powis)作为黑尔斯的辩护人代理了此案。
在庭审中,普维斯坚持认为,国王拥有无可置疑的特权,可以做任何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因此国王有权依据臣民的能力任命官职。黑尔斯虽然违背了《忠诚宣誓法》,但是国王的特权使他免受《忠诚宣誓法》所规定的处罚。为此,普维斯还援引1487年“尽管案”(Case of Non Obstante)〔32〕根据《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Non Obstante”译为“尽管”,旧时文件用语,表示预先排除任何同已宣称的目的或意图相反的解释。在英格兰古法中则常见于国王颁布的法令及签发的特许状中,表示准许某人做某事,尽管议会法律有相反规定。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75页。所确定的先例予以证明。最后,法院赞同了普维斯的辩护意见,判决黑尔斯无罪。〔33〕黑尔斯无罪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詹姆斯二世为了保证黑尔斯胜诉,预先更换了6名法官,这使支持黑尔斯的法官占了多数。参见程汉大:《英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首席法官赫伯特(Herbert)同样认为:“国王是英格兰的统治者,英格兰的法律应当是‘国王的法律’(King’s law)。国王不仅在特别的刑事案件中依据‘必要理由’享有对某人赦免的权力,而且国王本身就是决定是否应当使用‘必要理由’的唯一法官,因而国王有权赦免任何人。”〔34〕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204.
尽管辉格党律师没有参加该案的审判,但是,他们对普维斯和赫伯特的观点予以明确的反对。罗伯特·阿特金斯在一本名为《刑法赦免权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ower of Dispensing with Penal Statutes)的小册子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阿特金斯认为,议会所通过的《忠诚宣誓法》为“国王的良好臣民”提供了免除天主教徒危害的保护。如果任何任命违背了这一制定法,那么它就应当被“宣告无效”。在这本小册子中阿特金斯还通过菲尔塔、布拉克顿、福蒂斯丘等中世纪权威法律家的论述证明:“法律并不是由国王单独制定,而是由国王和臣民共同同意和选择产生的。这些法律是他们所有行为的衡量标尺。因此,国王不能声称他就是法律产生的唯一制定者,并依照自己的意志拥有不受限制的赦免权。”〔35〕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p.205-206.阿特金斯的论断在逻辑上指出,由于法律并不是国王依据个人意愿制定的,因而在法理上,国王没有任何权力去赦免任何违背法律的行为。正如科克曾经指出的那样:“那些明显损害臣民财产权和其他权利的案件或关于任命买卖圣职罪者(simony)担任政府官员的案件,国王是不享有赦免权的。”〔36〕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204.针对上述普维斯的辩护词,阿特金斯这样反驳道:“国王的最高统治权虽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里的‘统治权’仅仅意味着国王之上没有其他人,它并不意味着国王的这种权力是绝对的。《忠诚宣誓法》正是为了保护国王的统治权免受来自外国权力——罗马的篡夺。”〔37〕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206.
如果说辉格党律师在“戈登诉黑尔斯案”中将斗争焦点集中在国王的赦免特权上的话,那么,在1688年爆发的“七主教案”中又将矛头指向了国王的另一项特权——中止权。所谓法律中止权是指,国王通过公告、命令的形式暂时停止实施某项法律的权力,它是复辟以后国王特权的一种具体表现,其实质是通过专制权力干预司法。〔38〕据学者朗顿考证:“法律中止权并不来源于任何普通法先例。它与赦免特权一样都来源于中世纪的教会,是教皇所惯用的权力之一。它是通过《至尊法案》(the Act of Supremacy)传到英格兰的。”See 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p.208-209.
查理二世曾于1662年至1663年间和1672年两次颁布《信教自由令》(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39〕查理二世在1672年签发该法令,中止对罗马天主教和不从国教者的刑事惩罚,仅仅对其宗教自由有所限制,如新教牧师必须经过批准,天主教徒不得公开举行崇拜仪式。但议会认为制定法不能被皇家敕令中止,国王不得撤回其敕令。议会遂即通过《忠诚宣誓法》,反而加强了对天主教徒的法律制约。……1689年《权利法案》宣布废除了王室的中止权,并谴责国王的这种特许权。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试图通过法律中止权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但是,由于议会的坚决反对,查理二世只得收回《信教自由令》。
复辟后期,詹姆斯二世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决心利用法律中止权实现其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的计划。他于1687年4月和1688年4月两次颁布《信教自由令》,并要求主教向教徒们公开宣读,这激起了法官、议会、不从国教者和国教教士的普遍反对。就连一向顺从于国王的托利党律师也走向了国王的对立面,与辉格党律师一起走向联合。对于詹姆斯二世的行径,1688年5月18日以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为代表的7名大主教联合请愿,抗议国王如此使用法律中止权,并拒绝宣读《信仰自由令》。詹姆斯二世下令将他们逮捕,交付法庭审判,由此引发“七主教案”。
4名托利党律师索耶、菲茨、弗朗西丝·彭伯姆顿和克里斯威尔·利文,以及3名辉格党律师波莱克斯芬、泰比和约翰·萨默尔作为“七主教”的辩护律师出庭辩护。这一辩护团几乎汇集了这一时期律师界的精英,相比之下代表国王出庭的律师则相形见绌。琼斯甚至嘲讽国王说:“即使陛下您可以更换12名审判案件的法官,但是您却找不出12名与您观点一致的律师。”〔40〕John Maxcy Zane,The Five Ages of the Bench and Bar of England,in Select Essays in Anglo-American Legal History,Vol.1,Little,Brown,and Company,1907,p.708.
这7名律师在庭审中主要围绕着以下两个方面为主教们进行辩护:(1)主教们是否有权向国王请愿;(2)国王是否有权依据《信仰自由令》中止任何反对天主教徒和不信国教者的刑事法律。
索耶认为:“主教们的责任就是反对国王的《信仰自由令》。因为伊丽莎白时期颁布的《礼拜仪式统一法》(Act of Uniformity)的相关条款赋予了主教们上述权利。因此,他们有义务反对国王任何破坏英国国教会的行为。同时,他们也有义务反对国王任何违背王国法律的行为,因为国王在没有得到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中止法律的行为是不合法的。”〔41〕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213.作为例证,索耶接着指出:“首先,在理查二世时期《空缺圣职继任者法》(the Statute of Provisors)中,议会虽然赋予国王中止权,但是这种中止权直到下届议会召开时才能使用;其次,在1663年2月查理二世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我衷心地希望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宽容的权力’;再次,虽然议会上院同意了国王在特定情况下的这种中止权,但是它却在议会下院遭到了坚决的反对;最后,议会下院在1673年2月颁布的声明中明确指出:‘除了议会的法令外,任何人不得中止有关宗教事务的刑事法律。’”〔42〕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213.
辉格党律师波莱克斯芬在庭审过程中饱含深情地指出:“刑事法律是整个王国宗教和政治框架赖以正常运行的基础。詹姆斯的《信仰自由令》不符合王国法律的规定;并且……基于这个原因,它在英格兰一经公布就被宣告无效。”〔43〕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213.
最后一个作出辩护意见的辉格党律师萨默尔也通过辩护表达了自己有关法律与宪政的博学知识。他首先援引了1674年财政法院法官在“托马斯诉肖瑞尔案”(the case of Thomas v.Sorrel)中一致同意的观点,即“除立法权外,任何权力都无权中止议会法案的实施”。接着,萨默尔认为国王的赦免权与中止权是存在不同的。如果说赦免权在英格兰某些特殊案件中还具备一点点合法性基础的话,那么,国王通过《信仰自由令》所声称的中止权则明显不具备任何合法性基础,是非法的。〔44〕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214.因而,国王不能依据《信仰自由令》中止任何反对天主教徒和不信国教者的议会制定法(这里主要指刑事法律)。
在辉格党律师和托利党律师的共同努力下,1688年6月30日七名主教被无罪释放,“当主教们离开法庭时,人们欢声雷动,一生反对主教制度的人随着人群跪下,请求主教予以祝福”。〔45〕[英]温斯顿·丘吉尔:《英语民族史略》(第2卷),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学者朗顿这样评价他们在“七主教案”中所起到的宪政作用:“他们的辩护确立了议会立法权高于国王特权的地位;他们的辩护使议会立法权战胜了国王赦免权与中止权的随意运用。”〔46〕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249.
四、辉格党律师是英国“宪政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
辉格党律师在1678年至1681年通过他们在议会中的声音和1681年至1688年在政治案件审判中与日趋专制的王权进行的斗争,成功地推动了英国宪政的生成。对此,英国学者普雷斯特总结道:他们的斗争行为在以下三个方面不仅成功地推动了英格兰宪政的生成,而且影响了西方政治的发展。首先,他们不经意的行为为英格兰政治中“忠诚的反对者”(loyal opposition)这一原则作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们在反对国王与大臣时不是求助于那些非法的手段,而是在国家宪政和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抗争。其次,他们通过议会中的演讲、法庭中的辩护,坚定地反对了绝对主义原则,避免了英国走向类似于法国路易十四那样专制独裁的道路。最后,他们高扬的个人自由和限权政府等主张深深影响了1776年美国的建国者,后者在《独立宣言》和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中将其付诸于实践。〔47〕Michael Landon,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Alabama University Press,1970,pp.246-247.
可见,1789年英国宪政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我们熟知的议会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居功至伟的作用外,普通法律师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些法律人用点滴并富有责任感的行为推动着英国宪政史的前进。诚如英国学者普雷斯特所言,专制王权的脑袋虽是议会砍掉的,但是议会所用的斧头却是“普通法锻造的”,就此而言,“17世纪的英国历史是法律职业者创造的”。〔48〕Wilfrid R.Prest,The Rise of the Barristers:A Societ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ar 1590-1640,Clarendon Press,1986,p.1.如果说以科克为代表的英国职业法官在17世纪前半叶推动英国宪政革命前进,那么,以辉格党律师为代表的英国法律职业者则在17世纪后半叶继续着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
*李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国法治道路的国际经验借鉴研究”(项目号10CFX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陈 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