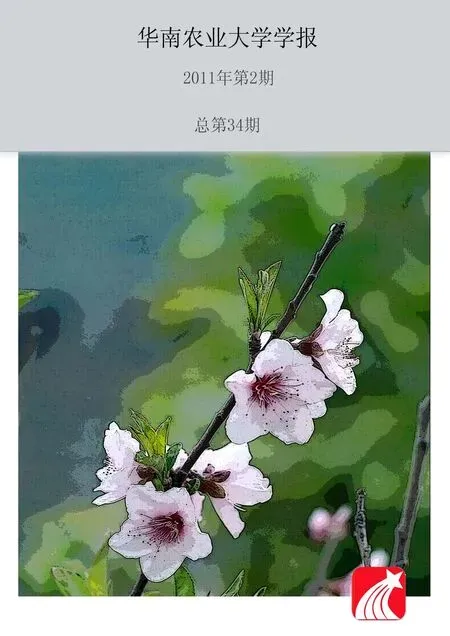从两次法律互动看《中美新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张龙林
(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署《关于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以下简称《中美新约》或新约),这是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美国在华治外法权体系的终结。在以往的研究中,《中美新约》的背景与经过已有较充分的探讨,而关于新约对此后双边关系的影响,则正如哈佛大学历史系柯伟林(W. C. Kirby)教授所总结,是一个应该重视却未得重视的方面,令人遗憾[1]。本文旨以史学界较少注意的两次中美法律互动为中心,具体分析新约对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 海尔密克来教与倪征燠往学
赫德(Robert Hart)曾言,治外法权是近代中外矛盾的核心[2]。《中美新约》则不仅废除“治外法权及其相关权利”,还带动英国、瑞典等13国相率签署类似新约,旧条约体系自此全面崩溃,百年中外关系为之一变。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司法界一面调整涉外法律体制,为切实执行新约未雨绸缪;另一面重拾西法东渐命题,冀望借西法之力振刷本国法治。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步入“蜜月期”的趋势下,这种努力的方向自然而然地投向了美国。
1944年11月24日,美国国务院委派前驻华法院(U.S. District Court in China)法官海尔密克(M. J. Helmick)访华,此为第一次中美法律交流的缘起。由于海氏的历史身份与治外法权有关,加之《中美新约》生效不久,负责接洽的司法行政部(以下简称司政部)部长谢冠生与曾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任职期间熟识海氏的司政部参事倪征燠,误判美方此举意在考察中国法制进展,以确保美国公民在治外法权废除后得到公正法律待遇,两人商定引领海氏参观重庆、成都两地法院。11月27日,海尔密克开始在重庆实验地方法院观察涉外案件受理情况,似乎未暇深入了解[3]66- 69。
事实上海尔密克的主要使命并非法律考察,而是为战后美国在华商业利益的拓展提前进行法律铺垫。《中美新约》签订后,因治外法权废除而担忧未来在华经济地位的美国企业联合组建“中美工商业协进会”(China-America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会员数从最初26家逐渐扩充到400家,成员遍布各行业领域,其主要宗旨是“为两国间的贸易和美国在华投资建立一个健全的法律基础”[4]。为达此目的,该组织一面向急需引进外资以重建经济的国民政府施压,另一面力图通过游说中美政府来改变对华政策的走向。这一利益诉求得到美国国务院的积极响应,并贯彻于同步酝酿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之中。为刺探中国战后重建计划,以便使美方正在设计的商约文本更富针对性,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法律法规施加影响,美国国务院挑选在华司法经验丰富、人脉广泛的海尔密克作为使节,并为其巧妙地披上了法律考察的外衣。
海尔密克主要采用了两个办法:其一,直接劝说国民党高层接受符合美国利益的公司法。在11月30日后的一系列游说中,海氏向蒋介石、宋子文、孙科等传递了美方对未来在华企业法律地位及中国政府管理政策的关注,竭力建议在个人财产、外国公司管理等方面,采纳美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据说这些政要均表欣赏,并已移交立法院以备修订之需[5]1150。其二,诱导国民政府司法界全盘放弃大陆法系而采纳英美法系,间接过渡到修改中国公司法的目标。1945年2月27日海尔密克离华返美,除邀请中方赴美交流外,另对中国法制提出六点建议:(1)明确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司法权限,以防僭越。(2)以民事、刑事案件区分证据法则的适用,保证司法程序之合理科学。(3)中国幅员辽阔,应推行巡回审判制,司法推行宜以法院就当事人之便。(4)废止自诉并赋予检察官监督权,以防恶意泛滥。(5)建立中央指纹机构并设立情报交换系统,使检察机关得享警务机关同样便利。(6)简化民事诉讼程序以减当事人诉累[6]8- 9。
然而上述努力基本以失败告终。海尔密克以法律考察为幌子进行商业游说,这一企图在其来华6天后便被识破[3]70。他希望中国公司法能够参照英美法的设想也未被采纳,直至1946年初,中美围绕企业登记、经商问题的争吵仍持久不息[7],这说明蒋介石等政要“欣赏”不过出于礼貌。至于其六点建议则遭到司政部逐条否定:(1)我国司法权限之设置原为适应我固有之国情,建议尚难遽行。(2)与我国现行民刑诉讼法用意相同。(3)本部已实施巡回审判制且颇著成效。(4)我国此制原系适应社会上制需要,自难废止。(5)本部曾开办指纹训练班,原建议足资参考。(6)我国现行规制即参照各国新法并修正案所订,无不以简化诉讼程序为鹄的。简言之,或不符国情,或已得实施[6]10- 11。
海尔密克访华的唯一成果,是激发了中国司法界赴美往学的努力。司政部副部长夏勤力倡派员考察美国司法实践,以弥补以往仅有书本知识的缺憾,并借机宣扬我国司法以资交流。倪征燠则论证了这一设想的可能性,认为海氏来华虽与法律无关却已有相当成绩,美方应能接受回访要求。1945年春谢冠生指派倪征燠赴美游学。在此后长逾一年的征程中,倪深入了解美国各地司法设施、理论及实践。例如在得克萨斯州观察美、墨人民互控案件的处理办法、法律适用问题,再如对中国了解较少的美国南方人士,专门介绍国人恢复法权的努力及《中美新约》的经过,尤其是中国法制及其与美国之区别,据说“他们都很感兴趣”。1946年1月倪征燠邀请哈佛大学前法学院院长庞德(Roscoe Pound)就任司政部顾问,继而赴欧洲考察,并于同年6月学成归国[3]80- 102。
倪征燠游学西法并无任何实效。据倪氏后来回忆,他曾将考察结果编成书面报告,在1947年11月全国司法行政会议上,散发给各省市高等法院首长审阅,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8]。期间他着重建议仿效美国法院限制检察官权限,如检察官不能与法官并坐,以免给人印象好像前者说了算。据说这段话伤害了多数人感情,时任最高检察长郑烈大声反对,宣称相关工作会因此每况愈下,附和者均表示此举大为不妥。倪氏还就美国司法实况制作报告并改订成册,“但头绪纷繁,不能概括一切。”此后其两年忙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如何将美国法精神融入中国法实际之事,不了了之[3]103- 104。
综上可见,第一次中美法律交流成就甚微。海尔密克来教及倪征燠往学,仅照搬来英美法样本,至于其能否以及怎样在中国落实?这些深层问题均未得到解答。正因为如此,谢冠生全面否定海尔密克建议,检察官们反对倪征燠的结论。第一次中美法律互动没有引起当时国内法律界的积极评价,人们将希望更多寄托在庞德教授法律援华之上。
二、 庞德法律援华与杨兆龙游学美欧
《中美新约》签署后不久,国内司法界获悉年届75岁的庞德教授荣退,一致主张邀其来华指导法制建设[9]308- 309。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集大成者,庞德之所以备受推崇,主要缘于其在近代中美法律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1935年8月与1937年2月,庞德曾以私人身份两次访华,受到中国朝野隆重接待,其具有自由主义、社会福利主义色彩的社会学法学理论,对民国的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产生了不小影响[10]。就像杨兆龙邀请信中所写:“当前司法行政部面临的大事是立法和司法体系的重建和合理化。我们一致认为您最有能力帮助我们完成这件大事。”[11]466- 4681946年6月28日庞德在上海登陆,近代西法东渐的最后一页由此展开。
截至1948年底,庞德在华工作可归为两类,“关于中国法律制度之研究”以及“关于法律实施状况之调查”[6]1。他对中国法律的变革与走向,主要提出了四方面看法:其一,中国应遵循大陆法系而非英美法系[12]461- 483。与海尔密克别有用心的建议相反,庞德从中国法律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出发,认为现代罗马法是具有高度学统的理论体系,易于教授并为其他地区所接受,英美法的适用技术特点及缺陷不宜移植和效仿。其二,建立统一的法律解释和著述。两年内由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扶植民间性质的“中国法学中心”,编纂一套“中国法通典”以为中国法之总纲[6]499- 503。其三,借鉴英美法以增进中国法官的独立性与律师之善用,扭转中国传统对律师的偏见,发挥律师公共职务的效用。其四,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是改良法律教育。通过发扬法学文献与统一的法律教育,培育优良的法官、律师和法学家,对各类具体问题进行专门研究[12]504。
庞德来教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首先,国民政府司法界往学西法的努力再次被促动。1946年11月谢冠生组建中国赴美司法考察团,以杨兆龙为团长与庞德会同开展研究,并接受教育部委托,代为考察欧美各国法律教育及搜集有关宪法实施各项资料[11]494。次年1月代表团抵达美国,以杨兆龙最受各界瞩目,除接受衣阿华、印第安纳等七所大学邀请,演讲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改革等问题外,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对外关系协会等团体也纷纷要求讲述“中美关系之将来”、“中国政治建设及社会之动向”等课题。同年6月,杨兆龙更被国际刑法学会指定为中国分会筹备人和会长。此后在庞德帮助下,杨兆龙遍游英、法、德诸国,考察司法情形[13]。
其次,庞德指出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进步方向。从西法东渐的整个历程来看,庞德的一整套改良方案,与此前来华的外国法律顾问所面临的中国法问题已然不同,带有一定的回顾和阶段总结的性质。自晚清修律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典编纂及相关设施的建设架构均已基本告竣,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于 “法律解释和司法审判活动方面的诸多适用成文法典的技术及与此相关的制度等问题”,庞氏来华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9]323。他对清末以来的法律发展予以总结性评价,同时又根据西方法律发达的经验,从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国法典体系的合理性出发,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建议[12]1。
但正如哈佛大学梅伦教授所评论,在1948年及此后的中国环境下,庞德的解决方案或许唯一可行,然而时局演变清除了其在华工作的所有踪迹[12]210- 211。司政部是庞德法律援华的发起者,其初衷是改良中国法制,但庞德来华以后,最高当局却力图乘机为专制寻找法律论据。1946年8、9月间蒋介石在庐山接见庞德夫妇,指示以优厚待遇续聘庞德,但蒋最终目的却是希望庞德对中国宪法草案进行论证[9]311。为此国民党官方媒体极力渲染,大谈清末以来法律改革之弊端,认为在撤废治外法权的压力下,我国“唯以移植外国法律为能事”,以至于司法建设缺乏创造力和适应性,而“如今不平等条约宣告取消,国家地位独立自主,法律界正应在此千载一时的良机,对此时此地现实生活所实际需要的法律,做独立自主的研求”[14]。这些貌似学术争鸣的意见包裹着现实政治利益,也就意味着庞德的改良方案注定沦为宪政斗争的牺牲品。他所提出的“内阁制不合国情”、“民主不能移植”等观点,尚未在司法层面得到检讨,便被批判为“外毒”[15]。随着1948年底时局重大变动,庞德终止在华活动,尽管此后他与台湾地区持有一定联系,但岛内整体环境并不利于法律改革。
作为庞德学说的忠实拥趸,杨兆龙游学美欧也并未产生多少实际效用。虽然他曾以国民政府检察长身份,在废除特别刑事法庭、释放政治犯等方面有所建树,颇具司法独立的进步趋向,但在中国之命运决战的时代,法制建设的政治空间已被挤压殆尽。庞德来教与杨兆龙往学,因其广泛深远的法律史意义,今日已获得愈来愈多学者认可,却已无法改写当时无果而终的历史事实。
三、 名义平等与实质不平等:《中美新约》的意义及局限
中美双方参与法律互动的不同动机及表现,反映出《中美新约》后两国利益诉求的变化和差异。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次法律互动中表现活跃,第二次则毫无踪迹,这说明它主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角度关注新约所造成的影响,着眼于防止治外法权的废除阻碍战后在华经济地位的实现,法律交流不过是商业游说的手段。而庞德在华活动可视为美国法学界对于新约的积极响应,尽管这不过是其此前对华交流的延续,而且就任司法行政部顾问的主因来自中方,但他积极改造中国法制的整套方案和积极努力,构成第二次法律互动的核心内容,赋予中美法律合作以更多实质性涵义,并在近代中国西法东渐的最后一页留下了相当的理论遗产。作为外交官的海尔密克与作为法学家的庞德,对中国应否采纳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前后居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美国朝野对于在华治外法权终结的不同反应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除此以外,美国其他社会各界对新约持何种看法?做出了怎样回应?有何异同?这些问题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
从中国方面观察,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希望通过两次法律互动实现双重目的:其一,从事若干问题之研究,考察近十年来欧美各国法制之变迁,尤其战后有关法制之重要设施;其二,趁便宣扬我国近年来法制改革之情形,期于可能范围内减少欧美人士,尤其美国人士,对我国之误解[8]15。这与《中美新约》缔结后中国舆论潮流所向颇为一致。无论国共两党或社会各界,均高度评价新约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意义,视之为百年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篇章,恰如时文所赞誉:“这个惊人的新闻,振奋了每个中国人,而狂欢,而舞蹈……这是在我国近代史上,系划时代的举动。现在,我们可以昂首了,可以不必畏缩地阔步了,我们能以一个自主独立的完全主权国家参加到世界舞台上,这多么使我们欢欣啊!”[16]在此基础上,各界不断吁求加强国家建设,尤以司法独立为首要任务,因为“新约虽是中国列于强国之林的始基,但它与一般国际条约并无差异,条约本身并不可靠,最可靠的还是我们自己”[17],而近代以来我国与英美等谈判收回法权之所以屡败,“除国力不足难以有力支援外交外,司法行政颓废不前是主要原因”[18]。正是基于对上述思潮的认同与顺应,国民政府自始至终从中美法律关系角度把握新约造就的历史机遇,先是在第一次法律互动中将海尔密克访华局限在法律层面[3]70,继而侧重与庞德合作及游学欧美。与新约后美国朝野的不同反应有所区别,中国社会各界表现出更为一致的立场,这也表明新约对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远甚于美国。
两次法律互动的发生发展体现了《中美新约》对于双边关系的积极推动作用。从20世纪40年代中外法律关系的基本格局看,新约后的两次法律互动仍属于西法东渐的范畴,外求独立、内求更新的历史使命仍待努力,但其性质和内涵已截然不同。其一,新约后的两次法律互动是近代以来中美之间第一次平等的法律对话。新约铲除了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法理依据,将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法律关系首次置于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双方以理论上对等的国家身份进行法律交往,历史进步色彩显而易见。其二,新约后的两次法律互动表明,治外法权的废除已使西法东渐的主旨发生根本变化。在此之前,中外法律交流的重点是废除治外法权,改良司法建设是手段;在此之后,治外法权宣告终结,提升法制水准上升为中外法律合作的主要目的。根源于此,当时舆论呈现出一种饶有意味的变化:治外法权撤废以前,国人大多避谈司法建设之不足,要求列强正视中国法制进展,并明确制订归还法权的时间表;治外法权终结后,舆论却又纷纷调转矛头,指责国家司法裹足不前,敦促当局有所作为[19]。尽管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未能在新约缔结后立即摆脱弱国心态——担心中国涉外法律事务的处理不慎会招致美方批评,但这种顺应潮流的努力本身值得肯定,它不仅将国家司法建设及时转入正轨,并在当时中美法律合作与交流方面造成了一种良性态势,为改善我国法制创造了外部契机。其三,两次法律互动取得了相当的理论成就,倪征燠、杨兆龙访学欧美以及庞德全盘改造中国法系的构想,对中国法制进步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和积累。
两次法律互动的无果而终,暴露了《中美新约》对于改善双边关系的局限性。从美国政府的立场观察,海尔密克打法律牌、算经济账的策略,不过是近代以来美国对华治外法权政策的翻版:以中国法律落后为借口,以律例西化为标准,以治外法权为保护伞。新约肇造于二战特殊背景之下,是美国政府为鼓励中国抗战而不得已提供的“非援助性质的安慰”[20],结合1946年11月《中美商约》“复活治外法权”[21]的历史事实,美方之所以战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为了确保美国战后在华获得垄断经济地位,必须在赢得战争的同时“重新披上治外法权的斗篷”[22],海尔密克访华的实质就在于此,而这不啻宣告《中美新约》的积极意义已荡然无存。
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看,两次法律互动体现了新约后重建国家、维护主权的积极趋向,但最终既未根本改良司法,也没有扭转美国对华法律偏见。就前者而言,如果说第一次法律交流的失效在于缺乏拿来主义的正确指导,那么第二次法律合作的失败,则应归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政局的复杂纠葛,它再次表明近代中国法制的变革,固然需要借助外力支援,却必须首先取决于内部政治、经济等根本问题的解决。就后者而论,谢冠生曾援引美国官员的评价——中国政府对司法程序改进付出了诸多努力[6]1,似乎相当满意,但这恐怕更多出自客套的敷衍。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司法缺陷的指责几乎充斥于当时的各类涉美案件中,其中尤以1944年“麦克米伦”案为典型。1944年3月7日,美国人麦克米伦(A. M. Macmillan)在重庆撞死一名中国妇女,重庆实验地方初审法院以过失杀人罪,判处麦氏四个月监禁并缓期3年执行,另向死者家属支付一定赔偿金。该判决结果相当轻缓,时任美驻华大使赫尔利(P. J. Hurley)也承认麦氏未受歧视性待遇,但中方司法审判程序却遭到严重质疑:其一,控诉非死者家属提出而由代诉人起诉,且代诉人起诉无证人;其二,麦氏无法自选翻译,中方所供翻译质量太差,以至麦氏不得不以中国话作证;其三,证据不足,法庭无视有利于被告的充分证据,起诉理由美方不能赞同。赫氏还援引此时正在重庆访问的海尔密克的评价——“美国绝不会有任何地方初审法院的律师会起诉如此案件,因为完全缺乏故意疏忽或粗心疏忽的证据,而依照我们的法律,这是支持控告(误杀)杀人罪的必要条件”。此后赫尔利一面鼓噪麦氏上诉,一面诉诸外交向中方施压,并于次年8月末迫使四川高等法院重审并宣布麦氏无罪释放[5]1450- 1451。
最后,两次法律互动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在这段中美关系史上,1943年《中美新约》与1946年《中美商约》是两个标志性事件,前者名义撤废治外法权,后者实际复活治外法权,两次法律互动恰处其间,其兴衰成败折射出中美法律关系平等与实质关系不平等并存的历史事实。应该承认,作为战时外交的一个重要成果,《中美新约》奠定了中美独立、平等的法律地位,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和进步,但它仅仅铲除了治外法权的条约依据,难以根除治外法权的事实和观念,其历史影响诚如时人所批评者,不过是纸上的平等,永久实际的平等仍有待于今后的努力[23]。
参考文献:
[1] 金 岩.对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伟林教授演讲纪要[J].近代史研究,1997,(1).
[2] 汪敬虞.赫德与中西关系[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09.
[3] 倪征燠.淡泊从容赴海牙[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 陶文钊.1946年《中美商约》: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经济因素个案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3,(2).
[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as FRUS) [M], 1945, Vol.7,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6] 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M].南京:司法行政部,1947.
[7] JULIA FUKUDA COSGROVE. United Stat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 1943-1946: From the End of Extraterritoriality to the Sino-American Commercial Treaty of 1946[M], New York﹠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7:149-153.
[8] 谢冠生.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议汇编[G].南京:司法行政部,1948:32-33.
[9] 翟志勇.罗斯科·庞德:法律与社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陆 燕.庞德法学思想在近代中国[M].重庆:重庆大学法学院,2007:3-4.
[11] 薛锦璧.杨兆龙法学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12] 王 健.外国人与中国近代法的变革[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3] 陈夏红.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170-173.
[14] 社论·欢迎庞德教授[N].中央日报,1947-07-13(2).
[15] 社论·辟“不合国情”说[N].大公报,1947-12-23(1).
[16] 刘世海.关于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J].力行,1942,(5).
[17] 刘伟森.祝约箴言[J].满地红,1943,(2).
[18] 魏廷鹤.庆祝平等新约感言[J].太平洋月刊,1943,(1).
[19] 陆季蕃.撤废领事裁判权与改进司法[J].建设研究,1943,(2).
[20]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M].张静尔,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130.
[21] 杨恒源.试析<中美商约>及其历史背景[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
[2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RUS[M], 1946, Vol.10,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al Printing Office, 1972:1320.
[23] 郑咸亨.对新约的认识和努力[J].湘桂月刊(新约专号),19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