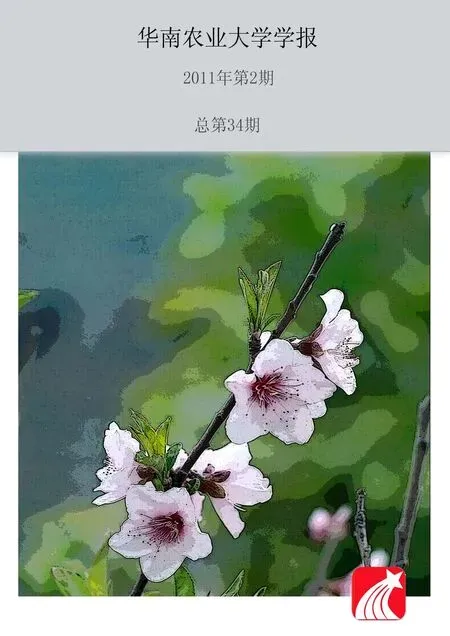语言接触与汉语方言的变化
孟万春
(延安大学 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语言变化的原因历来受到不同语言学派的关注,尽管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方言地理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都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但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充分。从总体上看,促使语言变化的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内部原因主要指语言结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外部原因有很多,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语言接触是促使语言变化的外部原因,而且常常与语言的内部因素共同起作用。既然语言接触是导致语言变化的重要原因,那么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语言接触对语言变化的影响机制问题。具体而言,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对语言的变化起了制约作用?不同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制约力怎样?语言接触究竟是怎样导致语言发生变化的?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才可能揭示语言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变化机制。
语言接触现象十分复杂,语言接触过程中的诸多因素都会对语言的变化产生影响,从而制约着语言变化的方式、程度和方向[1]。概括起来说,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制约或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有两个,即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结构因素。它们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一样,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语言接触的深度,决定了语言转移的方向,语言结构因素决定了语言接触的层次,二者是互为补充,相互不能替代的。
陕西南部地区地处秦巴山区,地形闭塞、地理位置特殊,加上清初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广填陕南”的移民运动,大量的鄂东北、皖西南地区的江南人和广东、福建沿海居民移居于此,与陕南本地的土著居民长期共处二百余年,因此陕南地区的方言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引起了方言学界的广泛兴趣和极大关注,成为方言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在陕南地区,本地土著居民“老民”的方言(“本地话”)与清初移民到此的“新民”方言(“下湖话”)之间相互感染、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为我们研究汉语方言之间的接触、转移和变异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是研究方言接触、方言融合的天然活化石。下文我们将以陕南方言作为语言接触的视点,试着归纳出制约或影响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
一、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混杂程度
在语言接触的方式上,目前各家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因此上划分出来的类型也各不相同。比如有人依据双方是否有群体的直接接触,或者是否通过其他的中介形式,把语言接触的方式划分为“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类;有人根据接触的密切程度,划分为“浅层接触”和“深层接触”两大类型;有人根据接触时间的长短,划分为“长期接触”和“短期接触”两类;有人则根据接触的途径分为“口头接触”和“书面接触”两类,等等[2]。毫无疑问,上述各种接触形式都会对语言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这里主要强调人口接触的密切程度对汉语方言产生的影响。
陕南人口从历史来源上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人口主要是指明代以前就一直生活在陕南的土著居民和明代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运动后安置在陕南的流民,他们的主要来源地是北方地区,如河南、山西、山东、直隶及陕西关中、陕北等地[3]。这些“荆襄流民”的移入方式是长期、渗透式的,因此他们和明代以前的陕南土著居民接触方式是“深层接触”,自愿放弃了自己的母语,改学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语言融合、同化的速度很快,他们就与陕南当地的土著居民合二为一,一起被当作“老民”,即本地人,讲的是陕南本地话。第二层次的人口主要是清代乾隆年间伴随着“湖广填陕南”运动后迁徙到陕南的南方移民,主要来自湖北、安徽、湖南、江西、广东等省,被称作“新民”[4]。这些移民到达陕南后,地理环境较优越的地方已经被“老民”占据,所以只好定居在交通不便的山区。这些“新民”们由于生活在地形闭塞、山高沟深的地方,所以与外界交流比较少,和本地的“老民”混合程度很低,属于“浅层接触”,因而语言就不容易被替换,发生变化。
可见,第二次移民的类型和语言接触的方式与第一次明显不同。第二次移民规模大,移民来源地与分布相对集中,与本地土著居民混杂程度低。并且,“开发式移民性质决定了大批移民填空式占据荒无人烟的山区,避免了移民方言与土著方言过多的接触和融合,使得移民方言特征在山区得以完好保存,从而导致陕南方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5]
二、方言人口的文化水平、职业
人口的多寡以及人口的构成也会影响语言的接触和变化。黄宣范指出语族人口多少、分布情形、都市化程度、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取向等也是影响语言转移或流失的因素[6]。一般来说,都市化程度或教育化程度越高,从事的职业越公众化,语言接触就更容易,越不容易维持自己的语言。原因在于:因为互动越多,越会迁就强势方言,发生语言结构变化的机会就更大。相反,在家务农的农民,由于和外界接触较少,所以发生语言转移的机会就很小,较好地保留了原有语言的特征。
陕南的“老民”讲的是本地话(多属中原官话),“新民”讲的是下湖话(属江淮官话、赣语等)。在陕南各县中,本地话是通行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本地话处于强势地位,是这一带的区域共同语,而下湖话则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利的山区,是弱势方言,属于一群离心型的方言[7]。在很多城镇,下湖人甚至主动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方言,积极向本地话靠拢。即便是母语为下湖话的政府官员在公众场合比如开会、做报告等也喜欢用“撇腔”的本地话而不讲自己的母语下湖话。笔者以为这决不是因为担心听众听不懂下湖话而转换语码,因为面对听众是下湖人也同样如此,所以这可能还有“官场潜规则”在里面。因为政府官员中本地人居多,这就意味着自己的顶头上司和同事多是讲本地话的,为了和自己的领导、同事保持一致性,拉近彼此的距离,增进双方的感情,所以他在公众场合一般不说下湖话而改说不地道的本地话,这样既可以更好地满足交际的需要,也可以融入到另一个语言集团中去,加强了认同感,从而不会由于语言集团的不同而被人排斥在外。相反,农民由于长期在土地上生活,与优势语族的互动不多,和自己交往的人多是本语言集团的内部成员,加以人口比较集中,这些因素都有助于他们方言的维持,不易发生变化,即便是发生语言的变化也主要是表层的。
三、方言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
一般来说,老年人比较保守,对自己的社群语言积极认同,语言忠诚度高,一般都会说自己的母语,所以倾向于维护它。青年一代的语言忠诚度很低,学习或传承祖宗语言的意愿并不强烈。美国社会学家弗格森说:“一些说话者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的同一语言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变体,每种都有其特定的作用。”[8]
在陕南山区,老年人思想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喜欢循规蹈矩,认为丧失母语是忘记了祖宗,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他们的语言不容易发生转移。年青人思想比较开放,对自己的母语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有的甚至认为自己的母语很难听,不如本地话好听,所以一般出外只讲本地话,在家里讲下湖话。可见这是下湖话的社会地位低下导致了该方言的语言转移。笔者在陕南调查方言时,经常遇到有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下湖人当听说要让他们讲自己的母语下湖话时,他们总是委婉拒绝,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的话怪怪的,难听死了,我讲不来!”因此,为了避免受到别人的嘲笑,他们会选择使用本地话和本地人沟通。这样下湖话就退缩到了某个特定的领域,局限使用使得它的活力逐渐衰退,这就间接助长了语言的转移或流失。可见,语言从结构上看是不分优劣的,但是对语言社会地位的评判,并非是由语言内在结构决定,而是取决于外在的社会标准。语言学家所说的社会地位平等的观点是一种语言事实,并非社会现实,人们对不同的语言经常有不同的评价[9]。
在陕南山区,大部分妇女婚后在家做家务、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较少,生活在一个狭小的交际空间里,所以语言相对也比较保守,不容易发生迁移。相反,成年男子的工作多是务农,但是为增加收入,农闲时节外出打工,因此在人际互动方面,男子有比较多的机会与不同的语言集团接触,语言较容易发生转移。
语言影响还和婚姻状况有关,陕南本地的“老民”和“新民”语言接触的广度和深度与双方互婚程度成正比。互婚程度越高,说明双方的关系很密切,语言接触就是深度的,反之就是表层接触。清朝初期“新民”们刚从南方移民到陕南时,受到了本地土著居民的排斥和欺负,为了生存下来并且能够在此地落脚,这些外乡人敢怒而不敢言,只得一味忍让和躲避,尽量不与本地人接触,互婚程度就更低了。这样的话,语言接触就是浅层的了。后来经过近二百余年的长期融合“老民”和“新民”已经逐渐淡化了这种本地人和外乡人的“差别意识”,相互通婚程度高了,语言接触的深度和广度就提高了。
另外,家庭结构也是影响语言维持或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家庭结构对其他语言集团移入的通婚女性,语言的约束力不尽相同。如果女方的语言相对夫家的语言处于弱势地位,那么通婚女性就有可能放弃自己的母语,而以夫家的语言为主要使用语言。相反,如果女方的语言相对男方家的语言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女方就会维护自己的语言,甚至子女的语言也会跟随母亲。据笔者观察:陕西商南县城老民和新民的互婚程度很高,如果夫家是县城本地人,妻子是乡下的下湖人,妻子结婚以后会自觉放弃自己的下湖话,改说夫家的本地话。如果县城本地人的女子嫁给乡下的下湖人,她的语言并不会发生转移,而是仍然保留自己的强势方言本地话。笔者在陕南商洛市商州区阎坪村调查陕南“广东话”(实为客家话,不是粤语)时住在了发音合作人陈世忠老人家里,发现他、他老伴、他儿子都会讲“广东话”,只有他的孙子不会讲,问其故,答曰:“因为他妈妈是本地人,所以他随他妈妈讲了本地话。”
四、方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语言还有社会文化功能,它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情感认同、价值判断、行为倾向等。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人们经常会遇到针对不同的交际对象选用不同语码的问题。这种对语言或方言的选择,其实反映的是人们的语言态度。当语言接触导致语言产生变异形式时,即在语言演变的初始阶段,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可能决定着语言变化的方向[10]。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认同以及相关的心理机制有着密切关系。在多语社会中,语言态度能反映出各个语言以及说话者的地位,同时也能影响多语社群的语言选择。对不同语言的态度反映多语社群,而语言转移通常是由低阶语言转移到高阶语言[11]。
陕南本地的“老民”比“新民”到陕南定居时间早,所以他们一般生活在地理环境较优越的平原、盆地等地势较平坦的地区,“新民”于清初才到达陕南,来的时间较晚,所以只能生活在自然环境较差的山高林密地区,相比之下“老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都比“新民”优越。因此“老民”的方言本地话势力非常强大,是强势方言,而“新民”的方言下湖话则是弱势方言。当然,这里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下湖人的主观语言态度。位于陕南商洛市商州区西面的牧护关镇即是很典型的一例。在这里,会讲下湖话的居民只有中老年人了,青年一代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而改说本地话。这一方面的原因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年轻人不愿意一辈子呆在大山里面,他们来到省城西安(西安的方言和陕南本地话同属中原官话)打工,这时候原有的语言集团就不复存在了,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重新融入到一个新的语言集团,从而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效益,这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母语而改说本地话,避免出现“自己是陕西人,说的却是南方话”的尴尬局面。语言的社会地位反映语言说话者的地位以及该语言对于提升社会地位的效益,尤其说话者的经济地位是决定各语言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12]。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有很多下湖人自己就觉得自己的母语很土,很难听,不能登大雅之堂,因而在公开场合自动放弃讲母语,改说本地话。这显然是由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所决定的效仿强势语言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变化的方向。
语言不只是一种交际工具,它还能体现出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由于我国目前城乡差别很大,人们的普遍心理是“城里人”的社会地位显然要比“乡下人”高。因此,某个人操一口标准的县城话就表明他的身份是“城里人”,会引起乡下人的羡慕和敬意。相反如果他讲的是乡下方言就表明他来自农村,或者至少他的祖辈以前是在乡下生活。这种强烈的“乡下人自卑情结”影响了人们对语言的选择。Fishman认为一般预期从地方口语向标准或优势语言的转移,是从都市、商业或工业化的地区扩展到乡下、农业化或与外界隔绝的地区[13]。
陕南商南县境内方言状况十分复杂,主要有两种方言,县城本地人的方言被称作“奤子话”,乡下下湖人的方言被称作“蛮子话”。县城“奤子话”(属本地话)分布范围很小,仅限于县城周围的几个村,它的周边则零星分布着蛮子话,形成了一种犬牙交错的模式。商南奤子话分布的区域较小,使用人口也很少,但是由于它是商南县城的方言,它的强势地位却很明显,可见人口的多寡并不是决定语言地位的唯一因素。笔者在调查了商南县城多个家庭后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家庭内部,如果父母亲以前都出生在农村,说蛮子话的,后来在县城工作,他们的儿女在家里面讲的是蛮子话,出外一般讲的是奤子话。父母双方有一方来自农村,说蛮子话,另一方讲的是奤子话,他们的子女肯定讲奤子话。近些年来,大量在外地务工的乡下人也开始在县城购买商品房,住到了县城里,摇身一变也成了“城里人”,这些人的孩子一般都主动放弃自己的父辈母语方言,改说成了县城话(奤子话)。很显然正是人们对县城方言的这种钟爱态度,才保证了商南县城的方言,不但没有因为使用人口少而被乡下蛮子话所代替,发生语言转移,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乡下人开始学说奤子话,语言的强势地位正在强化。
语言结构系统内部的变化原因,表面看来似乎跟社会文化因素无关,其实,从更深层上看,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都是有密切联系的。尽管语言变化有其内部结构原因,但真正推动语言变化的是社会文化力量。如果语言使用者缺乏某种使用语言变异现象的机会或者没有使用变异现象的动机,那么语言中的创新无论在语言内部系统方面显得多么自然,也终究难以扩展和传播。总而言之,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语言的发展变化,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文化因素密切相关。社会的交际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语言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影响是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起作用的,它决定着每一语言发展的特殊方向[14]。
参考文献:
[1] 王远新,刘玉屏.论语言接触与语言的变化[M]//薛才德.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35.
[2] 王远新.论我国民族语言的转换及语言变异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1988,(10).
[3] 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73.
[4] 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76.
[5] 郭沈青.陕南客伙话的性质和归属[J].中国语文,2006,(6).
[6] 黄宣范.语言、社会与族群意识──台湾语言社会学研究[M]. 台北:文鹤出版公司,1993:254.
[7] 邢向东.论陕南方言的调查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2008,(2).
[8] 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J].民族语文,2000,(4).
[9] 陈淑娟.桃园大牛栏方言的语音变化与语言转移[M].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4:321.
[10] 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78.
[11] GAL.SUSAN.Language Shift: social Determinant of linguistic change in Bilingual Austria[M].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9:227.
[12] FEIFELL.KARL-EUGEN.Language Attitudes in Taiwan-A soci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in social change[M].Taipei: Crane.1994:58.
[13] FISHMAN.J.A.Language in Sociocultural Change[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77.
[14]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