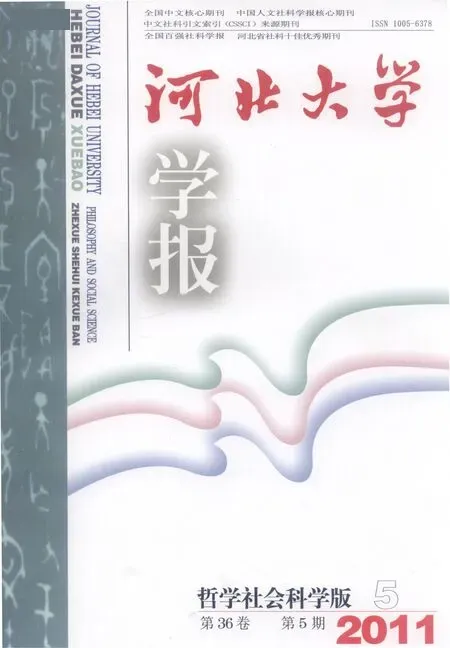“政法”:中国现代法律传统的隐性维度
徐亚文,邓达奇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政法”:中国现代法律传统的隐性维度
徐亚文,邓达奇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政法”是中国现代法律传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法政”到“政法”的语义变迁是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的结果。政法文化的变迁历经了五个阶段。“政法”的现代性、本体论和方法论维度是理解“政法”范畴的三重维度。
政法;传统;维度
一、问题的提出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自由与国家富强,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如何实现传统国家的改造与重塑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新 -旧”“古 -今”“中 -西”“变 -守”成为了近现代中国人现实生活和社会科学中最为凸显的几组关键词。面对如此剧烈的历史变迁,人们该如何观察、适应、改造和发展社会?在政治法律制度方面,从清末变法修律伊始,人们试图在西方和本土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和重构。然而,在研究视域内,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在社会科学界内,人们习惯于把西方的现代与中国的古代相互对立起来,非此即彼。此种思维定势抹杀了一百多年来在中西并存之下的中国问题,实不可取。因此,要走出理论和话语上的二元困境,就必须认真对待中国的现代传统[1]。这番评价针对的虽是整个社会科学,但同样准确揭示了法学领域内的常规分析路径,即在当代的法学论著中,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将古代的法律传统与现代西方的法律制度置于比较的两端。如有学者就将中国古代与现代西方的法制范式形态简化为:“礼治/法治,礼俗/法律,习惯、传统/国家权力,内在/外在,强调克己/主张权利,调解和教化/诉讼和审判,讼师/律师,相对不变/变动很快,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等等”[2],此般概念比对就是上述思考路径的直接体现。然而被人们所忽略的是,如此的二元思考范式没有充分考虑到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的中国域内历史、社会、经济、宗教、传统、文化等因素互相激荡交融的背景下,传统与现代有着复杂多元的联系和奇妙的张力,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与现代西方法律在交融中逐渐形成了一条中间地带即中国的现代法律传统。在过去的一百五十余年中,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也经历了剧烈变动,中国的法律传统已超越了原有的范畴,其脉络渊源纷繁复杂,头绪万千。笔者认为,中国的现代法律传统中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政法”——它是理解中国法律之过去、现状以及前瞻性地把握明天的一把钥匙,它作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始终贯穿于中国的法律理论与实践。从外表上观察,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某些体现于口号中的价值判断与趋向(如主义与问题之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已经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但其内核、运作方式和思维习惯并没有发生质变。这种由过去集成下来的、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的核心范畴为我们发现现实问题表象下的深层动因提供了认识论的工具;理解“政法”,从我们的生存状态来说,为“政法”和“政治的法治化”提供了一种更为深邃的洞察力。研究思考中国近现代百余年来的法律传统中的“政法”之维度对于当代及未来的法制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围绕“政法”概念的变迁,通过法律文本的考察、“话语”的解读,“穿过语言的丛林,抓住历史洪流中变迁的思想”[3],来观照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勾画出政法传统的形成过程。这是一个具有“中国”语境的思想变迁史,同时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命题将帮助我们对未来作更合理的抉择。
二、“政法”含义之解读
(一)“政法”之基本含义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政法”作为名词的含义有三:第一,法制。如,早在汉代,荀悦在《汉纪·惠帝纪》记曰:“其或犯逾之者,则绳之以政法。”管仲提出的“重修法政”亦即健全法制之含义。第二,法规、法度。第三,政治与法律的合称。从字面上看,政法一词为“政治”和“法律”两词合并后的简称。在现实语境中,该词以合成词的形式出现的用法频率比较高,从“政法部门”“政法大学”等常用提法中即是例证。
然而从词义构造而言,“政法”一词又是灵活的,可以看成一个动态比较的过程,体现了政治和法律两者的关系。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认为,从近代中国法制变革来看,中西方法律存在诸多差别,其中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政与法的相互地位,或者说政与法的关系,是政从属于法还是法从属于政。又如,张之洞的《劝学篇》中提到“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4]。在他眼里,西方国家是一个法律齐备、人人皆受法律制约的法治国家;西方之政是立宪之政,分权制衡之政,西方之法是限政之法,依法之政,依法行政,先法后政,法支配政,政从属于法。张氏的看法似乎是对的,但具有表面性。相对而言,中国之政则是集权之政,专政之政,法依政而定,依政而行,法从属于政,服务于政,先政后法,政大于法。
可见,如同一般的法律词源,“政法”并不存在明确可指的“语词对象”。对其单纯的概念定义,无疑等于借助其他抽象概念界定“政法”这一抽象概念,而其他的抽象概念又必然依傍于周而复始的抽象概念的“展览”。所以,对“政法”一词的词义解析过程并非是对一组文字游戏般地拨弄,而是廓清政治与法律的内在逻辑勾连,缕析“政治”与“法律”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的思维脉络。
(二)“法政”到“政法”的语义变迁
从“法”和“政”两词的构词搭配,以及“政法”和“法政”这两词的变化来看,词序上的区别体现了“政”与“法”两者的重要性和宾主关系。自洋务运动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法政”一词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政法”。洋务运动之后,以日本的政治改革为主要的学习对象,清政府派出的留日学生很多都就读法政学科。同时在日本语中,“法政”一词的应用范围与频率要比“政法”一词更为广泛,词义更为丰富。受此影响,国内“法政”一词也较早开始使用,如清末设有直隶法政学堂、京师法政学堂,清政府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高等教育的学制和科目,亦明确了大学堂中设法政科大学。我国历史上受此影响设立的第一间法律专门学校,是1906年9月沈家本等在修订法律馆内设立的法律学堂。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成为法政学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清末的法政学堂成为培训在职和候补官吏的专门学堂,是进入官场的捷径。1910年12月20日,清政府学部为统一办学,特制法政学堂章程。章程规定:“法政学堂以养成专门法政学识、足资应用为宗旨。”1912年设有北京法政大学,1924年设有上海法政大学。当代中国有些大学培养法科类人才的院系称法政系,我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培养法律人才的大学也一直称为法政大学。
“政法”一词的大规模使用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设政务院,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政务院下设35个部门,政治法律委员会就是四个一级委员会中的其中一个,一般简称为“中央政法委员会”,以此与地方的政法委员会区分开来。事实上,中共中央关于“政法”之名的审慎探讨早在1949年初就已开始。北平解放以后,为培养新中国的法律人才,中共中央决定接管朝阳学院以创办一所自己的法科大学。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在考虑用何命新校之名时,有人建议称为“法政学院”,有人认为应该称“政法学院”。董必武赞同华北人民法院审判长、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贾潜提出的“政法大学”的建议,该建议最后报经毛泽东批准通过。1949年8月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题写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校牌[5]。按照梁漱溟在《毛主席对于法律做如是观》中的看法是,“我固早知在毛主席思想体系中,法律只是施政的工具,非其所中,即如清季有法律学堂,民国初年有法政专门学校;毛主席却不沿用‘法政’一词,而必曰‘政法’者,正谓无产阶级专政为主,固非若近世欧美立宪国家,宪法高于一切也”[6]。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施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计划管理制度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统一的管理体制,打碎旧有统治机器,废除六法全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全面领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上至国家领导核心,下至普通群众,对政治和法律关系的认识是明确、固定的:政治处于统帅地位,法律服从政治并服务于政治,法律是实现政治统治的一种方式(这是和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紧密联系的,这个年轻的国家的命运存在着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稳定是当时国家最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和实践指导)。这种理念在中共中央关于政法部门工作的有关文献中有所体现。如“政法部门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7]“我们党从井冈山建立革命政权的时候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法工作。人民政法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济工作、文教工作一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逐步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这就是服从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结合生产劳动、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8]。可见,“政法”一词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逐渐全面代替了“法政”一词,此间的转化体现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三)外来词语对于“政法”的影响
从语源而言,到了近代,为了适应外来文明,汉语的发展也是不断引入和吸收“新词”的过程,诸如“社会主义”“法律”①虽然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曾出现过法律一词,但其并不具备现代法律的意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应来源于日本。刘正琰、高明凯《:汉语外来词词典》中指出“法律”的基本含义有二:(1)社会生活維持 のための支配的 な(特 に国家的)規範、物理的 な強制 が可能。为维持社会生活的具有支配性及物理强制性的(特指国家规定的)规范。(2)国会 の両議院 が可決 して成立 する法 の一形成(通过国会两议院表决成立的法的一种形式)。“政策”等词就是从日文引入的外来词。日本辞书对“政法”一词的解释为:“政治的方法。政道。”[9]这个释义为我们理解“政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按照牟宗三先生的看法,“政道者,简而言之,即是关于政权的道理……吾人论以往之政道,即以开始之德与力及后续之世袭两义为中心而论之”[10]。其认为以“德”(道德教化)和“力”(革命)两种方式来实现和确认政权的统治,这一实现的过程是与治理方法联系在一起的。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深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影响,以中国的广大农村为起点②与之相对应,在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所实施的“党国体制”,以“党政双轨制”的权力管理体系作为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模式。这既是西方政党理念,特别是苏俄政党体制进入中国政坛的结果,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与现代西方的政党体制及理念相互作用的产物。政党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其实质亦是“政法文化”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是政党对权力的实际垄断。它使遵守政党的纲领和规范的义务的范围从一般党员扩大到全体公民,法律在现代国家中的权威性地位由此被虚化。,最终国家通过政策来完成对社会的治理。此种“治理”虽然未必是一种理性、科学、以程序主义为标准的治理,但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成熟、精致的治理方法,比如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整党整风、说服教育、调解、批斗等,归根结底即“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定型化、条文化”[11]。
综合以上对“政法”字义的法律史学角度的体察、比较以及在法律文本中的使用和外来语汇的影响,尽管“政法”一词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其在中国现代法律传统中的内涵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的要素:第一,“政法”一词记录、刻画和揭示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的关系。我们并不能简单将这组概念归结为一元决定论,而应在这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对“文本后面的文本”包括“话语权”的争夺、权力的博弈、思想对行为的支配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解读,从而找到其中的互通性;第二,“政法”一词虽然具有外来法律特别是苏俄法制的基因,但它仍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广泛的牵连性使之形成一个问题链: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政治与法律的结合和界限,“政策”是什么,政党的意志如何上升成为国家意志,政教法度的本体地位是如何实现的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展开,形成了以“政法”含义为基点、从具体到抽象、由现实性到理论性的“政法”知识体系。面向复杂的中国现代法律知识谱系,“尤其是需要关注政法知识传统,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知识的重要特征。这种知识传统强调政策、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必须服务于、服从于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强调国家权力的相互配合和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在各种国家权力之间的主导、协调作用”[12]。然而,尽管在中国现代法律传统中的“政法”因素犹如一团“暗物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的法律生活,但为何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却“失语”、被遮蔽了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基于政治法学的视角,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法律可以超越政治的资产阶级虚伪的法律观。列宁就指出“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策”[13]。此种思维方式更多地凸显了法律的从属性,而忽视了政治与法律在制度层面的相互影响问题。无论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范式对比中,还是在中央和地方这种地缘性的架构之间,政治、政策一直起着建设性的勾连作用,法律则退居其次乃至消失在社会政治生活之中。正是如此,“政法”作为一个载体,一种认识论,而非“事件”本身,“暂时”离开了人们的视野。
其次,从权力与法律的互动关系来看,法律并不是社会控制力量的唯一形式,权力也是实现社会目标的重要工具。在现代社会,政治可谓无处不在,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权力的无处不在,但是绝对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的社会权力在现代国家已经极少出现。权力一方面争夺、蚕食法律的“自由领地”,另一方面,由于法律缩减复杂性,提供稳定性,它给绝对权力设置障碍,两者互动形成复杂的联系。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现代权力“不被看见,但能看到一切”的特点[14],“不被看见”为的是使那些受权力控制的人感到“尊严”,给人一种“统治终结”或“政治终结”的假象,此方面来自于“权利制约权力”的努力和治理效果的考虑;“能看到一切”,意味着它的功能强大,在社会的方方面面能够不间断地发挥作用。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作为国家主权的总体性权力,还是作为知识的微观性权力,都“和其光,同其尘”[15],通过制度、知识实现了更全面的统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被遮蔽”即证明它正在发生[16]。其实质正是政治弱化的表现。不仅要弱化,政治及法连同党和国家最终都是消亡的。但现在还远远没有到消亡的时候。
最后,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和私法领域的发展,对“政法”现象的观察产生了屏障。明确区分“公共领域”和“个人自治”,法治主义的兴起,使法学界更多地注意到了作为自由意志的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学者对“权力-权利”的视角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对范畴并不能全面揭示社会关系,取而代之的是更愿意使用“权利 -义务”的认识结构,但这种分析结构往往容易陷入循环论证,而对社会问题并不具有解释力。
百余年以来,中国的法律传统中的“政法”面相是实然存在的,它是中国法律、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一颗果实,我们要通过这个果实,找到它的家族谱系,发现它是如何成长的,从被遮蔽的背后发现一贯的内在逻辑。
三、“政法”文化之梳理
政法文化兴起的第一个关节点 ——清末修律与礼法之争。外来的侵略和民族的存亡使张之洞等人深刻体会到,洋枪洋炮固然精良,更为先进的是西方的政制,“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要十倍精于其军事技术,因此,欲自强,必学西方。不是简单地学习其“器”,重要的是学习西方之“政”。就修订新刑律以张之洞、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与沈家本、杨度为首的法理派之间的论争而言,焦点在于应当更多地保留中国传统礼教,还是应当更多地采用西洋法理[17]482。随着论争不断深入,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尖锐对立得到了极大显现。从思想层面来说,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法律传统的政法维度之先河:确定、静态、自足的帝国统治难以为续,西方的先进政制要学习,“宪政”作为强国之路逐渐被国人接受。然而,在制度运行上,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却屡屡失败,人们在“共和、民主”的理想号召下始终饱受专制之苦。
第二个阶段,“训政”与“党国体制”。早在1905年,在《同盟会纲领》中,孙中山即为革命胜利后逐步实行法治作了安排。他把革命后的进程分为三个时期,其中“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就是所谓的“约法之治”[18]。他提出了在实行民主宪政之前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要对民众进行“训政”,要教习人民学会行使民主权利。由于几千年的帝王统治,国家幅员辽阔,国民素质不高等内部因素,加上苏俄思想的传入,“共和宪政”的路难以行得通,国民党逐渐确立了精英治国的路线,通过集中权力建立国民党在国家中的中心地位,以国民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党在法上,党领导政府,一党专政。党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简而言之即通过党军、党国、党天下实现社会整合,最终形成了党国体制,这标志着中国政法文化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党国体制重视法制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完备,但党治国家并非法治社会,党治国家的法律充分体现的仅是党国体制的价值和原则,法律代表着政党的纲领政策。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在《三民主义之立法精义与立法方针》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三民主义是一切建国工作的最高原则和立法方针[17]529。在这种法律与政治相结合、政治体制控制司法体制得到充分体现的政法关系语境下,尽管民国时期大量引入了西方大陆法系成文法典,并形成“六法全书”体系,但实际的政治实践和社会现状与这些立法的初衷有巨大的反差,从“政法”的角度考察其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党、政、军利益的纷争以及“党政双轨制”的运作不畅,党内派系的斗争,与共产党的斗争,正面战场与日本的战争,党国体制遭受多方挑战而走向颓势,虽然最后勉强走向“宪法之治”,但这和孙中山最初的政治构想早已相去甚远。然而,政法文化并没有随着党国体制的衰败而停滞,此时的政法文化随着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有了不一样的发展轨迹。
第三个时间段,革命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法制。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颁布了一大批重要的法律条令,由于当时的形势和环境的限制,共产党制定的政策、方针、指示往往直接起到法律的作用。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治理上以“政策”实现民众与党的沟通。我们可以发现“土地革命”除了在政治上扭转中国农村的阶级秩序(农民翻身做主人)、在经济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构建、形成了党的领导与民众的响应、中央发布命令与地方积极响应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此种功能便是政法实践的突出表现。在司法审判工作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以深入基层调查、走群众路线、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简化诉讼手续、方便群众诉讼为特征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它在“政法文化”中具有里程碑的影响。我们通过文献的阅读大致可以看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一些基本法律理念:其一,法律是为政权服务的工具,并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其二,法律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法令条文,还包括党的纲领、决议、政策、布告等;其三,在审判方式上与国民党的法庭审判严格区别,尽可能采取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新民主主义的法律应是进步的法律,它必须对旧的法律进行革命”[19]。法学界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评价往往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究其实质,此种审判方式得以成为整个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法制实践,其内在的理路就是“政法”的运用。这个时间段是政法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确立了政策的运作方式、党与群众的沟通方式和处理问题的实践理性。
第四个转折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政策”“运动”的治理。新中国初期的法制,废除了“六法全书”,进一步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法制经验,引进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重新选择法制的现代化模式。在建国初期的司法体制中,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工具的临时的司法机关 ——人民法庭是政法文化的一个突出表征,它基于政治的需要而设立,审判的依据不是法律而是群众的革命热情与“民愤”,审判人员并不是专业的司法人员而是革命干部和群众。这种巩固新中国政权的司法制度,其实质是国家统治的整体性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司法的“群众路线”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正是政法逻辑的运行模式。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由于此种模式缺乏“对人民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也缺乏明确分开的司法和行政权力,因而很容易变成完全由党组织控制的实际运作,或者变成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1],在“文化大革命”这一非正常时期,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就是要以激进革命的方式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将法制边缘化,“服务于党和国家政制的一元化领导”[20]。这个时间段的政法文化是处于失序之中的。
第五个发展阶段是在文革后,从“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开始,社会综合治理,法制到法治的变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谐司法的提出。从“话语”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法运行模式的变化,政法文化的发展处于一个全新的时期,它汲取了新的养分,有了新的形态。毫无疑问,三十余年来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法治文化似乎全面压倒了政法文化,“依法治国”的口号铺天盖地,“社会主义法治”耳熟能详,然而法治在现实制度层面上其功能的发挥却略显无力,有时被扭曲甚至被消解。“法条主义”使法律更为主观,更容易受法律之外的权力所操纵,这正是政法基因在制度的层面上强有力的体现。“法治”与“政法”之间存在的内在的张力仍是正在进行,并深刻改变我们当下的社会结构。
四、“政法”维度之把握
我们从“政法”的内涵和其发展源流进行了梳理,对于政法的深化思考,笔者认为可以基于政法的三重维度来全面把握。
第一,现代性维度。美国驻华大使罗炳吉(1914-1924年在华任职)曾指出:“中国试图以西方法典为框架改造其法典,要说中国在这一进程上进展缓慢,是对其不适当的批评,因为要改造一个业已存在了逾四千年的法律制度,以适应有四亿人民的国家的需要,这绝非易事,危险伏于急遽而非慎重之中。”[21]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开启的中国法律体系和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尽管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但实际上仍属于同一套“话语体系”。在今天,当“政法”传统遭遇西方法律思想,法律领域内的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凸显,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视角、姿态和进路呢?我们现今在很多问题上简单的用西方的尺度来裁量中国经验,或者对中国的问题仅仅停留在哲学思考上,而不能从具体的事件和实际出发,因此难以找到现实问题表象下的深层次原因。政法维度就是基于这样一种主体性意识,以社会转型为背景寻求“第三条道路”,跳脱出王朝政治和纯粹西化的法治模式。
第二,本体论维度。政法维度的理论原点是权力关系,关注权力的源流和运作。现代社会,权力与权利之间形成了制约,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产生了适度的分离,国家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过度干涉受到约束,这无疑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政党因素不可忽略。“政党的崛起及其对国家和法律的广泛干预,改变了原有的权力结构”[22]。政党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应该还有政党权力。国家、社会、政党三者的互动,正是政法维度的内核。从社会效果层面来看,政法是一种社会控制。每个社会的社会控制的思维、范式、制度都有其意义,并且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状态相契合,其权力的源泉也许并非根植于法律的权威。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当代社会,这些隐匿于法律之外的权力是不可忽视的,只有认真考量,权衡利弊,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如何通过法律塑造有序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方法论维度。法律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品格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政法”维度的研究方法试图跨越法律形式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沟壑,在条文、制度、原则、价值中寻求动态平衡。政法并不是自发地从人的自然状态中萌芽发展,而是以社会治理为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家、法律人在革命斗争、政权建设、社会改造中逐渐创造和总结出来的。它通过实践来不断调整(如多次“修宪”,把“以人为本”写进宪法等),不搞绝对的古今之辨,既不将法律的合法性的论证固化为某一终极价值,也不将“法治”作为一剂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避免从法律虚无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法治全能主义。既不是理想性的乌托邦情怀,同时与绝对的功利主义保持距离,它是基于“常识”和“多元主义”“经验”和“理性”的政治与法律思想的智慧。
从目前的学术成果来看,我们现今对于“政法”的考察仍趋于零碎、肤浅,诚然已经有一些学者敏锐地观察到了“政法”问题的重要性,但对其内涵、界限、运行规律等问题都存在较大的模糊性,没能从散乱经验后面萃取整体性的含义,无法将之提升到范式的高度来加以研究。政法文化是与中国传统的礼法文化、西方的法治文化不断碰撞、选择重构后产生并发展的。我们研究政法文化的目的是要挖掘、再发现原有的传统理念、价值、制度,将“政法”传统从被遮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通过理论创新,产生新的导向,既不失去过去的底蕴,同时与现代对接,让传统更具生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建设富强、民主和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传统,它并不是久远的历史追溯,而是现实的召唤。
[1]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J].读书,2005(2):9-14.
[2]梁治平.传统与现代性[C]//法治十年观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7.
[3]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序言.
[4]张之洞.劝学篇[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0.
[5]熊先觉.熊先觉法学文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4 :544-581.
[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7卷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429.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1990年4月2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1.
[8]董必武.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7-211.
[9]新村出.广辞苑[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2005:1231.
[10]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3.
[11]冯象.政法笔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37.
[12]徐亚文.知识社会学能为中国法学研究带来什么?[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0(4):8.
[13]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0-41.
[14]邹吉忠.知识政治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46.
[15]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9.
[16]徐亚文.西方法理学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172-184.
[17]范忠信,陈景良.中国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8]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50-51.
[19]《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171.
[20]高全喜.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74.
[21]罗炳吉.中国法律导论[M]//王建.西法东渐 ——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改革.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0-51.
[22]喻中.关于当代权力结构的思考[J].法学论坛,2001(5):34.
“Politics-Law”:The Hidden Dimension of Chinese Modern Legal Tradition
XU Ya-wen,DENG Da-qi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
Politics-Law is a dimension of much importance in Chinese modern legal tradition.As the result of vicissitudes of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structure,a semantic alteration from Law-Politics to Politics-Law is happening in this course.The transition of Politics-Law culture has undergone five phases,in which modernization,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Politics-Law are the triple key dimensions to comprehend the relevant issues of Politics-Law.
Politics-Law;tradition;dimension
D911
A
1005-6378(2011)05-0103-06
2011-03-10
徐亚文(1966-),男,浙江天台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宪法学。
[责任编辑 卢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