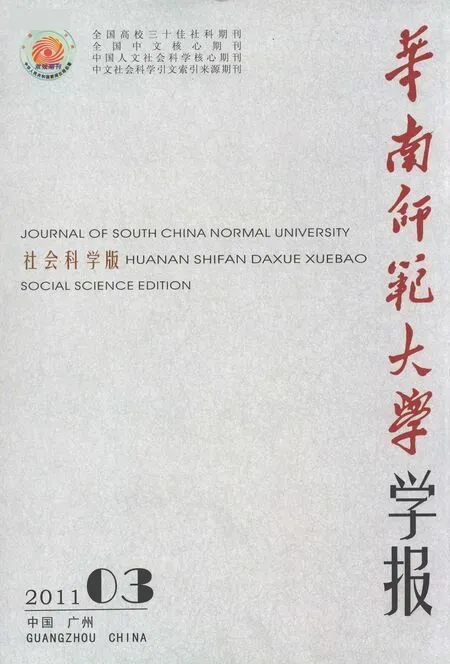身体维度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突显
李 重
(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2.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身体维度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突显
李 重1,2
(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2.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长期以来,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存在着对女性主义实践完全相对的双重解读方式。对于当代女性而言,到底是经济压迫还是文化统治构成了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主要困境。通过对当代女性主义身体理论的挖掘,可以重新理解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所存在的理论困境。
文化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身体理论 符号权力
伴随着经济巨大发展,科学不断进步,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已趋于完成和臻至鼎盛。特别时至20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结构、政治生态、斗争策略日趋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如何在复杂化、多元化的后工业社会冲突中,确立一个合适的女性主义政治斗争的目标,并且寻找到一种可以消除种种性别不正义的良方,成为诸多理论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重新反思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所存在的理论困境,以身体理论为切入点,通过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身体维度的发现,以期积极地推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经济压迫,抑或是文化统治?
长期以来,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存在着对性别实践完全相对的双重解读方式,就其路向来说可分为:一种是唯物主义(materialism)或者有时候也称为经济主义(economism),另一种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概括来说,双方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对于当代女性而言,是经济压迫还是文化统治构成了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当中,继而制造了一系列的理论上梳理不清的扭结,成为很多女性主义研究者相互诘难攻讦的主要理论问题。
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逐渐从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扩展到文化层面。从全球范围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权利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以及同性恋争取平等待遇等问题逐渐成为困扰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妇女、黑人、同性恋以及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或种族群体的成员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被排斥,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社会文化身份的差异性。这些文化不正义以及身份政治不平等的诸多问题在原有的经济再分配理论框架内已经无力解决。人类遭遇的普遍文化困境,导致了女性主义斗争策略的转移。文化女性主义(cultural feminists)认为,在这种特殊的文化境遇中,女性主义斗争策略必须要进行修正和转移,如果还停留于传统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忽略了总体性的文化操控问题,就会偏离社会的现实和人类生存的焦点性问题,并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失去创造力和现实的理论指向。
在当代学界炙手可热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正是这一观点名副其实的代言人和最有力的支持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者们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特别是在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的强烈冲击下,广泛吸收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女性主义理论和性别研究中的问题,以新的视角来研究女性问题。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传统女性主义批判的只是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只适合于特定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说明女性受压迫的真正根源和指明摆脱的途径。正如很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支离破碎的、混乱的、分散的、与历史极度割裂的。特别是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现代社会中文化因素越来越成为社会冲突和变迁的重要因素,经济斗争已成为抽象的概念,人们不再用阶级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属于那些不以经济基础而是文化身份来划分的特殊团体。正是如此,当代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种种不平等的根源主要是文化的。在这里的不平等被理解为一个社会的符号和解释系统以及交往模式,使一些弱势群体或个人无法享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充分表达自己主体性以及文化特征的能力和机会。不平等在这里主要表现为:文化统治,即弱势文化受主流文化的文化和解释模式的强制和支配等等。尽管传统女性主义也指出社会文化是女性屈从的原因之一,但是传统女性主义对社会文化的提及一般只是流于表面和现象,忽略对社会文化更本质的揭露和分析。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以此为基础,试图以文化承认取代社会经济再分配,坚持一种文化的建构主义,关注一种身份(Identity)的认同,主张需要充分发挥不同行动者的能动作用,在不同文化层面对统治规则进行挑战和颠覆。以后现代女性主义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义者认为,那些传统女性主义者在分析女性压迫状况的时候,依靠了一些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区分,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现实与表象、经济与文化等,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权力成为分析女性被压迫的最为主要的原因,因而归根到底难以逃脱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嫌疑。这种单一化的模式又必然会因为过于重视阶级压迫而忽略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性别压迫、种族歧视,在某种程度上使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从属于阶级斗争,从而削弱了女性主义整体斗争策略。
但是,与此同时,一部分女性主义者也清醒的意识到,这种醉心于身份认同和文化分析的斗争依旧出现在一个物质严重不平等的世界中——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收入和财产、就业机会、教育、医疗保障上,而且还体现在发病率、死亡率等方面。一种主张“让女性主义回到唯物主义”[1]的呼声又开始慢慢复苏,而一度受到冷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开始积极介入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来。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随着女权运动的深入,女性主义者为了寻找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融合。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为基础,强调经济制度决定上层建筑,她们认为物质生活塑造人的意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制度,因而需要到社会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中去寻找不平等的根源。对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来说,改变女性的不平等地位需要采取收入再分配、社会分工体系的重组或社会和经济基本结构的改变,因为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改变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提出,当代文化主义女性主义实际上一种“学院派的女性主义”。她们的理论单纯地将女性压迫归因为一种身份政治的危机,从而没有找对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正如特雷萨.艾伯特所指出的:“‘后’之后的女性主义,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很大程度上已经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实践(如决定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的劳动)不甚重视,并且对差异有一种盲目的崇拜。换言之,它消除了剥削问题,把对女性现实生活的一些根本性条件的认识分散成许多关于“压迫”的具体细节。女性主义接受了这个文化的转向(将文化具体化为各种有意义的实践的一个自主区域)而将政治变革撇在一边。”[1]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看来,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们以晦涩难懂的文本为乐,她们逃离真正的革命斗争,从游行、运动、联合抵制以及抗议活动中抽身而出,在精神花园里享受思维的乐趣,她们孤芳自赏,难得离开她们的极乐处境,随着时间流逝,她们的话与大多数女性越来越不相关了[2]302。因此,如果离开了经济关系及其由此决定的阶级关系的现实支撑,势必会使诸如男性统治、性别歧视、文化歧视等问题在一场“语言游戏”中逐渐虚无化,最终导致女性失去参与解放和争取自由发展的实践主动性。
总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逻辑往往要求经济安排尤其是劳动分工中的去性别化;而文化女性主义的主张则倾向于矫正文化评估模式以赋予女性群体应有的价值。然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两种模式都可能走向片面,以自己的一元逻辑削弱和取消对方。于是,试图消除性别差异和倾向于肯定性别差异的两种矫正措施使得女性抵抗政治陷入了二难困境。可以说,这样一场争论一直困扰着当代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因为分析策略不同,直接会导致了女性主义理论建构方式和实践路径上的重大差异。因此,一些女性主义者开始尝试寻求理论上新的突破,去探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急于断言两者之间的差异,或者是干脆拒绝接受这种“非此即彼”的理论观点。
二、视域的重置:当代女性主义对身体维度的揭明
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理论困境一筹莫展、踯躅不前的时候,当代一些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意识到,所谓的“二元对立”、“同一性”、“男女平等”的概念无非是男权思维逻辑的延宕,是按照男性话语构造出来的,体现了男性的权力,但它无法彻底改变女性受压迫的现状,也不能真正改变女性的地位。要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必须把女性从塑造了女性主体概念的男性话语和男性立场中解放出来,挣脱那些禁锢着女性思想和行为的压迫性话语和观念,消解现行的男女两性观念,抨击男性中心的理性权力话语。在女性自身经验的基础上,用女性的身体话语来重构符合女性自身特点的主体性,使女性成为自身经验的言说主体,重建女性话语,在观照性别的同时返回到“身体”来对抗和解构男性的理性权力和话语霸权。在此基础之上,她们掀起了女性主义的身体理论研究热潮。为何身体会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焦点问题?撮之其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理论渊源上说,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的转变,同当代哲学“身体转向”相关联。众所周知,西方传统哲学总是站在抽象的立场上,身体(body)始终是处于一种“异化”的分裂状态,心灵(soul)和肉体(flesh)成为了一种和周围事物永不相干的“单子”。现实的人被一种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模式给割裂开了。随着西方哲学从思辨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当代西方哲学毋宁说正在出现一种极其深刻的理论范式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使业已退隐的身体进入哲学视域而日渐朗现,还导致一种有别于意识本体论的身体本体论思想开始被哲学确立。从尼采的回归身体的呼吁,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哲学的推出,都为我们显示出了这一理论转型的轨迹。特别是福柯、拉康、罗兰·巴特、布尔迪厄等具有叛逆思想的哲学家们有关身体理论的推出,使身体在哲学理论以及社会学相关领域中异军突起,成为当代哲学的中心和焦点,彻底扭转了现代社会表述自身的中心语汇,身体以及与之相关的词语——激情、冲动、欲望、消费、性感、快感等成为时尚词语。用当代女性主义者巴特勒的话说,欲望是对存在的质询,是对同一性及其形而上学位置的身体性探问[3]33。与那种无名无性的、作为人类渴望的抽象结构的意识主体不同,身体总是具体的、性别化的身体。因此,“身体的历史”在理论上必然也包含“性别的历史”[3]234。
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身心二元论模式深深根植于一种等级和支配关系之中,并且这种支配权总是和男性而不是女性联系在一起。那么,当代哲学对身体的高扬,必然意味着身体的性别维度在当代哲学中的突显和推崇。故此,这种理论转型在解构和颠覆冥顽不化的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二元等级对立思维逻辑的同时,从哲学的高度给女性主义提供了破除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长期以来,男根—逻各斯中心主义所潜藏的对女性身体的贬抑,极大地忽视甚至贬低了女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女性主义者不得不将研究的焦点集中于身体之上,重新审视这种不平等性别身体观的表现及其根源。在这种话语条件下,以巴特勒、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者把女性身体作为一面骄傲的旗帜高扬起来,向男性中心话语发出了挑战。正如艾米莉·马丁(Emily Martin)所说的那样,作为女人,我们居住在我们的身体,而身体又是我们女性性别的符号,在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导的世界中,女性与其身体具有天然的同盟性与同一性[4]31。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理解下的抽象、僵死的主体不同,这种有性别的身体呈现出生命性、具体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的特点。逻各斯主义的根本困境就在于它难以解释不同于男性主体的女性为何是如此存在的。正是因为如此,当代女性主义者认为,身体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建构。她们力图从动态身体的角度消解逻各斯主体观的霸权性地位,为各种女性亚群体甚至女性个体的身体性存在提供理论解释与说明。她们将身体作为出发点展开了对意识理论和理性主义的批判,借用身体话语从边缘位置向意识话语的中心位置发起冲击,透过身体重新审视种种性别不正义的表现及其根源。这就从根本上解构了父权制社会中身体即命运的观念,颠覆了不平等性别观的基础。
其次,从现实层面来说,身体维度在当代突显的更根本原因还在于后工业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在当代,身体刚从道德领域、真理领域的辖制中步履蹒珊地走出来,但是却又落入到由现代资本逻辑所编织的新的陷阱之中,即身体被利用、被编写、被篡改、被消费,身体失去了本原的存在意义,日常话语权被剥夺殆尽。在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看来,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丰盛的、堆积的社会,马克思所描述的以使用价值为基础、以物的生产为目标的社会已不复存在;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的社会,它不再以人对物的占有关系也不再是以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为核心,而是以符号的生产和消费为核心。人们更多的兴趣不再是关注物品满足人的自然欲求,而是关注物品符号特征,通过无用的耗费、欲望满足的程度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予以区分,标明他们的身份地位、阶级和阶层。正是因为如此,身体的欲望和需求就成为了这种消费赖以存在前提。只有当人成为一架疯狂运转的“欲望机器”,才有可能维持资本的再生产流水线。[5]与之相应,当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和场所围绕着资本主义的利益需也做了相应调整。
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的权力形态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有关人性、人类历史、经济和力比多的总体理论之上的,是建立在宏观权力模式之上的赤裸裸的“硬权力”;那么,当代社会的权力则是自下而上、分散的,是隐含在日常生活中,是通过身体传输的,通过对身体无意识的操作运行的“软权力”,也即布尔迪厄所言的“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符号权力是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权力。”[6]117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社会的权力场中,一切权力都是通过符号权力发挥效力的。我们发现,“符号权力”的运行和再生产始终离不开对身体的控制,是以身体为媒介的。身体按照一定的统治需求被压制、制作和塑形,成为被人厌恶的、羞耻的或快感的等等身体样本(符号化),最终成为身体的符号,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无意识,这样,统治关系才能根本作用于身体,符号暴力才能最终实现。正是因为如此,这种所谓的“符号权力”不仅表现在显而易见的政治领域,也不仅表现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凭借对身体的无意识压制,实现某种权力的欲望,譬如性别、性、身份、种族、民族等等都可以成为权力欲望的场地。这也意味着,符号权力已然不是与政治经济权力或文化权力相并列的特定种类的权力,而是肆意流淌于任何社会层面的毛细血管当中,跨越了全部社会关系的统摄力量。因此,对“符号权力”的反抗比对政治经济权力的反抗要困难得多。现代人已经在这个由资本和欲望交织的大网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摒弃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范式,即将政治范畴简单划分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经济压迫与文化压迫。在当代,权力已经不是由一个具体群体拥有。针对另一个具体群体的力量关系,我们应该将其看作是由实践、习惯和技术组成的最终落实于身体的网络。
最后,从女性当代生存境遇来说,要更真切地、立体地、微观地分析女性当代处境,需要对身体进行一种所谓的微观政治学(Biopolitical)分析。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家乔治·吉尔德在他的《财富与贫困》一书中公开阐明的:资本主义是以男性至高无上为基础的[6]79。父权制既是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一体的。正是因为如此,女性身体受到的是双重的规训,除了接受一般身体所接受的规训外,女性身体还要承受另一重父权权力的规训。博尔多和桑德拉等女性主义者敏锐地指出,并不是所有人的身体都受到同样程度的仔细审视或者在其失控的情况下受到同样的冲击。特别是在女性的身体和欲望中,似乎最明显地表现在身体的高度自我监督和自律机制上。“一天内六次查看化妆效果看粉底是否结成硬块或者睫毛膏是否融化并且担心风雨会毁坏发型的女人己经像环行监狱里的囚犯一样毫无疑问地变成了一个自我警戒的对象,一个受到自身无情的监督约束的自我。”[7]260如同女性的相貌受到社会更为苛刻的审视一样,女性的欲望、饥饿和食欲在父权制社会中也被看作极具威胁力而成为被控制的对象。特别在商业传媒控制的今天,不断地制造各种类型的“身体时尚”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无论是屏幕上推陈出新的形象,还是生活中无孔不入的广告,苗条而富有曲线感的女性身体必不可少。在塑身广告不断地诱惑和鼓励下,人们感觉到个人的生活基本上失去对自我的主宰,禁不住想通过对身体的塑造找回自我。
勿庸讳言,这里隐含着潜在的暴力:如何使自己的身体符合某种认为的外在规范。这一现象再次向我们揭示出,女人“监视”自己的身体,注意它与标准化的差距,实际上暗中起着霸权功能的正是一种看不见的符号权力。女性按照这类主流话语的标准把身体对象化和客体化了,使身体处于标准化的窥视的监督之下,通过对自己的体重、衣着、化妆、生殖、锻炼等方面进行的自我监督迎合了父权社会对其身体的建构,使女性身体充当男性欲望客体化的结果,以此增加女性在事业上的竞争力,或者至少增加了在婚姻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而这些所得无非是让她们在符号财产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只是让女性在男人支配的场域中继续推动男性统治。正如布尔迪厄“符号权力”所揭示出的那样,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合谋”(complicity)的情况下完成的。“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可(recognition),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可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的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深处的观念。”[8]285因此,男性秩序的根深蒂固就体现在根本无需为之提供什么证明,它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普遍有效的东西。这就是符号权力的可怕之处,被统治者是站在自己不知情的基础上赞同了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并构成了统治基础的重要一环。因此,这种“身体的符号化”和“符号的身体化”的双向转化就成为了这场诡异游戏最秘而不宣的游戏规则。
三、新的尝试:当代女性主义身体理论的探索
近百年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女性性别悲剧依然不以时代历史为转移地在不断续写着,女性依然没有改变其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因此,那种宏观社会框架中物质/文化二元划分的简单思维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已然彻头彻尾地沦为了一种“虚假意识”。进而,上文所提到的女性主义关于经济压迫和文化统治之争,由于其或把这种悲剧归罪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归罪于一定的文化统治,却都没有真正洞揭在当代已然成为罪魁祸首的、作为一种“权力之权力”的“符号权力”统治,因而在对当代女性生存境遇的分析中显得力不从心。事实上,这种“符号权力”已经超越了文化(政治)范畴或者经济范畴狭隘区间,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以及符号统治的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已变得模糊不清。众多女性主义理论家虽力图为我们揭示女性悲剧所内蕴的普遍性根源,一味地寻找所谓的权力主体,期望通过一种结构化的整体社会变革,消解女性所遭遇的种种不正义,最终这样一种挂一漏万似的理论努力,导致了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家犹如堂吉诃德一般手持批判的利刃却遍寻不着自己的敌人,可惜可叹。明于此,凝结在这种“伪逻辑”中的困惑就会迎刃而解。
理论从来就不会仅仅局限于理论本身,而总是要越出自身的范围,转换为社会行为,成为社会实践。同样,“身体转向”在当代也不是单纯的哲学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讲,“自我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9]294。既然身体成为了受害者,那么首先需要解救的就是身体,也就是说以女性主义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身体。一些女性主义者在对女性生存现状的考察中,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无话语权、无身体权的严峻现实,力图找寻属于女性的独特特质。要建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就要认真地对待女性的身体,女性必须关注女性的体验、情感、思想和欲求,挖掘过去社会文化充耳不闻的女性身体的隐秘体验。如果女性没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没有言说身体的体验、精神和心灵的权力,或者女性的精神空间被男性主体意识所殖民化,女性无法真正拥有自己的肉体和灵魂,那么这样的女性是没有主体性的女性。因此,可以说,女性的解放离不开身体,而女性的抵抗也必然从身体出发。
在当代,一批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理论视角切入到对身体的研究当中。例如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在批判男权意识中的身体观后,提出的一种女性话语模式,即“女人话”(parlerfemme)。“女人话”是女性的语言,一种与男性中心话语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伊利格瑞看来,女人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东一句西一句,简直漫无目的,甚至自相矛盾,疯疯癫癫,完全谈不上逻辑。伊利格瑞认为,这种“女人话”的产生正是基于女性身体,或者说是女性与男性不同的生理特征。与男性身体作为单数“一”的向度相比,女性身体是一种复数的“非一”:“女性的性征是多重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女性没有性器官,她至少有两个性器官,并且不尽相同。事实上,她的性欲至少是双重的,甚至更多:它是多重的,以至于可以说女人全身都是性器官。”[10]正是这样的身体造就了流动的、非线性的、不合逻辑的语言。女性身体和女性话语一起向强调同一性、目的明确、以意识、理性及男性身体优越感为基础的男性中心话语发起了冲击。西苏(Helene Cixous)则提出女性不但被父权逐出她们自己的身体,同时也被逐出了书写。“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11]西苏呼吁女人应该书写自己,也就是所谓的“女性书写”。女人必须重回身体,重回历史,重回世界,从身体中索取包括欲望、体验、内驱力等创作资源,基于女性自身独特的身体和性欲的流动性、多样性、开放性的展开,才能使女性身体成为反男权、颠覆菲勒斯中心的巨大力量。作为当代法国女性主义三驾马车之一的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女性主义身体理论则主要关注处于“卑贱”、“升华”以及“净化”中,蕴涵在母亲身体内的真实体验、感受(包括压抑的、恐惧的欲望的)和情感,并把它作为一种符号化的话语纳入到整个话语体系之中。在母亲的法则、想象父亲的法则和父亲的法则的逻辑链条中探讨想象的、情爱的等话语内涵。因此,无论是伊利格瑞的“女人话”、西苏的“女性书写”、还是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都立足于女性特质的探求,都是与女性身体密切相关的父权制内部的颠覆力量。
伊利格瑞等人依然在追寻“女人如何是女人”之道,或多或少还是承认人类先天的生理性别(sex)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而社会性别(gender)是社会构建的产物,是从生物性的“现实”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性/性别是彼此分离的。在当代女性主义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看来,这样一种理论态度似乎还未彻底摆脱物质/文化二分模式。为了打破性/性别的二元对立,巴特勒提出“女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给定的基础,而是一个可变的建筑物,反对将“女性”作为一个稳定的、连贯的主体。她指出,“的确,也许它(生理性别)总已经是社会性别,结果是,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区别原来根本就不是区别”[12]7。巴特勒打破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是想要表明,所有的身体,从它们的社会存在(不可能有不是社会存在的存在)开始,就被社会性别化了。这意味着,不存在先在于其文化铭刻的“自然的身体”。也就是说,人的身体一出生就落入语言的象征网络之中,被语言所命名、区分、被赋予社会意义[13]。但这又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物质的身体本身,话语不能创造身体,而是意味着我们只能通过话语来理解这种物质性。用巴特勒的话来说,性别话语并不描述先前的物质性,而是产生和规范身体的物质性的可理解性[14]90-91。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系谱分析,巴特勒最终在《身体之重》(Bodies That Matter)一书中形成了“性别是一种表演”的重要理论主张,将女性主体放置于无尽的生成过程中,以期产生一种打破单一性、呈现多样性的“表演”效果,通过转换和颠覆“性别二元论”霸权的愿望与努力打开了性和性别政治的新的可能性。可以说,巴特勒的身体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理论和政治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可以说,身体视角的确立,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多元化提供了新的可能。这种影响不仅仅在于研究主题的转换,更在于一种研究范式的根本倒转。身体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意识哲学的更为根本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一全新视域的展开,不仅意味着当代女性主义对自身命运的当下把握,而且也意味着人们将更多地关注人自身的生活和生产。正是通过个人化的身体角度去切入历史,我们才有可能触摸到历史最隐秘的某种本质。
[1]特雷萨·L.艾伯特.让女性主义回到唯物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05(10).
[2]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Judith Butler.Subjects of Desire: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
[4]Barbara Brook.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he Body.London and New York:Pearson Education Inc.
[5]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Bomdieu.Symbolic power∥ D.Gleeson.Identity and Structure:Issues in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afferton Books,1977.
[7]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97.
[8]Sandra Lee Bartky,Femininity and Domination: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Oppression.New York:Routledge,1990.
[9]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Luce Irigaray.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Trans.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urk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28.
[12]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3]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1999.
[14]严泽胜.朱迪·巴特勒:欲望、身体、性别表演.国外理论动态,2004(4).
[15]巴特勒.暂时的墓础: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王逢振.性别政治.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李重(1980—),男,陕西汉中人,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2011-01-15
B089.1
A
1000-5455(2011)03-0089-06
【责任编辑:赵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