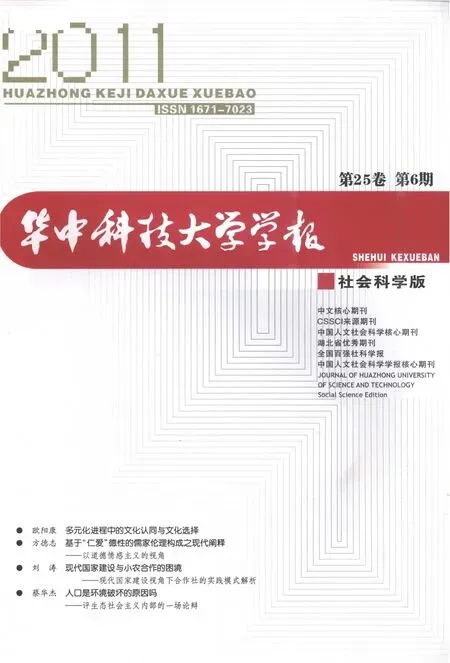中古人文精神的透析——从演绎中的六朝知音文化谈起
杨明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872
中古人文精神的透析
——从演绎中的六朝知音文化谈起
杨明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 100872
知音文化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中最重要的建树之一,它发轫于六朝时期,并以六朝人文思潮为思想根基,不失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独树一帜的思想文化体系。本文试图探寻知音文化的源起与本根,挖掘并阐释六朝知音文化的逻辑内涵,透析六朝知音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对于中古文化空间的拓展及其对中古人文精神的提升与超越。
六朝;知音文化;文化空间;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蕴涵着古人对作家作品鉴赏、批评等各种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知音文化就是这些成果的集成与内核,是贯穿和渗透于其中的浓厚人文价值意蕴的体现与结晶。综观中国古代文论,知音文化始终伴随着文人交往、文学创作、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等全部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六朝如梦,“知音”不空。经过六朝五百年人文思潮的发展,知音文化逐渐从一个普通的名词演变为具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完善的理论体系、经典的人文价值,并且结合了数百年大量的作者及其文学作品的博大体系。从汉末魏晋知音意识的发轫,一直到《文心雕龙》里堪称集大成的知音体系的高度成就,其间鲜活的历史告诉我们,知音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可以独树一帜、以古鉴今的中古人文精神的提升与超越。
一、六朝知音文化的源起与形成
中古知音文化作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建树之一,萌芽于先秦,发轫于汉末,肇始于魏晋,兴盛于南北朝,在刘勰《文心雕龙》的《知音篇》中蔚然成熟。具体可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简要阐释。
第一,知音其说的源起与先秦知音赏评意识的萌生。中古文学中的知音其说,源自“高山流水”的故事。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在先秦乃至秦汉被反复讲述,最早记载于《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中,成书于西汉的《韩诗外传》,在其卷九第五章讲述了这个故事,刘向编著的《说苑·尊贤》篇也同样完全引用了《吕氏春秋》的故事,还有成书较晚的《列子》中也记录了这一故事。仔细品读原文,我们不难看出,“高山流水”这个故事最初在《吕氏春秋》中被讲述的时候,并未明确提及“知音”,其原意也并非感慨伯牙子期之间是如何能够互相理解、互为知音的,然其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的关于统治者如何得贤的隐喻与本味,即“弹琴需要真正懂的人才能听,而贤者也必须要能够以礼相待才能得其用”,意在表明正当的统治者与贤者的关系,其对先秦“君臣以义和”的君臣关系的反应所蕴涵的对知音隐而未发的思考可见一斑。
与《吕氏春秋》对比可以发现,《韩诗外传》中的描述,从“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到“以为世无足与鼓琴也”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后面一句略有不同。①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吕氏春秋》)。非独鼓琴如此,贤者亦有之。苟非其时,则贤者将奚由得遂其功哉?(韩婴撰,许维遹集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他们论述“知音”都是从尊贤、进贤的角度,这一点则完全一致。
刘向编著的《说苑·尊贤》篇道:“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其中还提到哪些人是“贤人”,比如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然,中古历史告诉我们,这几位贤人与其辅佐的王者都是互为知己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一种超越了后来意义上等级森严的君臣大义的志同道合的关系。
简言之,“高山流水”这个故事最初出现在文献讲述中时,并没有明确提出“知音”的关系,而是与任贤更密切。若任贤也是一种“知音”,那么,“知音”的双方则是“任贤”和“乐于效力”之间不对等的关系,显然,其最初的意蕴仅与政治相关,而无关文艺,是后世知音文化的滥觞,但也一定要认清其本质是非文学批评的。
成书较晚的《列子》中有关“高山流水”的记录则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其意蕴与前者有着明显不同,即结尾处没有了“任贤”的尾巴。这个故事不再是君臣之间相知关系的隐喻,而是有了一个纯粹的、较为艺术化的结尾:“子之听夫志想象犹吾心也。吾于何逃声哉”,晋人张湛注曰:“言心暗合与己无异”,简短的解释却非常有意味,即指出这则故事的目的是描述伯牙和子期之间的“心暗合”,而这不正是“知音”之意吗?如此看来,“高山流水”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第一次有了纯然的“知音”叙述,从此摆脱了“任贤”的态度。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列子》之书,还是张湛的注,都比较靠近或身处六朝。而东汉后期刘向的《说苑》仍然在以“任贤”来讲述这一故事。这就有理由判定,“高山流水”这个故事直到六朝才逐渐摆脱“任贤”的政治话语,成功的转化为美学化色彩浓重的“知音”的美学话语。②其实,东汉蔡邕的《琴操》中已经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只是描述古琴曲谱的说明词,并不是“高山流水”这一故事的再现,所以虽然《琴操》是东汉末年的文献,但也不能改变正文此处的结论。且自《列子》后,“高山流水”就常被人增为“高山流水遇知音”了,而几乎所有引用这一故事的,都会从“知音”的角度来看待。正如《文心雕龙》之《知音》篇所说:“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行之笔端,理将焉匿?”刘勰已不必过多解释这里的“琴表其情”,因为无论是他原句的含义,抑或是后人的注释,都透着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弦外之音。笔者以为,“高山流水”的故事无疑在知音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知音文化形成的直接因子,亦可为知音赏评意识萌生的雏形。
第二,两汉时期知音的内涵拓展及其批评术语化的演变对六朝知音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高山流水”的故事虽给了“知音”以内涵,但并未明确提出“知音”的概念。那么,“知音”是如何在其内涵不断拓展的基础上演变为文学批评术语的呢?或者说,“知音”是如何从先秦模糊凌乱的意识中逐步形成概念性术语的呢?笔者借助对早期中古文学批评史料的考察发现,“知音”在两汉时期由单纯的动宾短语逐渐演变为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具体可作如下简要梳理。
顾名思义,“知音”一语首先在于“知”,即要有一种审美、理解和惺惺相惜,而这一行为当是相互的;其次在于“音”,亦即沟通、链接双方的媒介,对应于“高山流水”的故事中,就是指音乐。可见,“知音”已开始呈现出其对音乐、文学等艺术、文化作品的审美态度,而这一点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亦清晰可见。笔者以为,知音之“音”在从故事走向整个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其所表征的媒介就由音乐发展延伸成为文学作品了。如此,随着中古文学艺术的持续发展,知音一语的内涵便得到不断的拓展与深入。
在《礼记·乐记》中有载:“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於礼矣。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里提及的知音显然已由“高山流水”故事所呈现的只是一个名词拓展为与“知声”“知乐”相对的动宾结构词语,同时也解释了音乐与人心的关系。《乐记》所谈的音乐已拓展为对音乐的鉴赏层面,且将这种鉴赏置于“人心”与“伦理”之间,解释了“知音”也是要发乎人心,止乎伦理的,这与最初的只表征“知道声音”、“了解声音”等“知音”二字的本意相较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知音内涵的深入与拓展,进而言之,这种深入与拓展也为随后知音内涵的持续深入乃至知音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中古文学批评史可知,“知音”作为文学批评术语较早被使用是在西汉时期,这一时期的《韩诗外传》和《淮南子》中都有将知音作为对音乐的鉴赏的用法,如《韩诗外传》卷七第二十六章中提到: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贡侧门而听。曲终,曾子曰:“嗟乎!夫子瑟声殆有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趋利之甚?”子贡以为然,不对而入。夫子望见子贡有谏过之色,应难之状,释瑟而待之。子贡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参,天下贤人也,其习知音矣。乡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见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厌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参以丘为贪狼邪僻,不亦宜乎。”①269页。按:这则记载在《孔丛子·记义篇》中同样存在,不同的是《孔丛子》写作“鼓琴”。这里,“知音”已由纯粹的动宾短语演变成对音乐这一艺术形式的鉴赏了。这则故事中,孔子鼓瑟,被他的学生听到后,学生们通过欣赏音乐来探求孔子的心志。因为在门外,曾子从孔子的音乐中听出了邪恶的志趣,于是进门试图劝诫孔子,这才知道孔子是因为有邪恶的动物,“以瑟淫其音”,所以才演奏出这种音乐,并非他本人心志有缺。这则故事最大的意义,在于孔子称赞曾子“其习知音”,笔者以为,这里知音之意一方面是对音乐的欣赏,更深刻的一方面则是将对音乐鉴赏上升至对作者心志、志趣的探究上。而这显然要比一般的对音乐的鉴赏要深刻得多。如果从文艺理论的语境来看,孔子此处所说的“知音”已隐含了现代文艺理论中“读者”的部分含义,而且,这个知音的读者还要将鉴赏的触角延伸到作者的文本中去,于是,这则故事中透出的知音之意就更为深刻了。与《韩诗外传》时间大致相同稍微偏后的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有载:“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1]382
自这段话中,已可看出“知音”从鉴赏音乐的行为这一本义,逐渐生发出的引申义,即“能够鉴赏音乐”。高诱注称:“师,乐师瞽也。出,犹作也。新曲,非匹乐也。李奇,古之名倡也。”庄逵古按云,“《太平御览》引许慎注云:李奇,赵之善乐者也。”据此,邯郸师即生活在邯郸的乐工、乐师之类,而李奇是赵国的名倡,著名音乐家或歌唱家。这里特指听音乐的人,要根据自身的素质来追寻音乐家的本意而不可人云亦云。可见,“知音”的内涵在此时已又加深一层,不仅强调要领会作者,而且还当有自己的鉴赏标准,于是,对读者这一角色的重视开始萌芽,而知音所具备的文艺理论特质也在此时逐见端倪。
在东汉,对“知音能够鉴赏音乐”之意的解释也同样有文献史料支撑。如桓谭在其《新论·琴道》中,也通过“知音”表达了特殊的含义。成少伯工吹竽,见安昌侯张子夏鼓琴,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为知音。[2]67
由于《新论》原书早已经散佚了,这句话是从《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一中辑佚出来的,但看这句话,只能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即“知音”就是对音乐的欣赏,而且,要想避免“不足为知音”,还应多通曲目,有了大量鉴赏的经验,才能达到“知音”的地步。如果说这又从积累鉴赏经验的角度来补充了“知音”的内涵,那么,细细考察《琴道》这一篇,就能从这些已经散佚、复又辑佚的短简残篇中找到更为深刻的含义。仅存的《琴道》中,桓谭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卫灵公,一个是孟尝君,两个故事虽然不同,但桓谭却都在故事最后提到了相似的主题:亡国之音。可见,桓谭写《琴道》,对音乐的鉴赏并不是为了陶冶情操、改善精神生活,而是避免亡国之音。于是,“知音”的内涵也就因而更加丰富了。
综上所述,“知音”的内涵在汉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掘,其含义有三:一是,赏鉴音乐,此乃其本意,笔者以为,后世所有与其相关的文化与理论都是从欣赏音乐这层意思延伸开来的;二是,对音乐的鉴赏也像对《诗经》的诵读一样,也都有着“亡国之音”的意蕴,意即从艺术中观照政治的变化;三是,汉代文献中的“知音”已从对音乐的欣赏,过渡到对作者心志的探讨,以及对读者欣赏标准的要求,比单纯的鉴赏音乐更进一层。
第三,富含文学艺术内蕴的六朝知音文化的成型。
笔者以为,汉代知音之意中所涵盖的对读者和作者作用的递进及政治观照,并不是站在文艺理论的角度,也不是以文艺的立场来说的,而是源于汉代经学对文艺的政治性提升。毕竟汉一代,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没有走向自觉,所以,“知音”的内涵固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掘,但其在深度和广度上仍显不足,尤其是未能直接对文艺产生深刻的影响。据中古文艺批评史料可知,直到六朝时期,“知音”才逐渐真正成为富含文艺内蕴的文学理论术语。
这可以从曹丕著名的《与吴质书》说起:“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昔伯牙绝弦于锺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诸子但为未及古人,亦一时之隽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后生可畏,来者难诬,恐吾与足下不及见也。”这里也提到了“知音”,但其与汉代论及“知音”已存在明显不同,具体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这里的“知音”已经与音乐没有了直接关系,而是直接描述文学创作和鉴赏上的知己知彼。可见,在此时“知音”正在从单一的音乐领域逐渐扩大到文学领域。从修辞学的意义来看,也许这只是“知音”一词的扩大性使用,是引申义的扩展。但是,如果放大到文艺理论的领域,则这个细微的修辞变化带来的却是鉴赏理论从个别领域到共性领域的扩展。
二是,曹丕用“痛知音之难遇”来描述“知音”的难得,确定了“知音”清晰的境遇:知音难遇,而这恰恰成为后来《文心雕龙?知音篇》中“知音其难哉”的先声。可以说,“知音难遇”是“知音”这个名词的特殊气质。从先秦“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寓言,再到“知音其难”的经典论断,曹丕的《与吴质书》显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这显然也得益于六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涌动的众多人文思潮的影响和浸润。
综上所述,正是有了从先秦到六朝对“知音”一词内蕴的不断开掘,才逐步达成《文心雕龙》对“知音”的经典论证。《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刘勰首先指出了知音的苦难,包括诸多原因,有的因为贵古贱今,有的因为文人相轻,有的因为学力不足,有的因为泛滥无归。随后,刘勰分析了这些造成“知音其难”的原因,并指出如何才能正确鉴赏,成为合格的“知音”,这又包括了六观,意即观位体、观置辞、观通变、观奇正、观事义和观宫商。可以说,知音体系发展到南朝刘勰的知音篇时期,就已然蔚为大观,内蕴丰富了,而这恰恰是知音从对音乐鉴赏向完整的文艺理论乃至文化体系演变的充分表征。
简而言之,两汉时代的封建统治者将文学与政治相联系,忽略了其中的生命精神与人生体验,而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则建构在人生感受与体验的基础之上,使中国古代文学艺术赖以生成与激活的生命精神得以解放,同时将先秦两汉儒学的精粹得以传承与光大,直接促成了文学事业的自觉,以及文学批评的发展,这为《文心雕龙》特别是《知音》篇的成书作了充分准备。笔者以为,魏晋南北朝可谓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受到时代刺激的文学批评,将士人生命活动与审美精神融为一体。而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的生成,不仅是思辨的结果,更多体现的是生命精神和人生体验的升华,其中无不凸显出中国古代文化中人生与艺术相统一的传统。
二、六朝知音文化的逻辑内涵
六朝,《辞海》(缩印本)第421页解释为:“历史时期名。三国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康(吴时称建业,江苏南京)为首都。合称六朝。”六朝是一个文化交汇、思想融合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是我国政治、经济史上,同时也是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一直被学术界视为“人的觉醒”的思想解放期,也被视为“文的自觉”的重要时期。部分学者以为,六朝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文论自觉”的重要时期。而知音文化作为中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六朝。如此,就注定了知音文化在形成中必然与当时不断涌动的人文思潮交互杂糅并相互影响。笔者以为,这三种自觉应当是六朝知音文化潜在的逻辑内涵,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学创作之变所呈现出的文学自觉的萌芽与发展是六朝知音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
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3]382。鲁迅先生这样说是有理由的,我们评价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主要有四个标志,简言之,即一是要将文笔分开,即文学和经学是不同的,目的也不完全是服务于政治的;二是文学能成之为文学,是因为文学之下必须要有门类,如诗歌、抒情赋等,也就是文体意识的形成;三是文学的价值要独立于社会正义、政治正义等,要有独特的价值,也就是审美价值;四是有一批专门独立从事文学创作的个体乃至群体。
笔者以为,就文学创作而言,东汉班固等人的抒情赋是文学的自觉性开始萌发的标志,而自魏晋开始,文学的自觉性才终于走向前台。值得强调的是,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可谓贯穿整个六朝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呈现出题材多样化、文学独立化、价值审美化与作者个人化的倾向。而这种文学自觉性的发展,显然令“知音”这一理论概念在文学创作上具有了丰富的内涵。
具体而言,整个六朝时期文学创作之变大体有曹魏时期的“建安风骨”至“正始之音”的转变,有西晋“太康诗风”至东晋玄言诗的发展,更有南朝山水诗的勃兴。如果从这批诗人的创作方式上看,则会发现,建安风骨的代表诗人“三曹”和“七子”并世而出,以及正始之音的代表阮籍与嵇康,两晋和南北朝文体或诗风的开创者与代表等等,他们都是以群体的面貌出现的,尽管这种群体可能尚显松散,却亦可凸现他们之间较为一致的处世态度和创作风格,换言之,六朝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演进既反映了文人们对知音或隐或现的期许与渴求,更表露出潜在于他们之间的对知音文化的共同夙求。
第二,文学批评的发生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凸显是六朝知音文化的又一内涵。
在中古文学批评史中,六朝可谓文学批评发展的“青年期”,在这个思想大变革、社会大动荡的几百年间,儒家、道家、玄学、佛教都对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动力,使得文学批评终于得以独立,而知音文化也因此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深刻的文艺内涵。
一方面,随着六朝之时文学自觉的出现,文学批评逐渐独立,文人需要用各种富有稳定内涵的文学批评术语来进行鉴赏批评。虽然这些术语并没有像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术语那样语义清晰、富有逻辑,但在当时的文人笔下已具有了相当稳定的内涵。比如,曹丕著名的“文气说”中的“气”的概念,陆机在《文赋》中开创的“缘情”说对“文”和“笔”的区分,钟嵘《诗品》中对“滋味”的描述,直到刘勰《文心雕龙》中提出的包括“知音”在内的几十个现在已成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的术语,等等,这些无不折射出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
另一方面,六朝文学批评的发展又与文人之间品鉴的盛行密切相关。简而言之,这种逻辑是因为文人的本文意识形成后,他们之间会对彼此进行道德、生活、行为方式等多方面的品鉴,而这种对人物的品鉴会逐步发展到对作品的鉴赏,然,品鉴人物和鉴赏作品的相互交织正是文学批评逐步成熟的具体体现。前文提及的知音内涵在六朝时期拓展为成熟的文学批评术语便在此得以证实,蕴藏于其中且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知音文化也就在这一过程中走向成熟。
第三,文人交往方式之变所蕴含的人的觉醒与自觉是六朝知音文化的重要内涵。
文人交往方式的变化,其本质表现即人的变化,而在六朝时期则主要以士人的变化为核心。比如,由西汉人的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到东汉人的循规蹈矩、珍惜名节的变化;从汉朝人的重视儒家、渴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到六朝人的自由洒脱、奢侈糜烂的变化,等等。
具体到六朝时期,魏晋和南朝的文人交往方式也有着根本的转变。曹魏时期三国混战,反而人才辈出。除了“时势造英雄”的因素外,更是因为军阀集团之间的竞争,导致彼此都重视笼络人才,因而促使人物品藻的风气更加盛行,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中国人才品鉴的书《人物志》就诞生了,为六朝知音文化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完备的“才性论”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人物品藻与文学赏鉴的实践支撑。魏晋之后,作为知音文化主要内涵的人物评鉴以及文人士子的心态逐渐由对道德的评价转向对家世、血统的评价,如果有些士子试图突破这些桎梏,必然会遭到舆论的非议,因而出现“知音其难”的局面。当然,这里的“知音其难”只是对人物品鉴的描述,与文学批评还是两回事。但显然,人物评鉴上的“知音其难”也会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投射出自己的影子。
因此,六朝知音文化表现为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文人之间品鉴与评价之上的内涵就在这一时期的文人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的转变中得以继续深化,笔者以为,这种种转变无不透射出当时由士人性情和心态的变化所凸显的人们对于审美意识的追求以及对人性主体的深刻剖析和自我觉醒。
三、六朝知音文化的价值旨向
如前所述,知音文化萌芽于先秦、肇始于汉末、成形于六朝,潜行于历代文人及文论家们对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体认中,显在于丰富的文学创作和/或碎片、或体系化的古代诗文评说里,贯穿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我们以为,其形成虽得益于对文学批评鉴赏事实的阐释,却又决不应仅止于此,在中古人文精神发展的大背景下,六朝知音文化凸显出自身深挚的人文蕴涵和明确的价值旨向。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六朝知音文化是对中古经典阐释的独立评价。
六朝人文思潮中积淀下来许多经典文本,承载了古代流传下来的种种思想学说和人文智慧。而对这些经典文本的阐释和评价本身就是一种人生态度和哲学思考,代表着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六朝知音文化作为一种知音赏评体系,自然也担负着对这些经典文本的鉴赏、批评的评价任务。
笔者以为,六朝知音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六朝文人特立独行的个性与自由精神之上的,她主动摒弃了六朝人文思潮中偏重实用的思想,积极追求其中指向玄远的自觉品格。因此,六朝知音文化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和评价无疑也是独具特色的个性化阐释和独立性评价。六朝知音文化所赋予读者的这种独立评价的权利,既让六朝文人从汉儒经典文本的威权中解放出来,也使得六朝文人获得了挑战经典权威的阐释观念与方法路径,对六朝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匡乱救弊起到了革命性推进作用,也是六朝乃至中古人文思潮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二,六朝知音文化是对中古人文精神的自主选择。
由于知音本质上是在审美艺术层面对人文精神的选择性继承,从创作角度看,将人文精神的灌注文本藏之名山,并期待传之当时或后世知音君子是作者创作作品的根本动因;从作者的角度看,作者对“知音”的期待是以人文精神为标准的;从作品的角度看,只有符合人文精神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从读者的角度看,读者的最高要求就是成为作者的知音,而要成为知音,非得通过作品和作者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才行,而这种沟通又显然必须建立在人文精神的基础之上。
可见,六朝知音论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六朝人文思潮所赋予的以人文精神为鹄的的价值指向的选择性继承。从这种意义上讲,六朝知音论便是对六朝人文思潮中人文精神的自主选择。
笔者认为,六朝知音文化对六朝人文思潮中人文精神的敏锐甄别和自主选择,是通过感受、体验的方式,以审美激情和理性思考来实现的,其出发点在于文学本体,落脚点却在人生与艺术的审美指向,突破口在于人对自身目的、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深沉思考,而主旨则在于强调通过对现实的反思实现对人生的超越,这就必然开启六朝高扬人生价值与理想的审美境界,使之由现实存在升华到理想境界。这种境界的开启,本身即是对人文精神和人本价值的一以贯之,更是对六朝人文思潮的涤荡与提振。
第三,六朝知音文化是对人类主体意识的审美提升。
华美的诗文、精到的字辞往往更容易引起读者、论者在赏鉴、批评时的关注以致共鸣,从而也更易于由审美而生发出知音之感。而六朝知音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对六朝人文思潮中的文学风尚的审美化起到了重要的提升作用,极大地推进了六朝审美观的发展和成熟。因此,六朝知音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六朝审美观不断提升的过程。伴随着六朝知音文化的形成,六朝审美观则经历了从先秦的“功利”到魏晋的“尚美”,再到晋宋的“赏”的转向,这种转向处处展现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笔者以为,六朝知音文化表现出的主体自觉,首先是人的觉醒,六朝时出现了人的自觉、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张扬,当时的人们企求“不朽”,在感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永存,这是六朝主体性张扬和个体生命意识释放的表征,是六朝人摆脱功利主义目的、全面追寻人生意义、企求精神层面需求满足和追求审美价值的表现。
可见,六朝知音文化可以寻绎的发展、演化以及变迁之路既包孕着理论自身萌芽、发生、发展、成熟规律的内在理路,又浸润了当时政治、哲学、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人文思潮的外缘影响。然,六朝知音文化在其演绎与变迁历程中凸显出的人文蕴涵与价值旨向无不展现出其对中古人文精神的提升与超越,而这种提升与超越恰恰折射出中古文化空间的积极拓展。
四、结语
六朝知音文化的形成是六朝人文思潮涌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凸显出六朝知音文化在思潮与理论二者关系中的深刻的理论内涵和人文意蕴。
事实上,六朝知音文化作为一种对中古文艺作品进行美学审视的一种理论方法和评价体系,已经用于并可以继续用于对文艺作品开展解读、鉴评等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更进一步讲,六朝知音文化可以作为人们站在美学角度审视包含文艺在内的六朝人文思潮全部内涵的一种参照依据、评价体系。而且,当六朝知音文化呈现于历代文人和文论家眼前时,其基于人的觉醒、文的自觉、文论自觉的前提下所生发出的人本主义的主体自觉,便在对作家作品的知音赏评过程中,以一种审美自觉的评价的形式反作用于六朝人文思潮,既成为对六朝人文思潮内涵总结性的充实与梳理,也成为对隐藏于六朝人文思潮中的中国古代传统人文精神的选择性突显和提升,并表现为对人类的双重关怀,即对人类生存现状的现实关怀和人类精神心灵的终极关怀。
[1]刘安:《淮南子》,载《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版。
[2]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而已集》,载《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Analysis Humanistic Spirit of Ancient China——Discussion from Deduction on Zhiyin Culture of Six Dynasties
YANG Ming-gang
(College of sinology,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
Zhiyin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rt.It was unique thought culture system in Chinese nation spirit world.It started from Six dynasties,and the humanistic thoughts of Six dynasties formed its thought foundation.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origin and root of Zhiyin culture,explain its logic connotation,and thoroughly analyses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Zhiyin Culture of Six Dynasties and theirpositive ro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pace,as well as on the improve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ancient China.
six dynasties;zhiyin culture;cultural space;humanistic spirit
G03
A
1671-7023(2011)06-0028-07
杨明刚(1976-),男,湖北襄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
2011-06-02
责任编辑吴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