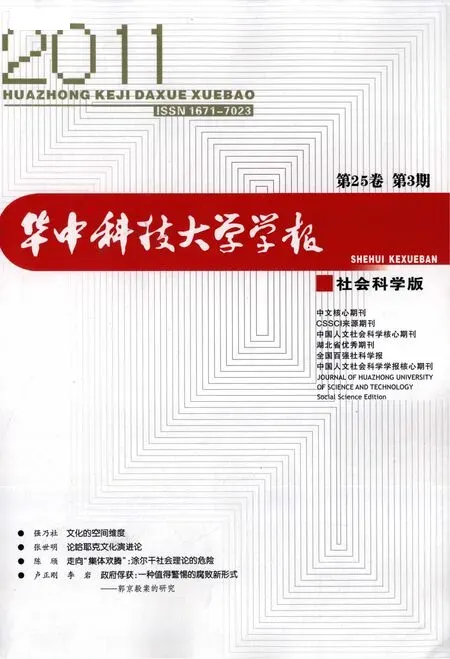阿奎那的身体哲学及其意义——评白虹《阿奎那人学思想研究》
段德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
阿奎那的身体哲学及其意义
——评白虹《阿奎那人学思想研究》
段德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
希腊文θαυμáζω有两个基本意思,其中一个为“诧异”,而另一个为“惊奇”。这两个涵义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对于思想发生学和思想生成论来说都意义重大。说它们相互关联,乃是因为离开了“诧异”活动,令人“惊奇”的思想成果就难以产生出来,而“奇”之所以为“奇”,其实也正在于其“异”。柏拉图哲学的诞生,可以说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令人“惊奇”的事件,以至于过程哲学家怀特海发出这样的感叹:“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脚而已。”[1]84然而,柏拉图的这样一种令人惊奇的哲学的问世显然是得益于他的“诧异”活动的。柏拉图的“哲学始自诧异”这一闪烁千古的名言所道出的正是他的这块哲学诞生地的秘密[2]5。
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在其削弱了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现在摆在作者面前的白虹博士的《阿奎那人学思想研究》也是一部既令人诧异也令人惊奇的著作。这部著作之所以令人诧异,乃是因为它对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按照流行的观点,特别是按照《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家》的作者A·弗里曼特勒的意见,中世纪是一个典型的信仰时代或宗教神学时代,一个“黑暗时代”[3]211,然而,作为中世纪哲学和神学主要代表人物的托马斯·阿奎那却竟然是一位对西方人学作出卓越贡献的思想家,这怎么会不让人感到诧异呢?这部著作之所以令人惊奇,乃是因为它对阿奎那人学思想的肯定性评价竟然稳定地令人信服地奠基于他自己的《神学大全》及其他重要著作的文本之上。
那么,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及其他重要著作的文本中究竟内蕴着一种什么样的令人惊奇的人学成就呢?
阿奎那的人学思想尽管内容极其丰富,但是集中到一点,可以说就在于他对其身体哲学的认真强调和系统论证。阿奎那对其身体哲学的强调和论证可以说主要是围绕着人的整全性或合成性以及人的个体性这样两个层面展开的。我们知道,虽然人的问题一向受到哲学家们的关注,虽然早在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就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口号,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至少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们所理解的人都只是一种“单向度”的人,一种剥离了“身体”的人。如所周知,泰勒斯作为西方哲学的第一人,其基本的哲学命题为“水是万物的始基”。然而,水何以能够成为万物的始基呢?乃是因为水具有一种被称作“湿气”的特殊的力量。而这种被称作“湿气”的特殊力量,在泰勒斯看来,不是别的,正是“灵魂”。因此,泰勒斯的“水论”说到底是一种“魂论”。至古典时期,虽然普罗塔哥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口号,但是,对人的单向度的理解的状况却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观。就普罗塔哥拉而言,他所说的作为万物尺度的人,归根到底,是一种感觉的人或人的感觉,是作为人的灵魂的低级能力的感觉或感觉活动。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并不是要人们认识自己的身体,而是要人们认识自己的灵魂,以便“照顾好自己的灵魂”,使之“由此界迁居彼界”[4]78。因此,尽管西塞罗曾经称赞苏格拉底,说“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5]43,但是,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说,苏格拉底之所以将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上,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使人的灵魂从地上升到天上。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更是明确地将人定义为“使用身体的灵魂”(anima utens corpore)①柏拉图:《斐多篇》,79C。。人的灵魂的神圣性质及其要素(理性、意志和欲望)在理性基础上的统一不仅构成了柏拉图理念论和回忆说的基础和前提,而且也构成了柏拉图的道德伦理学说、社会学说、政治学说、宇宙论或宇宙和谐说的基础和前提。“拟灵魂(人的灵魂)化,是柏拉图哲学的真正秘密”[6]序3。由此看来,古希腊时代的所谓人学其实不过是一种“魂学”而已。但是,这种状况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及其他重要著作中却得到了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纠正。按照阿奎那的观点,古希腊哲学家所讲的并不是实存的或现实的“人”(homo),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逻辑意义上的“人性”(humanitas)。针对古希腊哲学家的“灵魂是人”(anima est homo)的“魂学”,阿奎那强调说:实存的或现实的人“不单单是灵魂,而是某种由灵魂和身体组合而成的事物”(homo non est anima tantum,sed aliquid compositum ex anima et corpore)②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I,Q.75,a.4.。在阿奎那看来,如果说人之区别于其他物质实体的地方在于他之具有理性灵魂,而人之区别于天使的地方却正在于人之具有身体。因此,人之为人的特殊规定性正在于他不仅具有灵魂而且还具有身体,正在于他是一种由灵魂(理性灵魂)和身体组合而成的东西;那种没有身体的受造物是断然不可以被称作人的。阿奎那不仅批判了柏拉图的“魂论”,而且还进而系统深入地批判了德谟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的“灵魂形体”说、奥利金和奥古斯丁的“灵魂实体”说以及波那文都的“灵魂具有精神质料”说,比较令人信服地表明人的灵魂与人的身体的结合是一种本质性或实体性的结合,从而对人的合成性和全整性作出了相当充分的解说和论证。强调人的合成性和全整性是阿奎那人学思想中最为根本也最为重要的思想,他的全部人学思想可以说都是以此为基础和前提的。
阿奎那对人的身体在人的实存结构或本质结构中的地位的突出或强调不仅构成了他的人的全整性或合成性思想的关键性内容,而且还构成了他的人的个体性思想的决定性前提。古希腊哲学家既然恪守理性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既然恪守他们的“人即灵魂”的“魂论”,既然恪守他们的“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样一个人学公式,则他们所说的人也就势必因此而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学意义上的“类”概念,从而个体的人如果有什么实存性的话,充其量也不过是那种具有“副现象”意义的东西。然而,在阿奎那看来,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作为“理性动物”的人与其说是一种人,毋宁说是一个由“理性”概念和“动物性”概念组合而成的“第三个概念”。不仅“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不足以表达实存的或现实的人,而且即使“人是由灵魂和身体组合而成”这样的说法也不足以充分表达人的实存性或现实性。因为实存的或现实的人既不是由作为“类”概念的人的灵魂构成的,也不是由作为“类”概念的人的身体构成的,甚至也不是由作为“类”概念的人的灵魂和作为“类”概念的人的身体组合而成的,而是由被个体化了的人的灵魂与被个体化了的人的身体构成的。也就是说,在阿奎那这里,人的灵魂不再是古希腊哲学家的那种作为“公共形式”的“统一”的“不可区分”的一般灵魂①Cf.Aristotle,Metaphysics,1033b20.,而是那种作为“个体化形式”(formae individuantur)的灵魂;而人的身体也不是由“绝对的骨和肉”(os et caro absolute)组合而成的一般形体,而是由“这根骨头和这块肌肉”(hoc os et haec caro)组合而成的这个形体②Thomas Aquinas,“De Ente et Essentia”,2.。从而,实存的或现实的人也就是由“这个灵魂”(haec anima)和“这个身体”(hoc corpore)组合而成的“这个人”(hic homo),而不是像古希腊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由“一般灵魂”和“一般身体”组合而成的作为人之为人的“人”(humannitas)。换言之,在阿奎那的人学词典中,惟有具体的个体的“这个人”或“那个人”才是实存的或现实的人,才具有“本体”(hypostasis)和“位格”(persona)的意义。阿奎那的人的个体性思想还有更为深邃的一面,这就是人的身体何以能够成为“这个身体”,人的灵魂何以能够成为“这个灵魂”,从而人何以能够成为“这个人”的问题。要理解这个问题或问题的这一层面,我们就必须对阿奎那的质料学说作出深层次的考察。按照阿奎那的质料类型学,质料可被区分为三种类型,这就是“原初质料”(materia prima)、“泛指质料”(materia non signata)和“特指质料”(materia signata)。其中,原初质料和泛指质料只不过是一种逻辑概念,唯独特指质料才是一种实存概念,一种构成“个体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的东西[7]。这就是说,人的身体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身体”,人的灵魂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灵魂”,以及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人”都是由特指质料构成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决定的和促成的③Cf.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I,Q.75,a.4.Also cf.Thomas Aquinas,“De Ente et Essentia”,2.。只有当我们对作为个体化原则的“特指质料”或由“特指质料”构成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构成功能或生成功能有了真切的理解和把握,我们才有望对阿奎那的身体哲学以及以之为基础的人学有一种具体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不仅在人的实体性构成或本质构成方面极具创意,而且在人的存在性构成或生成性构成方面也极具创意,这一点无论在阿奎那的认识论还是在阿奎那的欲望论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例如,在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能力的理解和阐释方面,相对于前此的古希腊哲学家和教父哲学家以及早期经院哲学家,阿奎那的理解和阐释可谓别具一格。如所周知,在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那里,感觉和感性认识或者是一种完全负面的东西(例如在巴门尼德那里),或者是一种仅仅具有外在的或提示性功能的东西,或者是一种仅仅具有局部意义的东西(例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相形之下,教父哲学家和早期经院哲学家虽然较为重视感觉和感性认识,但是,既然他们普遍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感觉和感性认识也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奥古斯丁虽然把“知识”(cogitare)理解为“集合”(cogere),理解为心灵对感觉材料的“抽象”或“综合”,但是,既然他主张“光照论”,把“知识”理解为“理智所擅有的,专指内心的集合工作”[8]196,则感觉或感性认识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早期经院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安瑟尔谟虽然在“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之外另提出过“上帝存在的后天证明”,虽然在他的“后天证明”中也论及感觉,但是,构成其“后天证明”理论基础的却是柏拉图的理念论[9]237-238。但是,与先前哲学家和神学家们片面地强调理智的能动作用不同,阿奎那鲜明地强调了理智的被动性,强调理智首先是一种“被动能力”(potentia passiva),一种须藉感觉或感性认识活动方可以由潜在转化为现实的能力①Cf.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I,Q.79,a.2.。既然如此,则感觉或感性认识活动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也就永远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了。然而,倘若离开了人的肉体器官(感觉器官),离开了人的身体,也就从根本上无所谓感觉或认识活动了,这样,人的身体问题自然也就成了阿奎那认识论的一项必须预设的先行存在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奎那强调说:既然“感觉活动如果离开了有形工具是不可能实现出来的”,则“理智灵魂就不能不同一个胜任成为便利感觉器官的形体(身体)结合在一起”。他甚至还因此而强调说:“在人当中,那些具有最好触觉的人所具有的理智也是最好的。”②Cf.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I,Q.76,a.5.
人的身体问题不仅构成了阿奎那认识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前提,而且也同样构成了阿奎那欲望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前提。在阿奎那看来,人的灵魂不仅具有认识能力,而且还具有欲望能力③Cf.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I,Q.80,a.1.。诚然,在阿奎那的著作里,欲望(appetitus)被区分成了两种,这就是感觉欲望(低级欲望)和理性欲望(高级欲望,即意志)。然而,无论是低级欲望还是高级欲望也都是与人的感觉活动和身体密切相关的。首先,就人的感觉欲望而言,感觉欲望既然为“感觉”欲望,它就不可能与人的身体毫无关联。阿奎那曾将感觉欲望称作一种“被动能力”,称作“受到推动的推动者”(movens motum)④Cf.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I,Q.80,a.2.,并将感觉欲望区分为“愤怒”(irascibilem)和“情欲”(concupiscibilem)⑤Cf.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I,Q.81,a.2.,所有这一切都有意无意地强调了感觉欲望与人的感觉活动和人的身体的关联性。而理性欲望虽然有别于感觉欲望,但是,它之与人的身体的感觉、感觉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关联也是存在的。因为按照阿奎那的说法,理性欲望或意志“必然地坚持最后的目的(ultimo fini),即幸福”⑥Cf.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I,Q.82,a.1.,既然“幸福是人类的至善,是其他目的都要服从的目的”[10]264,既然人类的至善和幸福不仅包含“灵魂的快乐”,而且还包含“身体的快乐”(delectationibus carnalibus),则我们就不能说理性欲望即意志与人类的感觉活动和人的身体的实践活动没有关系。更何况,在许多情况下,理性欲望无非是理性化了的感觉欲望;而欲望的实现,无论是感觉欲望的实现,还是理性欲望(意志)的实现,也都是离不开人的身体的实践活动的。
总之,只要我们耐着性子下功夫对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作一番考古学性质的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创新性,不难发现阿奎那人学思想对西方传统人学的多方面的超越,不难发现构成阿奎那人学思想硬核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他的身体哲学,不难发现阿奎那主要地就是藉着他的身体哲学实现其对西方传统人学的超越的(尽管这些东西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被掩埋在地下”受到遮蔽而不为世人所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阿奎那的身体哲学视作我们进入阿奎那人学幽深之处的秘密通道。
阿奎那的身体哲学不仅是我们进入阿奎那人学幽深之处的秘密通道,而且还是我们审视阿奎那人学思想深广影响和现时代意义的理论制高点。因为西方近代哲学,一如古希腊哲学,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种意识哲学或“思”的哲学,都是一种“肉身缺失”的哲学。这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公式中得到了范式性的体现。费尔巴哈曾经深刻地指出:“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11]169显然,费尔巴哈在这里所批评的“旧哲学”并不限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不限于笛卡尔所代表的西方近代哲学,而是将古希腊哲学也包括在内的。既然如此,我们在费尔巴哈的人学思想中,便不难发现阿奎那的身体哲学及其人学思想的投影的。然而,阿奎那身体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是深广的。我们在尼采的“我完完全全是身体”和“哲学就是医学或者生理学”的格言中[12]31,在梅洛·庞蒂的“我是走向世界的身体”的宣言中[13]109,在海德格尔的“此在”和“在世”的概念中,在萨特的“作为自为的存在的身体”的宣称中[14]400-440,都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阿奎那身体哲学及其人学的投影。长期以来,在我们对后意识哲学或后反思哲学的解释中,比较多地关注的是它们所强调的人的存在的个体性、实存性和在世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却是不够深刻的,殊不知它们所强调的人的存在的个体性、实存性和在世性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需要由其内蕴的身体哲学予以阐明的。
倘若我们从这样的理论高度来审视白虹博士的这部学术专著,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首先,白虹博士的这部学术专著比较充分地注意到了阿奎那的身体哲学及其在阿奎那整个人学思想中的基础性地位。作者在第六章的开始处曾经对“人的统一性”这个贯穿该著的中心概念作过相当集中相当中肯的说明。这就是:“我们认为,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色就是对人的统一性的强调,他通过在实体论中强调灵魂与身体的本质性结合,在认识论中突显感觉与理智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合作,以及在意志论中肯定欲望在人的自由抉择中对理性的服从,并且从理智与意志的相互作用来认识人的精神活动,从而从人的实体结构和人的存在活动构成两个方面肯定了人的统一性,这就将强调人的统一性这个基本特色贯穿于他的整个的人学思想之中。”(本书第286页)不难看出,他的这段话从字面上看,是在强调“人的统一性”,但是,倘若从整个西方人学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能看到,作者实际上是在强调身体哲学在阿奎那整个人学思想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这是因为,对于古希腊的“魂学”来说,对于那些将身体与灵魂“撅然二分”的西方传统人学来说,是根本谈不上阿奎那所强调和系统论证的“灵魂与身体的本质性结合”、“感觉与理智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的合作”以及“欲望与理智的统一”的,从而也就根本谈不上阿奎那所强调和系统论证的“人的统一性”的。作者在从实体论、认识论和欲望论对“人的统一性”作出具体论证之前,专门用一整章的篇幅来探究这种统一性的“形上学基础”,并且着重探究了阿奎那的本质特殊性学说和能指质料学说,这就进一步表明作者之强调身体哲学在阿奎那整个人学思想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写作意图。白虹博士的这部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在不少地方给人以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这样一种努力。
注重理论的层次性也是该著作的一个相当突出的优点。在该著中,作者不仅对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作出了多方面的考察,而且还对其作出了多层次的考察。可以说,本书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其内容的丰富性,而且还在于其内容的层次性或深刻性。如果说,从实体论、认识论和欲望论三个方面对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作出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论证,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就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了,那么,像该书作者这样,能够合理地将阿奎那人学思想的这三个方面放到不同的理论层次上予以考察,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就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了。然而,令人高兴的是,作者在他的这部处女作中却把自己对阿奎那人学思想的深层次理解相当精辟,甚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他的第三章“阿奎那人学之实体论:灵魂与身体之统一”讨论的是“人在实体结构层面上的统一性”,“也就是作为形式和质料的人的灵魂和身体的统一性”;他的第四章“阿奎那人学之认识论:感觉与理智之统一”和第五章“阿奎那人学之意志论:欲望与理性的统一”讨论的则是“人在存在结构层面上,也就是人的能力及其运作中的统一性问题”(本书第166页)。应该说,作者对阿奎那人学思想理论层次的区分和阐述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因为正是得益于作者的这样一种区分和阐述,我们不仅可望对阿奎那的人学思想有一种逻辑的静态的了解,而且还可望对之有一种动态的和生成性的了解不仅可望对阿奎那人学思想的诸多向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且还可望对构成阿奎那人学思想诸多向度之间的错综复杂的逻辑关系(如存在于其实体论和认识论与欲望论以及存在于其认识论与欲望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有一个简洁、明快的了解。
该著的第三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其不仅注重对阿奎那的人的实存性、合成性、个体性和生成性的分析和考察,而且还进一步从中引申出了人的在世性。应该说,人的在世性是阿奎那身体哲学中的应有之义。既然人不仅仅是一个精神性的灵魂,既然实存的人或现实的人是必定有身体的,则他就势必是在世的。作者明确地将“在世性”规定为“全整的人、个体的人的存在方式”,断言:“既然灵魂与身体结合在一起构成的人才是一个全整的人,灵魂存在于身体之中才合乎人的本性;既然人的理智活动必须借助于来自身体的心像,而且只有物质事物的本性才是人的理智的合适对象,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必定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见本书第299页)毫无疑问,作者对阿奎那人学思想中人的在世性观念的强调同样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因为这对于我们从身体哲学出发全面理解阿奎那的哲学与神学的超越性和世俗性及其关系是不无意义的。这一点即使对我们理解现代西方人学思想也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例如,许多学者将海德格尔的人学思想区分为前期海德格尔和后期海德格尔,断言前期海德格尔强调“此在”和“人道”,后期海德格尔则强调“存在”和“天、地、人、神”的“四方图”。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毕竟有其肤浅和武断之处。因为海德格尔既然强调“此在”,也就埋下了他此后强调“在世”、强调“天、地、人、我”“四方图”、强调“天命”的伏笔,因而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与其前期思想也就没有什么逻辑上的隔障或矛盾之处。
不仅注重从形而上学的高度来审视和阐释阿奎那的人学思想,而且也注重从基督宗教神学的角度来审视和阐释阿奎那的人学思想,是该著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例如,作者在许多场合都运用基督宗教的“肖像论”来论证和阐述阿奎那的“人的统一性”的思想(见本书第47—48、289—290页)。他的这种做法无疑使其对阿奎那的人的统一性的思想的论证获得了极强的说服力。既然在上帝那里,存在与本质、理性和意志、真善美等等都是“统一”的,则作为上帝“肖像”的人在形式(灵魂)和质料(身体)、感觉和理智、欲望和理性、理智和意志之间的“统一”也就是一种完全可能的事情了。而且,既然上帝也“道成肉身”,则人之具有“肉身”也就成了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了。阿奎那不仅是中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而且也是中世纪最为著名的神学家之一,他的哲学与他的神学原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此,作者的这样一种努力对于我们本真地理解阿奎那的人学思想无疑是有帮助的。
毋庸讳言,该著也在所难免地具有一些缺点或弱点。例如,该著对身体哲学在阿奎那人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的强调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对阿奎那人学思想在西方人学史的地位的刻画还有待进一步细化。但是,无论如何,瑕不掩瑜,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这已经可以说是一部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多所创新的学术专著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者为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辛劳的。这一点既与研究对象的难度有关,也与研究者的原初的知识结构有关。就研究对象来说,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不仅广泛涉及阿奎那的实体论、认识论和欲望论,乃至阿奎那的上帝论、创造论和天使论,而且还广泛涉及中世纪哲学、基督宗教神学、整个西方人学史和现代西方人学。没有很好的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和宗教学功底在这个话题上是很难有所成就的。不仅如此,由于至今我国对阿奎那的人学思想的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泛泛而论的阶段或层次,作者所开展的这样一种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和写作,便几乎没有什么中文资料可资借鉴,从而不得不直接阅读和研究大量外文资料(尽管他曾经认真地借鉴了笔者所翻译的《神学大全》的“论人”部分)。因此,作者这几年不知疲劳的学习和研究,奉献给我们的便不只是这样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而且还有他那一份对宗教哲学和宗教学的挚爱和献身精神。尽管他的这部著作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我国的阿奎那哲学的研究都是极其宝贵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的后一个方面也许更是弥足珍贵。因为他对宗教哲学和宗教学的挚爱和献身精神,不仅能够推动他本人在中世纪哲学和阿奎那哲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加重要的成就,而且作为一种学术人格和学术精神也将为激励和鼓舞我国的宗教哲学工作者和宗教学工作者为推进我国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学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挥其当有的作用。
[1]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陈修斋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2]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5D。也请参阅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A·弗里曼特勒:《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家》,程志民等译,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4]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5]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6]段德智:“《希腊思想》中文修订版序”,载罗斑:《希腊思想》,陈修斋译,段德智修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段德智、赵敦华:《试论阿奎那特指质料学说的变革性质及其神学意义——兼论 materia signata的中文翻译》,载《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4期。
[8]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0卷,第11章,第18节。参阅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9]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阿奎那:《〈伦理学〉注》第 1卷,第 14讲。Cf.Saint Thomas Aquinas:Philosophical Texts,ed.by T.Gilby,Oxford,1960.
[11]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振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12]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余鸿荣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3]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4]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责任编辑 吴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