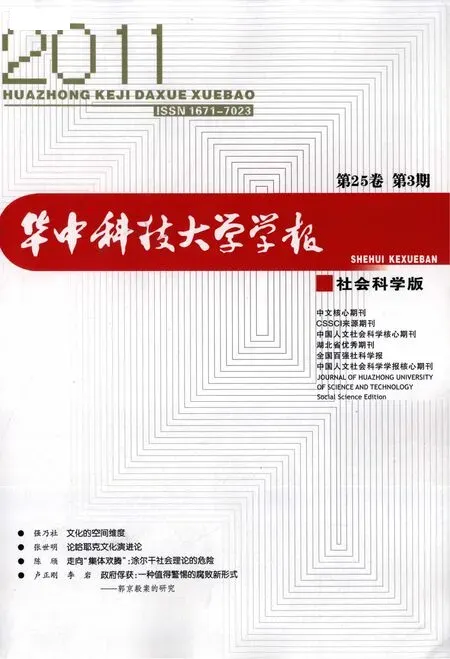在不平等中追求正义——儒家“礼治”的另一种解读
谢红星,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在不平等中追求正义
——儒家“礼治”的另一种解读
谢红星,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儒家“礼治”对平等、正义的理解与构想,可为解决当前中国平等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提供一种思路。儒家“礼治”精义一在于别,二在于仁,别指区分等级,仁指以他人为同类,推自爱之心以爱人。儒家认为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也是必要的存在,但不平等必须合理,不能过分,故儒家又“以仁和别”,意图将不平等控制在“仁”的范围内,也即,儒家认可合乎正义的不平等,但反对不正义的不平等。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对立问题的症由,不在于不平等太多,而在于不正义的不平等太多,儒家“以仁和别”的“礼治”构想,可为解决此一问题提供思路。
礼治;别;仁;平等;正义
在两极分化的拉动下,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公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已接近底线。传统儒家“礼治”对平等、不平等、正义、不正义等价值的理解与构想,或可为解决当前中国平等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背离提供另一种思路。
一、“别”与“仁”:儒家“礼治”的精义
所谓“礼治”,指以礼整合社会,规范行为,安邦定国的一种治理范式。儒家关于“礼治”的构想,总起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1)礼是治理国家的最高规范,是相对于“政”和“刑”的“高级法”。《礼记》称,“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运),[1]“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丧服四制)[1],儒家认为礼因天地而生,顺人情而行,因而是永恒的、神圣的、最高的规范,一切具体的政令及刑罚都必须依礼而生,合乎礼义礼制,否则必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子路篇)[2]。(2)礼是全方位的治理规范。儒家认为,礼的治理功能是全方位的,从小的方面讲礼规范个人行为,如冠、婚、朝、聘、丧、祭、宾、乡、军等,个人行为必须依礼、守礼、合乎礼,做到“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篇)[2],从大的方面讲礼整合社会,经国家定社稷,正是因为礼的治理,社会各阶层各安其份,各得其所,秩序得以建立,国家长治久安,总之在儒家看来,“礼治”意味着礼对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乃至个人生活的全面介入,大至施政治民,小到个人的修身养性,都必须依礼进行,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即此意也(曲礼上)[1]。(3)礼的实施既以自律,也以强制,而贵在自律。儒家并不反对以刑罚为后盾推行礼制,在他们看来,礼禁恶于未萌,刑惩恶于已发,礼之所禁,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但儒家更重视通过从天子到庶民的自制、自律、自觉来推行礼,对于兴刀兵、动刀锯之类的暴力与刑罚,儒家存在本能的抵触,《论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就有道,何如?”,孔子的回答是“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篇)[2],儒家希望通过上位者的表率和示范,化育百姓,使百姓识礼、知礼、认同礼,进而自觉以礼克己、依礼行事,教化是推行礼制的主要手段,上位者尤其是君主的自制与表率则是推行礼制的关键,总之,儒家虽也能接受百姓在刑罚的威慑下免而无耻的现状,但教而化民、有耻且格才是其追求的境界。
儒家“礼治”的构想,已然明了,然其精义何在?或者说,儒家希望通过“礼治”,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目标?儒家向往的“礼治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对此必须从礼的起源讲起。一般认为,礼源于祭祀,《礼记》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运)[1],“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统)[1],可见,礼起初只是“事神致富”的祭祀仪式,这种“事神致富”的祭祀仪式,缘何能演变成调整社会方方面面的治理规范?或者说,它有何特质,以至能从祭祀仪式上升为治理规范?《礼记》中一段话可为此做最好注解:
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祭统)[1]。
原来祭祀不仅可事鬼神,还可由此定君臣之义、父子之伦、贵贱之等、亲疏之杀、夫妇之别、爵赏之施、政事之均、长幼之序、上下之际(礼记)[1],换言之,当礼还只是祭祀仪式的时候,它就含有明分使群的潜在功能,这正是礼后来发展成为全方位治理规范的内在特质。礼源于祭祀,重在十伦,儒家“礼治”第一重精义由此可见,那就是“别”。所谓“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区分不同人群,划分等级,明确秩序,正如《荀子》所称,“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3]。儒家对于“礼治”之“别”的论述极多,如: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曲礼上)[1]。
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经解)[1]。
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哀公问)[1]。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3]。
故“别”可谓儒家“礼治”的第一重精义,儒家构想的“礼治社会”,首先是一个有阶级、有等差的等级社会。
然而,儒家“礼治”的精义,并不局限于此,如果说“别”是礼自初民社会以来就有的意义,是“礼治”的应有之义,那么儒家讲“礼治”,尚有更高的追求,儒家之“礼治”,尚有更深的内涵。正如周公制礼将夏殷之礼改造成系统化、规范化的治理规范一样,孔子等人通过对礼的重新阐释,给夏商周的礼治注入了新的内涵,这一内涵就是“仁”。儒家重礼之“别”,但也重礼之“仁”,如孔子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篇)[2],又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篇)[2],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心,礼乐不过是“玉帛”、“钟鼓”之类的虚文而已。《礼记》也称,“礼也者,义之实也”,“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礼运)[1],“礼节者,仁之貌也”(儒行)[1],认为仁是礼之本,礼之魂。荀子论礼虽对礼之“别”有所偏重,但也并未否认“仁”为“礼”的另一面,其称,“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于人心者,皆礼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大略)[3]。可见,“仁”是儒家“礼治”的第二重精义。
儒家的“仁”指什么?梁启超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梁启超认为,“仁者何?以最粗浅之今语释之,则同情心而已”,“仁者人格之表征也”,“若世上只有一个人,则所谓‘人格’者决无从看出。人格者,以二人以上相互间之‘同类意识’而始表现者也。既而,则亦必二人以上交相依赖,然后人格始能完成”,“仁者,同类意识觉醒而已矣”[4]83-85。依梁启超所言,所谓“仁”,乃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其个体的不同于动物的生理特性,而在于其对他人态度及作为,若视他人为同类,则为仁,不以他人为同类,则为不仁。仁从消极的角度讲,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恕己之心恕人;仁从积极的角度讲,为“能近取譬”,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成己之心成人。梁启超对于儒家“仁”的阐述,可谓精到之至,萧公权也称,“孔子所谓仁,乃推自爱之心以爱人之谓”[5]57,其义与梁启超所解相同。
儒家以仁作为礼之新义,表明其虽认可等级差别,却不欲将这种差别绝对化,盖儒家认为,不同等级之间虽应有差别,但本质上纷属同类,均应视对方为同类,以恕己之心恕人,以成己之心成人,不能因为差别的存在而心怀不平,进而视对方为异类,或凌辱摧残之如草芥,或背反逆击之如寇仇。“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篇)[2],“和”并不是“平等”,而是“和而不同”,即在承认等级差别的前提下,各阶级共同遵守被赋予“仁”之新义的礼这一规范,实现贵贱之间和而敬、长幼之间和而亲、上下之间和而顺,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儒家“礼治”的目标正在于此。
总之,儒家“礼治”的精义一在于“别”,即明分使群,确立等级秩序;二在于“仁”,即视他人为同类,以恕己之心恕人,以成己之心成人。儒家希望通过兼具“别”与“仁”之意义的“礼”的治理,建立起贵贱、长幼、上下之间“和而不同”的“礼治”社会。
二、以“仁”和“别”:儒家“礼治”的正义之维
对儒家来说,不平等(别)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人与人之间必然会有差别,这种差别或基于生理,或基于出身,或基于身份,或基于社会分工,因为差别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权利有别,责任义务有别,儒家永远也不能理解,男人和女人怎么可能“平等”,君子和小人怎么可能“平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篇)[2],孔夫子讲这句话并非在歧视女子小人,而是说女子在生理结构、性格禀性方面不同于男子,小人在道德修养、为人处世上不同于君子,正因为这些不同,所以他们的权利、义务、责任必须不同于男子、君子,所以他们“难养”。孟子也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滕文公章句上)[6],“不齐”既是“物之情”,也是“人之情”,是故农夫与商贾有别,大人与小人有别,君子与野人有别,劳心者与劳力者有别,“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章句上)[6],如果非要比而同之,等而齐之,则无异于以夷变夏,必乱天下。
儒家进而认为,不平等对人类社会而言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孟子已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了不平等的必要性,荀子更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角度阐述其必要性,荀子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3]。
荀子此段话,与其说是在讲礼的起源,不如说是在讲礼之“别”的必要性。在特定时期社会可供分配的资源是相对不变的,而人的欲望本质上是无止境的,“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荣辱)[3],若从人之欲,则必争,必乱,必穷,所以必须结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做不同分配,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3],这种分配当然不是平均的,但对每个人来说却是合理的。荀子认为通过这种不平等但合理的分配,可以使“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最终达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的理想境界(荣辱)[3]。
总而言之,在儒家眼里,不平等并不是一种罪恶,它是必然、必要的一种存在,反之对于平等,儒家从来就不认为它可以实现,也不认为它有实现的必要。
然而,儒家虽认可不平等的存在,却坚决反对过分的、不合理的不平等。孔子说君臣有别,但也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篇)[2],并不认为君臣之间隔绝如天地、君主对臣子可随意支配,对于以人为俑、残民虐民的统治者,孔子更是咒其“无后”。孟子虽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是“天下通义”,但对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极端不平等现象,孟子斥之为“率兽而食人”(梁惠王章句上)[6],孟子虽认为统治者有以民力为台、圈地为囿的特殊待遇,但认为统治者应与民同之,与民同乐,不应禁民入内,独自为乐。儒家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认可,是以承认“人”的同类性为前提的,在儒家看来,长幼之间、男女之间、君子小人之间、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虽然年龄、性别、道德修养、身份、分工上有差别,但本质上都是“人”,是同类,因此,任何权利义务上的不平等都不能超出同类的范围,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应该是同类间的不平等,不应变成异类间的不平等,儒家反对过分的、不合理的不平等,就是因为这种不平等超出了同类的范围,使人与人之间隔绝如异类。
可见,儒家“礼治”是以“仁”制“别”,以“仁”和“别”。儒家认可不平等的存在,同时为使这种不平等不走向极端,儒家又以“仁”和之。在“仁”调和下的不平等,是一种相对的、有限的不平等:(1)儒家虽将人划分为不同阶级,并认可各阶级权利义务之间的不平等,但各阶级成员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流动的、可变的。孔子虽重君子小人之别,但又认为“有教无类”(卫灵公篇)[2],孔子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篇)[2],可见其认为只要努力学习上进,小人也能上升为君子。孟子虽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滕文公章句上)[6],但也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章句下)[6]。荀子更明白宣称,“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3],可见儒家并不认为各阶级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儒家主张个人通过学习提升自我进而改变其社会地位及所处阶级,科举便是儒家此种主张的实践。(2)在“别”的精神下,儒家主张上层阶级应享有下层阶级不能享有的某些特权,但又认为,这些特权应该是公开的、明确的和受限的,孔孟诸贤虽未有暇论及此,但礼法合一、儒家化程度前所未有之深的唐律关于议请减赎的规定却反映出了儒家的此种主张。如八议,《唐律疏议·名例律》“八议”条称,“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7]17,这是规定八议的对象,《名例律》“八议者(议章)”条又称,“诸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议者,原情议罪,称定刑之律而不正决之。流罪以下,减一等。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7]36,这是规定“议”此种特权的适用内容及禁止适用情形,其余“皇太子妃(请章)”条对“请”的规定,“七品以上之官(减章)”条对“减”的规定,“应议请减(赎章)”条对“赎”的规定,无不遵循此种“适用对象—适用内容—禁止适用情形”的体例,议请减赎虽是贵族官员的法律特权,可依唐律规定,这些特权皆有其特定的适用对象、适用内容及禁止适用情形,并非上层阶级中的任何人都能享受,并非犯任何罪都能享受,即便能享受也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脱罪而不受法律制裁,可以说,唐律对议请减赎等特权的规定是公开、明确而具体的,这种规定保障了特权,但也未尝不可视为是限制了特权,这种公开、明确、受限的特权,正是儒家的主张。(3)儒家虽主张将特权赋予特定人群,但特权的享有并非无代价,在享有特权的同时,特权的享有者须承担起不享有特权的一般人不须承担的特殊责任。仍以唐律为例,依唐律,官员享有庇荫家属的特权,但同时,官员若有家人仗其官势收受贿赂,官员本人也须负连带责任,《唐律疏议·职制律》“监临之官家人乞借”条规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7]247。又如,依礼,娶妻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卑幼娶妻,既须尊长同意,也须尊长主婚,这是尊长对卑幼在婚姻成立上的特权,但这种特权也伴随着主婚不当的特殊责任,《唐律疏议·户婚律》“嫁娶违律”条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本条称以奸论者,各从本法,至死者减一等。若期亲尊长主婚者,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其男女被逼,若男女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7]296。儒家认为没有无责任的特权,而这正是以“仁”和“别”的体现。
作为法律价值的正义,首先指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社会结构的正义又包括利益及负担分配方面的正义和争端解决方面的正义,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分配正义是首要的正义,它意指各得其分,各得其所,如果从这一层意义上来理解正义,儒家“礼治”显然是合乎正义的:儒家认可不平等,但正义从来就不意味着平等,它指的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而不是相等的部分;儒家反对过分的不平等,因为过分的不平等违背了儒家所理解的正义——仁;儒家以“仁”和“别”,意图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平等控制在正义许可的范围内。总之,儒家认可的不平等,是合乎正义原则的不平等。因为“仁”的存在,儒家“礼治”闪耀着正义的光辉①当然,儒家所理解正义的具体内涵,未必同于现代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正义,不同场合有不同内容的正义,不同历史条件产生不一样的正义观,以现今价值观视之,儒家“礼治”及“礼治”之“仁”,皆有其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只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不宜过分夸大。关于儒家“礼治”及“礼治”之“仁”的局限性,学界论述已多,本文不再赘述。。
三、从虚幻的平等到可视的正义:儒家“礼治”的现代意义
千年来,平等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均贫富”到“平均地权”,人类对平等的追求可谓锲而不舍,然而,经过无数次失败的实验,平等已被证明只是一种幻象,人类永远触摸不到的一种幻象。
从概念上讲,平等有三重含义,形式平等、实质平等与结果平等,结果平等实为平均主义,在理论上已被判死刑;形式平等指机会均等,强调人人均应有参与竞争的机会,对于人的个体差异及与此相关联的过程及结果是否平等在所不问;实质平等指起点的平等及过程平等,重视人的个体差异,主张以合理的差别对待弥补弱势群体的先天不足,以促成每个人在竞争中的起点平等与过程平等。在结果平等被宣判死刑之后,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已是平等概念的剩余选择,学界论平等,或指形式平等,或指实质平等。然而无论是形式平等还是实质平等,在理论上均有难以克服的缺陷:形式平等过于抽象,如果说平等只是机会平等,完全毋论人在生理、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那它只会造就不平等,这样的平等又有什么意义?实质平等则近于空谈,人的个体差异各不相类,要实现实质平等,首先须辨明哪些差异必须弥补及可以弥补,然后选择合乎比例原则的差别对待,在弱势群体经特殊照顾获得了与一般群体同样的起点之后,这种差别对待又必须停止,以上诸环节只要有一个出问题,实质平等就是在造就不平等,成为新的不平等之源。
事实上,现实中人们希冀的平等,既不是虚无缥缈的形式平等,也不是可望而不可求的实质平等,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果平等。人的思维是功利化的,又是直接的,当他们看到贫富差距时,他们很少去思考贫富差距背后的复杂原因及这种差距正义与否,他们只会感受到贫富差距的存在,进而产生均贫富的欲求,对他们来说,结果不平等便是最大的不平等,结果平等才是平等,这种平等的欲求,与其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不如说是情绪宣泄的产物。于是,平等成为妒忌心的伪装,成为破坏的借口,最终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
总之,人类追求平等的历史证明,平等是虚幻的,也是无意义的②笔者如此表达,并不是主张公开的不平等和特权,只是认为差别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无须刻意张扬,也无须耗费心思抹平之(也不可能被抹平),关键是这种差别必须符合正义原则,所以,与其做抹平差别的无用功,不如想想如何使这种差别更合理、更符合正义原则,基于这一层意义,笔者才会说“平等是虚幻的,正义才是可视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是这样,“人生而平等”已被证明是谎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过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宣教,明知不可求而求之,只会制造普遍的虚伪、妒忌和不信任,积累破坏社会的力量,因此,与其追求虚幻的平等,不如追求正义,正如儒家所主张的那样,接受符合正义原则的不平等,唾弃不符合正义原则的不平等,虽然具体场合的正义仍须具体论证,但相比起平等,它仍然是可视的。而现阶段中国的问题,也不在于不平等太多,而在于不正义的不平等太多①当然,正义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内容,所以笔者说“具体场合的正义仍须具体论证”,而对于什么是正义的不平等、什么是不正义的不平等,也须结合实际具体分析。基于宪法至上和法治原则,中国现阶段不正义的不平等首先指抵触宪法及法律基本规定的不平等,这种不正义的不平等在现实中表现为各式各样的“歧视”。。人们或许能接受富二代开跑车、泡美女、上贵族学校,但如何能接受他们高考加分、飙车撞人轻判?人们或许能认可领导官员公车出行、公款考察的特殊待遇,但如何能认可他们出事先跑的特权?一方面是高喊平等,另一方面却是制造越来越多不正义的不平等,人们对平等的信心早已全无,人们对正义的信心也在逐步消失。因此,现阶段中国要做的,不是做无用的平等宣教,而是建立一种正义的社会结构,将不平等控制在正义原则的范围内,正如儒家“礼治”所主张的那样,以“仁”和“别”,认可正义的不平等,禁止不正义的不平等,在平等成为幻象之后,让人人都能看到清晰可见的正义。
结语
平等是虚幻的,正义才是可视的,可以有不平等,但不能有不正义的不平等,儒家“礼治”的实质即在于此,儒家“礼治”对当今中国的启示也在于此。
[1]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3]杨天宇:《礼记·祭统》,载《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张觉:《荀子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
[4]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杨伯峻:《唐律疏议》,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To Pursue Justice in Inequality——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Rule by Ceremony”of Confucianism
XIE Hong-xing
(Law School,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Rule by ceremony”of the Confucianism advanced its theory of equality and justice,which is useful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divorcing between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equality.
Its essence lies in two respects——inequality and benevolence,the former means grades,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treating and loving others as the same as oneself.In Confucianists’opinion,inequality is inevitable and essential to human,but it must be controlled to some proper extent.In other words,Confucianists admitted a just inequality,but opposed an unjust inequality.The problem of polarization in China implies too much unjust inequality instead of inequality.Therefore,“rule by ceremony”of Confucianism is likely to provide 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problem resolution.
rule by ceremony;inequality;benevolence;equality;justice
谢红星(1978-),男,江西于都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
2010-10-30
B82-052
A
1671-7023(2011)03-0028-06
责任编辑 吴兰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