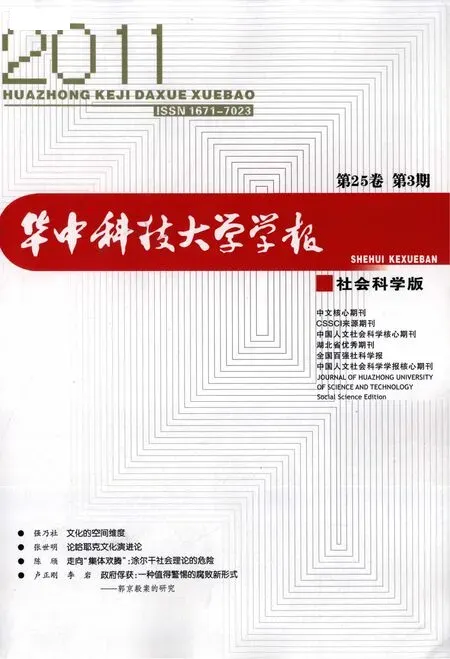谁之“文化”与何种“现代化”——立足“社会思潮”的视野对“文化现代化”研究所作的审视
李武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谁之“文化”与何种“现代化”
——立足“社会思潮”的视野对“文化现代化”研究所作的审视
李武装,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文化现代化”研究在理论层面上遭遇的诸多困惑与迷茫,事实上常常与“社会思潮”揭橥的论断及其引发的争论相关联。新自由主义思潮激活的“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争,无论从学术层面还是现实进路来看,都应该在辩证理解中得以有限展开。后殖民话语恰好适切了“地方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的现代化进路,对于文化现代化研究自当具有理论廓清和实践澄明功效。中国文化复兴乃至民族复兴直接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成功地实现现代化转型相关涉。某种意义上,东方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要比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激进和顽固得多。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研究进路,必须正视世界多元文化共存与新的“轴心时代”渐次发育之“捆绑式”历史真实与趋向。
社会思潮;文化现代化;实践创制
“社会思潮”研究是现当代学术的一个重要向度。有学者从中国“社会思潮”演进的角度解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1];或者反之,依据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资源,梳理归档中国整个20世纪以来的“社会思潮”。与之相应,学界以“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为旨趣的种种努力,不严格地说,也可以归划为“社会思潮”研究的畛域。也有学者“立足‘思想史’的视野对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做的审视”[2][3]。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更是有不少学人将其理解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精华”。可以佐证的是,德里达曾在上海发表的观点:“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
“文化现代化”研究在理论层面上遭遇的诸多困惑与迷茫,事实上常常与“社会思潮”揭橥的论断及其引发的争论相关联。因此,透视“文化现代化”之真谛与推进“文化现代化”之进程,除了加强“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理论研究之外,特别需要加强与之强相关的“社会思潮”的辨识和洞观。并通过对各“社会思潮”的比较研究,“通观”文化现代化内在机制的堂奥,进一步廓清文化现代化认识上的迷雾,寻驿文化现代化实践上的有效创制。如是,本文立足于“社会思潮”的视野来审视“文化现代化”研究中的理论困惑及可能的出路,以求对后者有所启示和帮助。需要指出的是,拙文截选的主要是在现时代影响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后殖民话语”,希冀挂一漏万、抛砖引玉式地资政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谁之“文化”拷问的逻辑生成
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翻版。所谓的“新”,主要是指凯恩斯主义的植入与改造,从而区别于古典“纯粹”的自由主义。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地基,主张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力挺国家与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弊端,在价值观上竭力彰显个人主义等。
毋庸讳言,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新自由主义,其所彰显和开拔的“普遍价值”或“同质性”文化价值资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而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色彩。即,新自由主义把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推向全球,旨在开显“文化霸权主义”。其最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最变相的观点就是上海大学朱学勤的“天谴论”。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不要说第三世界的人们,就是西方一些学者也看得很清楚。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和美国教授罗依克·瓦岗一致认为,美国在把反映本国社会结构的感知范畴强加于其它各国,力图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殖民征服。这只能导致一切看华盛顿的脸色行事。由此,市场成了“自由”、“开放”、“灵活”的同义语,而国家则变为“强制”、“封闭”、“死板“等的代名词。著名学者阿尔贝深有感触地说:新自由主义“等于硬要推销一种剧毒药品,而又不准备可以纠偏的解毒药品”[4]186-187。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指出:“西方,特别是一贯负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力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质。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5]200哈贝马斯也明确表示,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说法曾经风靡一时,但“我得声明我对历史终结的这种诊断不以为然”,并不是历史到了终结点,而是“被操纵的世界已经到达了崩溃点”[6]79。
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完全是“文化一元论”或“单面普遍主义”的逻辑设定和想象。其在文化现代化层面所激活的问难必然是:谁之“文化”?何种“合理性”根据与“合法化”限度?这种拷问逻辑的发育在“9·11”事件以后,演变为反思和重新考量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思想文化潮流,即一种反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正如某文章指出的,西方自由主义已经不能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当今世界需要一个新的马克思,一种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思想。而以英国首相布莱尔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此时的发微,不能不说是又一明显的例证。“第三条道路”理论通过中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旨在纠偏和“调节”新自由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表面看来,这是一种建设性的姿态,但实质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文化决定论”或“文化优势论”理念或观念依然无比坚挺。
诚然,文化的地位是平等的,世界上不存在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化。因为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由一种文化范式决定(不是由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决定)的文化模式从“轴心时代”起,就奠定了没有价值高低之分的世界几大文化(文明)样态的合法地位,也因此暗含了文化的多样性的合理性。历史证明,文化只有在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中才能获得“先进”和进化的动力;以一种文化模式强制置换或代替另一种文化模式,只能是在“文化空想”中得以落实,如同“巴别塔”的建造。而“将一种文化普世化,不管该文化是如何高妙,都是一种‘反文化’的虚妄”[7]189。A·兹洛宾·洛特曼就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有任何现实的机会成为普遍通用的文化而使所有其他文化服从自己,即文化的多元性是永恒的。日本著名的国际文化理论家平野建一郎基于文化涵化理论,虽也注意到“文化全球化”历史逻辑框架,但最终承认: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越趋于多样化。如此这般地共识性理解,在“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性生存”的21世纪,恰好切中了当下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讨论。讨论的“正价值”则是对“文化相对主义”存在的合理性限度的精当把握。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激活的“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争,无论从学术层面还是现实进路来看,都应该在辩证理解中得以有限展开。因为前者即“文化普遍主义”强调的是文化交往的普遍性和文化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后者即“文化相对主义”凸显的是“社会制度与文化价值”的差异性事实。二者不同的“问题域”和旨趣只能援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来化解,一如赵汀阳对相对性和多元性的理解:“相对性和多元性的事实仅仅意味着:存在着某种知识体系,它被局限于某个地方进行表述,而还没有成为普遍的表述。但它并不意味着:存在着某种知识体系,它永远只能是关于某个地方的特殊表述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意义。”[8]于是,一种关于“互相普遍主义”(reciprocal universalism)的基本信念成了化解“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争论的策略。所谓“互相普遍主义”,就是认肯以下三点并获得信念上的支撑:“(1)拒绝单方面专门推广某种文化和知识体系的那种普遍主义;(2)各种文化和知识体系同样都具有值得推广且必须推广的普遍价值;(3)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接受他者的文化价值是保持人类文化的总体生态平衡的必要条件。”[8]
其实,“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争论的问题谱系,从属于文化现代化层面以下几大理论误区的发散繁衍。(1)关于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理论扭结。在涉及文化研究的一系列论说中,言说者总是首先肯定作为“复合体”的广义文化及其“整合”功能,而在具体的论说过程中,由于出发点和域界的不同,狭义文化往往成为表述的关键范式,狭义文化的社会“分化”功能得以有力彰显,从而,在逻辑上混淆了文化之广义和狭义划界因之造成文化系统内部整合机制与社会文化分化体制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诸多理论困惑。(2)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与作为“去意识形态”的文化之迷。这实际上关涉“意识形态终结”甚至“历史终结”问题的本质。不同的主张必然导致不同的结论。(3)作为研究方法模糊的文化。一般认为,当下文化研究的方法从本体论着眼,有跨文化、人类学以及文化批判三种[9];而从认识论着眼,则呈现出民族志(ethnography)、文本方法(textual approaches)和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三种。诸种研究方法交织在一起,势必模糊着人们关于文化的哲学图像,不仅研究方法模糊,甚至研究对象也不确定了。以上三大误区归为一点,就是谁之“文化”拷问的逻辑生成图式。而此一图式在文化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解读中,则体现为“知识话语范式”(注重内在逻辑演化)、“社会语境范式”(注重社会背景)以及“意识形态范式”(注重观念、思想的阶级基础)[2]21-27之间所纠结的堂奥。
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泛起的“普遍价值”和“同质性”文化主张,虽然借助现代科技传媒等工具得以广泛传播并在非西方国家蔓延甚至被“接受”,但主要是表层的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而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层依然没有发生一如预设般的松动。甚至相反,可能激起作为其对立面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弹与复活。就是说,对于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反思因之历史地激起的“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论争逻辑,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还孕育了“文化身份”或者“文化认同”声音的日益崛起。这一事象立足于社会思潮面相,就是“后殖民话语”的出场。
二、后殖民话语:地方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的“现代化”路径
后殖民话语隶属于后现代主义。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后殖民话语,在“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重新成为国际关系主体、民族主义日渐盛行的“新全球化”之际,势必诱发新一轮高峰。诚如《后殖民研究读本》序言中描述的,“‘后殖民理论’在名字产生之前,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帝国主义语言与当地经历颇有争议但生机勃勃的混合造成了一种张力,一旦殖民地民族有理由思考和表述这一张力,后殖民‘理论’就应运而生了。”[10]88-89事实上,二战后民族国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前殖民地国家对民族文化独立性的追寻以及诸如斯皮瓦克等一批“两栖人”群的形成,共同构建起“后殖民话语”出场的语境。而1990年后,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只是起到了催化作用。
在援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以及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础上,后殖民话语不遗余力地大肆批驳“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旨在建构和确证“第三世界”特别是东方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从理论实质上讲,后殖民话语是后现代主义通过“第三世界”的介入,实践和扩展的一种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格局状貌。较之囿于边缘性喧哗与骚动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话语更注重从一种新的政治视角切入现代西方文明从而改写之,并据此在一种新的阐释中,即一种动态的、创造的过程中呈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其震慑力和效能则体现在对资本全球扩张的合理性理论证明的一系列殖民话语的有力挑战上。
作为一种新全球化境遇中的社会思潮,后殖民话语对当下东西方文化关系所作的重新厘定和“素描”,无疑具有“拨乱返正”的重大理论意义。但是,在实践层面上,新的“东方—西方”、“中心—边缘”以及“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随即生成。换言之,理论上似曾消解的二分问题或矛盾在实践领域又得以重新返回。这就使后殖民话语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新一轮理论误区。
面对文化现代化,后殖民话语不得不触及现代性的合法性问难。按照后殖民话语逻辑,对西方殖民文化的抵抗势必促成对西方传统现代性的彻底批判与拒斥,相应地,思想观念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或“防御性现代化”必然得以勃兴。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儒学复兴”思潮的升腾,不能不说正是这一逻辑进路的有力明证。因此,文化现代化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求得真正的“阿基米德点”,依然是需要澄明的一大理论难题。
幸运的是,对西方传统现代性的拒斥,同时开显了“地方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理式之文化现代化路数。正如现代性研究大家艾森斯塔特确认的:“‘多元现代性’一词的最重要含义之一就是,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性模式并不代表现代性的唯一真实,尽管它具有历史的优先性,并且相对于其他现代性来说继续有基本参照作用。”进一步讲,“现代性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持续变化表明,现代性的历史最好被看作现代性的文化纲领及其制度样式以多样性的方式发展、形成、建构和重构的故事”[11]27-37。无独有偶,杜维明也承认,一个佛教式现代性、伊斯兰式现代性或印度教式现代性是完全可能的。于此,我们可以觉知和洞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后殖民话语恰好适切了“地方现代性”或“多元现代性”的现代化路径,这对于文化现代化研究自当具有理论廓清和实践澄明功效。然而,“一元”与“多元”、“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如何深刻照面与有效沟通,成为文化现代化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另一理论砍陷或曰悖论性难题。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借助陶东风以下深彻的指导得以方法论上的启示:“中国保守主义的超越之路只能在于:在检视东西文化关系时,必须要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标准或文化相对主义来消解文化价值的普遍标准;否则就无法摆脱我们在文化的民族化与世界化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不必因为西方文化曾经并仍然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对之盲目崇拜;也不必由此而对之心存戒心、时时提防,惟恐上当受骗。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既不应是它受到崇尚的理由,也不应简单地就是受到排斥的原因。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现实。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东方的、中国的或边缘的就妄加蔑视或妄加张扬。”[12]93-94
实际上,按照笔者的一贯主张,现代性问题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分别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研究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不同层面的基本命题,需要深刻照面和有效践履。现代性(指跨越了民族界限的一种全球话语,其实质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延展的主轴)使文化现代化更加饱有活力;民族文化认同则使文化现代化更加拥有底气。偏执一端,必然导致文化现代化失衡和走样;而双向挂空,却永远使自己迷失。唯有对“张力空间”的殷殷关切和孜孜以求,才能洞晓文化现代化真蕴,从容地为当代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当然,立足于全球化视域,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现代性的“相同性”(“全球现代性”)使得文化现代化成为可能,正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相异性”(“多元现代性”)使得文化现代化成为必须。问题仅在于何以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以及如何践履文明的有效沟通。但无论是转换还是沟通,都是多层次、多渠道、“建设性向度”的发用和践履过程,是“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渐次呈现过程。
三、复兴之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
在当下文化现代化研究的诸多话语中,“复兴”一词被使用的频率甚高,“非西方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不仅成为一种学术理路,而且成为一种政治话语和文艺领域(包括体育领域)催人奋进的号角。东亚经济的起飞是“非西方化”的,因此,就理所当然地有了“非西方文化”复兴;中国绵延五千年的文化,在先秦时代就著称于世,之后虽然屡遭“他者”文化的不断挑战却依然健在并在新时代焕发了勃勃生机,显示了她强大的生命力和“复兴”的可能性,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当然也有像赵汀阳式的学者批评这种解释本身就隐含着“文化优越论”因子)。可以说,“复兴”浪潮正席卷全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1)复兴之路正当时;(2)文化复兴两由之;(3)复兴和“被复兴的”同时并存。
(1)和(2)都易于理解,此处主要谈谈(3),即复兴和“被复兴的”同时并存。就复兴而言,东亚经济的发展奇迹以及“东亚模式”甚至“中国模式”的出场,实在是东亚诸国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问题是,民族复兴一定会带来文化复兴吗?此一问难在中国的发微,直接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成功地实现现代化转型相关涉。众所周知的巴西、墨西哥诸国发达的经济之所以成为泡沫,前苏联发达的经济的突然夭折,与他们落后的文化事实不无瓜葛。故此,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客观上要求中华文化真正的复兴,而后者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真正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就“被复兴的”而言,主要指极端而左倾的民族主义思潮、温和而固执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潮、乐观而偏执的“普世主义”思潮也风生水起,成为与“复兴”相伴的“被复兴的”观念。复兴和“被复兴的”同时并存事象,使得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历史作证。自1918年斯宾格勒预言“西方的没落”以来,西方人逐步深入地检讨了“文化中心主义”的种种弊端。其间虽有诸如福山“历史终结论”式的极端化走向,但自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浮出水面后,一种相对温和的“文化中心主义”还是占据西方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我们经常援引的汤姆林森之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思、萨义德之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思考以及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之于“第三条道路”的诠释,都是最明显不过的佐证。诸如此类。事实上,对早期“欧洲中心主义”和之后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种种批驳之声,自最近几十年来就一直未曾间断过。
与西方思想文化界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规制”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在东方(特别是亚洲),一种极端而“左倾”的文化思潮正在被政治家们所利用,从而成为一种新的“极左”的意识形态或“新左派运动”。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极端民族主义的盛行,已经引起世界普遍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方的“文化中心主义”心态要比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激进得多,坚硬得多,顽固得多。当然,我们不是要为西方唱赞歌,更不是要打击东方的自信心,毋宁说是一种更加清醒地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以求中国文化现代化真正有效、健康地“创制”(institution)。
就中国文化现代化本身来说,自改革开放以降,我们相继遭遇的自由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家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互相论争和各自嬗变[13],已经清晰地勾画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进路。那就是:重新检讨中国寻求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条件和方式,不断吸纳自由主义的民主思想、发掘中国儒家文化有价值的资源(关键是如何把古代的“观念”转变为当代有意义的“理论”,而不是抱持一种敝帚自珍式的“古董情结”)和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养料,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当代重建(包括能体现现代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契机,来构思和开拓基于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综合创新”方法。关于这一点,汪晖教授一语破的,很有前瞻性和建设性:“自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思想界普遍流行的现代化的目的论世界观正在受到挑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习惯的那些思想前提。尽管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我们面对的这些如此复杂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但是,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那种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社会的再生能力,进而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历史条件和方式,将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考虑,却是迫切的理论课题。”[14]
四、何谓“文化现代化”以及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践创制
文化现代化,从其汉语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文化走向现代化。换言之,文化现代化就是寻找现代化征途中的文化标签。事实上,文化现代化的界定与对文化的理解相关联:如果把文化视作与政治、经济、社会平行的范式,那么,文化现代化就特指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经济主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个人倡导开放性、参与性、独立性、平等性等内容、过程和目标;如果把文化理解为大视野下的观念、知识和事象,即文化涵括政治、经济、社会等要素,则文化相当于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复合体”和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的“架构”,那么,文化现代化就是以现代“普遍理性”生活实体(生活世界)的精神气质、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符号话语和叙述逻辑。对文化现代化的后一种理解实际上就是广义解释框架内的现代性(不同于西方传统现代性),即一种广义上的文化心理与形态。本文显然更多指涉后一种文化现代化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习惯于政治、经济之于文化制约层面理解的文化现代化,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性生存”时代境遇,更需要深彻探析经济、政治、环境、社会、个人行为等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关系,尽可能使它们呈现出一种立体景观。因为诸如“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明冲突论”、“帝国衰亡论”、“历史终结论”等文化理论的出场确实模糊着我们之于文化的哲学图像,阻隔着我们之于文化的思维模式。事实上,一种超然的、非政治的、非经济的文化现代化是不存在的,文化现代化必须联系文化出场的具体语境并把它内化到社会历史进程的当代转换之中去理解。面对当下全球化浪潮洗礼的“文化现代化”,更应该定位在现代性(非西方传统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的互动交融层面。质言之,文化现代化就是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一系列新的生存“样法”的实践创制(institution)。
因此,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研究进路,必须正视世界多元文化共存与新的“轴心时代”渐次发育之“捆绑式”历史真实与趋向。面对复杂而多舛的“全球化”浪潮,预设中国文化现代化具体的实践进路,显然是不科学的,也一定是非理智的。我们只能在化解冲突、减少代价、防范风险的道路上继续执著求索;或许,只有在相关“社会思潮”的彼此激荡中,才能不断撞击出智慧的火花直至宏阔的理论方案,以此来资政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践创制,从理论视野或理论指导出发,比较合理的启示当是:(1)建设性后现代性(区别于解构性后现代性)本质上是对现代性的时代阐发和理论发挥,将成为未来现代化文化主旋律中的一个重要音符;(2)“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更应该被合理地理解为:越是民族的越要重新进行“包装”,就越能真正融入现代世界场域;(3)面向当代“普遍理性”生活实体(生活世界)寻找新的方向与新的“增长点”,当是文化现代化建设恒久的生命活力;(4)中国文化现代化作为全球化语境中的叙事范式,只有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目前主要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相结合才能最终真正落到实处;(5)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践,最终应致力于以下层面或内容的完善:文化生活现代化;文化竞争力;文化影响力。而文化生活现代化(即“民生问题”)特别是文化生活的整体现代化,尤其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现代化,应当成为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一切有识之士最为关切的基点和焦点。
从具体的带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立言,以下选择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践创制来说,不能不算中肯之举:(1)整合党的宣传部门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各种资源,站在深入落实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尤其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文化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组建并完善各级文化机构协调和指导委员会,从而竭力敦促“主流文化”“先进性”的引领功效,有效调控诸共同体之间的文化摩擦,诱导其不断向“正价值”方向发展;(2)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潜在的价值,营造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大众积极、健康的文化心态和文明作风;(3)极力萃取并内化世界各民族现代文明中的精华,并运用合理的“教化”机制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主体(当代中国民众)之真正的“启蒙”。(4)建立中国特色文化市场之良性的规范运营机制,并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法制化体系;(5)大力弘扬民主监督之社会舆论机构、团体和媒体的效力,极力发挥新闻舆论的监控效力和“示范”、“警示”之效能;(6)尽力促成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与文化对话平台的生成,保证保障不同“文明”之间平等对话与和谐相处;(7)发展和孵化文化产业的“游戏规则”,鼓励“文化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的合法培植与大胆创新,努力营造以“品牌建设”、“公共服务”、“低碳经济”、“幸福指数”、“城市名片”、“可持续发展”等为品味的文化产业化大厦,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譬如围绕《印象·刘三姐》的演出、东北“二人转”的传承所带动的“产业链”、江西“红歌会”及其带动的“红色旅游”、城市周边的“农家乐”等形式;(8)挖掘民间文化资源的“二次开发”和“文化遗产保护”(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开辟“开发”新路径,探寻“保护”新措施;(9)整合全社会的“文化资本”,促进城市化(现代化)。根据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分理论,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通过教育、出版和销售等环节),文化资本也可以涵养社会资本(通过知识、培训等提高素质,改善社会投资环境)[15]192,我们不可漠视“文化资本”在展示文化产业附加值基础上对“文化现代化”的“圆融”与促进功效。
[1]高瑞泉:《思潮研究百年反思:历史、理论与方法》,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袁祖社:《谁之“现实”与何种“合理性”》,载《学术研究》2010年第2期。
[3]袁祖社:《“虚无主义”的价值幻象与人文精神重建的当代主题——“私人性生存”与“公共性生存”的紧张及其化解》,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法)米歇尔·阿尔贝:《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6]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薛晓源、辛国锦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河清:《破解进步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
[9]李武装:《文化现代化”研究述评》,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10](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Eisenstadt.Some Observa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In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European,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edited by Dominic Sachsenmaier and Jens Riedel with Eisenstadt,Leiden;Boston;K.ln:Brill,2002.
[12]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3]李武装:《中国“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四大流派及其方法论回观》,载《探索》2010年第3期。
[14]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
[15](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Whose“Culture”and which kind of“Modernization”——A Survey of“Cultural Modernization”in the Perspective of“Social Thought”
LI Wu-zh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49 China)
Lots of experienced confusion and perplexity of the study on“cultural modernization”in the theoretical level,in fact,are often connected with the“social trend”and its associated controversy.The dispute activated by the new liberalism between“cultural universalism”and“cultural relativism”,should be understood dialectically with a limit,no matter in academic level or in reality road.Post-colonial discourse just matches the“local modernity”or“multiple modernity”,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and practical clearance of“cultural modernization”.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or even the national revival depends on whe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 carry out modernization transition successfully.In a sense,the oriental idea of“Cultural centralism”is deeper and more stubborn than the Western.Chinese cultural modernization must face the reality and trends of the multicultural co-existence and the new“Axial Age”.
culture;modernization;social thought;cultural modernization;practice institution
李武装(1974-),男,陕西富平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文化现代化。
2010-08-16
G02
A
1671-7023(2011)03-0014-07
责任编辑 吴兰丽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