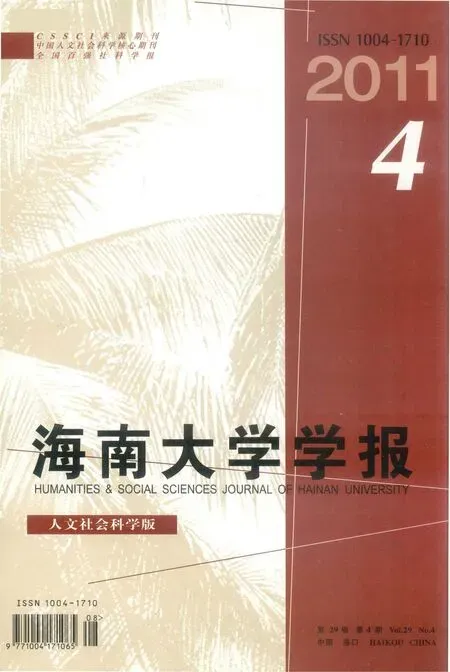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
罗旭南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
罗旭南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 570228)
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引入多样化法学方法综合适用,不仅能够克服中国法律史教学中法学方法原有的单一化,严重意识形态化、教条化、封闭化等种种倾向,还可以在各种法学方法之间形成互补。对应对复杂、多维的法律史问题,开阔法学教育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学方法;多样化;法律史教学
关于中国法律史课程,无论是“灭国先灭其史”的说法,还是“读史使人明智”的论点,以及教育部将该课程列为主干课之一,都说明学习该课程的重要性。但近年来,中国法律史课程在教学中面临的多种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少学者也都提出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见解。笔者认为,引入多样化法学方法,革新旧的教学方式,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主要途径。引入多样化的法学方法,则必须革新传统法学中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即唯马克思主义是从,法学方法单一化与一元化而造成其他法学方法轻视和漠视的倾向,同时必须革新法学方法的严重意识形态化、教条化、封闭化等种种倾向。革新旧的教学方式,则必须摒弃中国法律史教学中教学方法相对滞后,摒弃那种以阶级的方法讲授中国法律史的老套教学模式,吐故纳新。本文以法学方法多样化为理论视角,力图阐述法学方法多样化在开阔中国法律史教学理论视野中的意义及其运用。
一、法学方法多样化及其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适用之意义
(一)法学方法多样化之含义
法学方法多样化,即法学方法多元主义。它是指法学方法并存和在法学研究过程中多种法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法学方法上的多元论与一元论相对立,一元论“在理论模式上要么导致偏于一端的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多元论则“在理论模式上呈现给人们的是对于研究对象的多面观察,即既从实证的角度又从规范的角度,既从科学的角度又从人文的角度,更多的情况是上述角度的杂糅并存。”[1]
法学方法多样化,是现代法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是人类法律文化累积沉淀的体现,是法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体现,是法律思想家们探索法律文明的智慧结晶,是法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体现。法学方法多样化,更是法学研究的必须。法学方法是法学者研究和认识法律与法学发展规律并使其具有科学、明确的理论形式的规则、工具和程序。显然,那种自我标榜是惟一正确的规则、工具和程序的论点为学人所不齿。法学方法多样化,无论是法学研究,还是法学教学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诚如梁启超先生所云:“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2]
(二)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适用之意义
1.适用法学方法多样化,可以克服单一化与一元化的倾向 单一化与一元化倾向的教学研究倾向,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前30年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在这一时期,首先是将民国时期的法学彻底地否定。对其法学课程以及方法都进行极其严厉的批判。在法学方法方面表现为,以苏联老大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学”唯马首是瞻,以国家与政治为根本利益而强调“政治挂帅”的阶级论,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考察、判定特定历史阶段上法制的变化,其法学的方法往往是对中国传统法律加以抹杀。
单一化与一元化倾向,在中国法律史教材的研究方法上,无不千遍一律地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揭示历史上各种类型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以此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法理论的理解,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对其他法学方法忽视或认为其微不足道。在中国法律史教材的体例上表现为单一的“断代体”而拘于形式,形成亦步亦趋的手法。其结果是难以阐述中国传统法律一些具体制度的变化。内容的单一性则表现为,教材内容仍偏向于制度性史实,从夏商开始以朝代为单元分别设置立法、行政法律、民事法律、刑事法律、司法诉讼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到近代后增加立宪及宪法内容。
2.适用法学方法多样化,能够起到法学方法的互补 每一种法学方法,既具有局限性,又具有互补性。与任何研究进路和方法一样,每一种法学方法同样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性。多种具体的法学方法,因其内在的逻辑构成、运作程序的差异,具有各自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功能界限。因此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方法,因为不可能存在一种可以涵盖和认识整个法学领域的法学方法。各种方法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惟一和垄断的方法。每种法学方法,都只能用于探讨某个特定的法学问题,或用于研究某个法学问题的一个层面。多种法学方法的适用,才能起到兼容并蓄,开阔认识的视野,并因此获得法学某一领域的整体认知,起到互补的作用。
3.适用法学方法多样化,可以应对复杂、多维的法律史问题 中国法律史学的内容涵括法律制度的发生、发展、演变和规律的内容,还包括法律思想中儒、法、道等理论学说。从时间断代上还可以分成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法制及其理论。中国法律的历史源远流长几千年,内容丰富。浩如烟海的典籍及其资料,如果教学的方法是单一的途径,面对中国法律史复杂多维的问题必定苍白无力。不仅要使用多元方法,而且还要使这些方法适合于法的各方面的特点或法的某种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需要有解释法律规范和法律结构的方法,需要将法律规范系统化。为了研究法的心理存在,需要个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为了研究法的社会存在,大家公认必须广泛利用具有社会学研究及其一切研究方法。过去的法可以用历史研究方法而加以披露。”[3]
二、中国法律史教学中法学方法多样化之适用
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研究运用的意义不言而喻。在此,笔者仅就中国法律史教学研究中的语境论、律学注释论、文化类型学论等较为典型和常用的法学方法为实例,就其在中国法律史教学研究的运用分述如下,试图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语境论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之适用
所谓语境论,是指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其态度是对以往的法律作学术的研究而非政治的批判。总体而言,语境论切实注重特定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禀赋以及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把法律制度和规则都视为在诸多相对稳定的制约条件下对于社会问题的一种比较经济且常规化的回应[4]。语境论因而往往隐含对旧制度的同情和理解,而疏于对其严苛的批判。
由于语境论探讨的对象是“对于一种相对长期存在,据此可以认定获得了特定时代人们之认可的法律制度或规则。”[4]它因而是适用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方法,而适用语境论研究范围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可谓汗牛充栋。
1.亲属法律制度或规则 亲属法律制度或规则大多关涉风俗、习惯,国家可以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但如果以法律来促成这一方面的变革,往往事倍功半。“实际上我们却很少发现任何法律领域像家庭法那样发生那么深入而且迅速的观念和制度的同化。”[5]弗伦因德所说即是立法的形式改造社会习俗总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婚姻家庭亲属法律制度或规则与其他方面的法律制度比较而言,往往是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或规则。中国法律史中,大多有关内容都可进行语境论的尝试,如早婚、父母之命、同姓不婚、媒约之言、六礼、七去、义绝、三不去、良贱不婚、五服等。比如传统社会婚姻法律的早婚,语境论是从农业社会、传统社会人的寿命、信息与交通与当代社会的截然不同来分析的。
2.刑事法律制度或规则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历朝历代中,“汉承条律”、“清承明制”,各朝各代彼此相沿袭的法律制度多见于典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或规则如亲属相隐、恤刑、缘坐、八议、十恶、准五服以制罪、五听等等方面都是典型的事例。再如西周“明德慎罚”,它是以后历代王朝“德治”及“慎刑”思想的重要源泉。上述许多的制度,从语境论的角度出发,都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情理法中找到缘由。
(二)律学注释论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之适用
律学实质上是中国古代法学,它是中国传统特有的学术。它研究制定法的内容及其如何适用的问题,研究的对象是业已颁布的现行法。具体而言,传统律学探讨了律例之间的关系、条文与法意的内在联系,以及立法与用法、定罪与量刑、司法与社会、法律与道德、释法与尊经、执法与吏治、法源与演变等各方面,其微、其细、其博、其实、其用均为世界同时期所少有[6]。
律学注释论,它是一种以经学注释诠解的研究方法。律学的注释方法,其理论说明的方式是以文字和逻辑方法对法律条文进行详细解释,这种研究方法不探求学理,也不具有批判意味,只是为了有利于法典的宣传和实施。这种方法立足于法条的本身含义,进行字面解释、扩大解释或限制注释,以阐明以往法律的自身功能和社会功能,它对法律的专业化和职业训练及常规时期法律运作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律学的方法体系建立在中国传统两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法律学术基础之上,并形成了丰富独特、纤细备至的注释形式。如秦律的“答问”、汉律的“章句”、魏晋律的“集解”、唐律的“疏议”和宋代的“音赋”等。传统律学注释论,历经悠久历史延续不绝的运用与发展,其研究方法的使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晋代、唐代等朝代的法律史教学中,都无法回避该方法的运用。
1.晋代法律史教学研究中律学注释论的适用 在此仅就较为典型的《晋律》中的20个名词,以法律术语的规范性解释方法为事例,说明律学注释论的运用。《律注要略》较为详细地说明张裴对《晋律》20个名词的规范性解释的内容:“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漫,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贷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7]
上述20个名词主要包括侵犯人身权利的5个罪名:漫、诈、不敬、不道和恶逆,以及区分犯罪主客观方面行为的15个名词:戏、斗、贼、盗、强、略、故、失、过失、戕、造意、谋、率、群、赃。笔者认为,在晋朝法律史的教学研究中,介绍张裴相关法律术语的规范性解释方法,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使学生了解晋律对秦汉律中侵犯人身权利理论的发展。晋律是在秦汉律发展粗略的基础上,即在传统法律制度奠基之上,发展前代法律的。具体在杀人称为“贼杀”、伤人称为“贼”的基础上,采用上述方法而规定出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5个罪名的。其二,关于主客观犯罪区分为预谋犯罪、故意犯罪和失误犯罪,经过注释,特别是“二人对议谓之谋”的规范性注释,为隋唐律“十恶”及相关罪名中的预谋犯罪理论奠定了基础。晋律也发展了自西周以来的“眚”(音省,过失)和“非眚”(故意)以及秦汉律中的“端”(故意)和“失刑”(过失)等主客观方面的理论,区分犯罪主客观方面的15个名词,充分说明在前代基础上,晋律在这方面理论更加系统和完善。
2.唐代法律史教学研究中律学注释论的适用 唐代律学是传统律学的集大成者。就注律来说,“在《唐律疏议》中,唐律的律文只占全部篇幅的20%,而疏议则占了80%。而且,正是这80%的疏议,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集中体现了以往各朝代法律解释学的成果,……仅就对律文的解释而言,在《唐律疏议》中,就已经对前朝律学作出了诸多创新,出现了限制解释、扩张解释、类推解释、举例解释、律意解释、辨析解析、逐句解释、答疑解释和创新解释等多种解释方法。”[8]以下,笔者仅选择上述的“逐句解释”举例作说明。
唐律之《疏议》的产生,旨在帮助司法官吏完整准确地理解唐律的所有规定及律条的含义,解决立法和司法上的矛盾,统一标准。逐条逐句解释或称逐字逐句解释在唐律中比比皆是。
如《户婚律》(总第188条)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疏议逐句解释说:“‘卑幼’,谓子、孙、弟、侄等。‘在外’,谓公私行诣之处。因自娶妻,其尊长后为定婚,若卑幼所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所定。违者,杖一百。‘尊长’,谓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疏议的这一解释,实际上是将卑幼在外,而家中尊长为其定婚,但卑幼不知情的特例进行解释:如果卑幼已定婚并结婚,则婚“如法”,尚未结婚,则应当听从尊长,否则,要“杖一百”。
又如《户婚律》(总第179条)规定:“诸居父母及失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丧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减二等,妾不坐。”疏议主要解释了“服内嫁娶妻妾并离”:意即若作为儿子娶妻,作为在室女儿出嫁,属“不孝”,若作为妻子再婚,属“不义”。处徒三年,“各离之”。妾因地位低于妻,故娶妾,减三等罪,即徒一年半,婚姻无效。
(三)文化类型学论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之适用
“类型”是今日许多学科都加以利用的思考形式,首先将其引入社会学的是马克斯·韦伯。“文化类型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法律文化”研究,并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构成的一种具有独特意义的理论范式。这一研究的范式以“辩异”为基本路径,试图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中,从中西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定之外观上或功能上的差异、类似或相同的背后,去探究它们与其各自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去追究这些制度安排后面的观念形态、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等文化上的“根据”。努力从外观上或功能上的同之中求文化之异,从而进行一种文化“类型”学的研究。这是梁治平在国内法学界率先提出的“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理论[9]。“法律的文化解释在引入一种新的分析方法的同时,也确立了一个新的对象。这里,方法只是研究者‘主观地’加以运用的一套策略,对象却是研究者已经发现并且意欲给出解释的一个‘客观地’存在的世界,它们性质不同,但又关系密切,以致可以借用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法律文化”[10]。“法律文化”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视角,即“作为方法意义上的法律文化和作为对象化的法律文化”[11],笔者在此所要探讨的是方法意义上的法律文化,即文化类型学论。
文化类型学论以“辩异”为基本路径的研究范式实质是比较的方法,是通过比较来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这种“比较”或称“辩异”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揭示中国传统法律的文化性格。对于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引入中国法律史的教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治平的《法辨》一文是一个概念辨析的范例。它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法”这个概念的细致的历史辨析,同时以西方“法”的概念作为对比的参照系,指出中西历史上的“法”概念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安排秩序的观念。尽管近代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以“法”来对应英文中的“law”,但这只是一种翻译,是中西交流的必需和不得已。至少在历史上,中国的“法”并不等同于“law”,因为在这些概念背后所隐含的中西世界观、价值和秩序完全不同,尽管在功能上可能存在某些相似。在作者看来,如果忘记了这一点,用现在西方的“法”来套用、理解中国古代的“法”,实际上是在按照西方观念重新履行已经成为历史的中国法律制度。“辩异”为基本路径的研究范式是其他的理论范式不能替代的。“法律史教学只有充分展开中外比较,才可能真正开阔学生的理论视野,既使之免于闭塞与浅薄,又得到豁然开朗后的新奇与喜悦。”[12]64
三、中国法律史教学中法学方法多样化与统一性的把握
每一种法学方法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整合研究的优势。如何使用法学方法多样化,并且使各种方法适合于法的各该方面的特点或法的某种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避免其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应对复杂、多维的法律史问题,最终能够起到方法论的互补?这是中国法律史学科意义上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将适用的中国法律史的各种方法组织成为一个方法体系并予以理论说明与概括,这也是中国法律史教学法学方法多样化操作的主要困难。故此,方法论则是“把它所允许的各种方法协调起来,以保证其内部的和谐一致,从而形成具有一种特定结构的理论体系”[13]。笔者以为,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适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方法多样化之统一性关系不容忽视,以下两个方面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克服各种法学方法的缺陷,实现方法多样性的优势互补
因为每一种研究方法的本身都存在着自身难以避免的缺陷,语境论、律学注释论、文化类学型论也都如此。如语境论,“反对用一种自我中心的,上帝的,历史在我这里或在我们这里一代终结的眼光来考查和评价任何制度,而主张并力求进入适当的语境,移情、体贴地、具体地予以考查和评价制度”[4]。因此,这一方法也就往往隐含对旧制度的同情和理解,而疏于对其严苛的批判。如律学注释论,这种方法立足于法律条文的本身含义,进行字面注释、扩充注释或限制注释,以阐明以往法律的自身功能和社会功能,它对法律的专业化和职业训练并对常规时期法律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律学注释论,即是法条论的研究方法。它是从法条到法条,局限于学术资料本身。再如文化类型论,类型学的法律文化研究强调“差异最大化”,以致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律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14]。
因此,针对法条论的研究方法是从法条到法条,局限于学术资料本身的研究方法,而根本不同于语境论中设身处地,历史地注重社会中人生物性禀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将法律制度和规则放在当时社会诸多制约条件来观察。对“一种相对长期存在,被特定时代人们认可的法律制度或规则”,适用语境论。而对于《晋律》、《唐律》、《大清律例》中的概念、条文等方面的规范解释,则应当适用法条论。针对文化类型学论将中国法律文化形态化假约为一种不变的理想类型的缺陷,应清楚地意识到“它也会遮蔽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文明中法律本应具有的鲜活面容,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法律价值取向数千年来没有任何变化”[15]的情况,必须以更丰富的法学方法回答法律文化的流变和变迁。这样,才能使法学方法多样化适合于法的各该方面的特点。
(二)恰当适用各种法学方法,克服中国传统法史渲染现代色彩
由于中国法律史的内容涉及上下几千年的文化,法律文化又总是变迁发展的。而自晚清的西学东渐,中国近代法律史自晚清起便在不同的法律文化碰撞下变迁和发展。对于适用于“长期存在”法律制度条件下的语境论,显然不适用于中国近代法律史的诸多法律问题。即使是“类型学的法律文化研究因此也势必难以回答法律文化的流变以及地域的差异”[15]。每种法学方法要适合法的某种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并非易事。因此,“多学科的分析乃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客观需要;而对法律史教学来说,多学科分析不仅有利学生对法律史的理解,并使之在学习中免于知识单一的枯燥,而且还可以从根本上拓展其理论视野、熏陶其理论思维,使之面对纷繁复杂的法律形象时不致于就事论事、简单处理,而习惯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索。”[12]45如对于中国近代法律史基本上是一部西方法律在中国的移植史,它与中国古代法律的自我生成并发展的历史存在很大区别,在研究的方法上应采用系统方法、特定的比较研究方法[16]。法学方法在适用上要注重多样化的同时,还应适度的适用。否则,“使中国传统法史问题带上了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掩盖了中国传统法史问题的真相,增加了准确认识传统法史问题的难度。”[17]克服中国近代引进的西方法学理论方法(原则),有些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运用,造成法律条文和实际脱离则尤其重要。
四、余 论
法学方法多样化的适用,要求在适用某一法学方法的时候,应当兼顾其他种类法学方法的适用,以期达到法学方法的互补,最终推动我国法学研究向深层次发展,这也是我国法学教学研究的必然选择。法学方法多样化的适用,它同时是实现教学目标和事关教育质量的一个极其重要因素,它影响着学生多元和开放学术态度的生成。中国法律史学作为一门法学属性与历史学属性二重性质的交叉学科,就中国法律史“史”的法学方法而言,首要前提乃是“进入”历史本身,如果没有设身处地的研究态度,那么,我们将如何进入历史呢?进而,如果无法进入历史,作为符号存在的历史叙事,将何以获得真正的、有效的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解释[18]。在强调法学方法多样化适用的时候,必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法学方法,正确而恰当地运用这些方法,“进入”历史,才能达到中国法律史教学的最好效果。为此,法律史学者在探讨法律史新思路时不时殚智竭力,“法史的教学与研究若不能回答韦伯理论给青年学子的困惑,说不清历史长河中先贤们在解决中国日常生活问题,处理纠纷时有哪些法律智能及这些以往的智能与现实的法之间还有无文化上的传承关系等,法史学者在现代法学的处境将会进一步边缘化,乃至最后歇竭而不能复振。”[15]正如语境论要求运用人具有“无情的渊博知识”一样,于教师而言,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具备法学方法的丰厚知识,乃是驾轻就熟,综合适用各种法学方法,并最终克服中国法律史学教学困难的关键所在。
[1]李可,罗洪洋.法学方法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66.
[2]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M].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0:208.
[3]日夫科·斯塔列夫.社会主义法律科学的比较方法[G]∥国外比较法学论文辑.王正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34.
[4]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J].中外法学,2000(1):40-59.
[5]张德美.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2.
[6]张晋藩.清代律学及其转型[C]∥何勤华.律学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13-451.
[7]高恒.张裴的律注要略及其法律思想[C]∥何勤华.律学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17-140.
[8]何勤华.唐代律学的创新及其文化价值[C]∥何勤华.律学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55-172.
[9]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自序).
[10]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连书店,1994:2.
[11]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7.
[12]胡旭晟.解释性的法史学——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为侧重点[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3]刘亚丛.事实与解释:在历史与法律之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7.
[14]苏力.阅读秩序[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94.
[15]陈景良.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另一种思路[J].法商研究,2004(5):135-144.
[16]武乾.关于近代法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C]∥倪正茂.法史思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45-352.
[17]刘广安.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6(6):81-85.
[18]徐忠明.思考与批评:解读中国法律文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9.
Diverse Legal Methods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w History
LUO Xu-nan
(Law School,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Introduction of diverse legal methods in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w history is conducive to overcome the demerits existing in course teaching,which is monotonous,heavily ideological,dogmatic,closed,etc.Various legal methods can be complementary,hence,are beneficial to dealing with the complicated and multidimensional matters of law history,and significant to broadening the theoretic horizon of law education.
legal methods;diversity;teaching of law history
G 642
A
1004-1710(2011)04-132-06
2011-01-28
罗旭南(1961-),男,广东普宁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