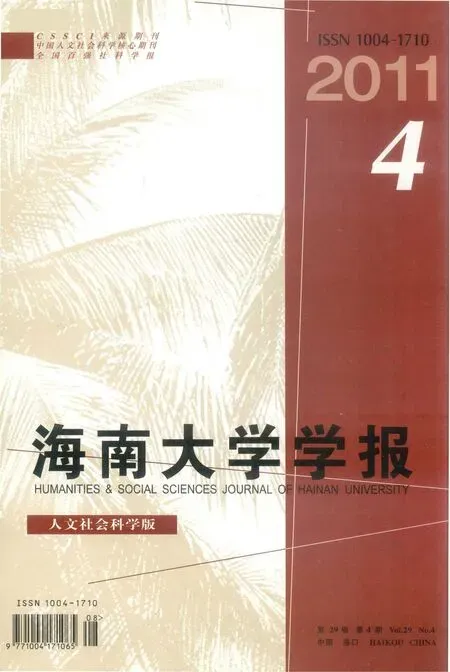翻译:构建诗性语言之桥——斯奈德英译中国古诗研究
李林波
(西安外国语大学欧美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710061)
翻译:构建诗性语言之桥
——斯奈德英译中国古诗研究
李林波
(西安外国语大学欧美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陕西西安 710061)
“荒野”精神是美国现代诗人加里·斯奈德思想的核心,它类似于“道”。斯奈德的语言观与诗学观与其“荒野”精神一致,主张用自然的语言来表现自然。他认为中国古诗语言与其理想中的自然语言接近,而且中国古诗中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非常完美。因此,他对中国古诗的翻译可视为一种创造更为完善的诗性语言的努力,其翻译也成为其创作的先锋与实验。
加里·斯奈德;翻译;中国古诗;荒野;自然
法国诗人马拉美曾说:“世上缺少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语言:没有修饰成分,甚至没有暗示,人们的所思即所写。”[1]327语言的发展似乎也遵循“正—反—合”的规律,即“简单—复杂—再简单”。当浪漫主义的超验、华丽发展到巅峰之时,现代主义作家与诗人们提出要用直接、简练的意象写法来净化诗歌语言、与自然建立直接联系。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现代主义、生态主义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便是坚持这种主张,并将其贯彻得彻底而全面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古诗的翻译在促成与实验这种主张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诗是自然的直接表达
加里·斯奈德思想的核心是“荒野(wilderness)”精神。他发现在英语词典中,对“野性(wild)”与“荒野”的定义是繁杂却又不切本质的,但在中国哲学中却可以找到与“荒野”最贴切的对等词——“道”。“道”可以这样理解:“无法分析、无法归类、自我构建、自我充实、不故作严肃、令人惊讶、不断变化、非实体、独立、完整、有秩序、不经中介、自由呈现、可自我印证、坚守自我意志、复杂、单纯。二者皆空且真。”[2]11同样,“荒野”也具有以上特质。也就是说,“荒野”就是“道”,它们是自然的本质与本性,体现在世界的一切方面,统摄宇宙的运转和人类的生存。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类在其文明进程中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最终会失去自己生存的家园,因此生态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倡导自然的自在状态,反对人对自然的介入与干涉。现代主义诗人对待自然的观念与此一致,反对超验、虚幻、浮华的诗风,主张自然在语言中直接、真实的呈现。并不是所有有关自然的诗歌都属此类,有些诗仅仅是“有关自然”,诗人仍处于自然之外。在真正的“自然诗歌”中,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然的直接呈现就是诗人情感的映照。
叶维廉曾引用中国禅宗《传灯录》中的一段公案来说明人和自然关系的几个层次: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叶维廉认为:“第三个阶段‘依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可以说是对自然现象‘即物即真’的感悟,对山水自然自主的原始存在作无条件的认可,这个信念同时要我们摒弃语言和心智活动而回归本样的物象。”[3]82-83
中国的山水诗很多都具有这种“即物即真”、“物我两忘”的境界。斯奈德认为“中国与日本传统中有文明社会中的人类所写的感觉最为敏锐、最发人深思的关于自然世界的诗歌。”[4]290中国山水诗中,人与自然之间不是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描述者与被描述者的关系,人对自然的描述就是对自身的描述,自然在诗中的呈现就是人自身的呈现。如哈贝马斯所说,即“人类把自然看做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般,把自然视作鲜活的、言说的生命,而不是被动、沉默的物质,人类才能倾听和接受自然的语言,才能避免凝视和被凝视、主体和他者的关系,而建立平等、模仿、对话的关系。”[5]
年轻时的斯奈德并没有领悟到人与自然这种内在的融洽关系,而将自然看作一个极端的、有别于人类世界的荒野之地,他说:
“十九岁时,我第一次接触翻译过来的中国诗歌。此前,我理想中的自然应是火山上的一道45度冰坡,或是一片绝对原始的雨林。(但中国诗歌)让我在一座老砖房的后院中‘看见’了田地、农场、丛生的灌木、还有一丛杜鹃花。这些让我从对荒野山林的极端追求中解放出来,以它们的方式告诉我,即便最为蛮荒的山也可以是人们居住的地方。”[4]295
中国文化向来主张人与自然的融洽相处,而不是对立。在中国诗歌、尤其是中国的山水诗中,自然不仅是外部世界,更是诗人内部世界。“远山空间实为生命空间。”[4]293这种内外的协调统一赋予中国诗人无限宽广的精神世界。“一沙一世界”,“荒野”不必去荒无人烟的蛮荒之地寻求,它既存在于“阿拉斯加,北方最开阔和蛮荒的地方”,亦存在于“中国,最富文学素养的文明”[2]80。它是种精神,而不是形式。
斯奈德对“自然”的追求是全面的。对他而言,对“自然”的向往不仅意味着在诗中体现自然,而且诗歌语言本身也应该是一种直接、简洁的“自然”语言,这在他看来也是更具诗性的语言。如其所说:“有些诗人宣称,他们为用语言的棱镜反映世界而写诗,这当然是个值得称道的目标。不过,还有一种写法,即并不凭借语言的棱镜也可看这个世界,然后将所见变为所写。这正是大多数中国诗与日本诗的目标所在。”[6]223自然的语言中应没有人类文明“加工”与雕饰的痕迹,要客观、直接地反映世界——所见即所写。
二、翻译是通往“完善”诗性语言的道路
20世纪初期,通过庞德(Ezra Pound)等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发起的意象主义运动,英语诗歌进行了一次简单化、直接化的变革。用直接的意象作为表达的途径,诗歌与自然的距离缩短。在庞德意象主义的形成中,中国古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古诗的意象主义表达方式为庞德提供了构建新的诗歌写作形式的灵感源泉。《华夏集》(Cathay)的产生见证与促成了中国诗歌与英语诗歌的融合,从而生成了引起美国乃至整个英语诗坛变革的意象主义。但二十多年后的斯奈德则走得更远,在斯奈德的诗歌中,意象不仅仅是表述方式,它就是诗本身。
与庞德一样,斯奈德在中国古诗中看到了自己理想的诗歌理念与语言形式;但与庞德不同的是,斯奈德不仅深受中国儒释道精神影响,而且精通中文。他对“完善”诗性语言的构想在学习中国古诗的过程中逐渐成型,并通过翻译对其加以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最好的革新语言的途径,因为在翻译中源语与译语相遇并发生作用,形成最具潜力和新意的新的语言。而且,在译作中,一切“异”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翻译便成为求“异”、显“异”的最佳载体。
斯奈德在翻译中实现中文和英文的融合,从而创造出一种更具有诗性的、更为完善的语言,正好印合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翻译观。本雅明认为:“翻译因此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表达不同语言之间最重要的互补关系”[1]323。在本雅明看来,“翻译的伟大主旨就是把许多语言融合成一种真正的语言”[1]327。在斯奈德看来,这样的一种“真正的语言”就是人类的“普遍的语言”,是与自然能够直接呼应的语言。这种语言与老子的“大巧若拙,大辩若讷”[7]236的精神一致。于是,斯奈德的中国古诗译文不同于其他任何译本,它质朴、简洁、直接、纯粹,但又精确地令人惊叹!正是:“如何是佛法大意?”“春来草自青”[3]91。
斯奈德的译文数量虽少,但其影响很大。在寒山诗的英译本中,斯奈德的译文最为简练,接受效果却最好。美国“垮掉的一代”中的寒山热,也主要是由斯奈德的寒山译本与凯鲁亚克以斯奈德为原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引起的。斯奈德所译寒山诗都以寒岩生活为主题,译本的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中国古诗句法与英语语言的结合,用科恩(Kern)的话说,便是“以汉语为美国话语(Chinese as American Speech)”[6]221。这既可以理解为英语的汉语化,同样也可以理解为汉语的英语化,用本雅明的话说,则是两块碎片向一个完整花瓶的努力。斯奈德的语言实验证明,这两个分属不同语系的语言实际上并不像其地理位置那么相隔甚远。他认为:“由于某种原因,把中国古典诗歌移译到英语中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因为中英语语汇都很精炼,句法十分相近,在某些诗人你甚至能把整个诗句结构从汉语搬入英语。”[8]241费诺罗萨的论文中也提到:“中文和英文句子之相似,使互相翻译特别容易。这两者的特征大致相同。通常,略去英文的冠词,就可以逐字直译,这样的英译文不仅读得懂,而且可能是最有力的,最富于诗意的英语。”[9]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真正的诗性语言应该是全人类普遍的、共同的语言,那么,不同语言之间经过融合提炼出来的语言共核或“第三种语言”就是与这种普遍语言更为接近的语言,因此也就是更为诗性的语言。用本雅明的话说,也就是使原文的“可译性”得以呈现和表达,是一种语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救赎”:“通过翻译,原作似乎进入了一个更为高级、更加纯净的语言境界”[10]62。
三、斯奈德译诗语言分析
以数量而论,作为译者的斯奈德远不能和理雅格、韦利等享誉英语世界的中国经典诗歌翻译家相提并论,但以风格而论,斯奈德是独一无二的。斯奈德一共翻译了24首寒山诗与17首唐诗。寒山诗的英译本中以译诗数量和影响而论,比较著名的有华生(Burton Watson)的《唐代诗人寒山的100首诗》(Cold Mountain: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1962年)、赤松(Red Pine)的全译本《寒山歌诗集》(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307首)(1983年)、韩禄伯(Robert Henricks)的《寒山诗:全译注释本》(The Poetry of Han-shan:A Complete,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Cold Mountain)(311首)(1990年)及赫伯逊(Peter Hobson)翻译的《寒山诗》(Poems of Han-shan)(106首)(2003年)[11]。这些影响较大的译本所选诗的数量都比较多,但在300多首寒山诗中,斯奈德只选了24首以寒岩生活为主题的诗,也许是因为寒岩是人与自然融合与统一的见证,更符合斯奈德的诗歌理念。他所译的17首唐诗基本上分为两类:山水诗与感怀诗。山水诗如王维的《鹿寨》、《竹里馆》,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柳宗元的《江雪》等,感怀诗中有送别诗如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爱情诗如王维的《相思》、描述古代女子爱情命运的诗如元稹的《行宫》、白居易的《后宫词》与《长恨歌》等。总体而言,以自然为主题的诗占多数,因为有一些送别诗如《芙蓉楼送辛渐》、《送灵澈》等也是以自然描写为主,用自然世界物象的呈现来作为诗人内心世界的表述。这是他译诗的选材特点。以语言而论,斯奈德的译诗语言比其创作的诗歌语言更能突出个性,表现出鲜明的实验性特征,以下面3类译例为证。
(一)词汇隔离模拟视角转换
认知和体验的过程是灵活的、不连续的,但英语用词汇、语法等语言手段将认识事物的阶段、视角、方位连接起来,因而也就将多种可能性确定为一种,并将不连续的行为续接为连续的过程。但在中国古诗中,这个过程并没有用语法或词汇手段将其固定下来,而是保持了物与物之间、物与人之间关系的开放性以及体悟过程的不连续性和多种可能性。斯奈德利用翻译,借用中国古诗的文法,对人在自然中的认知和体悟过程在英语诗中作了实验和模拟。如其所翻译的寒山诗《重岩我卜居》中“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12]19两句为:
In a tangle of cliffs,I chose a place—
Bird paths,but no trails for me.
“鸟道绝人迹”只有五字,其中没有任何连接词,但却并非是“鸟道”断绝了“人迹”,而是反映了从“鸟道”到“绝人迹”的思维判断过程和视角转换过程,同时又因词与词之间关系的自由性,读者可以在两者之间往复体验。从“鸟道”到“绝人迹”之间的视角转换和思维转换是隐含的,但也是灵活的,其组成方式是灵动的。任何符合常规语法和句法的译法都会抹杀这种灵动性,并将灵活、隐含的视角转换过程和思维判断过程僵化、固定下来。斯奈德的译文尝试用逗号将“鸟道”与“绝人迹”隔离,虽然在自由度、灵活性上不能与原中文诗句对等,但也部分模拟了观察和体悟自然的过程。不过,由于“but”的加入,凸显的是从“bird paths”到“no trails for me”的思维判断过程,视角层面的活动减弱。
再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中前两句“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斯奈德的译文为:
The boat rocks at anchor by the misty island
Sunset,my loneliness comes again.
“日暮”究竟意味着“在日暮中”,还是“看到了日暮”并不确定,也可以理解为二者皆有。因此,“日暮”与“客愁新”通过语法与朗读时节奏上的隔离保证了其独立性,场景与人物活动之间的关系生动、灵活、开放。符合语法的英文翻译必然要加上介词或者副词,场景的自由变换就被固定下来,美感流失。但在斯奈德的译文中,“sunset”同样通过了词汇隔离被予以独立自由的地位,从而保留了场景的自由特性。这是对观察视角的模拟。
斯奈德将中国古诗元素纳入英语现代诗,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古诗语言更具诗性,诗中蕴涵了人和自然的互动、互通方式与和谐融合的状态。斯奈德将中国古诗句法与英语语言相结合,是对英语与汉语语言融合的实验,也是一种用英语进行的在语言与自然之间建立契合的实验。
(二)词汇并置模拟自然存在状态
中国诗学中的“以物观物”(邵雍)[3]86主张语言要真实反映自然界的存在状态。自然世界中的事物是通过观察者的视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本身是独立的存在。在中国古诗中,意象之间的联系也是通过阅读者的视觉(或听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通过词汇或语法手段。但是在英语中,意象的这种呈现方式是与语法规则和语言习惯相违背的。即便如此,斯奈德也偶尔尝试这样的表达方式,用脱离语法的意象并置来模拟自然界中事物的存在方式,这也是庞德曾经用过的一种句法。但在两位诗人自己的作品中却很少用到这种绝对脱离语法的诗句。或许是在翻译的名义下,一切的“异”都有存在和彰显的理由吧。
在《达摩流浪者》中,“我”(作者杰克·凯鲁亚克)拜访诗人贾菲·赖德(以加里·斯奈德为原型)时,看到后者在译寒山诗。贾菲将《登陟寒山道》这首诗的中文基本上用字对字直译的方式读给“我”听,并为“不得不加入英语的介词和冠词”而感到遗憾。他说曾想到过用字对字直译的方式来翻译这些意象分明的诗句,但同时又要考虑到中国学者的认可,其英语表达方式也要清晰[13]。因此,最终的译文是一种中国古诗文法与英语语法之间的调和。即便如此,与其他译本相比,斯奈德译本仍然显示出了鲜明的直接、写实的特点。如《驱马度荒城》中,“高低旧雉堞,大小古坟茔”[12]42两句所呈现出来的物象存在状态是自由的:高低不等的雉堞,大小不一的坟冢,可以是先看到高的部分,再看到低的部分,先看到大的,再看到小的;也可以是先看到高高低低的物体,然后再判断物体是什么;还可以是高、低、大、小的物体同时纳入视野,等等。诗句中每一句中五个字的排列看似有序,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无序,因为“高”、“低”、“古”、“雉堞”中有实体、有描述,可以随意组合在作者头脑中投射出具体的印象。英译文为:
High,low,old parapet walls
Big,small,the aging tombs.
译文中词汇的独立性仍然保留,词汇并置,脱离了语法的连接、组织,因此词汇之间自由组合、灵活联想的关系就得到保留。
再如在柳宗元的《江雪》后两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译文为:
A single boat——coat——hat——an old man!
Alone fishing chill river snow.
译文不但使用了语法割断,并且还用破折号和明显的空格来加大词汇之间的距离。破折号与空格意味着时空的隔离和延长,凸显了物象之间的距离和人的孤寂,饱满的情绪在自然界的刹那定格中达到顶峰,“自然—语言”之间形成了互相映证的格局。这种翻译方法被称作“脱体法”(disembodiment)[8]233。叶维廉认为这是“西方语言的重新发明”,是“利用语句中的空间切断和语法切断来引发出并时性(如罗列意象、不同时间事物的同时并发并列)、蒙太奇和突显视觉性等效果”[14]。
阿兰(Alain)曾谈到:“我认为人们总是可以去尝试这样翻译诗歌(不论是英语、拉丁语或希腊语):逐字逐句,不要添加任何修饰,保留词语原有的顺序……在译诗中却能体味到蕴涵的力量,乍现的灵感,猛烈的冲击力。这样的译本比英语原文更英语,比希腊语更希腊,比拉丁语还拉丁……”[1]115-116之所以能“比英语更英语”、“比希腊语更希腊”,是因为这种语言距离人类普遍语言更近,更能反映语言的本质。形式是每一种语言的独有特性,翻译中若显现或最大可能地显现这种特性而不是抹杀或掩盖它,译语语言就可在自身的呈现中映照出对方的光亮,启示语言更多的可能性和潜力。此即如本雅明所言:“译作不去模仿原作的意义,而是曲尽原作的意指方式,如此一来就像那个器皿的碎片,使得原作与译作作为更高级的语言碎片清晰可辨。”[10]66
(三)不加修饰的用词
现代主义所提倡的简单、直接的语言也是人类文明经过繁华与发达之后返朴归真的诉求。此即“依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在这种复杂之后的简单背后,是观察者和写作者超脱的视界和丰富的历练。斯奈德对禅宗情有独钟,并亲历日本习禅多年,他每年都要去高山、丛林中体验自然的“野性”。道、禅、荒野交相融汇,斯奈德的思想中既有道家与禅宗的超脱、淡然、恬静,又有“荒野”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勇毅和刚性。他融于自然但不遁世,用词简单但不玄虚。同样的寒山诗和唐诗译文,他的译文用词最少,避免迂回曲折,但又往往能直击要点。
以寒山诗翻译为例,斯奈德译本与其他译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简单的用词、直接的表述。与寒山诗的语言类似,斯奈德的译诗采用日常简单词汇;与寒山思想类似,斯奈德追求人与自然的内在融合;与寒山诗的格律类似,斯奈德译本中的诗句有与中文相近的节奏。这些特点使得斯奈德寒山诗体现出一种日常语言的特点:用词直接、简单,情绪朴素、天然。如下面这首《多少天台人》[12]473:
多少天台人,
不识寒山子。
莫知真意度,
唤作闲言语。
Most T’ien-t’ai men
Don’t know Han-shan
Don’t know his real thought
And call it silly talk.
译诗使用了简单的日常生活语言如“real thought”、“silly talk”等,还原了寒山诗的口语特色。现代语言的发展趋势是运用“更短、更简单的词汇形式”[6]25,重新建立起语言和事物本质之间的直接联系。斯奈德的理想是“所见即所写”,正是要去除语言的过滤、雕绘,还原事物的本质。自然本是纯朴、简单的,因此,其对应的语言也必然是纯朴、简单的。这也是自休姆、庞德、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者以来诗歌发展的趋势:用“硬朗(tough)、干燥(dry)”的语言表达思想情感[15]。但这种对应关系和艾略特所主张的“客观对应物”又有不同,它并不是一种人为寻找与组织出来的情感与意象的对应,而且它关注的是具有“荒野”精神的自然世界而非其他,是一种更为简单、直接的相互映照关系。自然就是诗,诗就是自然,这就是斯奈德的语言理想国。
四、以译代作
就语言而论,翻译在各种语言之间建立起联系,在一种语言中映照出另一种语言的光亮。译语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杂合体,所谓源语取向的翻译和译语取向的翻译之别只是杂合程度之别而已。但更大的区别在于译者是否意识到译语的杂合本质及其对于人类语言发展的意义。相对于其他文体,诗歌更便于作为语言糅合的试验地。在翻译中,源语与目的语以某种方式实现了融合,为创造一种比现存的任何常规语言都更具诗性的语言提供了可能,从而创造了区别于源语与译语的“第三种语言”。这样的翻译事实上也是作为译者的作家或诗人的第二种创作,它往往是其主要创作的先锋或实验,成为推动各民族语言、文学的实质性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动力。
批评家认为,庞德译文的美学意义“与其说与翻译相关……毋宁说是与他自己对于革新20世纪初期英语诗歌的认识相关。”[6]5这个评论对于斯奈德同样适用。以寒山译文为例,300多首寒山诗中所选择的24首所塑造出来的寒山形象只能是斯奈德化的寒山。虽然斯奈德译文的语言与寒山诗原文的语言风格非常接近,但只是接近而已,其中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如译文表现出现代化、口语化、意象凸显化等自身独有的特点。事实上,斯奈德是以翻译为方式向寒山致敬,寒山子与斯奈德、寒岩与美国、寒山思想与斯奈德的荒野思想实现了转化和融合,难分彼此。钟玲认为斯奈德有些译文扭曲了寒山诗的原意,认为斯奈德“诗中的自然却是严苛的,具有侵略性的,对人有敌意的……”[16]。然而斯奈德本人及批评家如雅各布·李却并不认同她的看法。事实上,斯奈德的寒山译诗中包含了寒山思想与荒野精神的交融。斯奈德解释说:“我笔下粗野、严苛的大自然意象并非源自一种严苛的感觉,而是因为我的群山是西野拉斯山脉、卡斯克兹山脉——非常狂野,也非常美丽的山脉,有赖这些山脉,我感受到寒山的世界。”[17]在斯奈德看来,大自然无论是狂野还是宁静都只是形式之别,人与自然内在的契合是诗共同的追求,如他这首诗中所写:
When creeks are full
The poems flow
When creeks are down
We heap stones.[18]
诗的生成不是诗人纯主观的活动,而是大自然在诗人心中投射的自然结果。当然,这种投射并非随意、无序的儿语般的词汇排列,而是“大巧若拙”,是一种厚重且巧妙的简单,正如自然本身。
斯奈德的翻译指向其创作,是一种“创作取向的翻译”[19]。这种翻译可以说就是其创作的一部分,但又和其创作相区别。和创作相比,这种翻译中体现出来的实验性、异化性更为明显。它既不回指向原文,也不归属于译语文学系统,而是指向一种更“完善”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代表了译者的理想和方向,也指示了某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可能趋势。
[1]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SNYDER Gary.The Practice of the Wild[M].Berkeley:Counterpoint,1990.
[3]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4]SNYDER Gary.The Gary Snyder Reader:Prose,Poetry,and Translations 1952—1998[M].New York:Counterpoint,1999.
[5]郭军,曹雷雨.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6]KERN Robert.Orientalism,Modernism,and the American Poem[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7]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赵毅衡.诗神远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9]厄内斯特·费诺罗萨.1994,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J].诗探索,1904(3):151-172.
[10]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M].李茂增,苏仲乐,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11]周晓琳,胡安江.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2):125-130.
[12]项楚.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3]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M].梁永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0-21.
[14]叶维廉.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9.
[15]刘燕.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2.
[16]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40.
[17]钟玲.史耐德与中国文化[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4.
[18]SNYDER Gary.No Nature:New and Selected Poems[M].New York&San Francisco:Pantheon Books,1992:201.
[19]李林波.论创作取向的翻译[J].外语教学,2010(3):101-105.
Translation:A Bridge to Construct Poetic Language——A Study on Gary Snyder’s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LI Lin-bo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Wildness”is the core of the American modernist poet Gary Snyder’s thoughts,which is very like“Tao”.He insists on writing natural poems in natural language,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his idea of“wilderness”.He has found in ancient Chinese poems a language closer to the ideal natural language and an almost per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us his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has become an endeavor to perfect English as a poetic language and can be regarded as pioneer and a kind of experimental writing.
Gary Snyder;translation;ancient Chinese poems;wilderness;nature
H 315.9
A
1004-1710(2011)04-0119-06
2010-12-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XYY002)
李林波(1978-),女,西安外国语大学欧美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林漫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