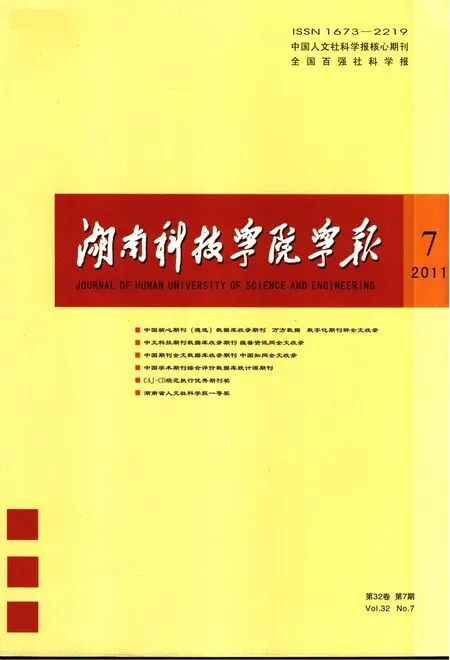后殖民语境下的《好人难寻》解读
杨 春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9)
后殖民语境下的《好人难寻》解读
杨 春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9)
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好人难寻》是奥康纳最受推崇的短篇小说之一,自发表以来就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作品暴力救赎的宗教主题、荒诞的艺术特色已成为评论家的热点话题。而作品中人物所展现的种族和文化优越感,“另类”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以及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对话”的失衡却被人们忽视。论文以后殖民批评理论为指导,深入文本,分析人物,从而挖掘该作品所折射的现实意义。
《好人难寻》;后殖民;种族
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被公认为是继福克纳之后美国南方最杰出的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影响巨大。小说《好人难寻》是奥康纳最受推崇的短篇小说之一,该小说于1953年发表于威廉·菲利普斯和菲利普·拉夫合编的《现代写作选》(第一卷)上,获得了欧·亨利奖二等奖。小说自发表以来就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作品中暴力救赎的宗教主题,荒诞的艺术特色已成为评论家的热点话题,而从后殖民角度分析文本却鲜有涉及。本文试以后殖民批评理论为指导,深入文本,分析人物,从而挖掘该作品所折射的现实意义。
小说《好人难寻》叙述的是老祖母一家驾车去弗洛里达州度假,途中因为老祖母的一念之差,使一家人和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叫做“格格不入”的逃犯不期而遇。由于老祖母认出了逃犯,并顺口道出了他的名字,结果,一家六口惨遭杀害。小说故事情节虽然简单,然而作品所体现的深刻的主题思想和现实意义却耐人寻味,值得探讨。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小说中老祖母对黑人的态度展现了白人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格格不入”的人喋喋不休的话语突显的是边缘人内心的矛盾和困惑,老祖母和家人的命运结局印证了以老祖母为代表的白人中心文化与“格格不入”的人为代表的边缘文化之间“对话”的失衡。
后殖民批评是融合了多种理论和方法的一种集合性话语,它广泛涉及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以及种族、阶级、性别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体来说,它指的是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1]510在后殖民批评语境中,西方中心主义从西方特权视角下审视世界。它利用种族优越性把自身行为规范强加于内部或外部的“他者”,认为西方是理性的、文明的、成熟的、正常的和先进的,而除欧美以外的其他地区和人种则是非理性的、野蛮的、落后的和迷信的。黑人则被视为“下等人”,是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也没有自由和民主自尊的所谓“原始野人”。[2]16对黑人的种族偏见与西方社会标榜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背道而驰,显示的是西方社会道德与文明的荒谬与虚假。《好人难寻》中的老祖母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她自以为是,终日陶醉在阶级和种族的优越感中,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虚荣心很强,时时刻刻都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位高贵的、优雅的文明人,这在小说中老祖母出门前的一番精心打扮中可以看出“老太太头戴一顶草编的海军蓝水手帽,帽檐上插着一束白紫罗兰,身穿一袭印有小白点的海军蓝连衣裙,领口袖口都滚着带花边的白色蝉翼纱,领口还特意别上了一枝布做的紫罗兰,里面暗藏着个香袋。万一发生车祸,她死在公路上,所有人都能一眼认出她是位有品位的太太”。[3]5对黑人,老祖母表现的是看不起和歧视。当她看见站在一间棚屋前的一个黑人小孩时,她用了pickaninny一词。而pickaninny一词在英语里是含有冒犯意的对黑人小孩的称呼,是“小黑崽”的意思。随后,老祖母给孩子们讲了个故事。她说她在做姑娘的时候,有位绅士追求她。那位绅士每周六下午都给她带个西瓜,上面还刻写上他的名字的首字母缩写E.A.T.。有一个周六,这位绅士照旧带了西瓜来她家,当时家里没人,他就把西瓜放在前廊上,然后走了。但那次她没有吃到西瓜,因为一个黑孩子看到西瓜上的那三个字母,就把瓜给吃掉了。在老祖母给孩子们讲的有关黑人的故事里,黑人成了没有教养和文化,贪吃愚蠢的被耻笑的对象。在小说里,奥康纳把老祖母描绘为一位自傲、势力、虚荣的白人形象,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奥康纳于1925年出生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尽管《奴隶解放宣言》多年前就让黑人获得了自由,但在佐治亚州的社会和经济最底层呻吟的仍然是黑人。他们长期过不上体面的生活,无权受教育,火车、汽轮、公共汽车无一例外地都将白人和黑人坐的位置分隔开来。在火车上,黑人即便是买的头等车厢的票,也被勒令坐在二等车厢。因此,黑人的境遇比他们做奴隶时并没有多大的改善。种族隔离和经济分化在奥康纳孩提时期开始就给她烙下了深深的记忆。她希冀通过自己的作品公正地探索自奴隶制度以来困扰在佐治亚州的种族问题,通过展现老祖母这一形象,奥康纳“用一切手段真诚地揭示了人类的堕落和耻辱”。[4]199小说《好人难寻》发表的时代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此时西方社会进入了高度物质文明的现代工业社会。但是物质繁荣却无法弥补经历二战后人们所经历的精神危机以及种族矛盾。在阶级和种族优越感的背后掩盖的是现代西方人的虚伪、孤独与绝望。作为一名洞察力敏锐,极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奥康纳了解美国南方存在的歧视黑人的现象,同时也意识到种族问题的复杂性。她在一次采访中明确的这样的观点:“(南方人的)社会现实使他们比别处的人生存得更为窘困。两个种族生存在一起没有一定的通情达理的气度怕是做不到的,尤其是两个种族的人口各占一半,而且他们的历史独特。非有一套基于相互博爱之上的行为准则是很难实现的……老一套的准则早已过时,而新准则须取之于旧准则的精华——即正真的博爱和需求做基础……全国其他地方,黑人一旦获得权利,种族问题便迎刃而解,而对不论是白人或是有色人种的南方人来说,那不过是开始。南方需要衍变出一种生活方式,以便使两各种族以相互克制的姿态共存。”[5]56而要正真实现种族相互克制,互敬互爱,正真解决种族问题,也许只有靠暴力或死亡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极端手段才能使人们从狭隘偏见的思维定式中解救出来。奥康纳在小说的结尾是这样描述半坐半躺在血泊之中的老祖母:“她的两条腿像孩子一样盘在身下,面孔朝向无云的天空微笑着。”老祖母肉体虽然死亡了,但她微笑的面孔却预示着其灵魂得到了救赎。
后殖民主义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由殖民而产生的“另类”或者“他者”即被殖民者。在殖民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控制、压迫和歧视下,他们无疑变成了劣等民族,自觉或半自觉地有一种自卑和自毁的情结。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受到肉体、精神上的摧残,没有人关怀他们,也不掌握话语权力,他们是既无个人身份,更无经济、政治及文化身份的无势个体,与中心文化“格格不入”。灵魂深处产生的痛苦使他们的心理扭曲,从而挣扎在迷惑与绝望之中。“另类”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在《好人难寻》中是以“格格不入”的人的形象展现的。这个戴着银边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一幅学者派头的越狱逃犯,一方面是“正常”社会的“破坏者”,另一方面又是这个“正常”社会秩序的“受害者”。他处处感到来自社会的压迫和不公,他说“监狱里有个医生头儿说我是因为杀了我爸才被送进去的,但我知道他在说谎。我爸在一九一九年死于流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被埋在霍普韦尔山浸礼会教堂,你可以亲自去看看。”没有人同情他、关爱他。他对生活颇感无望,如同他向老祖母谈到的监狱生活那样“右边是一堵墙,左边是一堵墙。顶上是天花板,地下是地板。我不记得是为什么了,太太”。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法律“对有些人加大惩罚,而别的人可以逍遥法外”。对于代表着中心文化的基督教,“格格不入”表现出的是质疑与困惑,他说“耶稣是唯一能使死者复生的人,他不应该让死者复活。因为基督将一切搞乱了套。如果他说到做到,那么你大可丢掉一切去跟他走;如果他不是说到做到,那么你只好尽情地去享受你最后短暂的时光——去杀人防火,或者干其他卑鄙的勾当”。生活的残酷让他心理扭曲,最后彻底疯狂,因为他“发现犯罪没有什么了不起。既可以这么干也可以那么干。杀死一个人或者从他车上卸下个轮胎,都一样,因为你迟早会忘记你做过什么,只是为你的行为受到惩罚”。塑造这样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另类”形象,奥康纳试图揭示一系列的现实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无法沟通,种族矛盾,现代“文明”的荒诞。在西方“文明”社会里,压根就没有“边缘”人的地位,他们感到的只有屈辱和敌意,感到孤独、绝望、和愤怒,“文明”社会最终把他们逼成了“野蛮人”。从这个意义上看,“格格不入”的悲剧即整个“文明”社会的悲剧。
在帝国主义殖民化进程中,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之间“对话”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这种“对话”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因为种族主义使殖民地人民丧失了自我意识,盲目的认同、臣服于白人的“普遍”标准,从而造成心理的严重扭曲。只有打破这种不平衡、不平等的对话格局,消除“中心”达到多元并生的局面,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不公正,维护社会正义,以达到彼此间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目的。因此,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奥康纳希望通过老祖母一家和“格格不入”的悲剧,让人们意识到现代西方社会道德与文明的狭隘、封闭、荒谬和虚假以及人性的堕落,转而以一种宽容、开放的态度对待一切人和事,从而实现平等“对话”的可能。在小说中,当老祖母在听了“格格不入”的不幸遭遇和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后,一改过去自私、傲慢,对周围人的苦难漠不关心的态度,意识到自己和黑人及其成千上万的如同“格格不入”的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她大脑顿时清醒了一下,伸出手去摸“格格不入”的肩头,并低声说:“哎呀,你是我的儿呢,你是我的亲儿!”从老祖母伸出的充满慈爱的双手,我们似乎看到了人类超越狭隘的自我,走向平等“对话”的希望之光。
衣阿华写作中心主任保罗·伊格尔曾评论奥康纳的作品:“对人性的弱点洞察细微,强硬却富同情心。”[5]44《好人难寻》无疑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反映了奥康纳自觉的批判意识和高尚的人文主义精神,其深渊的现实意义和精湛的艺术魅力定将永驻人间。
[1]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3]弗兰纳里·奥康纳(於梅译)好人难寻[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4]吴冰.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小说评论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5]苏珊·巴莱(秋海译).弗兰纳里·奥康纳:南方的文学先知[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I14
A
1673-2219(2011)07-0037-02
2011-03-01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0年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890408)。
杨春(1968-),女,湖南长沙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英语教学。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