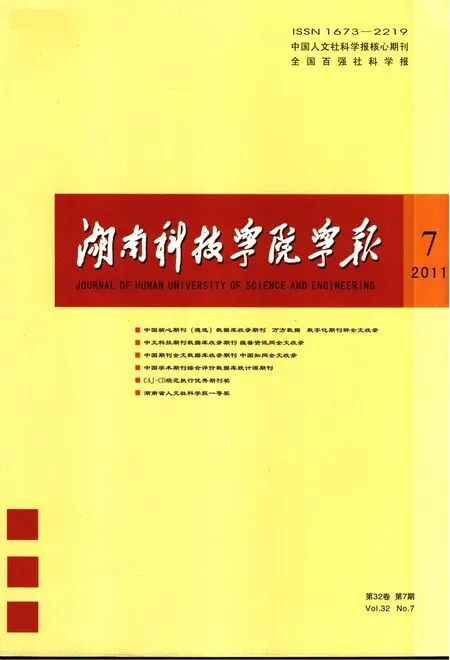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匪盗题材小说中的色语阐释
罗 维
(湖南警察学院,湖南 长沙 410138;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新时期以来匪盗题材小说中的色语阐释
罗 维
(湖南警察学院,湖南 长沙 410138;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国的正统文学意识中,性爱是表现的禁区。在新时期社会转型、文化重构的时代氛围下,作家们开始在文学中正视性和欲,而借匪盗想象来建构一种新型的色语,表达对于两性关系的思考,是匪盗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土匪、性以及女人成为了一个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极具吸引力的组合。可是匪性意识虽有张扬、自由的一面,根深蒂固的农民性却是其根基所在,作家们具有的传统文人趣味也值得怀疑。我们不能指望在对匪性的张扬中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性欲观念革命以及女性意识的解放。
匪盗题材;农民性;匪性
中国的正统文学意识中,性爱是表现的禁区。历史文化中的性总是处于被压抑或者被贬斥的状态,所谓“万恶淫为首”,在礼教文化中性与欲就是一种罪恶,遑论它作为原始生命力的创造性了。在古典的匪盗小说《水浒传》中,性就是被作为不齿的罪恶和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从肉体上对所谓淫妇的消灭成为了塑造绿林英雄的标准之一。
在性别观念上的狭隘性就是《水浒传》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水浒》中通行的“人”或“个人”的概念,完全没有女性在内。由于对性爱持强烈的反对与排斥态度;又由于作者将性爱与女性划等号,使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处理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水浒》中的所有具有性特征和性意识的女性都是红颜祸水,下场悲惨。
性爱主题也是十七年文学的禁区,“革命历史小说以排斥爱情生活来维持革命的清教徒式的纯洁和崇高”[1]63,意识形态中的禁欲倾向非常明显,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往往以“合理”甚至“正义”的面目出现,构成对正常“人性”的贬抑。在新时期社会转型、文化重构的时代氛围下文学对性爱、情欲的表达无疑是一种具有勇气的挑战旧有观念的姿态。作家们开始在文学中正视性和欲,并且体现在小说的主题之中。而借匪盗想象来建构一种新型的色语,表达对于两性关系的思考,是匪盗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土匪、性以及女人成为了一个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极具吸引力的组合。
需要首先认识的是,在真实的民国土匪世界中并没有女性存在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土匪世界是强人的世界,女人天生的生理条件决定了她们无法从事这一行当,还因为在土匪文化中,女人是一个禁忌,很可能和对于女性性活力的畏惧有关系。“其实在中国传统的英雄豪杰中,禁止强奸妇女更多地是因为他们惧怕女人的‘阴气’会带来厄运,而不是出于真正尊重妇女的考虑。”[2]204这种禁忌,从其根源说,还是受到农民的道德观念中对女性的贬抑、对性爱排斥的影响。因此它影响到文学对于女人和性的表现,则是充满贬抑和排斥色彩的。
然而到了新时期的土匪叙事中,一切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进入新时期后的匪盗小说多借匪表达了作家们自身对于历史、文化和人性层面的思考。在构建土匪叙事的视界中,作家们发掘了民间历史的存在(《红高粱家族》),对历史进行深度思考(陈忠实的《白鹿原》),展现地方风俗文化的生命活力(比如河南作家田中禾的《匪首》),以及复杂人性的真相(《黑风景》)。性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生命体验,同时又承载着历史文化的内容,对性的表现呼应着新时期以来对于人性表达和思想解放的诉求。于是性在匪的想象中被予以重新审视,便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蕴含。
女性开始被纳入到匪盗叙事中,和匪共同构成了奇艳的风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贾平凹《匪事》集中的数个中短篇小说,尤凤伟的“石门”系列也是从两性关系角度建构的土匪叙事。土匪、女人和性构成了这些土匪小说中最引人瞩目的地方。
一 性
匪盗想象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民族生命强力的呼唤即蕴含着性的解放诉求。性是原始生命力的体现,“在正常情况下,原始生命力是一种向对方拓展,依靠性来增强生命,投入创造和文明的内在动力。……它是一种确证我们自身价值的方式”[3]。新时期以后中国人在全球化背景下充满了民族振兴的危机意识,同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着对自我主体性的建构愿望。而性是主体性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罗洛梅所言,性是一种确证我们自身价值的方式。
土匪和女人似乎总能让人联想到浪漫和传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土匪和女人之间的性上升到了对于民族生命强力的张扬高度。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的野合写得壮美而野性十足,以性爱的张扬喻示了他们所拥有的壮伟民间力量。这个时候的性欲被赋予了壮美的色彩,和民族叙事这样的宏大主题站在了一起,具有前所未有的崇高之美。但显然这是一种被赋予了浓厚的理想主义和个性主义色彩的色语。
余占鳌把大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棵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了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裸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剽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高粱梢头,薄气袅袅,四面八方响着高粱生长的声音。
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我父亲可以说是秉领天地精华而孕育,是痛苫与狂欢的结晶。
新嫁娘和轿夫在高粱地的私通因为新娘的丈夫不仅有钱而且是麻风病患者而获得了叙述上的道德同情和认可。他们的野合成了对于礼法的蔑视,对于传统的挑战。不仅如此在《红高粱》中,生活在现实中的叙述人“我”以当下的伦理观念将“我奶奶”干脆标榜为个性解放的先驱,女权主义的典范。但所以这一切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轿夫余占鳖私通了新嫁娘、杀了她的夫家父子二人后便上山为匪了。
正是小说中浓厚的匪性意识的张扬(那一片充满生命活力的红高粱野地就是这种民间匪性的象喻),使对于新嫁娘和轿夫的道德约束被消解于无形,连我奶奶也成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女性”,只因为“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
我奶奶是否爱过他,他是否上过我奶奶的炕,都与伦理无关。爱过又怎么样?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红高粱家族》)
这样看来,匪盗想象中的性对于传统规范的大胆僭越似乎是得益于这种“强盗逻辑”,讲求无所拘束、痛快人生的匪性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带来了“女性的解放”和“性的解放”。但不能忽视的是,如果没有民族大义、抗日救国这样的崇高道德的价值支撑,女人和性僭越传统的张扬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更可能是因为我奶奶是抗日英雄,而对于她的其他方面予以道德上的宽容,否则作为后人的叙述人也无需给“我奶奶”头上弄一串英雄、先驱、典范这样空洞的牌坊似的称号了。因此被拔高的性实际上和被贬抑的性同样的不真实。进一步说,可以怀疑作者是否有着对于民间匪性所体现的原始生命强力寄望太甚,以至于忽略了它的污秽黑暗而有意拔高的倾向。
相比之下,陕西作家贾平凹、尤凤伟更多地是从性际关系中去探讨匪盗世界中性的存在,针对的不是匪性,而着意于写为匪者以及与匪有关系的人物们的情感世界,在主人公的情色欲念中表达对于人性的思考。他们只是借这些奇人奇事撑持起小说的叙事空间,于其中探讨生命和生存的本真内容。
而为匪就不易了,未为时便知是邪,死后显然还有遗臭,为什么偏有这么多的匪盗呢?看了志书听了传说,略知有的是心性疯狂,一心要潇洒自在,有的是生活所逼,有的其实是为了正经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正干不成而反干。他们其中有许多可恨可笑又可爱处,有许多真实的荒诞的暴戾的艳丽的事,令我对历史有诸多回味,添诸多生存意味。[4]206
在《匪事》系列中充斥着人的欲望:柳子言的欲望是四姨太,四姨太的欲望是健美的男性身体;白朗从和尚到英雄,再由英雄到和尚,把对女人的欲望熄了又燃,燃了又熄;五魁的欲望是一辈子背着那个天人般的柳家少奶,柳家少奶的欲望就是情欲本身。
匪与女人都是边缘人,与中心人相比,他们面临更多的人生绝境,在人生绝境中,欲望的狂野与绝望更能清晰地凸现。[5]性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种种复杂和冲突。在性际关系中演绎着男女人们的爱欲、仇恨、残忍、自私、怯懦、勇敢……
匪与性这两个元素被糅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奇丽的人性世界,但这不再是现实中的土匪世界,而是作者借以建构人性寓言的叙事空间。它缺少现实的依托,而呈现出一派庄子论道的高蹈虚澹的气象。这是非常文人化的匪盗想象。尤凤伟认为“匪”对于“性”的态度是有反封建性特征和掠夺性特征的。常人在社会规范的制约下,都自觉服从于一种伦理道德,不去表现这种性的掠夺性。匪却不同,他们往往离开社会的规范,直接进入到性的原始状态。而原生的东西往往是人最本质的。因此以匪为切入点,往往可以更好地抓住人性本原的东西,把复杂的人性写好写透。[6]
尤凤伟的《石门夜话》从表面上看,匪首二爷为了将一个有杀亲灭家之仇的女人“和平过渡”到床上滔滔不绝说了三个晚上的话。尤凤伟则称:“石门”写的是人性的隐秘部分,不可启齿的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写生命中理性与感性的搏杀,欲望与道德的搏击,写奔腾于血液中最原始最有力度的因素。写生命的执拗。“石门”不是写性的,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了性。其实性这面旗帜是壮丽辉煌的,上帝为使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给予了性,并为性注入了欢乐。[7]
显然,在匪盗题材小说中,性仍然是一个积极的表现因素。它有助于表达另一种原始生命力,即所谓的“酒神精神”的一面。但在和性紧密相连的“色”之中,却借匪的眼光和视角传统出某种传统文人的心态。
二 女性
在民国时期的匪盗小说中因为不涉及到匪与性的关系,所以几乎没有具有性意识的女性角色。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和匪有关的一切都是丑恶的,像蝴蝶迷和许大马棒的“那堆破事”除了淫荡和丑陋的意识形态标签,并不具有更多的可解读性。那么在新时期的匪盗小说中,性和女人的面目是怎样的呢?
在贾平凹的匪盗想象中,女人通常都是妖艳狐媚,心却率直缠绵,性是把这群大胆率真的男男女女聚拢到一起的纽带。贾平凹借这些奇人轶事描写了许多极端的性格,铺陈出迷离眩目的故事,这些故事具有历史感和蛮荒美,同时又充满了浓厚的地域民风色彩。
“我写作的时候,是出于人的本性,出于一个男人的本性,所张扬的是一个本质的天然的女人。”[8]贾平凹坦陈自己是从男性意识的角度表现本质天然的女性。他的小说里充满了从男性主人公的视角对于女性美的赞美。这种赞美和《红楼梦》中对于女性的赞美不一样,如果以灵与肉来区分,更多的是对女性肉的层面的赞美,也就是身体散发的色之美。值得商榷的是,他的视角是否能完全代表男性,而表现的女性又何种程度的具有纯粹天然的女人性。
在又一个炎热的中午,女人洗罢了澡来到楼室,头发蓬松地披在后肩,没有穿紧身的长袍而是短袖和裙子,露出了玉白的小腿和胳膊,甚至那没有扣起领而自自然然半遮半显的一截脖根,最是那一朵才摘下的沾满了水珠的玫瑰,让他看见,也见了插着玫瑰的那一处丰满异常的胸位了。(《白朗》)
咫尺之间,尤物一腿微屈,一腿提起,弓弓窄窄的一只小脚恰恰点地,将印花围裙系着的一件桃红旗袍裹弄得了美美妙妙的弯曲。(《晚雨》)
作者对女性的描写中有很多肉的意象和身体部位的意象,包括脖子、小腿、胳膊,还有男权社会旧式男性文人的最爱—小脚。在性与生殖目的相对分离后,女性价值就主要体现在所谓“女性美”上面。“女性美”究其本质,是对男性性审美欲求的迎合。它主要表现在面貌美和体态美两方面。因此对于女性美的描写中,作者的审美趣味里释放着男性性审美的欲求,但这种欲求似乎不脱旧式男性文人的趣味,区别在于:这里的肉感不断释放的情欲气息,是生命欲求的一种象征。只不过,这种富于挑逗意味的女性之美并不能反映女主人公本身对于生命欲望的追求和表达。她们仍然是被动地展示在男性的眼光中,而不是主体的内在欲求的展现。她们成为点燃土匪们内心欲望、张扬生命强力的原始动力。《美穴地》中姚家长工苟百都正是在姚家四姨太的艳色压迫下,横心上山为匪。
女性怎样的美才会移人,也就是点燃男性的欲望,甚至是“匪性”呢?
天鉴说:“仅是美色并不能移人,城西头绢丝店里有绢做的美女,颜色较王娘胜十倍,我去看了怎不害相思?美女能不能移人,在媚态二字,媚态在人身上,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王娘正是这般女子,一见即令人思之不解自己,才舍命以图你哩!”(《晚雨》)
这一段冒充知县的土匪天鉴所说的女人经,更像是从明清小说中抄来的文人秀才对女人的评头论足,无论如何也不像是杀人劫货的土匪对女人的心得。作者自己也觉得土匪说这话太不像,但又实在想表明对于女人之美的高明看法,于是让做了官的天鉴向王娘解释是从书里看到的。显然小说里对于女性美的欣赏不是属于土匪的,而是属于文人贾平凹的。最具有说服力的是,《红楼梦》中个个女子的美各有不同,而在贾平凹的匪盗小说中,女性只有类型特征,而并不个性化,因为不具有主体性。单从对于女性情欲的表现上看,贾平凹如此陈旧的男性意识,使他远远不能和四十年代写《饥饿的郭素娥》的路翎相比。
无独有偶,尤凤伟在他的匪盗系列小说“石门”系列中也有这样的对女性的评头论足:
二爷道:“说到女人,不免又要岔出些枝蔓,还望七爷拿出些耐心。不知七爷可会写个“女”字?圣人造字,其妙无穷,造“女”字为洞穴之状,潭渊之态,像形为女人之私。……女人亦如此,以相貌论有姣美丑陋分,以心性论有高贵粗俗别,然世事多有蹉砣,难尽如人意,有仙娥之态而伴之蛇蝎肚肠,妲己可证;有丑恶之貌者又赋之高洁之心性,宛其可证。优劣相交,良莠不齐,此便为大众。而集形美心怡为身者为女中尤物,芸芸众生,尤物难求。(《石门呓语》)
在《石门呓语》中自命风流的瓢把子二爷在表达对女性的看法时,并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是自高而下的审视,仍然视女性为物,最好的女性也不过是尤物。对新夫人也是由爱生怜,在爱怜中充满了男性的优势感。这哪里像土匪对女性的看法,完全是写作者“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
因此在土匪这个虚拟世界建构的两性关系上,虽然看上去很美,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野性和率真表达,女性也不再处于性受到压抑的状态。但实际上传统并未得到结构性的改变。也许贾平凹尤凤伟们自己也未曾意识到,他们小说中的男人视角中更看重的是女人的自然存在——性存在而忽视了其作为女人的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忽视了女性的创造力和终极价值。最终的结果不仅使女人得不到解放,相反还让女人在绝望中死得更加凄凉。
土匪出于自身的安全感对于女人的内心需求是漠视的。白朗尽管不近女色,他却不是出于对女人的尊重,相反是觉得“女人是老虎”,一旦陷进感情的漩涡容易误事;唐景一听说柳家媳妇是白虎星吓得马上让五魁把她背走,他把女人当作生活的必需品和山寨的配件。《晚雨》中天鉴对王娘的“牵挂”也是自己“尘根”惹的祸,根本谈不上对王娘的尊重与理解,所以一听到王娘过去作风有问题就觉得不得体,彷徨放弃,最终王娘在世人的恶骂和天鉴的冷落中死去。《美穴地》中四姨太被嫁给了姚家掌柜,又被当了土匪的姚家长工苟百都抢去做了押寨夫人。苟百都被杀后,她又被带回姚家,刚生下的孩子被当着她的面活活摔死。她为了抗争,生生将自己的脸给毁了,才得到善终。其他故事中的女性却都死得很悲惨。
白风寨的寨主唐景的押寨妇人只因为在荡秋千时,裤带断了裤子脱溜下来,让在场的人都看见了不该看到的部位。于是不允许在自己辖地有什么有违人伦的事情的唐景便开枪打死了秋千上的女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唐景自己却是母亲与儿子乱伦而生的。
这些土匪并没有因为女性同样深受男权社会的压迫而对她们有丝毫的帮助和解脱,相反还把自己所受到的压抑歇斯底里地发泄到女人身上,按照男权社会的逻辑变本加厉地摧残已是伤痕累累的女人。奴才苟百都当上土匪后抢走了四姨太,在回家的路上就对四姨太实施了强暴。女人只是性欲满足的工具,漂亮女人被当作挽回自尊的象征。沈从文在上半个世纪曾写的《在别一个国度里》的那种山大王娶亲的浪漫故事是看不到了。
当新时期文学中匪与性与女人相遇,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来自男权社会的农民的道德价值观作祟,这说明匪性意识虽有张扬、自由的一面,但根深蒂固的农民性却是其根基所在。我们不能指望在对匪性的张扬中能够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性欲观念革命以及女性意识的解放。
[1]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美]菲尔·比林斯利(王贤知译).民国时期的土匪[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3][美]罗·洛梅.爱与意志[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4]贾平凹.《逛山》后记[A].贾平凹文集·侠盗卷[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5]孙新峰.《山匪》:商州土匪题材的新突破[J].当代文坛,2006,(5).
[6]尤凤伟,王光东.关于一种创作倾向的对话[J/OL].当代中国文学网,http://www.ddwenxue.com.
[7]尤凤伟.文学与人的境遇[J/OL].当代中国文学网,http://ww w.ddwenxue.com.
[8]秦绍峰.《匪事》的女性意识[J].陨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5).
I247
A
1673-2219(2011)07-0033-04
2011-04-01
罗维(1974-),女,湖南长沙人,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年进站博士后,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土匪文化。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