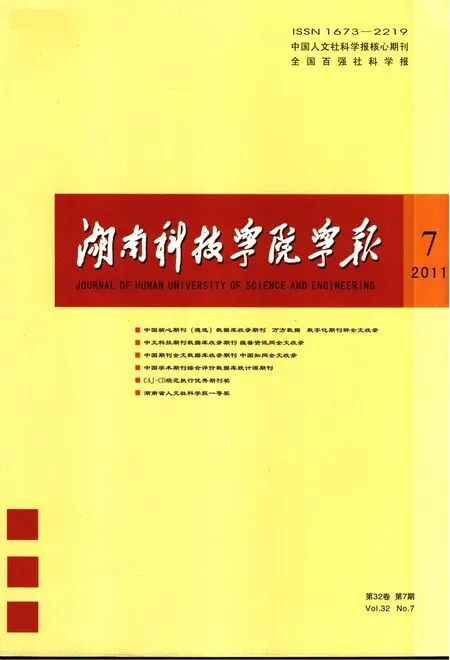公正与疏导:先秦儒家对社会“怨”情的防治
刘美红
(星海音乐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 广州 510006)
公正与疏导:先秦儒家对社会“怨”情的防治
刘美红
(星海音乐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东 广州 510006)
在先秦儒家看来,“怨”是一种潜藏着巨大否定激情和破坏动能的生存体验,它往往是社会失序、政治祸乱的根源,因而不可不严肃对待和尽量防治。先秦儒家对社会“怨”情的防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积极方面提出了一套制度设计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施,其中最基本的便是“天下为公”的政治原则,“各尽其能,各得其分”的分配原则以及救济社会弱势群体的人道原则;二是从消极方面强调统治者应对社会“怨”情进行及时、合理的疏导,而不是强行压制。
怨;社会防治;公平正义;合理疏导
一 引 言
在早期儒家的话语系统中,“怨”作为一种潜藏巨大否定激情和破坏动能的负面情感体验受到了极大关注。据笔者初步统计,“怨”字在《尚书》中出现20次,《左传》中出现95次,《礼记》中出现了30次,《论语》中出现了20次。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怨”被视作社会危机和政治动乱的心理根源。《左传·成公十六年》单襄公谓:“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荀子谓:“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作也”(《荀子·致士》)①把“怨”同社会祸乱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儒家的专利,而是先秦各家的共同看法。“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无怨也。”“凡祸乱之所生,生于怨咎。”(《管子·版法解》)“凡天下祸纂怨恨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从个体修养的角度来看,“怨”常常被赋予一种伦理的意义。面对人生境遇中的伤害和逆况,“怨”抑或“不怨”是“小人”与“君子”、“不仁”与“仁”的重要分际。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又言:“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论语·宪问》)孟子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荀子亦有“君子见闭则敬而齐……小人见闭则怨而险”(《荀子·不苟》)之说。对儒家而言,“怨”始终代表着生存的非常态和生命的不完美,因此必须努力加以克服和消解。先秦儒家反复强调“无怨”、“不怨”、“远怨”,并对如何避免“怨”以及“怨”出现后如何进行克服和消解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论述。
“怨”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不当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所致,例如利益至上主义(过度的欲望)②《论语·里仁》“放于利而行,多怨”,便是强调任由欲望牵引必然招致怨恨。,自我中心主义(病态的自爱)③自我中心主义歪曲了自我与世界的真实关联,实际上一张由病态的自爱和自尊编织的幻觉牢笼。这种唯我独尊,无视他人存在和价值的思维方式无疑是致“怨”的重要元凶之一。以及德福现世报应的正义论(不当的苦难释义)④艰难困厄处往往易生“怨”心。然而,“怨”并非苦难的必然产物,苦难对人所发生的实际影响与人自身对苦难的反应和诠释相关。不当的苦难释义将加剧主体与环境的冲突,导致主体心态的失衡。《论语·宪问》 “贫而无怨难”,与其说是要揭示苦难与“怨”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使“怨”的发生显得情有可原,不如说是要强调“贫而无怨”之难能可贵,即便身陷困厄苦难之境,人仍有“无怨”的精神自由。德福现世报应的正义论主张德福的现世配享,即有德者有福,常常使自居正义者将挫折和苦难释义为“不公正”,这是导致怨愤心态的导火索。都是致“怨”之元凶。正因为如此,先秦儒家十分重视道德修养与礼乐熏陶对个体心性品质、人格性情的改良和提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先秦儒家把“怨”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个体因素,否认“邪恶”环境对人心的负面影响,从而放弃对外在环境进行改良的努力。实际的情况是,先秦儒家同样非常强调怨忿情绪产生的社会根源。例如,民不聊生、分配的不合理、机会的不均等、权力的腐败等社会因素都是导致不满积聚和怨忿形成的重要动因。因而,先秦儒家对社会“怨”情的防治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心性修养和改良的问题,它还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外在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的合理安排建构问题。特别是当“民怨沸腾”,即怨愤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集体情绪时,先秦儒家往往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当权统治者以及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而非民众的心性品质。
先秦儒家对社会“怨”情的防治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积极方面提出了一套制度设计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施;二是从消极方面强调统治者应对社会“怨”情进行及时、合理的疏导。这些无疑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如何消弭民众怨恨,走向健康和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 社会公平正义的实施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诉求,是维护社会生活平衡、和谐和稳定的根基,也是先秦儒家防治社会“怨”情的根本内容,所谓“政均则民无怨”(《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也。
早期儒家心目中公平正义社会的典型形态便是《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其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儒家认为,一个公平正义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点:一是天下为公;二是各得其所,各尽所能;三是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这三个要点构成了先秦儒家社会公平正义论的基本内容,其中“天下为公”是公正社会最根本的价值原则,“各得其所,各尽所能”是公正社会的总体结构特征和根本分配原则,而对鳏寡孤独废疾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则是公正社会的内在人道要求。
(一)“天下为公”的价值原则
在先秦儒家看来,“天下为公”是“大道之行”的根本体现,因而是人类正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⑤实际上,这也是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看法。古代思想家普遍认为,“大公无私”是宇宙本体之道的本质属性,因此人类的各种制度、规范、思想、行为都应该以“公”为基本准则。儒家以天地之道“至诚无息”、“厚德载物”等属性论证“公而无私”的圣人之道;老子以天地“不自生”来论证圣人“无私”,并谓:“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老子·十六章》)法家则以道的包容万物、一视同仁的属性论证立君为公、法立公义、法治公平。阴阳家则以天地四时的公道诚信来解说政治起源和之道法则。《吕氏春秋·去私》以“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来论证天下、君位为天下之公有,而非一人所私有。。
“天下为公”首先是一个关于政治价值法则及合法性的判断。“公天下论首先回答的是设君之道,而公天下论的第一要义是立君为公。在这个意义上,公天下论属于政治本体论的范畴,它集中回答了君主制度的来源、目的和功能等根本性的政治理论问题。”[1]281根据这一判断,政治权力或君主之位的设立,不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特别是君主之私欲,而是为了实现天下民众之公益。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说得更为直接明了:“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其次,天下为公也是一个关于政治权力开放性原则的断定。先秦儒家对政治权力的开放性要求集中体现在“选贤与能”的主张中。先秦儒家认为,君位不可为一家一姓所私占,而应荐贤举能,让才德者居之。君位实质上只不过是为天下谋福利之公器,谁有资格占有这个权位,谁有资格使用这个公器,并不是先天预定、永恒不变的,而是完全取决于他是否具有利益众生的意愿和能力,即能否履行为天下谋福利的天职。不仅如此,臣下之位的任用也应当以后天的才德而非先天的血缘为主要依据。天下之善治不可能凭持君主一人之好恶才智而得以实现,选拔与任命贤能之士,“以天下治天下”,“与天下人共治之”,是明君圣王化成天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环节。
(樊迟)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再次,从具体的权力运作层面来看,天下为公还是一个关于行政公平原则的判定。“公则天下平矣”,“天下为公”之“公”本身即含有“公平”、“公正”的意思,它要求统治者破除一己之偏私与好恶,按照公共的理性精神和是非准则来(“公义”、“公道”)来治国行政。《尚书》中有:“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尚书·洪范》)孔子把公正视为评判政治家的重要标准,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荀子同样强调行政公平原则的重要性,他说:“上公正则下易直矣。”(《荀子·正论》)又说:“公生明,偏生暗,诚信生神,夸诞生惑。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荀子·不苟》)在先秦儒家心目中,礼(法)是公的体现,以之为准绳就能超越偏私地衡量事情的轻重,从而做到公平正义。“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以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队。故法而议,职而通,无隐谋,无遗善,而百事无过,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有其法者以法行,无其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辟也。”(《荀子·王制》)
(二)各得其分的分配正义
分配正义是社会正义的核心问题。每个社会的基本资源总是有限的。如何将这些有限的资源在社会成员间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使人人各得其分并免于恶性的利益争斗,是分配正义的根本主题,是关乎社群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先秦儒家防治社会“怨”情的内在要求。
先秦儒者认为,如果不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作出一种制度性安排而任由人的自然性情,那么势必导致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争斗并危及社群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在先秦儒家那里,理想而正义的分配形式便是礼。
无礼义,则天下乱。(《孟子·尽心下》)
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国》)
礼起于何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所谓“分”即通过划定度量分界,将社会资源按照一定标准或制度分配给社会成员。先秦儒家常常用“均”来表达其分配正义的诉求。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荀子指出,人君应该“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荀子·君道》)《礼记·祭统》:“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为政者如此。故曰:见政事之均焉。”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所言之“均”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而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利益均衡与和谐,它要求社会资源的分配与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地位相一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王制》)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第一也,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王制》)
在先秦儒家看来,等级差异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社会有序运转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孟子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也指出:“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并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终则始,始则终,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万物本来就是有差等的,人为地将他们齐平,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公平而正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等差分明,人人各安其分,不逾其等的社会。
然而,等级差异尽管不可避免,但等级差异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公正的,关键是划分与确立社会等级差异的原则是什么。进一步而言,“礼所确认的社会等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运作机制必须具备公正性、合理性,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否则就不仅无法有效地实现其社会功能,而且还会引发矛盾和冲突,导致社会的动荡和危机。”[2]等级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然的等级关系,指人们之间天然地存在着辈份、年龄、性别、宗法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等差异,由此而形成了父子、长幼、亲疏之类的等级分野。另一类是非天然的等级关系,指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尊卑、贵贱、上下的等级之分。前者因自然的血缘而来,不能为人自由选择和更改,因而无所谓公正与不公正。后者则是后天人为建构的,才有所谓公正与否的考量。
儒家的观念中,公正而合理的社会等级分定应当以品德和才智为基础,即让才德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享有较高的社会待遇。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朝矣。(《孟子·公孙丑上》)
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
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荀子·君道》)
凡爵位、官职、赏庆、刑罚皆报也,以类相从也。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不祥莫大焉。(《荀子·正论》)
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荀子·王制》)
以才德为主要标准来划分社会等级从而分配社会资源是先秦儒家对正义社会的基本信念。与之相应,由自然血缘关系决定的天然等级分野则退居次要的地位。荀子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才德与血缘不同,它是后天的,是人经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获致的,因此以才德为基准的等级社会必然是开放而流动的社会。如此一来,在儒家以严格的差等为正义原则的礼义分配模式中实际上又暗寓了平等的理念,体现了对社会合理性与公正性内在诉求。
(三)救济社会弱势群体的人道原则
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出现分化,因而产生一批社会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贫弱群体的诉求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表达与正确的应对,就会积压怨恨情绪,这种对社会的怨恨情绪在一定情形下还有可能不断扩散、蔓延,久而久之,会对社会稳定、和谐产生消极影响。”[3]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对他们进行积极的救助与扶持,使其基本生活和人格尊严得到保障是正义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消弭社会怨恨,实现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主题。
对贫困、年老及鳏、寡孤、独、废、残等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和保障是先秦儒家王制理想的重要内容。“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生活。孟子追述了文王养老的故事,认为“养老尊贤”(《孟子·告子下》)是仁政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多次强调,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五十岁以上的人有丝棉袄穿,七十岁以上的人有肉吃,并指出:“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离娄上》)《礼记·王制》则主张:“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荀子·王制》开篇即主张,对哑、聋、瘸、断手和发育不全的“五疾”之人要“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食之,兼复无遗”,又强调“收孤寡,补贫穷”。《周礼·地官·大司徒》把慈幼、养老、振贫、宽疾、安富称为“保息六养万民”。《礼记·礼运》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在先秦儒家那里,社会救济和保障没有停留于单纯的价值理念层面,而是落实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对老、幼、鳏、寡、孤、独、疾等因个人生理原因而缺乏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酌情减免徭役赋税。孔子:“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独、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国语·鲁语下》)《周礼·地官·乡大夫》中规定:“国中自七尺以上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贾公彦疏:“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这就是说国都及近郊十九岁以下,六十岁以上,郊外农村十四岁以下六十五岁以上,年老以及残疾、患病之人,都可以免除力役。不仅如此,对于年老或身患重症残疾从而生活无法自理,需要照顾者,不仅要免除本人的力役,还要酌情减免其家属的徭役赋税。《荀子·大略》提出:“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举家不事,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事。”这样的规定还见之于《礼记·王制》和《礼记·内则》:“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瞽亦如之。”
二是对懵懂无知的幼者,年高智昏的老者以及智力低下者酌情减免刑罚。《周礼·秋官·司刺》规定有“三赦之法”,即“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周礼·秋官·司厉》中规定:“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国奴。”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儿童,都不罚作奴隶。《礼记·曲礼》也提出:“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三是对丧失生产、生活能力的社会弱势群体由国家进行救济和供养。《礼记·王制》规定:“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之谓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喑、聋、跛、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对于矜、寡、孤、独废疾者,国家要按时给以救济。各类残疾人在国家收养的前提下,量能授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荀子·王制》亦云:“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夫是之谓天德,是王者之政也。”在先秦儒家看来,对社会弱者群体或遭受自然灾害者实施社会救助是君王的根本责任。荀子说:“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荀子·富国》)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社会的财富主要集中于国家,只有国家才有条件真正有效地进行社会救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秦儒家把实施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归之于政府国家。吕思勉先生曾指出:“时愈近古,则赈济之出于官者愈多,以官家之财产较多也。”[4]538
三 社会怨情的合理疏导
在先秦儒家的民本政治话语脉络中,民情具有神圣性,它与天意直接贯通,统治者要顺从天命,就必须遵从民意,正如《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遵从民意的首要任务便是充分体察民情,了解民众的需求、疾苦以及集体性的心理情绪。
天畏 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
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
民情即民众的好恶往往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共识和集体心理,它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得失提供了一面镜子,正所谓“大可见”,因此应该被统治者严肃对待。
在各种社会情绪中,先秦儒家尤为重视“怨”情。《左传·成公十六年》单襄公谓:“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荀子谓:“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乱所以自作也”(《荀子·致士》)先秦儒家认识到,“怨”是一种潜藏巨大破坏动能的情绪,它往往是社会失序、政治祸乱的根源,因而不可掉以轻心。《尚书·康诰》说“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又说:“呜呼,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就是告诫统治者应该防微杜渐,认真防范并及时处理社会“怨”情。
先秦儒家反对统治者以傲慢的态度置民众的批评和怨愤于不顾甚至进行暴虐地压制,认为此种方式不但不能止怨,还将导致更为危险的结果。《国语·周语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据载,周厉王十分暴虐,引起国人的极度不满,于是出现“国人谤王”。周厉王派卫巫监谤,强行加以镇压,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对之自鸣得意,并告召公曰:“吾能弭谤耳,乃不敢言!”国人敢怒不敢言,实际上酝酿着深重的政治危机,召公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极力劝谏厉王: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子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 诵,百公谏,庶人传语,进臣尽规,亲戚,补查,瞽史教诲,耆爱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召公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他奉劝厉王创造一个自由而宽松的言论环境,像疏导河流一样使民众畅所欲言。遗憾的是,召公的意见没有被周厉王所采纳,于是终于酿成了“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的恶果。
强行的压制只会加深社会怨情,而合理的疏导,有序的释放则能起到缓解怨情,化解矛盾的作用。舍勒就曾指出:“倘若这些激情释放出来,情形则将不同。例如,作为一种类型的群众激情及其释放工具,议会机构有极大意义。尽管这些为国家服务和立法服务的机构有时也对公益有害。净化报复的刑事法庭、决斗、(在某种程度也包括)新闻(只要新闻通过怨恨的扩散不是在加深怨恨,而是通过情绪的公开流露在减少怨恨)也同样如此。激情就在这些形式中释放出来,否则便成为怨恨的心理炸药。”[5]426-427与周厉王强行压制怨情表达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记载的“子产不毁乡校”的事迹: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子产执政的第一年,对郑国的田地疆界和沟恤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改革,以致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和怨忿,甚至放出“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左传·襄公三十年》)的狠话。子产没有对民众的不满情绪进行粗暴的压制,而是采取了合理疏导,择善而从的方式。子产执政三年后,郑人对子产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仇恨变成了爱戴。《左传·襄公三十年》:“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不毁乡校”的行为典型地体现了他成熟而高超的政治智慧,连不轻易许人以“仁”的孔老夫子也忍不住要称之为“仁”,可见赞赏之情非同一般。
在先秦儒家看来,普遍的民众怨忿情绪表达了民众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批判,它往往反映出为政者的过失,是民众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意愿没有得到尊重而发出的抗议。因此,明哲的统治者不应该迁怒于民众的詈怨,而应该善于从民众的詈怨中反省自己,察知己过,并及时调整政治、修订政策,从而纠正过失。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而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
社会“怨”情尽管具有十分重大的破坏潜力,但如果统治者能够及时而正确地对之进行回应,那么它不但不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相反,它能够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不断改善的重要动力。理想的社会政治理应是和谐、无怨的社会,但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它必然是在不断地与民众进行互动,不断地了解与满足民众需要,尊重和顺从民众意愿的基础上而动态地实现的。明哲的统治者,总是能够虚心而真诚地体谅民众的怨情,并从中了解民众的需求和意愿,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从而最终实现“无怨”的王道政治。
[1]张分田.公天下、家天下与私天下[A].刘泽华,张荣明.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白奚.儒家礼治与社会和谐[J].哲学动态,2006,(5).
[3]李迎生.制度建设与社会公正[J].教学与研究,2007,(5).
[4]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A].舍勒选集:上[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B222
A
1673-2219(2011)07-0064-05
2011-04-01
刘美红(1982-),女,湖南衡阳人,哲学博士,星海音乐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与管理哲学。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