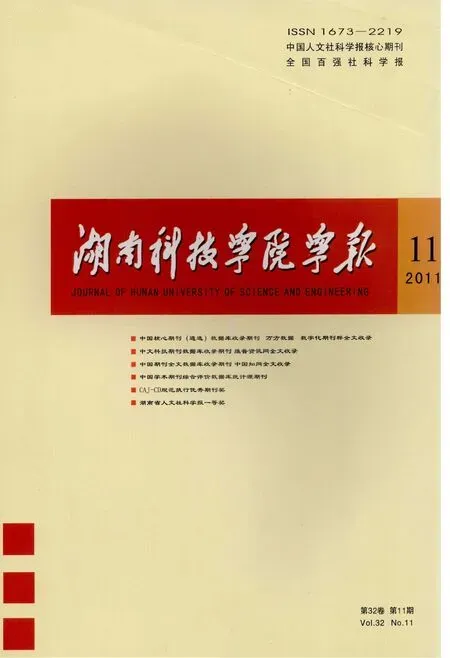妈祖“大爱”与基督“圣爱”的文化比较
吴晓红
(莆田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福建 莆田 351100)
妈祖“大爱”与基督“圣爱”的文化比较
吴晓红
(莆田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福建 莆田 351100)
妈祖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折射出的“大爱”精神对构建和谐世界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基督教的“圣爱”是西方文化传统中对爱的最高体现。对两种精神产生的文化渊源、实质和现代意义的不同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加促进现实生活中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相互交流,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妈祖;基督教;大爱;圣爱;文化比较
在中华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史上,以“博爱”、“仁爱”为精髓的中华“至爱文化”,历来为无数先贤所倡导也给炎黄子孙以熏陶。植根于中华传统“至爱文化”的妈祖大爱精神是社会发展进步中一股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而基督教的“圣爱”精神是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大爱”与“圣爱”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本文拟从文化的视角对二者进行比较,旨在更科学地认识“大爱”与“圣爱”,找出两种思想对人类文明发展可能会产生的积极影响,从而为人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帮助。
一 “大爱”与“圣爱”产生的文化渊源不同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在繁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汉民族文化为代表,又吸收各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体系,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性,又具有时代特征。历史上无数的圣哲先贤的思想是这一文化体系的主流,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中最为核心和代表性的是“仁爱”思想,其将“仁”与人的本质结合在一起,孔子认为“仁”是做人的根本原则,“仁”即“爱人”,“仁者爱人”的对象不仅超出了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也超越了血缘宗法之爱。[1][P55]儒家这一“仁”的思想是从最基本的伦常情怀出发的,但必须以“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为本。既肯定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与伦常感情的需要,又显然有一个超越小我,超越家国的指向,因而仁爱具有超越个人到天下的意义。[2]孔子的“仁”爱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道德精神和高尚情操,因此,他的“仁”的学说中蕴藏着大爱精神的萌芽,我们可以说大爱精神是我国历史文化中与生俱来的人文精神,具有民族特质。
与孔子同时代的墨子则在保留孔子之“仁”的“爱人”基础上,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他认为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要求君臣、父子和兄弟都有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的。因此,墨子的“兼爱”学说体现出“等同人我,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和博爱精神。
此外,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倡导“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把“道”引入对人的认识之中,他认为,人的本性同道一样,无为自化,自然而然,人与天、地、道具有同等的位置。老子强调,圣人和统治者不应有偏私之心,要随时以百姓的思考和需求为自己的思考与需求,即“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3]道家所倡导的这一道德原则也是大爱精神的合理组成部分。
传说中的妈祖聪明灵慧,悟性高,从小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自幼就养成了向善的道德意识,仁爱善良是她的天赋秉性,她将救人于危难视为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妈祖的大爱精神并不是单纯的继承哪一家的学说,而是取各家之长,扬长避短,提取其中最圣洁最纯真的爱的精髓,因此具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
西方基督教的“爱”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爱”在基督教义中占据核心地位,《圣经》中的爱有四种:亲情(Stergo)、友情(Philia)、爱情(Eros)、圣爱(Agape),而圣爱(Agape)是最高的。[4]“圣爱”在希腊文化中是指为了对方而慷慨地付出,又可指诚爱、敬爱、专一的爱和原则的爱,所以基督的“圣爱”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文化,古希腊语言和文化的广泛传播对犹太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犹太教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以供忘记了母语的希腊化犹太人之用”。[5]基督教就是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古希腊人强调人际之间的“爱”,即“友爱”(Αγάπη,英文为friendship and love),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对“友爱”这个范畴进行了深刻地分析,认为“友爱”是城邦团结发展所必须的。这种爱突破了血缘氏族的局限,而把“爱”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城邦,出现了公民之间平等的“友爱”,家庭中的亲情只是“友爱”的一种。[6]古希腊中“爱”的文化语境,无疑有利于基督教伦理思想的抽象提升,有利于犹太教“愤怒的”上帝,转化为基督教“爱”的上帝。[7][P146]
古罗马文化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的文化,公元前后在古罗马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是晚期斯多亚学派,它对正在兴起的基督教以直接的影响。[7][P115]斯多亚学派主张自然法思想,认为“逻各斯”或“自然法”是宇宙的主导原则,世界是理性的,人是世界理性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受同一世界理性的支配,因此,“人都是神的儿女,相互间都是平等的”。[8]这种平等思想打破了城邦时代对奴隶和外邦人的种种偏见,后来直接被基督教所吸收。既然自然法是普遍的,人类社会也应该是统一的,斯多亚派因此还提出了世界主义的国家学说,主张“真正的国家或理想的法律都是没有民族界限的”,“任何人都可以取得公民权”。这种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把所有人都放入视域的思想无疑也是有利于早期基督教“博爱”思想形成的。[9]
二 “大爱”与“圣爱”的实质不同
“大爱”精神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人们对人类自身的价值、前途和命运的自觉关爱,是人类在自身的社会实践中,逐步自觉于时代传承发扬起来的高度负责与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平等和谐的友爱精神。[10]妈祖生平有许多传说叙述了她的善举,据《天后志》记载的有十五则,据《天妃显圣录》记载的有十六则,如“祷雨济民”即妈祖烈日中应邀祈雨,解除莆阳大旱;“挂席泛槎”即妈祖以草席代舟,帮船民飞渡凶涛;“化草救商”即妈祖将稻草化为大杉,扶济商舟脱离海难;“灵符回生”即妈祖凭借药草和符咒,巧手救治疫民;“伏机救亲”即妈祖伏在织机上拯救溺海父兄等等。妈祖这种普世的大爱精神植根于广大农村,具有广泛的平民性,她生前的善举彰显了她忠义孝悌、乐善好施、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惩恶助善的美德。对社会大众而言,妈祖大爱无疆的精神是一种人文关怀精神,她将救人于危难视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不计较报酬,将生死置之度外。因此,妈祖的大爱精神可以说是“其对自身的价值、前途和命运的自觉关爱、高度负责与无私奉献精神”,[11]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的爱。
“圣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理念,在《新约全书》里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上帝对世人的爱;二是世人对上帝的爱;三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爱。这三者是一种因果关系:上帝即神创造了爱,并将爱赋予人类;上帝爱人,使人体验到圣爱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愿意以爱回应神的爱,进而博爱他人。人们接受圣爱就能够体验到并分享到圣爱,这样就有爱的动力,提升自己去爱他人,人对上帝的回报体现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爱的过程中,所以基督的圣爱是建立在神人的关系之上的爱。
三 “大爱”与“圣爱”所蕴含的现代意义不同
妈祖的大爱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脉相承,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妈祖的大爱精神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特别是从事海上海事活动中,面对自然灾害等种种磨难,特别希望有一种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超自然力的神灵来护佑他们。妈祖作为仁爱慈善、救苦救难的化身,向人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其消灾解困,这就有形无形中给人们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鼓舞人们去征服自然,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奋斗。其次妈祖的大爱精神与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所倡导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她的亲和力和认同感使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更易为群众所接受,特别表现在一批又一批的台湾同胞,怀着对妈祖的崇敬之情,从绕道到直通,从民间到官方,从几个人到几千人,如潮水般涌向湄洲妈祖庙朝圣,开启了两岸交流。台湾同胞从朝拜妈祖到寻根认祖,再到访亲探友、参观旅游、投资兴业,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又可喜的过程。两岸同胞年年齐聚一堂,同谒妈祖、共享平安、互相祝福,以共同的语言和心愿,表达炎黄子孙血浓于水的亲情。妈祖大爱精神不但成为连结两岸民众心灵的纽带,而且是架通五洲四海的连心桥,目前已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5000多座的妈祖庙,信奉者近2亿人。再次,妈祖大爱精神还具有潜移默化的社会教化作用,千百年来,人们心中的妈祖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社会道德楷模,反映妈祖优秀品质的传说故事从乡里四邻不胫而走,传遍四面八方,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几乎都有妈祖的宫庙和信众,人们在拜祭妈祖时,一方面祈求妈祖保佑,一方面以妈祖为镜子修身养性。受妈祖精神的陶冶和感召,在潜移默化中滋长了与人为善,与世无争、和平相处的思想。
基督教的“圣爱”精神同样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基督教作为宗教为人类提供了终极关怀的模式,它针对的是普遍的人性,能跨越国界的。“圣爱”精神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文化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再次成为人们共同寻求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的“爱上帝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的道德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为人们找到了一副医治道德失落感的药方。通过自我体验,人们将基督教的精神价值与现代科技文明中的知识价值结合起来,使人们在享受现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又能满足高度情感的需要。[1][P58]
最后,差异不等于优劣。对于妈祖的“大爱”与基督教的“圣爱”的不同之处,我们应当承认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要相互理解和包容这种差异,接受文化的多样性,把妈祖的“大爱”与基督教的“圣爱”有机结合,从而更好地推进人际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并发挥它们在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中的能动作用。
[1]朱全红,张苹英.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
[2]丁为祥.儒家血缘亲情与人伦之爱的现代反思[A].郭齐勇.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C].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443-454.
[3]王少安.大爱精神的思想渊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4.
[4]路益师.四种爱[M].台北:雅歌出版社,1989:123-147.
[5]约翰·巴克勒(霍文利译).西方社会史:第一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16.
[6]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2.
[7]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46.
[8]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52.
[9]张路,解光云.析论早期基督教“博爱”思想产生的背景[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3):115.
[10]田瑜,李建峰.大爱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特征[J].学理论,2011,(3).
[11]王少安,周玉清.试论“大爱精神”的普遍性和特殊性[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85-286.
C04/B97
A
1673-2219(2011)11-0078-02
2011-08-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妈祖信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1CTQ031);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08HX01(1))。
吴晓红(1977-),女,福建莆田人,莆田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语言文化学及翻译。
(责任编校:张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