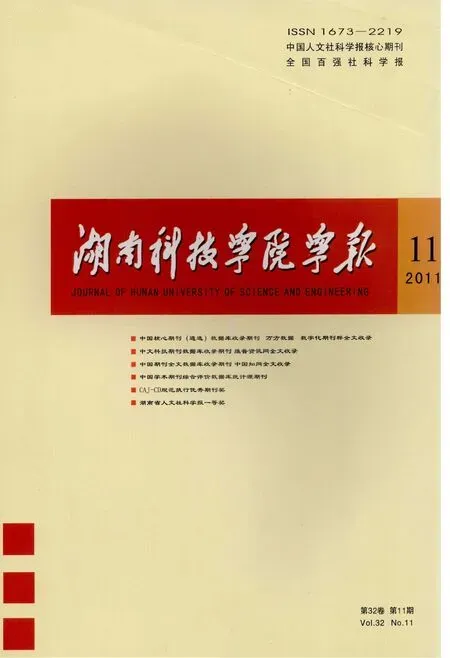张舜徽学术生平与治学志趣综论
许 刚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所,湖北 武汉 430079)
张舜徽学术生平与治学志趣综论
许 刚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献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按学术历程来看,张舜徽一生大致可分为四期。其之所以取得世所瞩目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最主要的是他追求会通的学术志趣所使然。
张舜徽;会通;学术历程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在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造诣精深、创获甚巨,留下大量著作。他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和成就,使其成为学贯古今的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通人大家。
张舜徽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有渊源,从小即嗜书好学,恣情披览,故其终生以学术为业,与典籍相伴。按学术历程来看,其一生大致可分为以下四期:
(一)少时(十七岁以前):启蒙之时志于自学
张舜徽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这一年,与外界的政治风云、社会动乱相比,他的少时较为安静地获得了良好而得法的家庭教育与学术训练。他幼承庭训,七岁发蒙,习文字之学。稍长,又涉览群书。其父张淮玉终身未应科举考试,一心埋头钻研朴学,尤长于天文算法。既重旧学,又乐于接受新知,不仅为张舜徽亲授课业,而且在治学方法上也给予了悉心指导。这和他的自学成功经历与自信,都给了张舜徽很大的帮助及影响。张舜徽后来在《自传》中说:“父亲一生自学的精神,给我的影响很深。他常教我说:‘凡是用文字写成的书,只要肯专心钻研,没有看不懂的。我早年用功于天文算法,便是无师自通。’我听了这几句话,受到很大鼓励,便决心走自学的道路。”[1]P75又说:“我一生坚决走自学的道路,刻苦钻研中国文史,是和家庭提供的读书条件和父亲自学精神的感染分不开的。”[2]P626皆表明父亲是他一生决心自学和坚定治学的引路人。①先生自其父家学所获治学经验方法,往往贯穿其一生,影响甚巨,如分类法初学《说文》,经史部以《尚书》与《史记》比读,书本与实验相结合等,皆于其著述中授予后学,一无保留。前辈大师之无私风范,俱见于斯!今人苟能循此勤加用功,虽不敢曰即如先生般之国学大师,然而左右采获,自在众人之上,要亦可知。刚以为先生此等治学经验之法,亟宜裒录为一册,广为刊布,以嘉惠学人。而研究先生学术思想者,于此特为拈出,引归己用,尤学术史研究外最大之收获。
十多岁时,张舜徽已经在父亲的指导下打下文字学的扎实基础。这时,他读到张之洞《书目答问》中的一段话:“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恍然领悟到做学问是有次第步骤的,应循序渐进,不可躐等、不可急躁。为此,他对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下了大量功夫,然后才以此为初阶,进入到经传子史与文辞的诵习。初治《毛诗》,后及《三礼》,钻研郑学,锲而不舍。十七岁那年,张舜徽撰《尔雅义疏跋》,为一生自述心得、撰述考证文字之开端。不幸的是这一年父亲因患肺结核病,医治无效去世,此后张舜徽便离家外出求学,开始了奠定一生治学规模和志趣的奋发时期。
(二)青年(十七岁至三十八岁):授课之余坚持自学
十八岁后,张舜徽孤身负笈出游长沙,寻师访友。先师从孙文昱先生,受声韵学。后应四姑父北京大学教授余嘉锡先生之邀,旅居北京并住于其家。时余嘉锡先生任教数所大学,名重一时,与之交往的学者专家甚多。经余先生介绍,张舜徽博访通人硕学,多识长者,诸如陈寅恪、陈垣、张尔田、高步瀛、吴承仕、沈兼士、马衡、孙人和、骆鸿凯、黎锦熙、杨树达、钱玄同等名流,他都虚心请教,或称贽称弟子,左右采获而为益无方,学问由是日有长进。又自朝达暮赴北海图书馆读书,日有定程,为一生读书进展最速之时。
1931年,张舜徽二十岁,与金詠先女士结为伉俪,其后终生治学甚得襄助之力。年二十一,乃自京还湘,先后于长沙文艺、兑泽(后迁至临澧)、雅礼等中学高中部任文史教员。授课之余伏案读书,坚持自学。湘中老辈诸儒,亦时有奖掖与诲导。抗日战争爆发后,从1942年起,年方三十一的张舜徽开始在大学任教,先应马宗霍先生之请,任国立师范学院(即蓝田国师)中文系讲师,教授“基本国文”,继而任北平民国大学(南迁至湖南宁乡)中文系教授,并曾任系主任。在三十四岁那年,《广校雠略》刊行长沙排印本,这是张舜徽平生第一部著作。抗日战争结束后,张舜徽应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先生之邀,至兰大中文系任教,为诸教授中年龄最小者。旋任系主任,兼任西北师范学院教授。《积石丛稿》五种刊行兰州排印本。
这一阶段,张舜徽教学相长,始终没有放松自学,“那时兼任几个学校的课,授课钟点虽多,但是年纪轻,精力强,下了课堂,便自伏案读书”[1]P75。他以“读书如克名城”的精神攻读大部头典籍:七月之时读《通鉴》、十年之时校读廿四史、五十日涉览《皇明经世文编》,都是在这一时期。虽战事纷扰,执鞭屡迁,仍无妨张舜徽乱世向学。《八十自叙》所谓:“年十有七,遽倾严荫,于是负笈出游,求师觅友。及旅居燕蓟,博访通人,公私藏书,得观美富。弱龄还湘,为中学师,讲授之余,伏案不辍,教学相长,期于积微末以至高大。”[1]P78正是这一时期的简约写照。而厚积薄发,稍事著述,像《广校雠略》之刊布,大可借见张舜徽四十岁前的学术思想。其中校雠学名义及封域论、汉唐宋清学术论等,均已成熟精洽,既被他平生坚持不弃,亦复为学者所津津称道。而他对郑玄经学、司马迁与郑樵史学的推崇,更表明他在这一时期即已树立了治学务求会通的博大志向。1949年,三十八岁的张舜徽至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任教授,后随学校并入华中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背景下,张舜徽的学术人生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中年(三十九岁至六十五岁):排除干扰著述不断
1950年,三十九岁的张舜徽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从1951年开始,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其后一直在该校(1985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工作。盛年的张舜徽极其关心学校建设,事业心强,当华中师大从昙华林迁到桂子山之际,作为建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努力工作,为在荒山野岭上建成桂子飘香的学府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循循善诱,教书育人,成效卓著,深受学生爱戴和崇敬。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而且越来越“左”。知识分子的处境日益艰难,张舜徽由于树大招风,更成为华师历史系的主要批判对象。但所有这些政治上的冲击,连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生活窘迫,都丝毫没有影响他治学的沉潜与著述的勤奋。这一时期,张舜徽著述不断,长期的累积相继付诸剞劂,共出版成果六部(《广校雠略》与《顾亭林学记》再版不计)。这些著作开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舜徽先生的学术业绩遂为国人所理解”[3]。如1949年后出版的第一部专书《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由于他对史籍的极其熟悉,介绍既带知识性,又带学术性,出版后深受高校文史学科师生和社会欢迎,“文革”前再版达七次之多,香港也有翻印本向海外传布,不但为不少院校所采用,并且服务面也更加扩大。《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则“成为历史学、文献学的必修书目”,“在文献学方面独露锋芒”[4]P141。此书是为指导后辈校读古籍而作,力求通俗简明,“全书写作的初衷虽只是普及文献学知识,但持论谨严,内容丰富,在文献学理论的研究上(如辨伪辑佚部分)有所发展。故当时学者称赞此书‘纲举目张,索微显隐,为初学引导正路,谆谆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见明灯’”[5]。而尤以《清人文集别录》最著。这是一部罕见的汇集清人文集精华的提要性质的佳作,以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交口称赞。武汉大学刘永济先生评价是书说:“非有渊博之学,弘通之识,不足以成此书。观其评骘学术,论而能断,即足见其有学有识也。况其文笔雅健,又非常人所能逮;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能读此书者已不多矣。”[6]P19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则说:“先生所作诸书,示学者以途径。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輶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然彼二书,对我辈之效用已极巨。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7]P406这样的称美,实在是够份量的了。它与《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一同构成了此时期张舜徽清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古代汉语研究方面,张舜徽的文字学研究方面体现了独特的治学方法,即既继承清代乾嘉以来考据学之实证遗风,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4]P170。他紧密配合文字改革的基础研究,发表了《古代汉字在构造和运用中相反相成的原则》,《从祖国文字发生、发展、变化的史实说明今日实行字体简化的必要和可能》等论文。当然,时代的政治因素也开始在他的学术研究中露出印记。《中国史论文集》收有张舜徽1949年前后所作十篇论文和十篇论文书札,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政治史、社会史,而以文化史为主,是张舜徽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工作的结晶。其中如《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材料问题》,对古史研究中材料的运用提出了系统看法,尤其是拈出《墨子·节葬篇》的记载,提供周代有人殉制度的实证,在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但他也强调史学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基点,将史学考证工作集中到劳动生产生活中来,其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即有此因素在内。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十年浩劫开始。在那政治动乱、举国上下激进的年代,学者多被卷入其中,张舜徽由于过去出版了几本书,被人目为冲击的重点对象,进行无情的大批小斗。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奋而述作,静观风云而笔耕不辍,坚信我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决非一二跳梁小丑可断送!在此理念支撑下,张舜徽最终彰显儒士气节,于艰难中继续他的学术研究①李学勤先生《读〈清人笔记条辨〉札记》一文即强调:“《条辨》一书序成于‘文革’时期的1974年,更足以体现张舜徽先生的志向学行。”参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一九九七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第5页。,从而在文革后接连推出晚年的一部部坚实巨作。(四)晚年(六十五岁后):不知老之已至而融汇博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学术界欢呼进入“科学的春天”的时期,张舜徽恰好在此时进入到他学术研究的丰收季节。他自强不息,壮心未已,以耄耋之年,继续为学术事业的繁荣勤勤恳恳地工作。这一阶段,他与学界同仁1979年4月初于桂林发起成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推动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并在会上被一致推举为首任会长,以后连选连任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退下来以后,仍被推为名誉会长。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初创阶段,张舜徽不仅以其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领导有方,而且与他的诸多同事一道奔走呼号,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精到的学术造诣、在文献学方面的权威地位为研究会赢得了重大声誉。这是研究会蒸蒸日上、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基本因素。如今文献研究会已成为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声望和深远影响的一个学术团体,入会者遍布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新闻出版部门。这一切都与张舜徽做出的极大贡献密不可分。他指导创办的学会刊物《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集刊》,是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的大型学术年刊,为此他亲赴北京、上海等地,联系有关事宜,征集20世纪以来大量的名家文稿,使会刊得以问世,并得到了顾颉刚、谢国桢、张政烺、胡厚宣、尚鸿逵、邓广铭、周祖谟、何兹全、赵光贤、杨伯峻等文史学界巨子名流、亲朋友好的积极支持,不仅使得《集刊》的出版在内容质量方面得到保证,而且其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影响也大大提高,行销全国各地、港台等处,颇受欢迎,欧美各国也有不少订阅者,对推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①先生创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之重大贡献,可进一步参见崔曙庭先生《张舜徽先生创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重大贡献》一文,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一九九七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第27页。为了培训学术队伍,提高历史文献工作者的素养,1981年张舜徽利用暑假时间专门为研究会广大会员选编并出版了《文献学论著辑要》一书,起初排印2000部,以供取用。未几而闻风函求此书者纷至,以大专院校及大图书馆为最多,乃至无以应之,对于提高文献工作者的理论素养与专业技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1983年3月,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三大巨册出版,并创办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他为所内的人员配备和基本设施,多方奔走,花费了大量心血。在其带领和指导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以整理研究古代文献为主,出现了一批历史文献学专家,建成了一支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承担了一些国家级的大型古籍整理项目。“以历史学家张舜徽为学术带头人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是武汉地区历史文献研究机构中的突出者,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张舜徽被称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奠基人之一。”[4]P417他为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他为学术带头人在全国率先创建了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他为全国首位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随后,又被评为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在教书育人,培养研究生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培育国家建设人才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张舜徽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及其研究机构的创立和发展,是功绩昭然不可泯灭的。
晚年的张舜徽老而弥笃,余勇较诸壮年毫不逊色,像《周秦道论发微》、《中国文献学》、《史学三书平议》、《郑学丛著》、《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清人笔记条辨》、《旧学辑存》、《说文解字导读》、《汉书艺文志通释》、《爱晚庐随笔》、《清儒学记》、《讱庵学术讲论集》等代表作,均成于他在世的这最后十余年,“舜徽先生的学术生涯进入最为辉煌的时期”,“一代国学大师的风貌遂展现于海内外”。但他依然勤奋如故,每天早晨四时许必起,“书房兼卧室的灯光闪烁于浓密的夜色之中,仿佛导引桂岳众多年轻学人奋力前进的北斗星”[3]P2。到80年代初,各种旧作整理出来后,《中华人民通史》的撰述工作摆到了张舜徽面前,他开始拟定提纲,商榷体例。正式的写作从他七十三岁时即1984年动手,历时三载,于1987年初完稿。1989年5月,《中华人民通史》出版,张舜徽实现了自己一生的最大心愿。他一生学术研究的精华,不少汇入到了这部书中。会通之学,暮年渠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一生治学,没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是从容不迫埋头苦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到积之既久,自然水到渠成。古人所云‘欲速则不达’,真是千古名言!”[2]P6331991年8月5日清晨,金夫人突患脑溢血,入院急救无效,7日下午四时弃世,终年七十有八。25日,张舜徽悲伤不已,撰《八十自叙》以追忆往事,兼叙夫人懿德多能。1992年11月27日凌晨五时许,张舜徽因心脑血管疾病突发而猝然逝世于寓所卧榻,享年八十二岁。在留给了世人文史哲领域千万余言的学术著述,充实地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后,一代国学大师安祥地离我们而去。
纵观张舜徽的学术一生,可以说是勤勤恳恳、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孜孜不倦、自强不息的一生,他以教育和学术事业为生命,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淡泊宁静,甘于寂寞,不追求名利地位,不贪图安逸享受,诲人不倦,著述不辍,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就在他逝世前十天里,还为朱祖延先生主编的《尔雅诂林》撰写了典雅凝练的题词,又为历史文献研究所内最大的集体项目《资治通鉴全译》,工工整整地撰写了六千字的长篇序言,对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价值和特点,提出了不同寻常的见解,这同时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字,可谓“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竭精殚虑,为中华文化的绵延发展奉献终身!”[3]P2他的已出版书籍24部(含50多种著作),超过850万字,内容涉及小学(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经学、史学、哲学、文献学等方面,有创新发微之作,有集成总结之书,有首倡奠基之著,总的说来多为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佳作,可谓成效卓越、著作丰硕,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为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增添了光彩。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研究宗旨,其著作涉及领域之广,战线之长,成果之丰硕,探讨之精深,在当今文史学界的名家中是实不多见、屈指可数的。不少著作获得湖北省和国家级奖励,其中,《说文解字约注》、《中华人民通史》都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中华人民通史》还获得 1990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他博治四部,冶经史子集于一炉,继承前人成果而不囿于成说,勇于创新而不凿空立论,于传统学术文献,阐幽发微,常予人以新的启迪,其学术影响,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且遍及港台、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和欧美等国,斐声海内外,被誉为当代中国成就卓越的历史文献学家、国学大师。
张舜徽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固然与他严格遵循清儒由小学而经学而史学这一治学途径密不可分,但从根本上说,最主要的是他追求会通的学术志趣所使然。这在《自传》中有明显说明,同时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每一个研究领域和每一部学术著作中。以他的清代学术研究而言,他独具慧眼地发掘、提出并表彰扬州学派,认为扬学在清学中较之吴派和皖派,最为博通,而这一点也恰恰是他肆力对其研究的内在原因。他说:“清代扬州之学,以广博继吴、皖两派以起,由专精汇为通学,一救乾嘉诸儒固隘之弊,而清学始大。余往者特撰《扬州学记》以表章之,所以张其恢廓之功也。”[2]P47在《清儒学记》“扬州学记”中阐论道,扬州学者治学的特点,首先在于能“创”,像焦循的研究《周易》,黄承吉的研究文字,都是前无古人,自创新例;其次在于能“通”,像王念孙的研究训诂,阮元的研究名物制度,汪中的辨明学术源流,都是融会贯通,确能说明问题,这都是吴、皖两派学者们所没有,而是扬州诸儒所独具的精神和风格,强调我们今天对扬州学派所以还有重视的必要,道理便在这里。又指出扬州学派所以能极一时之盛,不是偶然的,他们治学的规模、次第和方法,集吴、皖二派之长,但是又有他们独具的特点和风格,远非吴、皖所能及。并综括扬州学派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独特精神,用“能见其大,能观其通”八个字来总结他们的学风。
学派如此,学者亦如此,他对顾炎武极为推崇,为之专门作学记,又于清儒王夫之、朱彝尊、钱大昕、孙诒让等颇为赞赏,也都是因为他们治学广博,是通人之才。再如与清代学术研究共同构成其治学综合体系的汉代学术研究,亦复如此。许慎博通五经,张舜徽乃对其《说文解字》精加研究,对他的学术成就作一总结;郑玄遍注群经,张舜徽尤为宗仪,不但私淑为郑学传人,更就博杂的郑学予以整理,在《郑学丛著》一书中给郑学来了一次千余年的总结。特别像司马迁,张舜徽不但在著述中极力表彰,而且发扬其编撰通史的弘愿,在晚年以古稀之龄、一人之力撰成《中华人民通史》,可以说为他的会通之学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本世纪以来所有的通史著作都不同,这部书打破王朝体系,分为《地理编》、《社会编》、《创造编》、《制度编》、《学艺编》、《人物编》六部分。各部分的内容皆可顾名而思义,体现了通史之全面:即所谓“通”,既为古今纵向之“通”,又系事物横向之“通”。很显然,如果没有通人之识、会通之学,是很难创此新体、撰就此书的。①参见拙稿《论张舜徽先生文献学与史学思想之会通特征》,《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6页至第9页。“这里,体例绝不仅仅是个形式,而反映了丰富的内容思想。”[5]P24会通之义真正在这里得到了精湛的体现。
此外,像汉儒刘向、扬雄,宋儒朱子、郑樵等,都是张舜徽所推崇的会通之人,因而在著作中,屡屡给予了充分的表彰。特别如《顾亭林学记》自序中,针对有人认为学贵专精的说法,张舜徽指出这仅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多方面。他强调,学问博通的学者,由于治学范围比较宽,知识领域比较广,在某些专门研究的工作方面,实际已做了发凡起例、开辟途径的工夫,给专精的学者们指出了研究方向和下手方法,这种功绩是不可湮没的,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博通与专精二者的看法。赵吉惠先生曾说:“张舜徽学术最基本的特点是‘博通’,这可从两方面去看:一个是学术求通,一个是走广义文献学之路,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通’字。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张舜徽以‘通才’著称,像他这样博通‘经’、‘史’、‘子’、‘集’四部学问并且对于每部学问皆可以名家者,在当代学者中确是屈指可数、寥若晨星。”“只要深入认识、理解张舜徽学术的‘博通’特点,其他特点都可以联系起来得到说明。”[8]这个分析,是很精辟的,一语道出了张舜徽治学的志趣及其学术成就之关键。他早年在兰州大学、晚年在山东大学、扬州师范学院为文史两系诸生作演讲,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博通”。这是张舜徽毕生汲汲以求的治学志趣,也是他对青年学子今后成长的殷切瞩望。
[1]《张舜徽先生纪念集》编辑委员会.张舜徽先生纪念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张君和.张舜徽学术论著选[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章开沅.往事杂忆——纪念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七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1).
[4]简永福,张笃勤.武汉社会科学发展史[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5]周国林.张舜徽先生治学的求实精神与博大气象[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一九九七年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18).
[6]张舜徽.旧学辑存(下)[M].济南:齐鲁书社,1988.
[7]张舜徽.讱庵学术讲论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8]赵吉惠.张舜徽与梁、钱鼎足而三的清学史研究——评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A].周国林,刘韶军.历史文献学论集[C].武汉:崇文书局,2003:45-46.
K092
A
1673-2219(2011)11-0001-04
2011-08-20
许刚(1977-),男,山东烟台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兼职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近现代学术史、《孝经》与中国孝文化、国学普及。
(责任编校:傅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