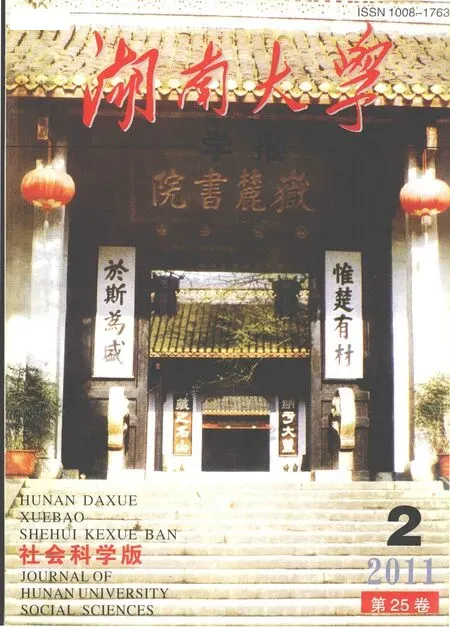废名新诗理论与中国“自然”诗学传统*
赵黎明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2.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047)
废名新诗理论与中国“自然”诗学传统*
赵黎明1,2
(1.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2.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047)
废名新诗理论与传统“自然”诗学有着极深的渊源,主要表现在其提倡情感的自然性、感兴的当下性、境界的不隔性以及主体的自由性等方面。废名自觉接续古代诗学生命,带有极其强烈的建构目的,只有从其利用传统诗学资源、创造现代新诗学的“目的论”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废名诗学的理论意义。
废名;新诗理论;自然诗学
一
废名谈论新诗[1]①据载,1936-1937年,废名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现代文艺”课程,编定讲义凡12章,1944年由北平新民印书馆以《谈新诗》书名印行,署名冯文炳,1946年废名返回北大续编四章,分别发表于当时报刊。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仍以《谈新诗》为名出版,署名冯文炳。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陈子善先生编定本以新民版为底,参校人文版,增加内容若干,冠以《论新诗及其他》之名出版,署名废名。其他版本还有陈建军、冯思纯编定的《废名讲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均编定《新诗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风编订《废名集》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本文所引废名诗论,均出自辽宁教育出版社《论新诗及其他》1998年版。,概括而言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围绕“诗的内容”这个核心,之前强调“当下感兴”的诗意创造,之后强调“横竖乱写”的自由境界,三者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其完整的诗歌生命体。如果要对其进行再度提炼,那么“自然”一定是三者共有的基质。在废名那里,“自然”包含了诗歌创作的整个过程,从诗的孕育、情的原质,经由感兴的发挥,直至诗歌的境地,都应具备那种“自然而然”的本色。正因为如此,废名的新诗理论才与传统“自然”诗学找到了生命相续的接榫之点,从而使其成为现代诗论史上最具传统家法的新诗理论家。
首先,“自然”能否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种“传统”?我认为是可以成立的。从词源及构成看,自然由“自”与“然”复合而成。《说文》“自”字从“鼻”,而鼻在古习俗中是人反指自身,因此“自然”意谓“自己如此”。这和西方思想史上之“生长”、“万物之本原”、“自然物之集合”等意涵,是有所区别的。也就是说,西方的“自然”首先是指“自然界”即“自然事物的总和”,[2]而中国的“自然”除指本来生成的大千世界外,更多是指向一种精神生活的趋向与本性。“道家的自然是一个精神生活的概念,就是自由自在,自己如此,无所依靠。”[3](P86)
作为合成词,“自然”诞生于先秦,在老庄那里它是一个哲学范畴,后经魏晋玄学家的渲染,“自然”逐步由哲学向文学让渡,成为一种“潜诗学”范畴。一般认为,中国思想史上较早将“自然”引进哲学领域的是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P163)这里,“自然”是与“人为”相对的范畴,后世多认为老子的“道”就是“自然”,“老子承认万物都出于道,道的本性是自然,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5](P43)而自然则是“宇宙万事万物原原本本的‘自己而然’、‘自身而然’罢了”[6]。它除了具备“自己如此”涵义外,还指一种“自由”状态,“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是人类所获得的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绝对自由的向往的象征和确证。……自然也就是自由。”[7](P29)徐复观还将“自然”一分为四,“以自然说明道自身的形成”,“以自然说明道创造万物的情形”,“由政治的要求以言人民的自然”、“以人所得于道之德,为人生的自然”。由此四项与人文相对的“自然”,“渐渐演变而将山川草木花鸟虫鱼风云月露等称为自然,此即为一般之所谓‘自然界’。并且魏晋以来,因玄学之助,而特别发现了山川草木等自然之美,影响于文学艺术者至大,”他还指出,“自然”一词另一种演变用法是作形容词或作副词用,或作由形容词副词而来的名词用,它与“当然”“固然”用法略近,意义指“自自然然地如此”。[8](P430-431)
老子之后,“自然”一词常常被用来指称一种区别、高于“人为”的状态。在这一意义下,“自然”被视同于“天然”。庄子把老子“自然”哲学从思辨推向了直觉,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天籁”、“天”、“自己”、“自取”等等。[4](P43)对于庄子“天籁”之说 ,有人认为,“齐物论对天籁的解释是‘夫吹万不同,而使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谁耶?’‘自己’即是‘自取’,即是‘自然’,即是‘自由’。”[9](P349)指出庄周之提出“自然”“自己”“自取”等观念,俱是为了强调“自由”。也有人认为要在庄子驳杂的思想中抓出一个提纲挈领的要害与核心,那便是“天”,“‘天’与‘道’、‘真’、‘自然’、‘素朴’等是同一层次的概念,都指人或事物的本质的、原初的、自然而然的状态。而这方面,‘天’与‘人’相对。‘人’指人为、人工、人的智慧和机心、人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等,它们破坏了人和事物的本真与自然,产生了虚伪和矫饰。”[10](P22)由于庄子论天道、自然,特别讲究虚静、心斋等诗性直觉,因此“天籁”之说一直被后人视为诗学极境,庄子自然之说自然也具有了“潜诗学”的特质。
魏晋玄学实际是对老庄“自然”哲学合目的的阐释。在“名教”与“自然”的纠缠之中,魏晋士人对“自然”的理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指向是明确的,即指与“名教”相对的天地万物的本真状态和人类自身的自然本性。正始名士王弼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竹林学派嵇康、阮籍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其“自然”范畴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概念,而是“自是”和“自在”之意,在人学的意义上“自然”就是自由境界。值得注意的是,魏晋“自然”一词已经被用于品评诗歌了,鲍照在评论谢灵运与颜延之诗之优劣时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11](P881)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12](P13-14)二人都是在赞美谢诗风格的“自然”。而对于“自然”正式加以诗学阐释的是“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有人称《原道》篇“自然之道”之说是“《文心》为书”的“第一要旨”,[13](P58)“道”是《文心》一书的主旨,但至于“道”的确切内涵是什么,阐释家们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道”可分为儒道说和自然之道二类,范文澜、王元化、徐复观等认为刘勰的“原道观”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圣贤”之道,黄侃、刘永济、朱东润、郭绍虞、郑振铎、王礼卿诸先生则坚持“自然之道”说。黄氏认为“原道”是“自然之道”,而“文以载道”是“圣贤之道”,二者不同。[14](P3)对于“自然之道”说,汤用彤认为:“自然一语本有多义,自然者,乃无妄然也……自然者即自尔也,也即抉然,掘然,突然也。”[15](P4)一般地讲,不管是天地万象所呈现的自然之道,还是就社会人事乃至精神现象的自然变化,后人多倾向于将“自然之道”理解为事物变化的自然而然和天然生成。其实,刘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诗歌产生的,其“明诗第六”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6](P56)
由此可以看到,魏晋之前,“自然”一词的演变显示出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演进路径上由哲学领域向诗学领域逐步过渡;二是语义上呈现复合化特征,意义涵盖自然而然、自由自处、天然去饰等等方面。在魏晋之后的诗歌创作与评论中,“自然”一词使用频率更高,以至成为诗歌品评的最高范畴和诗学史上最为基本的范畴之一。因此,“自然诗学”的概念不仅能够成立,而且还应该成为中国诗学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中国的“自然诗学”包涵的内容相当广泛,它几乎涵括了诗歌行为的始终,既指情感的自发性、主体的自由性,又指感兴的偶然性、抒写的直接性,还指诗歌生成的自足性与诗歌境界的不隔性。本文拟从废名新诗理论与传统“自然诗学”上述若干方面的关联点入手,探讨一下他是如何借鉴点化传统诗学资源,并为建构现代新诗理论服务的。
二
“自然”诗学强调的情感自然性与废名的“诗的内容”说取得了精神的一致。废名反复强调的“诗的内容”,主要说的就是诗人的自然性情。有时,他也用“真实”“质直”代之。在评价胡适的《晨星篇》诗时他说,“这些都不是虚夸的情感,作者的诗意里实有此质量,故我们能觉其质朴”,[1](P14)称赞其“放进月光满地”,与“遮着窗儿,推出月光”,与“回转头来,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之句,表现了诗人的想象与情感的自然性。对于情感的自然性,明代徐祯卿早有生动描述:“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17](P765)在徐氏制定的诗歌创作流程图中,“情”的自发性具有本体性作用。
废名多次用“幼稚、纯洁”来强调情感的自然性,这一点与明清自然诗学可谓遥相呼应。中国文艺的政教传统与自然诗学向来有着不可调和的紧张,传统诗教须臾不离净世化俗之责,但稍有不慎就易误入虚情假意之歧途。明清之际一线相承的自然诗学,无一例外都是在载道文艺发展到极端之时提出来的。李贽提出“童心说”,其目的就是用“绝假纯”的情感来抵抗“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的政教积弊。“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夫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8](P117)这里,童心就是真心,就是去掉任何粉饰、杂质的自然情感。袁枚承袭此说,更以“赤子之心”称之。“余尝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妙在皆孩子语也。”[19](P74)袁枚所谓“赤子之心”“孩子语”,除了去粉饰之义外,还具有以孩童眼光观物写意的意涵。孩童的情感是最自然的情感,孩童的世界是最少受到污染的世界。废名谈论新诗多次提到孩童气息。他举应修人“你尽管慢慢地开,我底纯洁的蔷薇呵”之句,有“一种诚实的气息”,这种“不染一点习气”的“幼稚”“纯洁”,并说这种气质正是新诗应该具备的特质,这种诗人才是真正的新诗人。因为他们“字里行间并没有染一点习气,这是最难得的。他们的幼稚便是纯洁。”[1](P102)这里所谓“幼稚纯洁”颇类古人所谓“生”,所谓“沾染习气”又近古人所谓“熟”,生熟之辨古已有之,废名以“生”即感情的自然状态作为论衡新诗质地的标准,虽然某种程度上泯灭了诗的“新旧”界限,但是利用旧诗“失去的生命”为新诗寻找生存根据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自然”诗学在创作论中十分突出“兴感”的援物起兴作用。在传统诗学家那里,兴感是自然而然、当下发生的。文论家喜欢用“当下性”与“自然”互释,因此,“当下性”实际上成了“自然诗学”的另一种表述。周策纵说有两种当下性,“一种是所谓‘自然’、‘天然’或‘浑然天成’。另一种是‘直寻’、‘直致’、‘直寄’或‘如在目前’或‘不隔’。……前一种偏重一切事物的本身,后一种则注重事物与我的关系。目的却都在提倡一切事物包括自我在内之本身的直接呈现。”[20](P186)王元化在点评钟嵘“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李渔“妙在水到渠成,天机自露”时说,“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只有克服了人工补缀的方式,完全沉浸在喜悦的激情里面,自然而然地抒怀命笔,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21](P394)王元化把钟嵘的“直寻”,李渔“天机自露”等,与刘勰的“从容率情,优柔适会”,一并称作“创作的直接性”,视为自然诗学的重要特征。废名兴感之论①关于废名与传统兴感诗学的关系,可以参照拙作《废名新诗“兴感”理论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原载《学术论坛》2010年第四期。该文主要从废名“直接的抒写”之论与传统“直寻”、“现量”之说,其“忽然而来”之论与“不以力构”之说等方面,说明了废名新诗理论与传统诗学的深刻渊源。另外,笔者在梳理废名诗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还考察了其“生命诗学”的特质和“在传统语境中建构现代新诗”的思想,分别参见《北方论丛》2010年第五期和《文学评论丛刊》2010年第二辑.与中国传统诗学相关论述一气相承。[22]
自然天成是传统“自然”诗学的至高标准。然而要达到这一极境必须具备上述触物而成,凑手偶然、漫然成篇诸般条件;反过来讲,具备了这若干条件的诗歌,才有可能成为诗歌中的极品。王夫之称赞寒山子《无题》诗,“天然成章,非元、白所能望津”。[23](P118)胡应麟称赞“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无工可见,无迹可寻”。[24](P5532)严羽激赏《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25](698)因此,“不以力构”、“风飞电起”的随兴之作乃是诗歌之中的极品,“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此着力不着力之分,学之者不必专一而逼真也,……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26](P127)废名论诗,传此衣钵,其品诗论第,也以自然为尚。他以为《扬鞭集》的压卷之作乃是那一首《母亲》,因为它是“诗的纯净的表现,是新诗里最完全的诗篇之一了。那首诗只有三行文字,写得那么容易那是庄严,那么令人亲近。正非偶然,是作者整个人格的蕴积,遇着一件最适合于他的题材,于是水到渠成了。”[1](P66)相反,他认为徐志摩一派反而有点“虚张声势”,原因大概是过于注重形式,缺乏诗的自然感兴吧。
传统“自然诗学”还强调诗作的自足性,即诗歌创作是诗的自我完成,是诗写诗人而不是诗人写诗。废名亦多次应和此说,废名认为,一旦诗情被外物触发,情不能已,便会借助诗人之手自我完成。“好比一座雕刻,在雕刻家没有下手的时候,这个艺术的生命便已完全了,这个生命的制造却又是一个神秘的开始,即所谓自由,这里不是一个酝酿,这里乃是一个开始,一开始便已是必然了。”[1](P26)这里,他结合温庭筠词谈到了艺术创作的一般原则,大凡艺术家要表现一个“完全”的东西,必须在他还没有下手之时,这个艺术生命就已完成,为什么呢?因为艺术创作完全是自主、自足的活动,物我相遇是不经意进行的、诗情的酝酿是自主完成的,任何人为的努力必然扼杀诗美。他把这种放之古今而皆准的艺术通则据为新诗独有,显然也为新诗建设找到了更为丰富的资源和更为广阔的道路。
三
如果把“直寻”、“直致”、“直寄”等创作的直接性视为诗歌生产的过程,那么其产生的结果——作品之于读者的效果来说,就是“如在目前”或“不隔”境界,这个过程与结果共同构成了自然诗学的整体。关于这种境界,古代诗家赋给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如“天籁”、“化境”、“神境”等等。庄子所谓天籁指的是完全自发,不依赖任何外力、天然生成的美,是美的至高境界;司空图笔下的“自然”一品被生动描述为,“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神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巧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语,悠悠天钧。”[27](P205)姜夔要求诗歌境界自然天成,“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28](P402)袁枚进一步总结,极品之作乃是天籁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有著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此即陆放翁所谓‘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也。”[19](P126)这种举重若轻、不露痕迹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又常被称为“化境”,贺贻孙对此境界的描述是:“诗家化境,如风雨驰骤,神出鬼没,满眼空幻,满耳飘忽,突然而来,攸然而去,不得以字句诠,不可以字迹相求。”[29](P1029)皎然进一步以“神”来描述这种不加任何人为修饰的至高境地,“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30](P31)严羽则用入神称之,“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25](P8)对于上述诸俱说之“神”,今人陈良运结合杜甫有关诗句总结为“或是指灵感骤至时那种‘凌云健笔意纵横’的创作快感;或是指主客体豁然贯通时那种兴会淋漓的审美愉悦;或是指作诗功力老到娴熟、技巧自由发挥的状态;或是指心游物外时那种‘六合之内,一举万里’的气势。”[31](P371)这里要补充一点的是,“神”还指境界上的一任天机,抒写性灵,深得对象的精微神韵。
我们在谈论“自然诗学”之时,不能忘记这个“自然”里面还包含着主体的自由。老子的自然之道就是人类所获得的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绝对自由的向往的象征和确证。“自然范畴包含着自由的内涵,正是自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得以成立的关键”。[7](P37)在“自然”和“自由”之诗学背景下考察废名境界说,我们发现其“横竖乱写”与“随意吐露”之说可谓渊源有自。“横竖乱写”与“随意吐露”是废名对郭沫若和冰心诗才的概括,也是对李商隐和温庭筠诗兴的赞美。他赞美郭沫若,“这首诗之成,作者必然是来得很快,看见天上的云,望着荒原的山,诗人就昂头诗成了,写得天衣无缝。”[1](P128)指出郭沫若新诗作的价值,“他的诗本来是乱写,乱写才是他的诗,能够乱写是很不易得的事。”[1](P129)赞赏冰心,“一个灵魂真是随处吐露消息。”[1](P10)他同样叹服李商隐,“写得很快,多半是乱写的,写得不自觉的”,[1](P155)敬服温庭筠压根儿不需用典,他照样可以“横竖乱写,可以驰骋想象”[1](P29)。在废名看来,不论古今,只有艺术巨擘才能达到这种自由境地。对于他们而言,什么文字、音韵、典故等等外在形式,都不会真正构成威胁,这是废名论诗与胡适不同的一个思路。胡适论诗,曾把用典列为新诗八病之一,但在废名眼里,这个问题大可商榷,用典与否均与艺术需要和艺术手腕有关,如需用典,则典故可帮诗人驰骋想象;如不用典,诗人一样可以赤手千里。李商隐长处在于用典,其诗借典驰骋神思,雄傲今古;温词则随意而为,需要用典时,诗人借典故神驰;不需要故实,则即目成咏。在废名看来,用典与否并不构成伟大诗人或作品的真正障碍,关键看能否以生命强力统摄文字、能否真正达到自由境地。
废名还多次直接用“自由”状写新诗境界。在废名眼里,自由有几种含义:一是创作题材的自由选用。废名强调康白情《草儿》和湖畔四诗人之值得肯定之处就在于其“小孩子的题材”、“旧小说的文章”以及“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等选材方面的自由;二是文学资源选取的自由。有了所谓“诗的内容”后,废名主张新诗形式建设,不妨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这个文章可以吸收许多长处,不妨从古人诗文里取得,不妨从引车卖浆之徒口中取得,又不妨欧化,只要合起来的诗,拆开一句来看仍是自由自在的一句散文。”[1](P109)三是做诗态度的自由自在。对于湖畔派诗人的肯定,废名强调的是他们做诗态度的任意而为,“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做诗了,他们又真是诗要怎么做便怎么做了”,[1](P96)比如康白情,本来是旧诗写手,但摇身一变却自由地写起新诗,对于他来说,旧文学中的合理因素都被随手拈来,加以生命点化,所以能够“得到解放”。
[1] 废名.论新诗及其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 J.S.Mil1.Three Essays on Religion[M].New York,1874.
[3]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 王庆节.老子的自然观念[J].求是,2004,(6):41-50.
[7] 赵志军.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自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 徐复观.徐复观文集(2)[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9]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A].徐复观文集》(3)[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10]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1]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M].台北:正中书局,1968.
[1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明)徐祯卿.谈艺录[M].(清)何文焕.历代诗话选(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明)李贽.童心说[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9](清)袁枚.随园诗话(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20]周策纵.弃园文粹上海[M].北京:文艺出版社,1997.
[21]王元化.思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2]赵黎明.废名新诗“兴感”理论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J].学术论坛,2010,(4):172-177.
[23](清)王夫之.姜斋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4](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A].吴文治.明代诗话全编[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5](宋)严羽.沧浪诗话[A].[清]何文焕.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26](明)谢榛.四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7](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A].中国历代文论选(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8](宋)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A].中国历代文论选(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9](清)贺贻孙.诗筏[M].转引自霍松林.中国诗论史(下)[M].合肥:黄山书社,2007.
[30](唐)释皎然.诗式·取境[A].(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上)[C].北京:中华书局,1981.
[31]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Fei M ing’s New Poetry Theory and the“natural”Poetic Tradition
ZHAO Li-ming1,2
(1.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10097,China;2.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Chongqing No rmal University 400047,China)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Fei M ing’s new poetry and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natural"poetry mainly lies in the emotional nature,the moment of invigo ration,the directness of state and the freedom the subject.FeiM ing consciously follow the life of ancient poetry w ith a very strong construction purposes,so only from point of view of taking advantage of traditional poetic resources to create the modern poetry,can we truly underst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his poetry.
Fei M ing;new poetry theo ry;nature poetry
I206.6
A
1008—1763(2011)02—0090—05
2010-05-05
中国博士后科学研究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09046113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0035915)
赵黎明(1968—),男,湖北宜城人,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二站博士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