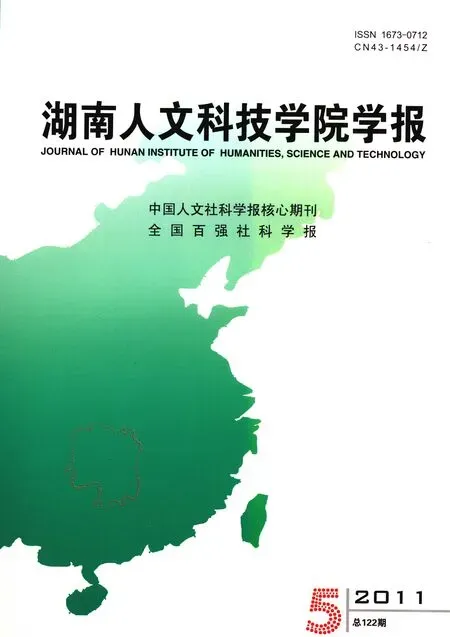主题学与人类学关系之考辨
高文惠
(德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德州 253023)
主题学与人类学关系之考辨
高文惠
(德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德州 253023)
主题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不仅在学科基础上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而且在学科发展实践中,也有着很多的交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为主题学的研究提供了阐释的依据,另一方面人类学对于主题学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反过来,主题学的研究也势必会形成对人类学研究的有力支撑,进而拓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地。
主题学;人类学;关系
主题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决定着其跨越性质。也就是说,主题学的边界是一个模糊边界,和许多学科都有交叉渗透。除了主题学与民俗学的关系之外,最密切的要算主题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了。但是主题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并非一目了然,尚需要进行一番学理的考辨。
1 学科基础上的天然联系
要弄清主题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首先需要从人类学与文学的关系这个源头做起。
尽管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在在19世纪中叶,但人类学的研究其实自古有之,19世纪之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生物和遗传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属于体质人类学的范畴。进入19世纪之后,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得到极大拓展,体质人类学之外,又生发出以风俗、文化史、语言等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和专门研究史前时期人体和文化的史前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无论有多少个分支和学派,也无论出现怎样的变化,人类学始终是一门研究人的科学。关于文学的实质,古希腊人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们把“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刻在阿波罗神殿上,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更是对文学实质的经典概括。文学即研究人(尤其是人的欲望、情感和心灵)的学科这个观点在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在这一点上,文学与人类学这两个不同的学科之间有了相通的基础。甚至有学者这样表述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本质上是‘人学’,只不过是用‘形象’来表述,用‘情感’来表现的‘人类学’;人类学本身潜在着文学取向,因为它不但要从体质与文化两方面研究人类的生长,还要从心灵或情感上去把握与审视生长中的人类。”[1]
人类学与文学这两个学科之间还存在着一些重合区域。一方面,人类学研究中有诗性的因素。对此,解释人类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有集中论述。格尔茨认为,在人类学著作中,往往会让“分析渗入对象体内”,这就导致作为自然事实的文化与人类学家所写的作为理论实体的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所以,“人类学著述本身即是解释,并且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它们是‘虚构’的产物”[2]19-20;因此,人类学家同作家所做的工作一样,也是在进行写作,凭借的武器是虚构,人类学著作没有一致的观点,而是“以辩论的巧妙为其标志”[2]37。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中又深藏着人类学的经验。菲利浦·伯克对此总结道:“伟大的文学作品,借助于读者的想象,常常能够比数月的实地体验传达出更多的有关异文化生活方式的经验。……”“事实上,对任何艺术作品的敏锐思索——从荷马史诗到毕加索绘画,都能扩展我们的人性观念,并加深我们对自身的理解。这正是人文主义的人类学所追求的宏伟目标。”[3]
正是这种文学与人类学在根源上的趋同性和学科发展中的交叉性成为叶舒宪、萧兵、彭兆荣等人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提倡的“文学人类学”的学科立足基础。所谓文学人类学,就是试图实现文学与人类学的汇通,从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去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以文学的思维去诗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人类学研究的是整个人类及其文化,提倡从人类学的视角进行创作和研究的文学人类学就必然地具有了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等特性,因而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作为文学人类学研究重要板块的主题学,其研究对象既包括书面文学,也包括民间故事等口传文学,研究方法强调贯通性,重视根源的追溯、过程的梳理、结构的归纳、演变原因的剖析,因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主题学研究这块领地,最容易结出硕果。
在学科基础上,主题学与人类学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而在学科发展实践中,两个学科之间的交互影响始终存在,主题学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文本的比较从某一个角度上为人类学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资料,提供了人类情感是共通的文化整体主义的佐证。而人类学对主题学的影响则更为广泛而深入。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直接为主题学研究转化吸收,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为主题学研究带来了直接的启示。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主题学的研究成果是借助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而获得的。
2 人类学为主题学研究提供阐释依据
主题学不仅要研究同一文化中的母题、题材和主题的演变,而且还要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文化中的流传,揭示世界共通性母题、题材和主题产生的根源和隐藏的文化意蕴。在这方面,人类学的许多相关成果为主题学研究提供了阐释的依据,弗雷泽的《金枝》的贡献首当其冲。对于这部人类学著作的文学批评价值,诺斯罗普·弗莱曾经总结道:“《金枝》一书旨在写成一部人类学著作,可是它对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影响超越了作者声称的自己的目的,而且事实上,它也可能成为一部文学批评的著作。”[4]56
《金枝》开篇讲述的那则在意大利内米湖畔阿里基亚丛林中反复上演的金枝习俗,成为文学作品中通过杀戮承继王位以及弑父娶母母题反映的人类深层文化经验的合理阐释。弗雷泽分析的金枝习俗中包含两个核心要素:第一,祭司职位的继承必须靠杀戮来完成;第二,祭司的名号不仅意味着“森林之王”的权力,还意味着成为狄安娜女神的情人或丈夫的资格和义务。折取金枝的动作就直接出现在了古罗马的神话中,传说埃涅阿斯在去冥间寻访父亲的亡魂时,就折取过金枝,而通过杀戮承继王位这一带有巫术色彩的意识在维吉尔的大型史诗《埃涅阿斯记》中则置换为拉丁姆战场上的厮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希腊神话中三代天神的权力之争、巴比伦创世史诗《埃努玛·埃利什》中原父原母与其子孙们之间的战争、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与其兄弟赛特之间的纷争等神话以及人类文学中所有围绕君权展开的战争均可看作金枝习俗中包含的“通过杀戮承继王位”这一母题的不同呈现。森林之王即是女神的情人或丈夫的要素则可用来解释世界文学中频繁出现的弑父娶母题材的情节结构。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无意间杀死了父亲拉伊俄斯,通过杀戮完成权力的继承,同时也获得了迎娶前任国王的妻子,也即自己的母亲的权利,因而酿下了悲剧。这部悲剧算得上是金枝习俗在文学领域里的直接呈现。同样是弑父娶母主题,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对金枝悲剧的呈现则更为复杂。在这部著名的作品里,金枝习俗不仅在作品情节中直接再现,而且内化于人物心理经验中的巨大恐惧作用于人物的行动。克劳狄斯通过杀戮,取代了老哈姆莱特成为新的国王,并继承了老国王的王后乔特鲁德。哈姆莱特在复仇的过程中行动延宕,某种意义上,来自他内心无意识文化经验中的恐惧,因为杀死克劳狄斯成为新一任国王的同时,也意味着要与自己的母亲产生乱伦关系,深受人文主义教育和颇具道德感的哈姆莱特无法接受这可怕的后果,因此导致了行为的延宕。
弗雷泽在《金枝》中,运用交感巫术原理充分证明了原始思维的某些特点,大自然的荣枯与神及其人间化身——国王——精力的盛衰之间有神秘关联。因而原始人会在神或国王露出衰弱征象的时候,杀死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让世界保持旺盛的生机,“杀死神的人身绝不是消灭神,而是为了让他更好地复活,在一个新的充满精力的媒介中苏醒,使神拥有一个更强大的代表。”[5]331而分享神或具有神性的动物的肉,则“除了可以获得该动物或人体质上的特性外,还可以将其道德和智力上的特性据为己有,所以一旦质朴的原始人认定某生物有灵性,必然会希望把它的体质特性和灵性中的一部分吸收过来”[5]541。弗雷泽的分析为揭示世界文学中所在多见的嗜食人肉的形象、荒原情境、圣杯意象等背后的深层文化意识打开了一扇开阔的窗。
弗雷泽还运用大量实例说明耕作与两性关系的原始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类的性交同植物的生长之间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5]155季羡林先生将弗雷泽对这种风俗的分析稍加变形地借用过来,在《原始社会风俗残余——关于妓女祷雨的问题》这篇文章中分析东方文献中普遍存在的“妓女祷雨”的题材。他从域外汉学中关于中国的妓女祷雨的记载谈起,联想到印度史诗、神话和佛典、梵文文学和佛教艺术浮雕中的妓女祷雨故事,并进而受弗雷泽的启示,揭示这类题材背后深层的文化观念:“原始人类对大自然了解得非常少,甚至毫无了解。他们从妇女能生小孩这个现象观察起,相信人类的丰饶多产,特别是妇女的丰饶多产,与大自然的丰饶多产属于同一范畴。换句话说,他们把人类的再生产和农业的生产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相信,二者加以模仿,就能产生影响。佛雷泽说,原始人类把人类再生产自己的族类的过程同植物起同样作用的过程混淆起来了:他们幻想,只要利用前者,就能促进后者。”[6]季羡林先生的这篇文章算得上利用《金枝》里的人类学研究材料和观念进行主题学研究的成功范例。
人类学研究非常重视各地习俗中的仪式研究,在他们看来,仪式是文化意义的储存处,“在仪式中,生存世界与想象世界借助一套单一的符号体系混合起来,变成相同的世界,从而在人的真实感中制造出独特的转化。”[2]158在原始人的观念中,仪式所表演的世界在象征层面上与宇宙秩序的变化相对应。仪式举行的最终目的,正如柯普所说:“我们可以最终看到,作为特殊的强调功能,仪式的展演在社会进程中,在具体的族群中起到了调整其内部变化、适应外部环境的作用。就此而言,仪式的象征成为社会行为的一种因素、一种社会活动领域的积极力量。”[7]弗雷泽的《金枝》里收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习俗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各种各样的表现原始观念的仪式,因此,弗莱称“《金枝》是一部论述朴质戏剧之仪式内容的著作”[4]155,因为 “对文学批评家说来,仪式是戏剧行动的内容而不是其源头或由来”[4]155。
仪式直接进入文学领地,甚至有可能是文学产生的根源。关于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产生的源头是民间的酒神祭仪的观点已经是一种公认的观点。如果说仪式是整个文学的源头这种说法过于断然,那么最起码说仪式与戏剧(泛指整个文学)的关系非常密切,文学中时常会闪现着仪式的身影。而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学中出现的类同或相似仪式的展演则成为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神话、古埃及的奥西里斯神话、古巴比伦的坦姆兹神话这些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植物神死而复生的故事是对杀死神献祭以求丰收的民间仪式的摹仿。这种仪式在近现代文学还会以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反复搬演,如索尔·贝娄的《雨王亨德森》、奥尼尔的《琼斯皇》、索因卡的《酒神的伴侣》等;在民间习俗中,存在大量的在特定的日子,往往是岁末,举行杀人献祭(后演变为杀死神的象征——偶像)或将某人驱逐的仪式,用弗雷泽的说法,这是一种“大众化的驱邪方式”,被杀死或驱逐的人的功能是“公众的代罪者”。这种仪式在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大量存在的“替罪羊”形象,他们包括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中的伊菲格涅亚、希伯来族长传说中的以撒、英国现代小说家D.H.劳伦斯短篇小说《骑马出走的女人》中那个主动将自己献祭的英国女性、南非作家库切的长篇小说《耻》中的卢里和露西父女、尼日利亚当代作家索因卡的剧本《强种》中的埃芒和他的父亲、《路》中的“教授”……总之,人类学对各种类同或相似仪式的搜集及对其中隐含的人类最初观念的揭示,为主题学研究中的相关论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托,当然,反过来,文学创作中对相关母题、题材、主题类型中蕴含的仪式的研究又会极大地丰富人类学的研究论据。
3 人类学对主题学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主题学的研究提供了阐释的依据,而且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给主题学的研究带来了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启示。
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结构人类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非常密切,它的研究成果不仅本身就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研究也具有直接的影响。结构人类学主张从结构的角度来进行人类学研究,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著作《结构人类学》中将结构研究的方法引入人类学研究,他提出:“词汇不如结构重要。不论神话是个人的再创造,还是来自传统,它从其个人的抑或集体的源泉中(在这二者之间不断地进行着互相渗透和交换)汲取它使用的形象材料。但是结构保持不变,而象征功能则是通过结构来完成的。”[8]40他在《神话的结构研究》一文中对俄狄浦斯神话所做的结构分析则详尽地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他将俄狄浦斯神话故事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割出来,他称这些部分为“神话素”,然后对这些神话素进行重新组合和编配,结果发现了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图式,表面无序的神话世界在他的排列组合中,获得了一个明晰的秩序,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就是纷繁万千的形象材料背后深藏的不变的结构。这个结构也可以称作神话思维中的逻辑,因为“神话和科学中存在着同样的逻辑过程”[8]69,因而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神话。
正如结构人类学对神话所做的分析一样,主题学研究也把文学分为表层结构和隐在的深层结构。在主题学研究者看来,“同一个主题在流传演变的过程中会发生种种形态的变化,会以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得以呈现,演绎为多种多样的艺术作品,或者说借助于多种多样的艺术作品而存在,从而使得主题本身成为隐在的结构。它在不同民族文化的语境之下可以呈现为风格、形态、功能迥异的类型,从而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阐释空间。”[9]主题学研究注意表层结构的梳理和归纳,更注重深层结构的挖掘,表层结构即外在的叙事,深层结构即一组故事背后隐藏的共同的主题。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关系呈现为多种形态,文学中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这种多种形态呈现又进一步致使主题学研究路径的多元化特征。
灰姑娘是格林童话中塑造出来的经典童话人物形象,但灰姑娘的故事并不是仅属于德国的特产,“据说关于受继母虐待的‘灰姑娘’的故事,在全世界竟有五百个以上流传各地。”[10]而夏洛蒂的《简爱》、狄更斯的《小杜丽》、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等作品可以视作现代版的灰姑娘故事。虽然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的名字不叫灰姑娘,故事在细节上存在很多差异,但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深层结构:出身贫寒、遭遇不幸的女子靠其善良、贤淑、坚韧的品性获得好姻缘。这个深层结构反映出人类精神结构中普遍存在的希望好人有好报的伦理思想和打破等级关系的社会意识。对灰姑娘主题的这种考察是试图在文本表层结构的差异中看到深层结构的相似的实践操作;在早期各民族的神话中,普遍存在着大洪水神话,因而构成一个洪水主题。普遍存在的洪水神话一方面反映了人类早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是人类早期共同生存经历、生命体验的一个艺术折射。然而进一步深入考察,又会发现这组神话相似或类同的情节结构之下的文化意蕴却相差悬殊。古巴比伦的大型史诗《吉尔伽美什》中记载的大洪水神话反映了古巴比伦人的多神信仰;直接受古巴比伦的这则神话影响的古希伯来人的诺亚方舟神话则表现了希伯来人独特的一神教信仰和惩罚-救赎论;中国的鲧、大禹父子的神话则反映出了中国传统群体本位文化中特有的为集体利益牺牲自己、乃至禁绝个体欲望的道德诉求。对于洪水主题的这种研究既包含了对相似的表层结构下的相似的深层结构的探究,又包含了对相似的表层结构下深层结构的差异的考察。
类型研究也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在这方面,弗雷泽的《金枝》也是一个典型范例。虽然全书由意大利丛林里的金枝仪式开始,所做的工作都围绕着对这一仪式的释读展开,然而在引用论据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弗雷泽又将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风俗仪式进行归纳,分别放在了“树神崇拜”、“耕作与两性的关系”、“食物禁忌”、“名字禁忌”、“神王之死”、“五谷妈妈”、“圣餐”、“大众化的驱邪方式”等类型之下。列维·斯特劳斯运用结构的哲学思维所做的人类学研究也颇为强调类型归纳,在他看来,“如果把一致的传说和神话汇编起来,将是卷帙浩繁,蔚为壮观。但如果我们从各式各样的人物性格中抽象出若干个基本功能,就可将其归纳为为数不多的简单类型。至于情节这种个人神话,同样也可归纳为几种简单类型,从中产生了许许多多变化无穷的实例”[8]40。
人类学对研究对象所做的类型划分的研究方法也直接为主题学研究所借用,或者也可以说主题学的学科特点本身就决定了人类学式的类型研究方法是其根本方法之一。因为主题学以不同文本的比较为基础,而把不同文本放在一起的条件则是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找出了一组文本的相关性,也就是发现了某种类型。从某种意义上,主题学的实践操作就是一种类型研究。如空中云、飞蛾扑火、蚕、山、黄昏、竹、雁等意象类型的研究,“阿比库儿童”(非洲文学中的“鬼孩”)、拿破仑、唐璜、浮士德等形象研究,失乐园、情感与义务的冲突、徒劳、三角恋、乌托邦、梦境等情境类型研究,梦想成真、二妇争子、父子相残、乡愁、贞德等题材类型研究,变形、流浪、复仇等主题类型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人类学者从神话中划分出各种神话素,重新排列组合,通过在横向与纵向上的重新审视发现结构的方法也直接进入了主题学研究领域。万建中等著的《中国民间散文叙事文学的主题学研究》中的“魔宝主题”、“难题主题”、“镜子主题”、“难题求婚主题”、“变形主题”等类型的研究都是使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方法,以其近乎科学的严谨性而令人信服。
人类学对人的研究是一种过程考察和整体性研究。体质人类学主要是从形态、遗传、生理等角度考察人的体质的演变,而文化人类学则强调对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变迁过程的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归纳出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特征及它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从而探索人类总体文化的演变规律。而与此相似,“主题学旨在从事主题的比较,而比较的目的在于考察主题的构成、延伸和流变。这就决定了主题学必然要采用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两种方法”[11]。
对于建立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学比较的基础上的主题学研究来说,借鉴吸收人类学研究的过程考察方法和整体性研究思路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主题学的基本研究路径是首先在收集的材料的基础上归纳类型,其次找原初(类似于原型批评中的“原型),然后追踪相关材料的演变过程,分析其变形的原因。当然,这种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的整体性视野。对此研究路径和研究目的,许多学者都以实践操作的形式予以了认可和强调。顾颉刚早在上世纪20年代所作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就以创造了“历史演进法”和“地域系统”而将主题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收集在陈鹏翔的《主题学论文集》中的许多论文都对某种主题或题材的演变做了历史的追踪;季羡林先生早在1948年完成的论文《“猫名”寓言的演变》在主题学的过程研究方面具有演示意义。
综上所述,主题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不仅在学科基础上存在着天然的联系,而且在学科发展实践中,他们之间也有着很多的交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为主题学的研究提供了阐释的依据,另一方面人类学对于主题学的研究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反过来,主题学的研究也势必会形成对人类学研究的有力支撑,进而拓展人类学的研究领地。当然,主题学不等于人类学,虽然都是研究“人”的学科,但是主题学毕竟是文学研究的一种,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和视野,文学性始终是其立身之本。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中的一组文本通过科学的方法被归纳为某种类型,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并不意味着今后的创作都是对最初文本的重复,因而失掉了或折损了意义。正如同布吕奈尔等人所说,“没有只能用一种诗意来表达的主题,而任何主题都包含着一种潜在的诗意。想像,照波德莱尔的说法,是‘官能的皇后’,它所带来的不是一种中性的主题材料,而是一种根据其固有的结构模式整理好的材料”[12]。在作家个体不同的想象趋向之下,同一主题在不同的文本中会焕发出不同的文学魅力。
[1]萧兵.文学人类学:种生存方式[J].百色学院学报,2010(4):9.
[2]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86.
[4]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5]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 赵日日,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季羡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05-206.
[7]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人类学关键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3.
[8]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陆晓禾,黄锡光,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9]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6.
[10]刘守华.民间童话之谜: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M]//张隆溪,温儒敏.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293.
[11]周发祥.中国文学主题学[J].文艺批评,1997(6):151.
[12]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M].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77.
(责任编校:文君)
OnRelationshipbetweentheThemeandAnthropology
GAOWen-hui
(Chinese Department, Dezhou Institute, Dezhou 253023, China)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heme and anthropology is very close. There are not only natural contacts in basic principles of these two subjects but also many intersections in the practice of subjects. The anthropolog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supply evidences for the theme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anthropology gives apocalyptic significance to the theme in methodology. Conversely, the theme study must form a powerful support to anthropologic research and then broaden the demesne of anthropologic research.
the theme; anthropology; relationship
2011-09-20.
高文惠(1971—),女,山东德州人,德州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东方英语文学。
IO-05
A
1673-0712(2011)05-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