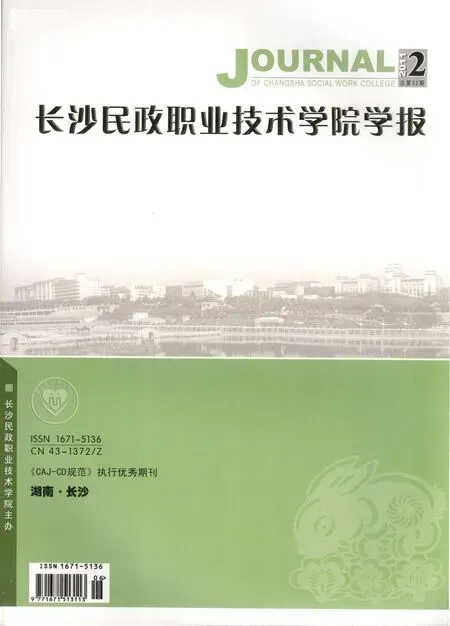湖湘戏剧语言特征及其对区域文化的传承
盛光希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湖湘戏剧语言特征及其对区域文化的传承
盛光希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湖南地区区域文化底蕴深厚,作为综合性艺术的湖湘地方戏曲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特征。其戏剧语言主要从民间音乐美术、民间歌舞特技、自然?与社会环境资源等三个方面吸收营养并传承文化。
湖湘戏剧;言语特征;文化传承
戏剧是综合性艺术,一方面,它成熟于其它艺术形式之后,广泛地借鉴、吸收了说、唱、道白等自然语言形式和音乐、美术、舞蹈、杂技、动作等非自然语言(社会语言)形式,综合性地表情达意、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另一方面,它产生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综合而集中地体现了地域文化特征。湖湘文化属荆楚文化的南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地方戏不断地传承并发展着湖湘文化尤其是湖湘民间文化。
一、民间音乐美术与戏剧舞台背景语言
戏剧舞台背景语言包括舞台美术与舞台音乐两个方面。脸谱是戏剧艺术的一种特有的化妆方式。湖南地方戏剧花脸的表演,又叫“动脸壳子”、“动脸子”,这系承袭“面具”这一名称而来。因为“面具”在湖南南部一带称为“脸子”,在北部常德一带称为“鬼脸壳子”。带面具表演,普遍用于古代的“傩”。“傩”是一种祀神驱疫仪式,借歌舞以娱神,常戴面具表演。湖湘之地多山与水,高山与深谷纵贯,森林茂密,野物出没,气候变幻,人们信仰鬼神,民间巫术、迷信非常普遍,“傩”十分盛行。早在战国时代,湖湘民间祀神便由巫师演唱歌舞,屈原流放其间,见辞鄙俗,乃作《九歌》以供演唱。汉·王逸《楚词章句》卷二:“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优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就是说的这件事。
傩本为祀神驱疫仪式,它在长期发展中,逐渐由娱神转向娱人,走向戏曲形式。湖南的地方傩戏就是在傩歌傩舞基础上形成的,迄今还有一些带面具表演的节目。其他民间小戏乃至一些地方大戏剧种,其脸谱表演也或多或少受到巫傩的一些影响。又因湖南地区祀神驱疫的面具表演极其俚野,源于此的戏曲脸谱以大幅度夸张图案刻画人物的外部形象。而且湖南地方大戏的脸谱,风格古朴,一般只用红、黑、白三种基本色,按传统有“红忠、黑直、白奸”之说,如关羽开红脸,以示忠勇;包拯开黑脸,以示正直;曹操开粉脸,以示奸诈。另外,专用脸谱常以不同的图案表现人物的性格、能耐、出身和经历,如祁剧中司马邈额上书“正直无私”四字,以示为人正直;孟良额上画倒置的火葫芦,以示其善用火攻;张奎额上书“煞”字,表示他是黑煞星转世;夏侯惇右眼画瞎,表示他拔矢啖睛的经历,这也显示了湘人好恶分明、耿直忠义的性格特征。
服饰是戏曲舞台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为少数民族集居的区域,55个少数民族在湘境内均有分布,各民族传统服饰种类繁多,风格迥异。得益于此,湖湘戏曲服饰争奇斗艳、别具风格,以至各剧种都有一些独特的服饰,如祁剧的活动紫金冠、蓬头、罗口袖、荆河戏的飞裙。与此同时,由于民族错杂分置,风土民情各不相同,也带来了舞台布置甚至道具的风格、含义的千差万别。如武陵戏的“貘”、荆河戏的“人面兽”、武陵戏和荆河戏共有的“皮鞭”、辰河戏的“纸扎”,祁剧用于制扎各种临时道具的“三十六根无名索”等,都极具特色。
湖南的民间乐器同样影响着传统戏曲的音乐语言。湖南地方大戏的音乐包括唱腔音乐、过场曲牌、打击乐曲等几个组成部分。演奏人员按传统称“场面师傅”,简称“场面”,即今乐队。过场曲牌分唢呐曲牌和丝弦曲牌两类,唢呐曲牌雄壮、高亢,丝弦曲牌秀丽、柔婉。打击乐曲传统称“锣鼓点子”或“锣鼓经”,源于“车马灯”、“对打子”之类的民间歌舞,或源于民间的“喜庆锣鼓”、宗教性的“法事锣鼓”,一般为大、小剧种共有,分单点子和复点子两类,各剧种都有专用的“开台锣鼓”。“场面”则分文场和武场。操管弦乐者为文场,操打击乐者为武场。不仅如此,各大戏剧种有各自的乐器,如祁剧的“祁胡”、“战鼓”、“祁锣”,荆河戏、武陵戏的“马锣”、湘昆的“怀鼓”。它们大都来源于民间流行的地方乐器,即使是源于其它区域流行的乐器,也在弹奏、击打手法和音乐旋律风格上实现了地方化。
二、民间歌舞特技与戏剧表演语言
歌舞是戏曲艺术的重要元素,民间歌舞为地方戏曲提供了基本的舞台语言形式。前面所述的“傩歌”、“傩舞”亦属于民间歌舞的范畴,是一种带有宗教性的歌舞。
除此之外,湖湘地域还流传着大量的其它民间歌舞形式。湖南的民间歌舞源远流长,而且多种多样,唱的有山歌、田歌、船歌、炉歌、采茶歌等,舞的有花灯、龙灯、狮子灯、车马灯、竹马灯、车儿灯、采莲船、打花鞭等,还有属于百戏的踩软索之类。约在唐代湖南就有演唱的记载。唐代的一些文学家、诗人的诗句中,有一些反映湖南歌舞的篇章。许棠《咏洞庭》诗:“惊波常不定,半日鬓堪斑,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鸟飞应畏坠,帆远却如闲,渔父时相引,行歌浩渺间”。这即指民间演唱的渔歌。踏歌是一种群舞,又名跳歌、打歌,是湖南地道的民间歌舞,从汉唐及至宋代,都广泛流传。舞者成群结队,手拉手,以脚踏地,边歌边舞。刘禹锡做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时,写有《踏歌词》:“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联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既描绘了踏歌者趁月色在堤上结伴歌舞的生动情景,又可供踏歌者唱演。多姿多彩的歌唱曲目和舞蹈动作为湖南地方戏曲的歌舞表现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乾隆以来,湖南各地元宵“扮演采茶、秧歌诸故事”、“耍狮、走马、扮采茶妇”、“甚唱采茶灯曲”,这种民间歌舞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逐渐形成一丑一旦演唱的对子戏,后来由于演唱题材扩大,又增加了小生一角,演唱的声腔主要是民歌、灯调(小调),湘南有牌子(锣鼓牌子、走场牌子),湘北有打锣腔。这些歌舞形式孕育和催生了花鼓戏、阳戏等湖南民间小戏剧种。
湖南地方戏的另一剧种花灯戏的三个流派——湘西花灯戏、湖北花灯戏、湘南花灯戏同样是在文武花灯、平田花灯、嘉禾对调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地方戏中的动作特技同样是对民间杂技动作的传承。民间乐舞杂技表演即“百戏”,起于秦汉,盛于唐宋,包括扛鼎、爬竿、吞刀、吐火等各种杂技艺术,还伴有装扮人物的乐舞、简单的故事表演,以及马戏、猴戏等。湖南一般农民也常以百戏节目自娱。每逢新春正月,农村遍耍龙灯、狮子,玩耍时便结合表演各种百戏节目,如舞拳弄棍、跳桌子、翻椅子、堆罗汉、砌牌楼、耍蚌壳、玩采莲船之类。“筋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项目,“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者,谓之“板落”;“筋斗掷身入水”者,谓之“水秋千”。从汉代的“侲童”、唐宋百戏中的“筋斗”,到今天戏曲舞台上的筋斗,是一脉相承的。今天戏曲舞台上的其它不少表演技艺同样源于这种民间表演。如戏曲中的“交阵”源于民间表演中“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牵马”源于“引马”;“拿顶”源于“倒立”。不仅如此,这种百戏节目也与巫傩结合起来,巫师利用百戏节目丰富表演技艺,使其进入戏曲后,技巧更高。迄今,湖南地方大戏中的《木连传》、《岳飞传》等连台大本戏中,仍保留了较多的百戏技艺。
湖南地方小戏的舞台角色中,具有艺术特色的是小丑、小旦、小生——“三小”。“三小”中,又以丑、旦为重。长沙花鼓戏丑行分“长身子丑”、“短衫子丑”、“烂布子丑”三种戏路。在各剧种丑行的表演中,除“扇子”、“矮步”外,还须会讲各种官话乡谈,并掌握一些民间武术。旦行的表演更重“手巾”、“花扇”的运用,还要求娇巧,如岳阳花鼓戏有“三娇”、“三妖”、“三俏”的讲究,其与湖湘乡野多喜武术之风以及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中崇尚玲珑娇媚之审美趣味相关。另一方面,湖南民间小戏动作多从生活中提炼而来。如地方戏中的“开门”、“关门”、“进门”、“扯鞋”、“掸灰”、“端茶”,劳动生活如“砍柴”、“挑水”、“摇船”、“采莲”、“耕田”、“推磨”、“摸泥鳅”、“摘棉花”,都是在生活动作的基础上加以舞蹈化而成,动作优美自然,富于生活气息。源于祀神法事的傩戏,其表演中则有不少如“玩师刀”、“按诀”、“走罡”(踩八卦)之类的民间法事动作。衡州花鼓戏基本功训练多接近于民间武术、舞蹈训练,如“赶桌”、“爬梯”、“罩鱼”、“筷子功”、“碟子功”、“板凳功”等,其表演技艺吸收民间百戏、杂耍的痕迹非常明显。《池塘洗澡》中的“纸龙舞”、《逃水荒》中的“耍筷子”、“耍杯子”,都近于百戏、杂耍。这些表演技艺中,相当一部分带有特技性质。
三、区域自然社会资源与戏剧文学创作语言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荆楚成为周朝的一部分。自此人民生生不息,文化源远流长。湖湘之地,四面山水环绕,形成了相对封闭独立的区域,区域内山清水秀,山水相离,民族众多,民风各异。因地扼江南之要,自古兵家必争,战乱频繁,居民屡为迁徙;又为历代朝廷政要贬谪之所。特殊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源流演生了自然文化、民族文化、移民文化、战争文化、贬谪文化等多文化交融发展的独特的文化形态,使湖湘文化整体上呈现出底蕴深厚、丰富多彩、个性强烈的显著特征,使反映这种文化面貌的戏曲种类繁多,个性突出,派别纷呈。湖南地方大戏有湘剧、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舞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等八种。湘剧有高腔、低牌子、昆腔和弹腔(南北路及一些杂曲小调)四大声腔。民间小戏包括形成较早、带有宗教色彩的傩戏、戏曲化程度较高的花鼓戏和阳戏、歌舞性强的花灯戏。傩戏又分为湘西、湘南、湘北、湘中四路,分别有不同的叫法。湖南的花鼓戏,以流行地域和声腔、剧目、舞台语言等方面的差别而分为长沙花鼓戏、常德花鼓戏、岳阳花鼓戏、邵阳花鼓戏、衡州花鼓戏、零陵花鼓戏6种。阳戏分为南路阳戏和北路阳戏两个流派。花灯戏有湘西花灯戏、湘北花灯戏和湘南花灯戏3派。地方戏剧目丰富多彩,湖南地方大戏传统剧目即有1470个;民间小戏中,花鼓戏、阳戏传统剧目共计556个,花灯戏200个,仅傩戏约60个,而且地域特色鲜明。这种影响还体现在“湘剧”、“湘昆”、“楚南戏”等剧种名称上。
湖湘之地人杰地灵,引“无数英雄”“折腰”。“炎”、“舜”、“湘妃”等远古传说流传甚广,“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腾(子京)范(仲淹)”、“李(白)杜(甫)”流连其间,“文(天祥)石(达开)”、“曾(国藩)左(宗棠)”扬威沙场。及至近世,“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更建不世之勋。这些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素材。这一方面体现在《洪江渡》、《湘江大会》、《楚宫听琴》、《打零陵婆》、《划龙船》等具有湖湘地域文化标识的剧目中,更表现在戏剧所展示的湖湘文化内涵上,如湘剧高腔《山鬼》塑造了不同以往的屈原形象,《风箫怨》中融入了流传于长沙民间两千多年的“定王台”故事。《松坡将军》、《罗大将军》、《黄公略》、《地下火焰》则描写了近世以来不同时期湖湘人物形象。更为可贵的是《铸剑悲歌》、《姑嫂忙》、《打铜锣》、《园丁之歌》等一批剧目贴近现实生活,表现了湖湘地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时代风貌。
[1] 龙华.湖南戏曲史稿[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
[2]钟璞.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湖南地方戏剧文化自觉缺乏[J].民族艺术研究,2011,(1):37-39.
[3] 刘旭.湖湘文化概论[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I236.64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标识码] A
A
1671-5136(2011)02-0120-03
2011-06-02
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2008年立项课题《新时期湖南区域职业语言研究》(课题批准号:0806065B)的研究成果。
盛光希(1964—),男,湖南长沙县人,湖南女子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职业语言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