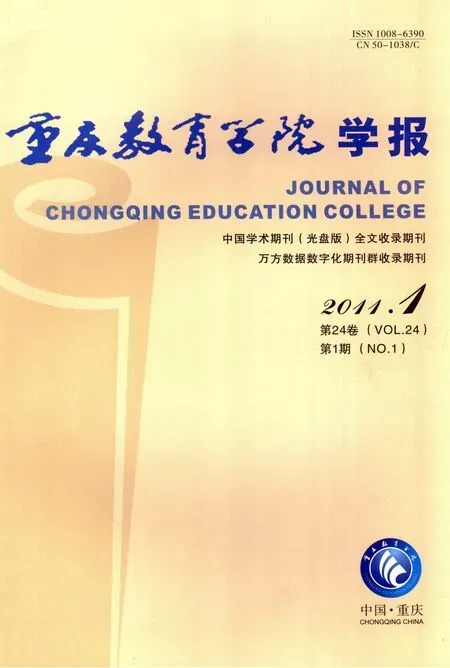文革时期科技法律秩序的历史反思
侯 强
(宁波大学 法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文革时期科技法律秩序的历史反思
侯 强
(宁波大学 法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文革时期虽然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严格的科技法律秩序被破坏殆尽,但与这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科技管理与科技生活的运作机制及实现科技生成和运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并呈现出特殊类型的科技法律秩序。在法律缺失的语境下,文革时期特殊类型的科技法律秩序已成为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历史文本。
文革时期;科技法律秩序; 历史反思
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新中国科技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其中断了党和人民经过十七年艰苦创业的科技发展的正常进程。但值得注意的是,综观文革时期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虽然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严格的科技法律秩序此时被破坏殆尽,事实上与这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科技管理与科技生活的运作机制及实现科技生成和运作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并呈现出一种特殊类型的科技秩序,颇值得我们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和反思,很可惜迄今为止学界对此还鲜有人作专题探讨。在笔者看来,文革时期特殊类型的科技法律秩序已成为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历史文本,对其进行一番历史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新中国科技法制发展的社会文化机理和运作机制,认识隐含于其中的不同的价值、发展模式的冲突,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极左路线所导致的空前的民族灾难,从而更为深刻地总结文革时期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左”的科技口号和言论凌驾于科技法律之上
从1957年开始蔓延和盛行的法律虚无主义文化认同,对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挠,法律成了仅仅服从于阶级斗争的便宜性政策的需要。1958年,在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的讨论中,竟出现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权威观点。法律虚无主义文化认同在文革十年浩动中发展到了极至。它中断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导致了法治化的夭折,以至人治观念横行。在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和发展的这种法律虚无主义文化认同,一方面,弱化了社会对党和政府守法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强化了民众对“守法”的漠然和屈从。文革时期,整个中国陷入一种严重的混乱状态,而科技战线又首当其冲成为公认的“重灾区”。在“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浪潮冲击下,建国后十七年社会主义科技法制建设的成果遭到了全面破坏,导致新中国法制现代化发展的扭曲和灾难。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开始之日起,就完全置法制于不顾,用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掀起的“大民主”代替了有法制保证的真正民主,并在1975年宪法中以根本法形式确认“四大”为“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明确指出 “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文革十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科技方面的立法,国务院也基本没有制定过科技方面的行政法规。国家科委于1970年7月同中国科学院合并。唯一的法规性文件是1972年10月财政部与国务院科教组发布的《关于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科学研究补助费使用管理的几项规定》。”[1](P543)这是新中国科技法制建设的空白期,也是科技法制遭肆意践踏的时期。
文革时期,我国科技领域在极左思想理论指导下,科技政策被过分推崇,其结果是:科技政策高于科技法律,科技政策代替科技法律,科技发展在实践中变成了只依靠科技政策,不需要科技法律,甚至出现了科技政策阻碍科技法律实施的不正常状况。事实上,在“不破不立”口号声中,建国以来一切正确的科技政策被破坏殆尽,而此时党并没有制定出明确而具体的科技政策,构成此时科技政策内容的只是一些“左”的科技口号和言论。具体而言,这些“左”的科技口号和言论主要来自:一是领导人讲话中有关科技的只言片语;二是以党中央、国务院等名义发布的各种形式的决定、命令、通知中对科技领域做出的若干规定;三是“两报一刊”中有关科技工作的社论、评论。严格地讲,上述载有“左”的科技口号和言论的文本都不具备作为法律所必备的要素,但在文革时期其事实上充当着规范科技发展的“法律”形式,并实际发挥着法律的效力。文革时期,在没有任何制度化机制和法律加以约束的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P329)“毛泽东的一本语录集‘小红书’,超过了从未创下的印刷纪录。只有‘伟大舵手’的形象、其传记和著作才是真正的崇拜对象。”[3](P599-600)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讲话以及毛泽东著作的摘要被称为“最高指示”,成为人们最高行为准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具有莫大的权威和效力。其中,有关科技的只言片语虽不具备现代宪法的精神和严格的法律形式,但实际上扮演着科技“宪法”的角色。与之相伴随的是,在法律虚无主义文化认同的影响下,文革时期不仅许多重要的科技法律没有制定出来,而且已经制定出的科技法律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得到认真实施。在科技立法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下,文革时期以党中央、国务院等名义发布的有关科技工作的各种形式的决定、命令、通知等,其虽都不具备现代法律的系统性、严谨性和稳定性,也不具备现代法律的形式化和程序化特质,但实际已成为规范此时科技发展的“基本法”。至于文革时期“两报一刊”则是党中央的喉舌,充当着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其中,有关科技工作的社论、评论对于科技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着“法律”的效力,实际成了文革时期的科技“特别法”。例如,1966年5月《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蔑视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社论,就开启了十年“文革”对我国科技事业严重摧残的历史,破坏了我国科技事业和科技法制现代化发展的正常进程。
在这种“法律”背景下,“到1966年末,整个中国都呈现出一种无政府状态”[3](P599),有“科技宪法”之称的《科研工作十四条》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纲领,一系列“左”的口号和言论甚嚣尘上,广为流传。虽然处于文革动乱和逆境中的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科技领域的纠“左”努力,如“周恩来于他去世的前一年(1975年)又重新发出了他在196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教育和科研现代化)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为竞争、知识、技术、科学和生产恢复名誉,而这一切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反动的,或与革命信仰相比是很次要的内容。然而,1975年春到1976年4月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重新把他们排斥到政权之外了,”[3](P601)并没有改变文革时期整个社会科技发展呈现出的无序性和周期性震荡局面。文革时期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环境影响着新中国科技的正常发展,我国科技事业自此进入了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科技领域反科学活动的“合法化”
由于毛泽东对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升温的阶级斗争和科技领域的政治化,至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1966年开始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要求实行全面大批判,全面大夺权,全面阶级斗争,全面专政,彻底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道路,结果造成几乎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全面内战’,使中国处于社会动乱、国家瘫痪、经济崩溃的边缘。”[4](P103)在阵阵高涨的席卷全国的“横扫”、“打倒”等滚滚政治声浪中,文革十年科技领域反科学活动变成“合法化”。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严厉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是在“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要求“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由此确定的一套科技理论、路线和方针,一方面,彻底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科学技术事业的成就;另一方面,对科技领域整体做出领导权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持的政治定性,实质是在科技领域发出了反科学活动“合法化”的动员令。
同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阐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明确“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具体是“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强调采取的方式“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文革时期“左”倾科技政策的主要内容在《五·一六通知》到《十六条》中已经基本形成并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自此,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开始走入歧途。此时,新中国科技法制建设不但全部停滞下来,而且已经建立起来的科技法律制度也遭到了完全破坏。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对发明家的奖励为例,文革开始后,对根据《发明奖励条例》评选出的“近300项发明,既未发奖金,也未召开大会,只是冒着‘风险’将《发明证书》、奖章寄给发明人了。我国第一次发明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草草完结。”[5](P253)事实上,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科学技术发展已被纳入“兴无灭资”的政治斗争轨道,深深陷入了反科学非理性的泥潭。也正由于此,文革时期维护科技秩序和进行科技管理,完全依靠中共中央文件等非法律手段,科技法律已被彻底抛弃了。
文革开始后,科技战线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领域,许多科研机构被撤消或被迫停止工作,除个别领域外(主要是军工方面),整个科研系统的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70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被撤消,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被大批取消,本来就不十分健全的科技制度因之被冲得更加零乱不堪。以中国科学院为例,1973年,中科院所属研究机构仅剩53个,到1975年又减少到36个。再如,全国300多种科技刊物一度全部停刊,国际科技交流活动几乎中断。[6](P1190)
在文革十年中,科学完全被反科学所取代,知识成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没有知识和文化倒成为骄人的资本,“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各地造反派掀起的揪斗“牛鬼蛇神”的浪潮中,广大知识分子被污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批科技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一些学有专长的科学家则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横遭批判、斗争和迫害,甚至被关进变相的监狱——“牛棚”。据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起诉书中的统计,文革时期,在卫生部直属14所高校的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达500多人。1965年,全国高校有教授、副教授7800人,到1977年减少为5800 人,其中不少是被迫害致死的。[7](P82)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由工农群众采用“四大”形式去“造反”和“夺权”,显然是不可能有任何法理上和逻辑上的根据的。这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而且导致公民对现代科技法律的信仰也由此几乎完全被摧毁。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政治化科学观的主导下,科学完全被反科学所替代,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荡然无存。1967年6月,“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在其创办的《科研批判》杂志“创刊词”中,对17年来科技战线横加批判,指责其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制定了一系列黑纲领、黑文件以及种种规章制度,把中国的科技事业引入了歧途。[8]与之同时,随着科学批判活动在全国的广泛开展,自然科学理论被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编造的。1968年3月,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组织,爱因斯坦被认为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科学思想已经成为危害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爱因斯坦之雾”。实际上,文革期间的相对论批判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是反右派以来的反科学思想登峰造极的再现,想借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实现无产阶级占领科学阵地。于是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被选作典型遭到反科学的哲学批判。”[6](P1156)这种事实上连相对论究竟是什么也没有搞清楚的批判,留给人们的只能是黑色幽默。其实,“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和1961年国家制定的《科研十四条》都明确规定,不允许给自然科学理论贴阶级标签和进行哲学批判,自然科学理论的是非问题只能通过学术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文革’期间所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是明显地违背国家所制定的这些正确的科技政策的。”[9]十年浩劫中,将科学技术人为地抹上强烈的阶级色彩而归入上层建筑领域,是对科学肆无忌惮的践踏,其实质是对科学本身实行全面专政。历史对此已经作出了结论:反科学的哲学批判对科学发展是徒劳无益的。
三、科技战线纠“左”的政策与实践
文革时期,面对科技界乱象纷呈的局面,以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极端恶劣的政治气候下,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坚持建国以来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形成的正确的科技政策,并以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动乱中与反科学的行为进行抗争,不失时机地纠正科技领域的极“左”错误,整顿和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被点燃后,危险日益向科技界的知识分子逼近。为尽力保护好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宝贵财富的知识分子,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经聂荣臻的艰苦努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意见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这个文件第十二条中明确规定:“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这个限制性政策规定,虽在群众运动兴起后,被群众运动的激流冲得形同虚设,并不能改变科技界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命运,但其多少还是发挥了一点挡箭牌的作用。如,1966年12月7日,周恩来在接见中科院京外单位代表时就一再指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当然要保护,一般的科学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应当保护。[10](P100)再如,周恩来在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虽然是资产阶级的,多数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因而不能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说 “干部大部分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也是可以改造的,如蒋南翔,也可以改造好嘛!”“主席的红线是照耀干部的”。[5](P350)
在文革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周恩来无法抵制住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科技事业破坏的发生,但他始终抱着对人民和国家负责的信念,以清醒和理智的态度,牢牢掌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如履薄冰地运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想尽一切办法限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范围,把破坏尽可能减小到最低限度。如,周恩来于毛泽东作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立即抓住时机,巧妙运用尚方宝剑,因势利导,制止“停产闹革命”,坚定不移地维护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1966年9月7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仅从1967年3月至11月间,周恩来和毛泽东等就先后签发了22封电报,指示“不准夺权、“制止武斗”、“坚持生产”,对核科学家采取保 护 措 施。[11](P574-575)1970 年 11 月 21 日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国家计委地质局 “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针对某些错误观点进行了抵制和批评,说:“‘专家’前面不要再加‘修’吧!骂得太宽了!所有‘专家’都‘修’?”[12](P548)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尽可能淡化处理,要求他们多做些自我批评,竭尽全力保护科技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免受伤害,减少了科技力量上的损失。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于1972年在科技领域进行了纠“左”。面对基础理论研究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周恩来多次发表讲话,要求重视科学实验,重视科学理论研究,尽可能对科学家们的要求给予有力的支持。如:在周恩来的鼓励和支持下,周培源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组写成《搞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课教学》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72年第9期上,其 《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刊登在1972年10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虽然在1972年8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后期,周恩来的这些正确意见遭到了批判,但“在周恩来的一再督促下,在有关部门的要求下,在科学家们强烈呼吁下,中国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展了几项重大的研究工作,虽然遭受非难、批判和斗争,终究做了一点工作,有的还打下了初步的基础。”[5](P366)
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我国科技对外交流也开始逐步恢复。1972年,根据周恩来、李先念的指示,拟定用43亿美元进口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在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后,经毛泽东、周恩来的审批于1973年初执行。引进这些项目,不仅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工业生产的能力,而且提高了我国工业的技术含量,推进了工业的现代化进程。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经周恩来批准,1972年我国又派出科学家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出访欧洲和美国。针对代表团回国后慑于极左思想的影响畏首畏尾的做法,周恩来批评指出:“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13](P474)关于怎样学习和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1972年10月13日,周恩来在一份科技合作的请示报告上也批示:“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14](P423)通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至此我国科学技术的封闭状态虽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但我国科技界毕竟又趔趄地重新睁开眼睛看世界和走向世界了。
在文化大革命处于僵局的背景下,除了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纠左整顿外,邓小平又领导了1975年的全面纠左整顿。“邓小平把毛泽东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作为整顿依据,即‘以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反复强调四化建设是全党全国的大局,实际上是把‘三项指示’中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到了首要地位,着眼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15](P390)在邓小平看来,“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不把领导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岁的人来搞。好的可以管党务工作,管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很重要,它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保护和管理好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这也是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工作。党的、科研的、后勤的工作,三个部分,没有后勤,科研搞不起来。不能叫科研人员还去搞后勤,整天东跑西跑。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2](P33)这些方针和措施的提出和贯彻,鼓舞和调动了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全国人民工作的积极性。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两次整顿一开始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都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的否定,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但毛泽东难以从‘文化大革命’的陷阱中自拔,不容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每当整顿进行到一定程度时,毛泽东又以‘反右倾’、‘反复旧’的名义否定它们。”[15](P388)1976 年 2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 2 期发表了《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重头批判文章,把邓小平主持的科技战线的整顿诬蔑为“右倾翻案风”,鼓动在科技战线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接着,从3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所谓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至此,已经开始取得成效的科技整顿工作停了下来,已经好转的科学技术工作重新被打乱。
[1]杨一凡,陈寒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4]王东.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6]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7]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8]无作者.创刊词[J].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主办《科研批判》,1967,(1).
[9] 胡化凯.“文革”期间中国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3).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11]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周恩来与中国核工业[A].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2]见地质矿产部档案.转因自宋瑞祥.周恩来与地质矿产事业[A].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3]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 (下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14]曹应旺.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15] 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于 湘]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of the legal ord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HOU Qiang
(College of Law,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Zhejiang, China)
The strict sci-tech legal order of the modern democratic and law-governed society was disrupted almost completely in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but there were, to some degree, the mechanism for the sci-tech management and life and the approach to realizing sci-tech production which matched tha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eriod.Thus there appeared a special kind of scitech legal order.In the situation of insufficient law literature, it has become very important and special historical text.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sci-tech legal order;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DF08
A
1008-6390(2011)01-0038-04
2010-09-25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法制建设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0CGML10YB)”、浙江省教育厅项目“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反思(Y200907088)”的阶段性成果。
侯强(1966-),男,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法制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