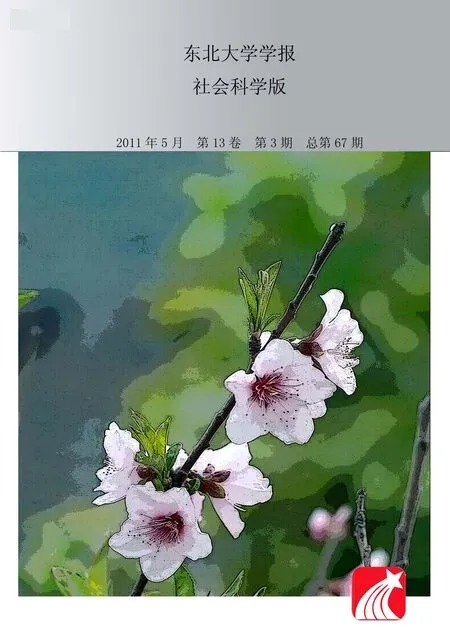躯体化:苦痛表达的文化习惯用语
朱艳丽,汪新建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天津 300071)
躯体化是指个体表现出生理症状,但找不到确切的器质病变的一种现象,有研究发现在病人呈现的最常见的症状中,只有10%~20%有明确的生理基础[1]。研究者认为,在许多非西方社会和文化中,躯体化是个体将苦痛通过一种生理疾病的习惯用语表达出来,例如Kleinman[2]在中国湖南长沙的调查,他对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病人重新评估,认为87%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因此认为神经衰弱是中国人通过躯体化的过程来表达情感苦痛的一种方式。
一、 躯体化概念及解释
1. 躯体化与心理化
躯体化(somatization)指个体的情绪问题或心理苦痛以躯体症状表现出来,本身却坚持认为自己身体不适,否认有任何的心理或情绪症状[3]160-163。躯体化一词是20世纪初Stekel创用,指“根深蒂固”的神经症藉以引起躯体性失调的过程;Katon等描述为以躯体症状表达心理不适与应对社会和个人烦恼,主要是由于社会文化背景造成;Lipowski称为是个体在心理应激下体验和表达躯体不适和症状的倾向,不能用病理发现来证实;Kleinman认为躯体症状是表达和解释个人和人际间种种心理方面的问题。这里的躯体化不能与DSM-Ⅳ(《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的躯体化障碍相混淆,DSM-Ⅳ把躯体化障碍归在躯体形式障碍类别之中,是指患者长期感到某个系统不适体验,但医学反复检验,无相应的器质性病变的医学证据,是一种疾病名称,而前者是作为心理问题伴发症状的概念。当然,并非一切不能用躯体疾患来解释的躯体性症状都算是躯体化。
与躯体化相对的概念是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心理化是指个体通过情感和认知的方式理解和表达自己及他人心理状态,尤其是心理苦痛的能力。心理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出现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当90年代初期Baron-Cohen及Krrish.Fritz等将其运用到神经生物学和精神病理学中研究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等,此概念开始变得较多样化。其中,Kleinman认为所谓心理化是在对事件和身体状态的前因后果的理解上更多地归结为主观因素,对主体的人的地位的突出,是Max Weber所说的理性化进程在个人身上的体现[4]。这样,情绪也就更多地表现为对“我”这一行为主体的评价,更少地表现为生理的兴奋或抑制。
2. 躯体化的几种理论理解
(1) 医学人类学。对躯体化的医学人类学理解是建立在对病痛和疾病,以及医学模式的生物医学模式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区别之上。当个体生病的时候,体验到的是病痛和不便,而共享的文化情境则规范和指引着个体如何解释病痛的含义。当个体寻求医学诊断治疗,医生对症状分析和诊断的时候,在生物医学模式下,疾病的原因是生理异常,干预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药物、手术等手段改变机体的物理和化学过程;而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病痛的原因不仅仅是生理的,同时也是(而且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和社会的。
(2) 精神病学。在精神病学领域,躯体化既是躯体形式障碍的一种,又泛指为各种精神障碍伴发躯体症状的现象。在ICD-10(《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本》)中,躯体形式障碍作为一种临床现象,表现为某种身体上的症状,但不能从医学角度对身体疾病作出合理解释。在临床实践中,使用较广的心理卫生量表SCL-90(症状自评量表90)、MMPI(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表)、TAS-20(多伦多述情障碍20条目量表)[5]以及OAS(述情障碍观察量表)[6]中都有与躯体化现象密切相连的因子。作为疾病名称的躯体化障碍与作为心理问题表达方式的躯体化概念是有区别的,为了有利于厘清躯体化的诊断标准及相应治疗,有必要对此进行区分。
(3) 心理学。在心理学领域关于躯体化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精神分析理论假设个体用躯体化症状置换内心不被他人或自身接纳的或未得以满足的情绪。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心理苦痛体验与表达的文化差异,如Kleinman在中国的调查[2],他认为中国人倾向于以躯体方式表达心理苦痛,而西方个体较多以心理学范畴的词汇来表达苦痛体验,也有研究者指出西方人在陈述躯体症状的同时也有相当比例陈述心理症状,而非西方人则较多陈述身体症状[3]160-163。认知理论[7]认为躯体化与信息加工过程有关,这类个体有着根深蒂固的遗传易感素质和人格特征,倾向于将身体知觉误解为严重生理疾病。作为一种现象,非西方社会的高躯体化已是一致的结论,但对现象的解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
二、苦痛的习惯用语(Idiom of Distress)
从以上概念辨析和理论解释来看,社会科学家认为在不存在精神疾病的情况下出现的躯体化是一个交流和应对社会及个人苦痛的过程。有学者将此表述为苦痛的习惯用语。关于苦痛的习惯用语研究是对于个体和所生活的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该概念首先由Nichter于1981年提出[8],“在任何一种既定文化中存在各种表达苦痛的方式,这些表达模式的文化构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某种特殊的相互作用,与文化中普遍的价值观、标准、繁殖主题和健康关注等相联系”。因此可以说,苦痛的习惯用语就是社会文化群体中的群体传达苦痛的特殊方式,如同文化的习惯用语千差万别,这种差别源于文化中最显著的隐喻和最流行的传统。Kleinman和Katon等都倾向于将躯体化解释为以身体疾病和医学求助的习惯用语表达个人和社会苦痛[9-10],认为躯体化病人是“那些具有心理苦痛和情绪问题的病人通过身体症状来表达他们的苦痛”,并且躯体化是在非西方社会中将苦痛作为合适的习惯用语。而在西方,尤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中的白领等中产及以上阶层群体中多数以情绪表达和心理化形式应对压力冲突和情绪苦痛,这减少了将社会和个人苦痛躯体化的可能性[11]。应用某种苦痛习惯用语须要调动关于体验分类和因果解释的系列背景知识,文化中流行的苦痛文化习惯用语反映了关于身体、情绪和社会关系的知识。每一种习惯用语都表达了在不同的社会现实中个体疾病体验发展的持续过程,所有的习惯用语在个体的日常生活意义创造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各个文化领域里都存在着混合了躯体症状及情绪症状的躯体化表现,例如,越南人的“肾虚”“心虚”“中风”可以描述为惊恐和焦虑的习惯用语,中国的神经衰弱、印度的dhat、日本的shinkeishitsu、韩国的hwabyung、中国台湾的肾亏、非洲东部的brain fag,以及波多黎各的ataque de nervious等都是心理苦痛的文化习惯用语[12-14]。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Butler[15]认为一种习惯用语指体验生命的一致感和认同感,实际上表现为道德和文化维度,并与心理、社会或身体维度不可分离。Whyte[16]认为习惯用语在一个社会中普遍流行(共享的,如方言),以引导行为并传达意义,如同词汇一样被理解,并以一种特殊的方法组成情景。Williams[17]认为习惯用语也是指对于疾病的叙事建构,用目的性和功能性的成分表达这些解释,不仅仅是信仰或缘由。这些理解突出了习惯用语是一个社会文化中为了相互理解而凸显出的适宜表达方式。因此,躯体化与心理化只是关于苦痛的文化习惯用语的一部分,其他还有关于宇宙观、道德、人际以及政治的习惯用语,它们也同样被用来谈论去道德化及其他类型的苦痛,这些术语也具有文化显著性和社会合法性。个体采用何种表达用语取决于具体的背景、情景和文化,这就使习惯用语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过程具有动力性。
三、 文化:躯体化表达的背景
1. 文化与习惯用语
一般来说,现有的疾病和情感会在所有人类社会都存在,但是由于文化、情景和个体的特殊性,这些疾病和情感也是不同的,他们习惯的表达方式也不同。不同文化下的习惯用语千差万别,这种差别源于文化中最显著的隐喻和最流行的传统,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都将转化成关于苦痛和躯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我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文化塑造人类体验并赋予体验以意义,因而,人们运用文化习惯用语去表达他们的心理苦痛时并不是自由的。习惯用语只是被用在一种文化之中,文化中的成员为了相互理解拥有共同的表达参考。每一个苦痛的习惯用语都基于文化符号,是人们用来表达解释和转化他们苦痛的共享的行为或语言等。文化背景调节着社会对个体的影响,躯体化的流行和模式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不同的。在社会结构更紧密的地方,社会控制机制限制了关于自我和社会的话语,而集体体验和表达的意识形态对苦痛的身体性和其他习惯用语的强调多于对于心理和社会习惯用语的强调,躯体化就会盛行[18]。
2. 中国人的躯体化
众多研究证实中国人更习惯以躯体化表现表达心理苦痛问题。由于社会文化传统的不同,人们对于症状的体验方式和表达方式也不同,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躯体化”是一种不良的反应(躯体形式障碍),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它却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方式,关于中国人高躯体化的文化解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受文化形塑的情感表达方式。作为社会结构紧密的典型和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的中国社会,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高于个体内在情绪体验的表达,强调态度合适的情感表达高于个性的情感表达。因此,社会对于在家庭范围外公开口头表达个人苦痛持强烈的负评价,只有通过身体问题而非心理问题才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缘由。在遭遇社会和个人苦痛的时候,个体倾向于压制自己的苦痛表达,往往借助丰富的文化代码对心理问题使用躯体化的隐喻,诸如身体动作、服饰、环境描写以及富有寓意的语言等微妙而间接地描绘出来的,这些传统文化概念和规范决定了中国人表达个人和社会的苦痛采用的是一种身体术语,而不是通过直接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样就可得到社会的接受和认可,避免情感疾病给家庭带来的污名。因而,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在表述内在感受方面是存在困难的,而是更倾向于一种以外在身体术语表达内在感受的认知模式。
(2) 整体的身心观。中国人在表达情感时通常不会严格区分躯体和心理,会用一种混合的途径来表达情感,而西方社会个体则较多关注心理,较少关注于躯体[19]。这来自一种文化的差异,即文化中不同的身心观。不同于西方社会里基于笛卡儿哲学的身心分离观,中国人的身心观是身心一体,中国语境中的身体不仅是生理器官组合的生物躯体,也是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中医里的情志学说认为人的情志活动是以五脏精气为物质基础的,五脏化为五气,如心-喜、肝-怒、脾-悲、肺-忧、肾-恐,不同的情志刺激可影响相应脏腑,致使种种病变发生。中医的器官并不完全等同于西医解剖学的器官,而是对一组功能的概括,这种学说把心理活动身体化了。因此,身体感觉处于一个复杂的位置,身体的动作与神貌,不仅仅是人体的生理活动与器官功能的体现,更表现主体的切身感悟与情思,成为心理意向的表达途径之一。基于这种身心观,躯体化或者心理化的差异就可以理解为对症状关注的差异,这也更好理解中国人混合身心的表达方式,也解释了中国抑郁症患者对躯体症状关注的文化根源。
(3) 社会对心理问题的污名。污名化就是目标对象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这个受损的身份可能是精神疾病患者、社会越轨者等。长久以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讳言“心病”的,如果心理方面出现了问题,就会惊恐地认为自己的脑子出现了病变,担心一旦自己的心理疾病被他人发现,就多少会受到他人的歧视。因此,躯体化形式就比直接表达心理苦痛更被社会接纳,也较少对个体的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产生影响。
还有研究者从语言应用角度去分析。根据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情感与其在特定社会中有关日常生活的实践话语被分类和使用的方式是分不开的。与躯体化有关的词语传递出与他们的特定文化背景有关的独特含义,也就是说指代的是一种共享的普遍性体验,当然,中国也是如此。所以,个人在表达苦痛的时候躯体化的比例会高于那些语言中含有较丰富情绪词汇的国家。但是,语言应用与躯体化的关系到底是解释关系,还是表现关系,也许很难阐释清楚。此外,还有研究者从躯体化患者的人格特征、应对方式、述情障碍特征及其抑郁症状等角度进行研究[20-22],探讨可能的影响因素,使躯体化研究越来越具体深入和可操作化。
四、 启示与思考
1. 躯体化的适应功能
当其他表达方式不能够很好地交流的时候,苦痛的躯体化表达具有一种适应性的功能。虽然一些学者认为躯体化是适应不良的,但是如果把躯体化描述为一系列表达苦痛的文化习惯用语,以便有效地应对这种苦痛,那么躯体化是不同文化中适宜地表达个人和社会苦痛的自然而然的方式和现象。在其他方式不被社会文化接受的时候,病痛不仅是一种交流的媒介,而且还能表达苦痛、去道德化,以及其他平常不允许被表达的感觉。与躯体化术语相关联的习惯用语,把关键的社会和心理文化信息传递给他人,这些信息包含着重要的文化含义,具有社会和个人功能。假设这在社会中得到文化规范的积极认可,那么可以说,躯体化具有社会适应功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装病或者去理性化地选择躯体化,因为它有时会制造出新的问题。
2. 临床评估与治疗
许多研究表明,躯体化的表达倾向引起临床诊断偏差,因而浪费了医学资源,造成社会与家庭的严重负担。在临床评估中,如果无视其作为苦痛表达的文化习语这一含义而仅仅以躯体疾病来对待,会导致对卫生保健资源的不当和过度使用,对个体无必要的和危险的检测及不适当的治疗,造成个人和家庭的苦痛。为了能够作出完整的诊断评估与治疗,不仅要关注到病人的躯体主诉,也要关注到病人的情绪、生活经历和人际关系;不仅要看到他的生理基础,也要看到他的心理和社会原因。因此,对于躯体化反映的求医者要区别对待,那些作为诊断的躯体化有着比较严格的标准,转诊即可;那些作为行为和现象的躯体化,或者说是作为心理苦痛的习惯用语的躯体化,须要考虑病人的心理需求,考虑他们通过躯体传达何种不能表达的情感,及早推荐他们作心理治疗,避免躯体化症状慢性化,防止因慢性化而影响到病人的人格和社会生活。
3. 本土化心理治疗
作为心理苦痛习惯用语的躯体化,最合适的对待方式是引导进行心理治疗,或者类似心理治疗的带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治疗。研究者指出[23],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比较研究的结果证实,西方现代心理咨询与治疗只不过是助人恢复心理健康的策略之一,而非唯一的策略。那么,如何开发既能满足快速有效诊断,又能为中国人解除心理疾患的心理治疗方式,为寻求适合中国人的诊断方式提供可行性参考,有待于躯体化研究进一步开展。关于苦痛表达的文化习惯用语的主要研究是在临床设置中[24],在做这一项工作的时候,有四个问题可以为研究提供思路:①人们用哪些习惯用语去表达他们的心理问题;②这些习惯用语如何建构人们体验苦痛的方式;③当遇到心理健康问题时,这些习惯用语如何控制、整合和转换心理苦痛;④在不同的心理健康服务设置中这些习惯用语如何传播。
参考文献:
[1] Kroenke K, Mangelsdorff A D. Common Symptoms in Ambulatory Care-incidence, Evaluation, Therapy, and Outcome[J].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989,86(1):262-266.
[2] Kleinman A. Neurasthenia and Depression: A Study of Somatization and Culture in China[J].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982,6(2):117-190.
[3] 郑泰安. 华人常见的心理症与社会心理问题[M]∥曾文星. 华人的心理与治疗.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7.
[4] Kleinman A. 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and Disease: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5] 蚁金瑶,姚树桥,朱熊兆. TAS-20中文版的信度、效度分析[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17(11):763-767.
[6] 朱熊兆,蚁金瑶,姚树桥. 述情障碍观察量表中文版信度和效度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3,11(4):276-278.
[7] Brown J.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 An Integrative Conceptual Model[J]. Psychol Bul, 2004,135(5):793-812.
[8] Nichter M. Idioms of Distress: Alternatives in the Expression of Psychosocial Distress: A Case from South India[J].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981,5(4):379-408.
[9] Kleinman A, Kleinman J. Somatization: The Interconne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Among Culture, Depressive Experience, and the Meaning of Pain[M]∥Kleinman A, Good B. Culture and Depress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0] Katon W, Reis R, Kleinman A. The Prevalence of Somatization in Primary Care[J].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1984,25(2):208-215.
[11] Katon W, Kleinman A, Rosen G. Depression and Somatization: A Review[J].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1982,72:241-247.
[12] Barrett R. Cultural Formulation of Psychiatric Diagnosis. Death on a Horse's Back: Adjustment Disorder with Panic Attacks[J].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997,21(1):481-496.
[13] Hinton D, HintonS, Pham T, et al. “Hit by the Wind” and Temperature Shift Panic Among Vietnamese Refugees[J]. Transcultural Psychiatry, 2003,40(3):342-376.
[14] Kirmayer L, Young A. Culture and Somatization: Clinical, Epidemi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J].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98,60(4):420-430.
[15] Butler C, Evans M, Greaves D, et al. 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Found Wanting[J].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2004,97(9):219-22.
[16] Whyte R. Questioning Misfortune: The Pragmatics of Uncertainty in Eastern Ugand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 Williams G. The Genesis of Chronic Illness: Narrative Re-construction[J].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1984,6(2):175-200.
[18] Keyes C, Ryff C. Somatiz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diom of Distress Hypothesi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3,57:1833-1845.
[19] Kleinman A. Writing at the Margin: Discourse 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0] 张朝辉,陈佐明,宋景贵. 躯体化障碍的人格特征与应对方式的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16(5):524-525.
[21] 马丽霞,邱亚峰. 躯体化障碍患者抑郁症状的对照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4,12(2):194-195.
[22] 朱熊兆,姚树桥,蚁金瑶. 神经症患者述情障碍及其特征的探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4,12(3):276-278.
[23] Pedersen P. The Intercultural Context of Counseling and Therapy[M]∥Marsella A J, White G M. Cultural Conceptions of Mental Health and Therapy. Dordrecht:D. Reidal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24] Parsons D, Wakeley P. Idioms of Distress: Somatic Responses to Distress in Everyday Life[J].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991,15(1):11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