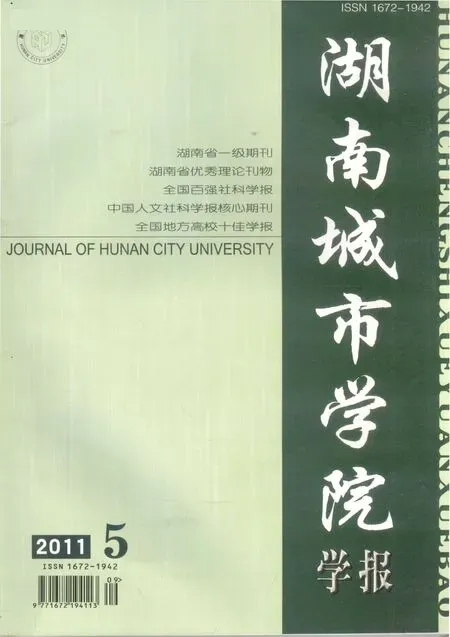隐喻研究的语篇转向
张 蕾
对隐喻的认知研究强调了隐喻作为思维方式创建人类知识结构方面发挥的作用,指出隐喻与身体体验的密切关系,它在语言层面的体现以及文化的蕴含意义,成为社会科学领域许多研究的出发点,包括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文化研究和教育学。尽管,隐喻的认知视角在隐喻的本质认识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研究成果对社科研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其研究方法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研究者引用的语料一般基于个人的内化语言和诱导式语料,与自然产生的语料有所不同。另外,概念隐喻所采纳的传统隐喻表达形式 A=B在实际的语言表达中很少出现[1]。由于隐喻认知研究的上述缺陷,研究者近来开始关注隐喻存在的以及它所创建的真实的交际语境,以便从语言、认知和文化各个方面对隐喻有较全面的理解。
在国内,学者突破了传统隐喻研究只关注词汇层面的局限,把隐喻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在更为广阔的言语环境中寻找隐喻意义的支点。[2][3]他们强调无论是相互作用,还是语义选择或是空缺填补,隐喻的产生都离不开语境,因而隐喻的产生和理解都是和语境密切相关的,隐喻的意义可以直接从语境中推导出来。在这一点上隐喻理论与语篇分析理论是一致的。因此,从语篇的角度来分析隐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4]。在隐喻研究语篇转向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注语篇隐喻在真实语境中的各种功能,包括语篇功能、人际功能和概念功能。
一、隐喻的语篇功能
Lakoff与Johnson早在1980年就论述了隐喻的连贯功能。由于隐喻在人类经验的理解和表达中起着中心作用,在语篇中就具有衔接力,是一种具有语篇组织功能的语篇策略[5][6]。当隐喻概念在语篇中作为宏观命题组织语篇时,就会制约着语篇中命题内容和语言的选择。在许多语篇中,写作者往往借助隐喻来说明和解释读者不太熟悉、不太了解的事物,以一个隐喻贯穿语篇始终,形成一个核心隐喻,支配若干由隐喻或由一个中心意象引申出若干相关的次要意象。这种扩展式隐喻一方面使隐喻创造的形象完整一致,使隐喻产生的意境和谐自然,另一方面是使语篇结构严整、浑然一体[7][8]。作为一种语篇策略,隐喻不仅通过类比转移机制的运作,使概念域之间的互动在语篇中形成语块之间的映射关系,同时还在语篇中形成系统的词汇衔接关系或网络,实现隐喻在语篇层面上的延伸(苗兴伟 & 廖美珍,2007)。研究发现在普通语篇中,隐喻转换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也就是说,语篇在发展过程中会从一个概念隐喻转换到一个不相关的概念隐喻,从而导致复合映射的产生[10]。
对隐喻语篇功能的揭示,为语篇衔接和连贯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的认知机制制约着语言运用的深层次连贯性,是实现语篇连贯的重要的隐性衔接手段[11],能够帮助我们揭示篇章结构与信息处理、储存和取回时所涉及到的心理活动
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揭示说话人是怎样建构概念体现和表征,以及他们是怎样引导听话人可及这个概念的。在日常交际中,隐喻不仅能够生动、简洁、准确地表达交际者的思想,使交际过程有序地展开,同时它所构成的认知网络又是开放的、多层次的和动态的,允许交际者根据语境的变化对话题进行不断地细化和扩展,保证交际的成功。[5]
另外,对隐喻语篇功能的阐释丰富了语类研究。例如在文学语篇中,隐喻成为突出主题,塑造人物的有效手段[12]。在叙述语篇中,随着情节的展开,对人物经验的陈述为隐喻提供了经验基础,同时涉及到作者想要突出的社会现象和伦理问题。而统驭语篇的隐喻完成了对经验的概念化,不仅确保了语篇的连贯,还体现了作者对经验的诠释,反映了作者的理性思考。因此,在不断更新的话语空间中,隐喻化的过程实现了作者对经验的主观诠释,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隐喻的人际功能
语篇的人际功能指的是语篇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前者对其所说或所写内容的态度。语篇生产者使用隐喻,通过对两个不同领域事物的对比,将抽象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帮助接受者更准确地理解信息。同时,接受者对语篇信息的接受过程并非客观被动而是主观能动的。他们有自己的经验和相关的“认知结构”。当接触到某个隐喻,与之相关的背景知识就会被激活,从而帮助他们对所输入信息进行理解。但是双方对同一事物的“认知结构”是有区别的。隐喻表达可以突显这种差异,即存在于交际者之间任何方面的距离,包括概念和情感上的差距。而这种差异往往是交际的起点和动力[13]。因此,隐喻的使用和解读在促进交际双方相互协商,消除认识上的差异,最终达到共识的交际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交际双方由于社会地位、文化背景、个人经历和知识结构存在很大差异,或者交际涉及敏感话题的情况下,往往需要隐喻这种特殊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去建构交际者的话语,解释一方不熟悉的概念,直接或间接地表达情感、观念和态度。
由于隐喻常通过一类事物来说明另一类事物,具有表达的间接性特征,因此许多隐喻带有“委婉”的功能[14]。当交际会威胁到对方的面子,我们会采用隐喻间接地进行表述,使听话者不因表述过于直接或粗俗而反感,可以起到人际关系“缓冲剂”的作用。以课堂话语为例:老师在反馈话轮中对学生进行负面评价时经常使用隐喻表达,降低威胁面子的行为产生的负面情绪。例如一位舞蹈教师在纠正学生的舞姿时,使用话语“and your toes are a little bit out.But not that much.About at five to one.Not like this.It looks funny like Charlie Chaplin”,将学生错误的舞姿与卓别林的滑稽动作进行类比,产生的幽默效果有效地化解了学生的尴尬。
另外,隐喻机制涉及到社会成员熟悉的社会活动以及相应的知识、信仰、意图和态度。它的使用能够形成一种默契与认同,增强归属感,有效地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例如,前意大利总理Berlusconi在竞选时反复用“政治是足球” 这一隐喻,将他的参政比作“进入球场”,将他领导的右翼联盟与“一支球队”相类比,而将其与左翼党的政治对决比作“一场比赛”。Berlusconi在政治话语中提及意大利选民最熟知的体育运动足球,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与能够激发他们强烈情感的文化价值结合起来,从而迅速地打破地域、阶级、性别的界限,取得了最大多人的支持。
除建立和维持某种社会关系,隐喻还是一种间接表达态度的手段。态度子系统是整个评价系统的核心,包括情感、判断和鉴赏三个子系统[15]。当人们使用隐喻,用一个事物去谈论另一个事物时,源域在其所属社团触发的情感反应,以及对相关行为的判断和对相关事物的鉴赏都会被映射到目标域。比如,新闻报道者将奥运经济中的隐性营销策略表征为乒乓球选手打出的“擦边球”。这种球落在球台的边缘,对手很难接到,隐含着对球员能力的正面评判。这种积极判断被映射到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获取利益,在不交纳任何费用的情况下把自身的产品和经济活动与奥运相联系的商业行为中,强调了隐性营销是弱势企业在市场上生存的一种策略,突出这种经济行为的正常性。再如,在美国大众语篇对移民现象的描述中,将移民与动物进行类比的隐喻表达“IMMIGRNTS ARE ANIMALS”使用频率最高,暗示美国社会对移民存在的歧视,移民社会地位地下,缺少平等权利。[16]
可以说,隐喻的人际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隐喻的社会性。对于Lakoff和Johnson的隐喻理论的解读,人们往往易于接受隐喻的认知性,而忽略隐喻反映现实和创建现实的功能。事实上,正如Lakoff自己所言,“从认知的角度看语言包含从社会的角度看语言”。[17]隐喻作为认知手段,发展并发挥于群体之中,是一种人际意义,具有社会性。
三、隐喻的概念功能
隐喻的社会性更多地体现在它的概念功能上。隐喻的阐释涉及到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源域为目标域概念化过程提供了基础,对它的理解是整体性的,即接受了它的一部分,就等于接受了它的全部。比如,如果你用疾病去表征移民,你就会很自然用有关疾病的其他常识去谈论移民这个社会群体。就像希望把身体中的疾病驱除一样,人们将移民排斥出主流社会。对于无序的、模糊的以及抽象的现象,这些伴随源域的预设含义能产生丰富的推论。因此,隐喻是构建某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拥有权利的语篇生产者左右接受者对有关事件理解的有效途径。[18]同样是对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的概念化,“immigrants are flood”这一隐喻表达将移民描述成自然灾害,汹涌的洪水与人数骤增的移民形成映射。洪水往往威胁生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对这种自然灾害的畏惧和抵制情绪通过跨域映射被转移到移民身上,表达了社会主流群体对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排斥和抵制。因此,隐喻能够反映隐喻生产者的态度和观点,在帮助接受者认知事物的同时限制并影响着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反映了隐喻的主体间性。
另外,在语篇的生成和理解过程中,隐喻经常与其他概念因素相互作用,包括人类大脑中贮存的有序的文化知识。隐喻本身所涉及的不同概念域之间的映射以及隐含意义是社会成员共有的一种文化知识,体现了他们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19]作为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背景知识,隐喻会潜移默化为一种常识,对它的使用和理解往往是无意识的,其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不易被人觉察。因此,Chilton指出隐喻类似于社会成员共享的常识,其背后隐藏的思想和观念不易被普通读者所觉察。
Fairclough同样认为隐喻是一种构建特殊“现实”的一种途径。他指出使用不同的隐喻对企业之间的竞争进行表征[20],产生了不同的公司管理语篇。用“赛跑”隐喻和“社团”隐喻再现企业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不同的管理理念。前者强调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后者突出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各类隐喻不同的组合方式经常产生不同的商业语篇,而这种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
因此,隐喻成为在语篇社会活动中一种比较隐蔽的反映和强化现存社会结构的认知和语言手段,对它的研究成为阐释人类行为中最核心元素的一种有效途径,包括各类政治语篇中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21-23],以及经济语篇所折射的对待各种经济现象的态度和观点。[24][25]
政治语篇往往涉及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包括国内外事务、国家的政策方针、社会平等和种族问题等。对此类语篇隐喻的研究,能够了解某个国家或特定的利益集团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和政治目的。如美国福特时期的“控制通货膨胀的战争”、卡特时期的“能源危机战争”和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都是通过公众熟悉的事物对国家面临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进行界定。战争目的域触发的一系列关联的蕴含,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能够唤起公众的共鸣,更易于以这个隐喻为基础去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26]
同样,富含抽象概念的经济领域也常使用隐喻定义一些特殊的经济现象。近来,受到社会科学领域“批评”思潮的影响,作为隐性评价手段以及具有意识形态承载能力的隐喻[27]表征在大众经济语篇中的功能受到关注[28]。这类语篇在帮助媒体遵守“客观性”职业道德,利用大众熟悉的具体事物去解释和描述抽象的经济事物的同时,比较隐蔽地向大众传播某种经济观念。研究者大多采用对比方法,研究不同媒体用隐喻对同一经济事件进行表征时存在的差异,如对欧元语篇的研究。Charteris-Black 和 Musolff[24]发现英国的媒体更多地使用战争隐喻,把欧元描述成战争积极的参与者,德国媒体则通过隐喻将欧元建构成社会机构(银行和政府)行为的被动受益者,反映出前者更多地受到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市场看作是一场生存斗争。而英国国内媒体《泰晤士报》和《卫报》对欧元的介绍,分别使用了容器隐喻和机械隐喻这两个结构隐喻,折射出英国社会在采纳欧元方面存在的分歧和争论。[29]
除了针对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和经济转型时期进行的个案研究,还有研究着重分析不同种类的隐喻模式对人们经济理念的折射,如隐喻使用者能利用生命隐喻和无生命隐喻之间的差异表征不同的经济理念中经济组织与市场之间不同的关系。[30]另外经济语篇中的隐喻研究已经成为研究社会问题一个重要的视角和补充。经济语篇中具有强烈男性特征的战争隐喻和体育隐喻大量存在,并在语篇中相互作用,揭示出经济领域男权思想的强势和女性的弱势[31],是对女性问题研究的重要启示。
为了更准确、深入地揭示隐喻表征与社会结构,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观的相关性,除了强调类比映射中源域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情感意义,还需关注由词汇所激活的同一源域中不同的概念场景。[32][33]它在语义上属于源域的下义范畴,却具有更丰富的心理再现,涉及与源域相关的形式、事物和行为。例如,以下隐喻表达均实现了“经济是旅途”这一概念隐喻,构建出经济域和旅途域之间的映射。但是,例(1)中的隐喻词“前行”和例(2)中的隐喻词“step”激活了旅途中前行的概念场景,将旅程进度与经济主体取得的业绩进行类比映射。例(3)和例(4)中的两个隐喻词“roadblock”和“重负”,在旅途域中指代行程中的障碍物和负重物,一同激活了阻碍前行的概念场景,再现了经济主体需要克服的困难。
(1)“品牌前行”(《中国经济周刊》,2008/08/11)
(2)In Beijing this summer, Lenovo will take the next step.(《经济周刊》,2008/04/25)
(3)Nike remains the No.1 seller of footwear and athletic apparel in the world, but the acquisition of Reebok by Adidas-Salomon, could throw up a considerable roadblock to the swoosh across Latin America and Asia. (《纽约时报》, 2006/01/28)
(4)北京奥运能否承受类似的经济重负?(《中国经济周刊》,2004/08/28)
以上对隐喻功能的探讨表明认知语言学与语篇分析的结合已经成为隐喻的研究的一个趋势。语篇是理解隐喻的重要载体,是隐喻意义的体现形式。以真实语篇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关注隐喻在语篇中的实现形式,能更充分地揭示隐喻使用现象。隐喻也是语言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体现在语篇的各个层面,镶嵌在语篇系统中,是语篇生成和语篇构建的重要机制,它不仅能确保语篇的连贯,建立某种人际关系,直接或表征地表达人们的情感、态度,还具有表征和构建现实的功能。随着隐喻研究跨学科、实证性与实用性的趋势不断加强,有必要在将来的研究中更多地借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基于大型语料库的共时或历时研究。
[1] Cameron L.Operationalising ‘metaphor’ for applied linguistic research[A].In L.Cameron & G.Low (eds.).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3-28.
[2]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7.
[3]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7.
[4] 魏在江.隐喻的语篇功能—兼论语篇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的界面研究[J].外语教学, 2006, (5):10-15.
[5] Ponterotto D.The Cohesive Role of Cognitive Metaphor in Discourse and Conversation[A].In Barcelona, A (ed.).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A Cognitive Perspective.Berlin:Mouton de Gruyter, 2000:283-297.
[6] Wee L.Constructing the Source:Metaphor as a Discourse Strategy[J].Discourse Studies, 2005(3):363-384.
[7] 廖美珍.英语比喻的语篇粘合作用[J].现代外语 1992, (2):32-34.
[8] 冯晓虎.隐喻—思维的基础 篇章的框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89.
[9]苗兴伟,廖美珍.隐喻的语篇功能研究[J].外语学刊, 2007,(6):51-56.
[10] Shen Y, Balaban N.Metaphorical (In)Coherence in Discourse[J].Discourse Processes, 1999(2):139-153.
[11] 卢卫中, 路云.语篇衔接与连贯的认知机制[J].外语教学, 2006,(1):13-18.
[12] 任绍曾.概念隐喻与语篇连贯[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6 (2):91-100.
[13]Cameron L.Metaphor in Educational Discourse [M].London & New York:Continuum, 2003:32.
[14] 束定芳.论隐喻产生的认知、心理和语言原因[J].外语学刊,2000(5):23-33.
[15] Martin J, R White.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M].London:Palgrave Macmilan, 2005:35
[16] Santa Ana, Otto.Like An Animal Was Treated:Anti-immigrant metaphor in US Public Discourse[J].Discourse & Society, 1999(1):191-224.
[17] Dirven, R & Frank & C.Language and Ideology.Volume II:Descriptive Cognitive Approaches[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2001:37.
[18]Chilton,P.Analyzing Political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4:45-47.
[19] Van Dijk, T A.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Cognition[A].In P.Chilton & C.Schäffner (eds.).Politics as Text and Talk:Analytic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Discourse[C].Amsterdam:John Benjamins, 2002:203-237.
[20] Fairclough N.Analysing Discoure: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USA and Canada:Routledge, 2003:131-132.
[21] Chilton,P.Missing links in mainstream CDA:Modules, blends and the critical instinct[A].In R Wodak & P.Chilton(eds.).A New Agenda in (Critical)Discourse Analysis:Theory, Methodolog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C].Amsterdam:John Benjamins, 2005:19-51.
[22] Hawkins B.Ideology, metaphor and iconographic reference[A].In R.Dirven, R.Frank & C.Ilie (eds.).Language and Ideology.Volume II:Descriptive Cognitive Approaches[C].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2001:27-50.
[23] Santa Ana, Otto.Three mandates for anti-minority policy expressed in U.S.public discourse metaphors.In R., Dirven, R.M., Frank & M., Pütz (Eds.), Cognitive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Ideology, Metaphors and Meanings Berlin:Mouton De Gruyter, 2003:199-228.
[24] Charteris-Black, J.& Musolff, A.Battered ‘hero’ or ‘innocent victi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aphors for Euro Trading in British and German financial Reporting [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003(2):153-176.
[25] Semino, E.A Sturdy Baby or A Derailing Train? 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Euro in British and Italian Newspapers[J].Text, 2002(1):107–139.
[26] Lakoff G, 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158.
[27] Charteris-Black, J.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M].New York:Palgrave, 2004:11-12.
[28] Deignan A.Readership and purpose in the Choice of Economics metaphors[J].Metaphor and Symbol, 2006, (2):87-110.
[29] Vaghi F, Venuti M.Metaphor and the Euro[A].In A.Partington, J.Morley & L.Haarman (eds.).Corpora and Discourse[C].Bern:Peter Lang AG, 2004:369-382.
[30] Charteris-Black J, Ennis T.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taphor in Spanish and English financial reporting.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J].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1(3):249-266.
[31] Koller V.Metaphor and Gender in Business Media Discourse:a Critical Cognitive Study[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4:172.
[32] Musolff A.Metaphor and Political Discourse:Analogical Reasoning in Debates about Europe[M].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2004:17-18.
[33] Semino E.Metaphor in Discours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