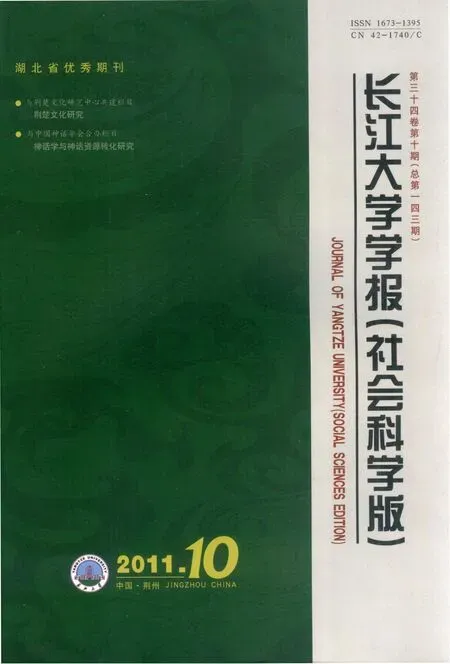古代山水诗与生态美学的现代承接
杨家海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古代山水诗与生态美学的现代承接
杨家海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古代山水诗要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与现代语境承接。生态美学是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而产生的,肯定人具有不以人为转移的审美性质和价值,主张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目的是为了人的可持续发展。对山水诗的特质与生态美学的内核做一比较性分析,可以认为它们在哲学基础、整体特色、美感经验三个方面具有共同性,从而论证了它们的承接可能性。
山水诗;生态美学;空间;意境;生态美
古代山水诗在现代语境遭遇了生存困境,亟需与现代语境承接。生态美学是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而产生的,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肯定人具有不以人为转移的审美性质和价值,主张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目的是为了人的可持续发展。古代山水诗需要当代思维的指引,从而在现代语境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生态美学需要与中国文化资源进行链接,从而寻找到在中国现代语境里的生长点。它们有无承接的可能性,在于它们之间的特质有无共同之处。
一、哲学基础
中国哲学在解释世界的本源与宇宙自然万物(包括人)之间的关系时,是用气的哲学。“气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气非无,乃是有;气又非形,乃是无形之有而能变成形的。”[1](P40)故而气的哲学是生成论的哲学,它的生成方式是“聚”和“散”,即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P232)《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3](P733)原来,“气”就是一种“生气”。气的生成作用构成了自然万物的生命,人与自然都是气的生成产物,是同构的,这说明“在生命存在上,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不可分离。客观地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主观地说,自然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在一定的层面上说虽有内外、主客之分,但从整体上说,则是内外、主客合一的”[4]。因此,可以说中国山水诗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生态美学就是在后现代文化语境里诞生的。现代性的极度扩张导致人的生存状态不可遏止的恶化,衍生出一系列的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甚至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后现代则着重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以改善人的生存状态。较之以往的艺术美学,生态美学是从人的生存境况出发的。关于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尽管还有分歧,但归结起来不外两种。一种认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智慧中的道家哲学。如刘恒健认为:“生态美学是以大道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生态美学的本源性即它的大道性”,或者说是向着本源性的大道回归的美学,所谓大道是指“终极真实的存在,或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5]王玉兰认为,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天道观,以遵循万物运行本性为终极境域。[6]另一种将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归为国外的某些思想,如人类学、存在主义或现象学,代表人物有仪平策、聂振斌、陈望衡等。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生态存在论”来源于海德格尔对“此在与世界”的“在世”关系的分析。海德格尔认为,“在世”关系之所以能够提供人与自然统一的前提,就是因为“此在”即人的此时此刻与周围事物构成的关系性的生存状态,此在就在这种关系性的状态中生存与展开。这里只有“关系”与“因缘”,而没有“分裂”与“对立”。诚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存在的“实际性这个概念本身就含有这样的意思:某个‘在世界之内的’存在者在世界之中,或说这个存在者在世;就是说:它能够领会到自己在它的‘天命’中已经同那些在它自己的世界之内同它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缚在一起了”[7](P64)。在此基础上,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是一种“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哲学基础,包含主体间性的存在论美学,追寻人的‘诗意的栖居’,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突破技术的生存方式达到审美的生存方式”;生态美学所包含的生态整体主义是“生态文明时代的新人文精神”。[8]
就两者的哲学基础比较来看,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的第一种说法与山水诗有着天然的共同性。就第二种说法来看,尽管两者的哲学基础不一致,但在关系人的生存境况上,两者是一致的,而且都主张人与自然相融共处。基于此,山水诗要在当下语境发挥作用,生态美学是可以借助的思想资源。这是它们承接的基础。
二、整体特色
由于人与自然万物共存于宇宙之中,为了体现这种整体感,山水诗人尽力捕捉耳目所及的山水全貌,谢灵运的山水诗就给人一种“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木”的印象。但山水诗以短诗见长,缺乏长诗,篇幅小,有字数和句数的限制,不能大规模描写山水情态,所谓“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文心雕龙·物色》),因此就需要一种能够“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的表现方式。中国山水诗中的这种全貌呈现主要是靠空间叙述结构。王国璎认为:“诗人经常利用对比的技巧来表达他对山水全貌所怀的空间意识。”[9](P271-280)这样把不同视点(如高、低、远、近)和不同瞬间(如朝夕)的自然景象并置、共存于空间,构成了中国山水诗的整体特征。在空间结构里,与诗人相关的所有景物排列组合成一幅气韵生动、流化不息的艺术画面,读者也可以从多重角度同时看到山水的全貌。这样,山水诗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建构,以人与山水相融为基点,启迪人的生存智慧,使诗人和读者居于宇宙的大化流行之中。
生态美学是从人的整体生存环境出发而发展、建立起来的,从诞生伊始就背负着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使命,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立足于人的需要与满足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是人类的利益。这是造成当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而生态美学首先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促进人与社会、人自身的和谐。“对于生态美学,目前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生态美学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关系,提出特殊的生态美范畴。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存在论美学观。我个人赞成广义的生态美学,认为它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最后落脚到改善人类当下的非美的存在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的存在状态。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10]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生态美学不同于生命美学,生态审美也不同于自然审美。这一美学以人对生命活动的审视为逻辑起点,以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考察为轴线而展开”[11]。生态美学是对主导西方的时间叙述结构的反拨,它主张人与周围环境的整体性和融合性。
“生态美学作为环境美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却是从实际发生的环境空间感出发的,它必然涉及‘身体诸觉’在‘空间感’上的生成,以及在‘时间性’维度的存在——在静态上是‘身体诸觉’的‘同时性’并存与延续,在动态上则是空间环境美感的存在受‘意义’与‘价值’的激发与引领。”[12]从中可以发现,生态美学将人置身于与周围环境的立体空间里,人与万物同时性存在。
就其总体特征而言,两者都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整体性和空间感,注重人在此在世界里的生存境况,开启人在此世里的生存智慧和生命体验。相比于时间结构而言,空间结构更注重人与世界的整体性,使万物具有生命力和立体感。
三、美感经验
山水诗通过空间画面的整体构建,“它们表现的,不是美感经验的片面,而是美感经验的全部;揭露的不是从固定位置,依据单向透视法来经营安排的山水构图,而是和中国传统山水画家那样,以多重或回旋的视点,来把握大自然的全境”[9](P281)。在山水诗里,不是人对自然的征服占有,而是人与自然万物相融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原来,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中国历代山水诗人普遍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即人与自然山水形神相感相通,人以此参契天地万物之道,从而达到任情自适的精神境界”[13](P5)。所以,情景交融的山水诗创作和批评实践,促进产生了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意境。
生态美学是背负着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使命而诞生的,在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进而反思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形成了生态美。“生态美就是整体美、系统美、结构美、和谐美、生命与环境的统一美。”[14]就生态美的特征而言,它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统一性,同时都是为张扬整个生态的生命力,呈现人生境界。徐恒醇指出:“所谓生态美,并非自然美,因为自然美只是自然界自身具有的审美价值,而生态美却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和谐的产物,它是以人的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作为审美关照的对象”,“生态美是人的生命过程的呈示和人生境界的呈现”。[15](P119)生态美学是为了塑造一个诗意的空间,让人栖居于世界之中,正如聂振斌所说:“生态环境生机盎然,栖居其中的人,就会感到有旺盛的生命活力,产生无限美好的希望。”[16]
原来,“意境”与“生态美”虽是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个概念,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内核,即人生境界的呈现。
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古代山水诗与生态美学尽管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代,却有着许多可以承接的地方,尤其在现代语境里,它们具有合作的基础。其实,对比二者的长处和不足,恰好说明二者具有合作的可能性。生态美学具有批判性、当下性和全球性特征,其理论缺陷是缺少艺术的智慧,对艺术审美问题避而不谈。山水诗对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具有高超的智慧,在艺术上也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但对生态危机的改善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人的欲望被极大释放后几乎没有回头余地的情况下,山水诗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几乎难以确定。可以说,二者在当下语境里,有潜在的合作可能性,同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尤其是要激活山水诗的文化资源潜力,与生态美学合作不啻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同时,也可以看出,文化的核心是人生。中国古代山水诗与生态美学都是紧紧抓住此核心的,都为人生的诗意栖居提供着各种思考路径。山水诗曾经是中国士人的栖居地,如何在当下的语境里仍然发挥相关作用,为中国先进性文化建设提供资源、参考和借鉴,这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黄柏青,李作霖.气与中国传统美学审美方式[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刘恒健.论生态美学的本源性——生态美学:一种新视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6]王玉兰.生态美学和审美心理图式[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S1).
[7](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8]曾繁仁.生态美学: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观念[J].精神生态通讯,2005(4).
[9]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11]徐恒醇.生态美放谈——生态美学论纲[J].理论与现代化,2000(10).
[12]刘彦顺.论“生态美学”的“身体”、“空间感”与“时间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13]陶文鹏,韦凤娟.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4]张之沧.论生态美的觉识和创造[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15]徐恒醇.生态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6]聂振斌.关于生态美学的思考[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4(1).
I207.22
A
1673-1395(2011)10-0001-03
2011-08-10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1jyte018)
杨家海(1978—),男,湖北潜江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美学、文学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