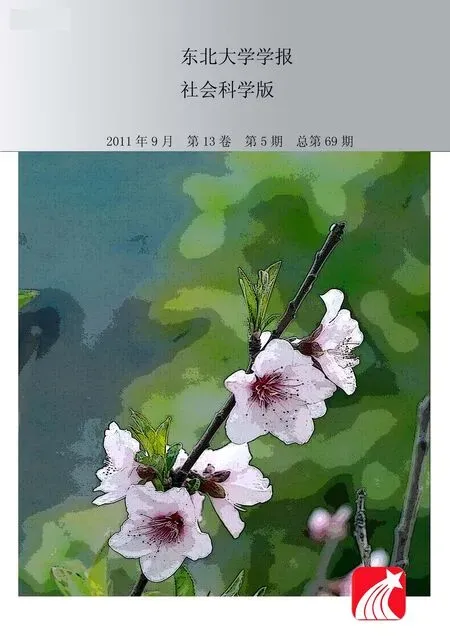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
----以身-心关系论
支运波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433)
生态观便是对现代性、理性和笛卡儿开创的二元论思想的一次清算和反驳。针对现代性、工业与科技所导致的人类与其环境之间情感的丧失、物质诗性的丧失的现实,生态观要求人类要像自己的身体器官一样对待自然与环境,重视它作为产生经验或体验的母体性,善待知觉安放之地,彰显内在身体的生活体验和感知,而审美则是生态学介入环境的一种有效策略。
一、 自然美与生态美
生态学介入美学,必然会涉及到自然美学问题。就美学史而言,艺术一直是作为一种元话语存在的。如“美学之父”鲍姆嘉通命名美学为“研究认识和感性表现新方式的科学”,其客体明确指艺术和美,许多德国美学家也都是在“艺术的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美学的。由于美学在词源学和元对象的学科历史,使自然美问题始终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而长期缺席或被“悬置”,普瑞格恩就曾指出:“在我们文化的历史里,自然一直被理解为一个外在物”[1]。作为一个难题,自然美一直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富有效度的阐释。原因在于对艺术知识和艺术欣赏向来重视有加,而对于欣赏自然美所需要的大气、地理、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却严重缺乏,加之自然的神秘性、易变性等特性又加剧了自然审美系统的难度。当然也并非完全基于此,文字使意识从世界抽离而与自身相联系,自然沉默与人类独白[2],即是说意识和精神已经从世界甚至从身体退回到脑壳之下[2],这背离了柏拉图将物而非词视为哲学起点的初衷。意识脱离了生活在环境中的肉体,演变为纯粹逻辑和概念性的理论推演显然是造成自然美难题的原因。
尽管如此,但却不能漠视自然对人类的吸引以及人们对它的思考。杜夫海纳说:“在这世界里,人在美的指导下体验到他与自然的共同实体性,又仿佛体验到一种限定和谐的效果,这种和谐……就是上帝……就是自然。”[3]伽德洛维奇主张自然界的所有东西具有全面的肯定的审美价值,卡尔松认为自然界在本质上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哈格若夫更是极端地声称自然是美的而且不具备任何负面的审美价值[4]。事实上,自然美问题在美学上就表现为美学生态观,如苏兹·噶布利克所说:“全部艺术的潜台词于是就应该是恢复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就应该是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万物都联结在一起这样一个观念。”[5]阿多诺甚至把人在自然中的审美与人的存在联系起来。
环境美学可视为自然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过渡形态。依海德格尔的观点,对存在者存在的思考是哲学的最崇高、最严谨的使命。那么,在环境中审美地生活便具有了最高的哲学意义。因为,“世界是自然环境,我的一切想象和我的一切鲜明知觉的场”[6]。可现实却与之背离,人类越来越生活在远离世界的地方,如齐泽克所言,在某种程度上,生态危机先于、抵抗和干扰着象征界的表征,甚至当它每天都在压迫着我们、改变着我们存在的实际基础时,它仍然奇怪地逃避着我们的思维[7]。环境美学以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虑和思考不断启发美学研究者进行学理探讨。
生态美学是美学在当今的现实形态。自然美学以自然现象(多是崇高的)作为主要审美对象,沿袭艺术美学的审美范畴,对自然奇观持不可知论。环境美学突破了自然美学的单纯、狭小视角,将自然和社会都纳入环境范畴进行审美探索,强调了人的实践性和对象的系统观。生态美学观则更加开放,以自然系统作为审美对象,着重于对象的关联、生成、变化以及未来性上的考量,强调对象之间的主体间性,就审美主体而言,更加关注的是参与、体验和感受性、整体性。特别是在景观审美、自然灾难、地球意识、心身一体、场所体验、民主社会等方面区别于传统美学。整体观、系统论、生成性以及场所中的身心体验是生态美学的核心思想。
关于生态美学,学界一般认为源于利奥波德1949年出版的《沙郡年记》一书。弗莱德和克里考特将其概括为自然的审美魅力与环境的“进化中的遗传因素和生态进程的完整性有关”[8]。高博斯特认为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围是生态系统的审美属性、人们的生态审美体验、环境的多重价值、景观认知中的生态美学理论、生态审美教育以及森林景观的体验特质等诸多方面[9]。生态美学以整体主义、系统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二元论以及区别于如画性静态美学、艺术的形式主义美学、伦理关怀缺失等传统美学的面目而出现。以卡尔松的观点来说,当代环境(生态)美学以非中心、聚焦环境、严肃认真、客观性、关涉道德等为鲜明特征。对此,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都被视为生态美学的理论资源。
二、 杜威的审美生态观
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经验艺术哲学思想被生态美学所借鉴,作为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同时,诸多学者也从杜威与欧陆哲学,特别是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似性上对杜威的审美生态思想作过诸多考察。以研究杜威美学而著称的美学家亚历山大对杜威的生态美学思想有较深入的探讨[10]129,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一书中。生态学家拉伍洛克的“盖亚假说”也是杜威的情境论与连续性原则的例证。里德等也论证了杜威的审美哲学是有关公民环境主义的审美生态学[11]。这种经验主义的审美思想是强调身体在环境中感知的日常生活美学。
1. 连续性思想
杜威的经验主义美学首先强调的是身体在场所体验的连续性。在《自然与经验》中,杜威陈述了二元论的流弊,同时批判了“区分”观。他始终坚持在广泛的人类日常生活中看待艺术问题,如果不充分考量自然、环境和人类诸方面而去谈论艺术和自然则是无效的。艺术的外在性、分离性和僵化的物质性是导致艺术缺乏美学的原因所在。杜威主张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经验的连续性与整体性,让身体回归场所(环境)去发现经验中所拥有的审美性质。杜威以经验的环境意识、体验的连续性原则、身体的场所感以及环境公正思想等构筑了自己的生态美学观。
为了突出经验的审美意义,杜威强调“经验与自然本是和谐地存于一体的,经验乃是‘达到自然’、‘揭露自然秘密’的一种方法,而且是惟一的方法”[12]。他认为,经验既可指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也可指互动的内容,它是身体在环境中的一种生活。这便使生活成为审美经验、连续性原则和处所意识的统摄。杜威认为活动和感受都与意义分离,因此,工作、生产性活动、有意义的行为均由单纯的外在结果驱动,然而,幸福的、充满意义的感受性却来自身体的激情与兴奋。审美感受通过身体与环境的相互激发才得以生成。“诸多可能性”为审美的诞生提供了前提,经验是介入的方式,不管是智力的还是实际的经验,严格地说都是审美的。经验、处境与场所是系统交织的。它是一个自然的有机过程,“实际的审美经验……是知觉”[13]。知觉标志了审美的真正诞生,因为知觉性是审美经验最为根本的东西,并且“审美经验是一种处于完整状态的经验”[14]304,舒斯特曼也主张“精神生活依靠身体经验且与身体进程并不完全分离”,其过程性是种生活处境。
2. 经验的审美性
杜威在任何生物中都看到审美的无所不在,任何生物都是生活在其感知程度之上的。在生活的时刻,人与世界连接在一起[10]226。特别是以下情况具有审美的性质:存在着完成一个经验的兴趣;完整地得到实现的任何实际行动;带着欲求、盼望结果;对行动中事情带着兴趣并最终完满的整体。而审美不存在于松散的连续性中,也不存在于那些相互之间只具有机械性联系的活动中。人居于自然世界中,与环境生成参与关系,参与的直接与完满在杜威看来就“构成一个经验的审美性质” 。审美经验则是一种出于完整状态的经验[14]304,经验标志着世界的栖居,一个经验就是栖居在世界中的过程。“凭借与世界交流而形成的习惯,我们住进(in-habit)世界。”[10]270在世界中,“每一个获得感受性的活的生物,每当它发现周围存在着一个适合的秩序时,都带着一种和谐的感情对这种秩序作出反应。只有当一个有机体在与它的环境分享有秩序的关系之时,才能保持一种对生命至关重要的稳定性。并且,只有这种分享出现在一段分裂与冲突之后,它才在自身之中具有类似于审美的巅峰经验的萌芽”[14]14。对象的世界发源于作为活动的世界,这预示了身体回归场所的身-心合一的美学思想。
在被经验之前,世界就在那里,身在其中的“世界成了家园,而家园又是我们每一次体验的一部分。一个经验就是栖居在世界中的过程。我们的习惯创造性地进入对象之中发挥作用,而且这个对象变化成了我们的感知,完全可以说,在这一整合时刻,人在世界中,而且有意识地实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同时,世界的意义也靠经验得以反映”[10]270。人容身于世界,经验是人类的艺术萌芽,也是审美经验的知觉允诺。通过“参与和交流”来实现肉身与自然的“一个经验”的联系可以激活肉身与世界之间的感知地带。恢复自然与经验的连续性就消除了心身分离的问题,理解杜威以审美经验、连续性原则和处境意识所构筑的审美生态学必须将其置于身-心的处所意识上去认识。
对杜威而言,连续性也指秩序更新、更广泛的类型。杜威在《人类本性与行为》一书中,十分重视冲动和习惯在将世界建构成一致的、先验主义的模式时所扮演的角色,习惯提供了稳定的回应的全部内容,旧习惯参与其中,并起着建构、解释新语境的作用,扩展、生长着经验,而冲动为直接的重建提供刺激。情感则是习惯破碎、重组而升起的,它具有意向性,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理想的形式出现的事物。就是说,现象自身是具有知觉、感性的肉身存在者。杜威认为美学家的任务就是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精致、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情、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因此,“人所创造的艺术和人的审美经验是人的幸福的基本成分,人的幸福只能从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寻找”[15]。
三、 梅洛-庞蒂的生态美学观
生态美学强调生态整体主义和系统论,主张审美的感知、体验、参与和动态性,倡导身-心合一的有机体在环境中遭遇的和谐、有序的审美以及生态自身非平衡性的审美因素,生态美学是生活美学而非概念美学。与艺术美学和哲学美学相区别,它考虑的“是一个身处某一个环境中的感知者的动态系统。这种直接感知理论不会割裂任何一个侧面”[16]114。现象学引导的新美学与这一思路不谋而合。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看来,生活世界是充满感性知觉、感受性和感性-身体需要的此在世界,对生活世界及其经验的回归,即是人的生态学。美学作为人类认识整体性的一种媒介,可以使人参与生物圈一致性的感知、认识与沟通。
参与性的生活世界中,以审美为基础的感知与交流具有迷人的潜质,对此,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有清楚的说明,一个人在认知一条路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感知的过程中已经走上了这条路。“与刻板的科学探讨相反,艺术与美学的魅力可以用社会人类学的术语‘着位’(emic)和‘非位’(etic)来解释。……一个人对世界的多维度的和使用多种感官的感知能力,就是美学”[17]140。即是说:“有意识的身体并没有沉思性地观察这个世界,而是积极地参与到经验过程当中。”[18]当然,感知研究不应只局限于研究感觉器官,而应把它视为整个身体都参与的活动[16]116。生态美学更强调身体的感知,因为感觉系统既是身体内部的,又是镶嵌在身体上的。其实,“身体与环境的关系,会受到多种感知、联觉的影响,反映在精神和感官中,导致出现了一种审美倾向。由此而言,感知即意味着世上万物间的不断的给予与获取,正是这种不断的、亲密的、直接的和复杂的万物关系才使得地球上的所有物理过程成为可能。这也正是生态网络所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感知、美学和生态可以被看做是密切相关的”[17]138。身体在处所中的感觉-知觉性,在现象学美学那里,连同身体一同被强调。
何为人类环境,以及环境如何与美相关?因为,自然环境是一个感知系统,对于人类来说,它是一系列体验的体验链,只有主体感知和体验到的世界,对主体来说才是审美的世界,所以,回到生活本身也就是回到审美本身,审美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日常事件。环境的审美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体验,将这种体验提炼表达出来,就升到了美学[19]。梅洛-庞蒂指出,现象学的全部努力就在于重新找出某种与世界的朴素接触,他关注身体在世界的安置和人类所经验的生活。生活中的行为可谓是身-心合奏的美:音乐构建了人们靠听觉参与的知觉感受;舞蹈会带来观众潜在的机体神经反射;文学用想象与虚构描绘的世界则需要被理解与感动;戏剧场景和剧情牵涉到观众的想象性身体介入;影视与雕塑则需要视觉的参与;社会美更是人实践的结果;环境则是身心合一在“审美场”的“审美介入”即心身合一的感知活动。
我们知道,西方自黑格尔以降尤其是自尼采始,西方哲学出现了身体转向,身体成了人的在世存在处境意识的表征,人类与自然共存。因此,探讨生态的美学问题,必须探讨身体问题。身-心关系是求索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路径。审美不仅是认知行为,更是身体行为和感性行为[20]。齐泽克也指出:“精神永远依附于身体”[21],“思想是身体自身的思想”[22]。身体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就是探讨人身体行为与知觉的论著,实质上亦是人与环境的生态美学论著,这里的环境是周围环境,是现象场。通过身体与处所(place)的相互渗透,人类成为了环境的一部分,环境经验使用了整个的人类感觉系统。因而,我们“不仅仅是‘看到’我们活生生的世界:我们步入其中,与之共同活动,对之产生反应。我们把握处所并不是仅仅通过色彩、质地和形状,而且还要通过呼吸、通过味道、通过我们的皮肤,通过我们的肌肉活动和骨骼位置,通过风声、水声和交通声。环境的主要的维度----空间、质量、体积和深度并不是首先与眼睛相遇,而是先同我们运动和行为的身体相遇”[18]。全部感觉、知觉系统随身体一道进入生态的整体性活动,其中一切感知都是身体发出的,并居停在身体内。我们必须“意识到,在环境鉴赏当中肉身感性(somatic sensibility)的重要性:对体积张力的身体意识,空虚空间的牵引力,在身体运动中的运动知觉的贡献,连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的性质一道,都充满在所有的经验当中”[18]。并且,身体各部分之间存在着目的性关联,“通过目的性的这样交织,新类型的各种关系在身体中建立起来”[23]154。身体是物质与直觉的中介。
梅洛-庞蒂强调身体是为了突出主体概念的情境或处境意义,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再是认识关系,而是一种存在关系。主体只有作为身体,只有借助这一身体进入世界之中,才能够实现其自我性。身体的突出是对纯粹意识的克服,与此同时却拉近了人与世界的关系[23]200。身体的现实处境向往一种美学图景,重建身体在场的和谐系统。作为“场所的知觉”,“我们的身体(作为某个容器、容量的身体空间)与外部空间相互蕴含对方,并共同形成一个‘实践的体系’”[24]。身体带着意识和体验的实践性进入知觉场,审美内在于主体且是不断生成的。以此,生态美学与哲学美学见出了区别:身心之在而非无身之思。
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定义为身体另一面的精神是“侵入到身体之上,被掩饰在身体中----与此同时,它需要身体、终止于身体,扎根于身体中,存在着精神的身体、身体的精神,存在着它们两者的交织”[23]313。身体与世界的关系是由相同的肉构成的,况且我的身体的这种肉被世界所参与,世界反照它,侵越它,而它也侵越世界,身体与世界处于越界或者跨越的关系之中。“世界成了身体的作用场,甚至是身体的延伸:这一并非自我的世界,我与它也如同与我自己一样密切联结,在某种意义上,它不过是我的身体的延伸。……‘我的身体一直延伸至星辰’。这明显扩张了现象物或行为环境的概念,更加突出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23]227和身体在环境中的感受性、意义性。这种意义是生存意义、审美关系、伦理意义、经验感知意义以及真理意义。即他所言,“我们用身体知觉世界”。这也使生态美学与艺术美学见出了区别:身体在世界之中而不是意识匍匐在艺术作品的敬仰之中。
四、 结 语
杜威的审美生态观和梅洛-庞蒂的生态现象学美学以对身心共同进入处所、世界的强调和相关论述重塑了人类在世界中的互涉、交织、生成性,并解决了人在处所中的亲近感、存在感、意义感和交往中的民主诉求。它不仅解答了人们对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质疑,也澄清了生态美学的一些关键性认识,诸如认为它是生态系统美学、生态无区分美学、生态学加美学、生态平衡审美和人类中心主义美学等时兴之见,也厘定了生态美学的学术路径,变革了传统美学的一贯认识,对于当代生态美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身心的关系论也开拓了生态美学的探讨范围,比如生态美学应该恰当地处理人对自然的关系、经验中的敏感性的意义,以及城市性的消费生活等问题,恢复身-心在场所内的原初经验,以及对美学重要性的重新评估等。生态美学兴起与人们对环境恶化所产生的思索有关,与审美泛化也不无关系。它也是一种日常生活美学,关系到大众在场所(环境)中的生活状况;它是身体回归场所的身体美学,关系到身-心关系和感知、体验系统;它是一种时代的生活美学,它关系到人活在世的存在哲学;同样,它也是一种实践美学,它关系到人的现实的实践方式。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世界中的存在”、梅洛-庞蒂的“原初的意向性”、列维纳斯的“深不可测的存在”都是心灵与世界相互交织的统一。如果“采用生态智慧学,责任性就会走出自我,进入他者”[25]。美学作为人类的感受、情感和知觉,它是由“连接精神和世界基础的自然界所唤起的”,而且“先于认识论和本体论”[26],它或许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敌对关系的”有效办法。
参考文献:
[1] 雅克·里纳尔,赫尔曼·普瑞格恩. 生态美学或审美生态[M]∥李庆本. 国外生态美学读本.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154.
[2] 梅勒U. 生态现象学[J]. 柯小刚,译. 世界哲学, 2004(4):82-91.
[3] 米盖尔·杜夫海纳. 美学与哲学[M]. 孙非,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51.
[4] 彭锋. 环境美学的兴起与自然美的难题[J]. 哲学动态, 2005(6):26-30.
[5] 彼得·哈里斯-琼斯. 理解生态美学:贝特森的挑战[M]∥李庆本. 国外生态美学读本.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216.
[6]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5.
[7] 热拉尔·热奈特,琳达·哈琴,拉尔夫·科恩,等. 文学理论精粹读本[M]. 刘玲,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190.
[8] 保罗·H.高博斯特. 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中的森林美学、生物多样性、感知适应性[M]∥李庆本. 国外生态美学读本.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32.
[9] 保罗·H.高博斯特. 服务于森林景观管理的生态审美[M]∥李庆本. 国外生态美学读本.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48-61.
[10] 亚历山大·托马斯. 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M]. 谷红岩,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 赫伯特·里德,贝茜·泰勒. 约翰·杜威关于公众智慧以及公民环境主义基础的审美生态学[M]∥李庆本. 国外生态美学读本.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120.
[12] 刘悦笛. 杜威的“哥白尼革命”与中国美学鼎新[J]. 文艺争鸣, 2010(5):20-25.
[13] 阿诺德·贝林特. 介入杜威----杜威美学的遗产[J]. 文艺争鸣, 2010(5):32-37.
[14] 约翰·杜威. 艺术即经验[M]. 高建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15] 赵秀福. 杜威实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 2006:87.
[16] 安德雷·路易兹·冈萨尔伏兹·奥利维拉,路易兹·菲利普·奥利维拉. 走向生态美学:新的有发展潜能的音乐[M]∥李庆本. 国外生态美学读本.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
[17] 翟拉·艾兹恩. 生态美学与赫尔曼·普瑞格恩的艺术[M]∥李庆本. 国外生态美学读本.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
[18] 柏林特A. 环境美学的发展及其新近问题[J]. 刘悦笛,译. 世界哲学, 2008(3):22-36.
[19] 陈望衡. 环境美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6.
[20] 温迪·林恩·李. 论生态与审美经验:价值与实践的女性主义理论[M]∥李庆本. 国外生态美学读本.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10:266.
[21] 格林·戴里,斯拉沃热·齐泽克. 与齐泽克对话[M]. 孙晓坤,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2.
[22] 让-吕克·南希. 解构的共通体[M]. 郭建玲,郭建华,张尧均,等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371.
[23] 杨大春. 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24] 鹫田清一. 梅洛-庞蒂认识论的割断[M]. 刘绩生,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80.
[25] 伽塔里F. 重建社会实践[J]. 关宝艳,译. 世界哲学, 2006(4):29-35.
[26] 苗建时. 生态学、美学与道教修炼[J]. 孙建,译. 学术研究, 2010(4):2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