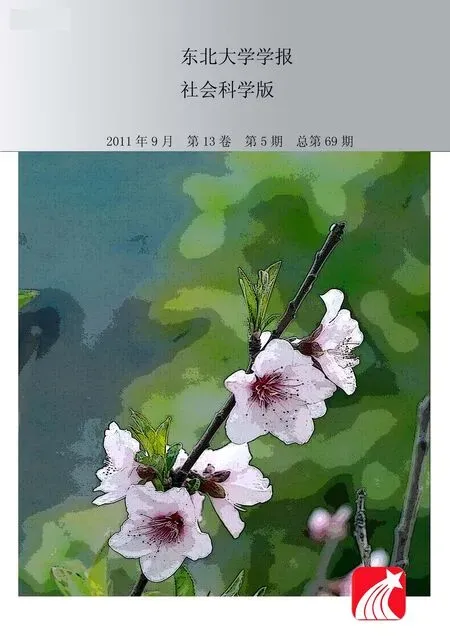张学良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
王海晨,张晓丹
(1.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2.张氏帅府博物馆,辽宁沈阳 110011)
张学良研究一直可谓为“显学”,研究成果比比皆是,众多成果尽管在对其评价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海峡两岸,甚至截然对立,不过,总体趋势是不断趋同、深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也包括其他海外学者,在研究张学良时,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现象:几乎都将笔触集中于大的政治活动,并多以政治价值尺度去评论他的功过是非。这种探索的意义与贡献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从“人之所以为人”的逻辑来考察,人物研究本来应该具有的人性取向,却在这一进程中被模糊了。因此,笔者提出要想将张学良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人性取向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政治取向检讨及人性取向价值分析
学界目前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无论从何种角度,采用什么标准,持什么主张,都有其自身的道理,这些研究汇聚在一起,无疑丰富了人物研究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就总的来看,对民国人物的研究,多数学者从政治性出发,以民族、国家、阶级、党派利益为出发点,以大的历史事件为主线,来寻求政治人物与历史事件和个人政治追求与国家、民族、阶级、党派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并进而评价其是非功过。如果可以将同时代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倾向称为主流取向的话,那么这种对“政治”和宏观的偏重,无疑就是民国政治人物研究的“主流取向”。
我们必须看到,历史人物研究中的这种“主流取向”对历史的真实性与丰富性及其评价的公正性,也包括对史学研究走向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反映了中国史学的褒贬传统、爱憎分明的理念,民族、国家、集体高于个人的社会“主旋律”,而且,也符合“以德治国”、历史为现实服务的追求。因为自近代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要从落后、软弱、分裂走向进步、强大和统一。在这一进程中,如何组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如何凝聚人心,如何统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如何抵御外来势力的干涉与破坏,如何唤起人们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自强心、自信心,都迫切需要从历史人物身上寻找力量,从历史宝库中寻找资源。人物研究的这种偏重政治与宏观的主流取向,恰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鉴往知来的学术支撑。
笔者无意否定从现实需要出发研究历史的路径,也从不否认从政治、宏观的角度研究历史人物的学术价值。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如果学者都一窝蜂式地采用相近的方法,从单一的角度研究复杂的历史人物,就可能使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单化”或“脸谱化”,使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历史人物的政治脊梁和宏观的轮廓,从而淡化或忽视了人物的其他方面;其二,尽管马克思说过“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1],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只有政治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人物的研究只能选择政治取向。值得欣慰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大胆地突破了主流取向,将笔触延伸到了政治以外的领域。如有的学者开始将笔触深入到张学良的性格、亲情、乡情、爱情等领域,注意到了政治人物的私人生活、情感世界。不过,这样的研究几乎被探讨“政治取向”的宏观大潮挤到了史学的边缘。众所周知,无论历史人物的政治生涯有多么重要,它也不是政治人物的全部。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经济、军事人物,他首先是人,政治性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
强调对历史人物研究的人性观照,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值得提及:
第一,关注历史人物人性的一面,有助于对复杂人物的整体认识。历史本身蕴意无穷,人物更是丰富多彩,但文献记载的相对于历史本身来说都是碎片,这就决定了史家必须站在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甚或同一角度或同一侧面的不同层面入手,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的整体还原。基于这样的理解,从人性视角出发研究人物,至少是增加了一个研究选项,自然有助于丰富对历史人物复杂性和整体性的认识。尤其是对张学良这样复杂人物的研究,首先须要调整研究主体的姿态,扩大研究视野,变换研究角度。
第二,有助于摆脱历史人物研究“脸谱化”、“简单化”倾向。人物研究的“简单化”首先来自于研究视角的单一和研究方法的简化。如只从政治的视角出发研究张学良,看到的只是政治层面的他,也只会专注于对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几个大的政治事件的研究,而这几个大的政治事件只发生在他全部人生的不足十分之一的时间里,其他十分之九的人生如果被忽略,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之所以十分之九的人生不能进入史家的视野,是因为研究视角把它们排除在外了。
第三,有助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研究主体之间的学术交流。学术交流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学术上的分歧、碰撞、争吵固然也是一种交流,但如果长期处于截然对峙的状态,长期找不到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交流。如对张学良的评价,海峡两岸分歧较大,持不同见解的学者碰到一起先是吵,继之是避而不谈。这避而不谈主要是因为价值观基础相异导致结论上的截然对立,在谁都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就停止了学术争鸣。这显然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如果双方都从人性的视角出发,恐怕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当然强调人性视角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弥合不同价值观主体之间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为了深化研究,很难想象,舍弃人性视角如何能复原一个立体的张学良。
第四,对历史人物的人性观照是史家的思维基础。英国学者沃尔什认为:“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们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终于决定了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2]62
二、 人性取向研究的一般把握
历史学不仅与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人类学、人种学等学科一样从不拒绝人性,而且它恰恰是通过对人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及精神生活的梳理,进而对人的本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探索。对人性的探索是历史学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之一,同时也是历史学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之一。
关于人性问题,生活在不同价值观体系中的人可以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但又无法终止对它的讨论,只要我们承认人离不开人性,承认个体之间的人性是有差别的,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我们对它的研究就不可能结束。但长期以来,“对人性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若明若暗,非此即彼的状态。它被分析得支离破碎,甚至越研究,距离真实的人性越远。它像一面多棱镜,同样一束光线射进去,却反射出走向完全不同的多束光线,使人感到迷惑甚至眩晕”[3]。人们为了避免此类分歧和迷惑的发生,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在人物研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对张学良的研究,人们习惯从政治的角度解读他的整个人生,当用政治的标准无法解读他短暂与辉煌的政治生涯和漫长与“离谱”的情感世界时,无法解读他为了全民族抗日可以对“领袖”实行兵谏却面对部属汤玉麟临阵脱逃下不了狠心时,无法解读他既是一位民族英雄又曾是一位花花公子时,则采取只述其一不述其二,或只述前者不述后者的简单办法加以回避。产生这种现象最深刻的原因无疑与研究方法相关,忽略了涉及人的“心灵及其心灵的本性以及它们之同公民生活和雄辩术的关系的那部分学说”。“全都没有对民族的人性的某些起源作过思考,而无疑,一切科学、学科和艺术都来自这些起源。”[4]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维柯的这段提醒人们重视人性的论述尽管不是针对张学良研究现状而讲的,但最起码对张学良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深化张学良的研究,人性视角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取向。但长期以来,“人性论”遭到了批判,人所固有的本性,包括私欲、激情、亲情、爱情等,都远离了史家的视野。随着思想的解放,史学研究中一度盛行的“英雄”无私情、“坏蛋”无公心、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式已经被打破了。从而,以人性为价值取向的研究不仅成为一种必要,也成为了可能。
人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不理解马克思对人性的论述,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以往学界对历史人物研究所造成的偏颇,许多都与误解或片面理解马克思的人性观有关。以张学良研究为例,就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人性具有“自我性”。任何历史人物首先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任何具体的人都有七情六欲,如果漠视人人所具有的这种本性,就有可能偏离历史的真实和人物的真实。张学良在晚年口述中谈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情感方面的经历,甚至赋诗:“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5]。有学者以此贬责张学良“格调低下”、“不像个英雄”;有学者虽未对此发表看法,但在研究中故意回避这方面内容。我们在这里无意评价张学良的人格高低,关键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都缘于研究者没有把张学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而是把他单纯地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符号,或者说是“类性人”----英雄。在马克思看来:“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6]78-79这种自我性是人的第一性----本性,本性虽然是人性的第一个层次,但要认识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7]。离开了人的一般本性,我们就无法理解具体的人性。就像张学良这样的人物,他为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他为民族所做出的贡献这点上看,他是英雄,但英雄首先是人,首先具有人的一般本性。不能因为他是英雄我们就忽视他本性的一面,也不能因为他是英雄,就拿英雄的标准衡量他整个人生的方方面面,也不能以他表现出来的一般人所具有的本性的一面来抵消他的崇高。抵消的方法是错误的,避而不谈的方法也是不对的,抵消和回避的方法虽然将研究简单化了,但却偏离了真实,历史一旦偏离了真实,也就没有学术意义可言了。
第二,人性具有历史性。任何历史人物都生活在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具体的人性也无不打着时代的烙印,所以,我们拿起人性标尺的同时不要忘了它是哪个时代的人。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标尺去衡量古人,历史人物就会变得不可理解。有人拿今天的道德标尺分析张学良的某些行为,就得出“自私”、“生活放荡不羁”、“无法无天”等结论。恩格斯指出:“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8]567。也就是说,人在历史中活动,历史在人的活动中被创造,历史是人的,人性是历史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历史条件必然导致人性的相应改变。“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6]172不仅如此,人性的概念“是以最显著的方式在随着每个时代而变化的。在一个时代(例如中世纪)看来是正常的东西,在另一个时代(例如18世纪)就显得十分不正常”[2]65。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张学良所处的民国时代有许多不同,即使史家努力地克服这些不同,也是不能完全成功地克服的,更不用说不做这种努力了。所以研究张学良必须考虑他所生活的时代,否则就会误读历史,误读人物。
第三,人性具有总体性。任何历史人物都在一定的群体之内展开自己的活动。这里所说的群体包括家庭、集团、党派等,人物的活动无不受他所生活群体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分析一个具体人物时必须对他所生活的群体进行系统考察。还必须注意,他所生活的群体依与他关系的密切程度呈放射状外延,对他的影响有大有小。一般来说,离他越近对他影响越大,反过来说,他所做的一切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关系圈的利益。有人分析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九一八不抵抗的原因时,说这都是张学良出于维护自己和东北集团的利益而作出的自私选择,从而否定他的进步、正义与无奈。这样的逻辑分析似乎也有道理,但所犯的错误仍然是把张学良当做一个超群体的“符号”,而忽略了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56这段话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论点:第一,人性具有总体性----类属性。第二,人性的实现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才可能获得实现。如果我们抛开张学良所生活的群体来探讨张学良的功过是非,既不客观,也缺乏人性关怀。
第四,人性具有主体性。任何历史人物既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无时不在朝着自己追求的方向奋力地争脱着各种束缚,以此改变着、创造着凸显自己个性的历史。如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步伐的情况下,蒋介石仍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并把东北军送上了剿共的战场,对张学良来说,这是当时最大的客观,但他不断地努力改变着这一客观。如向蒋介石诤谏、哭谏,最后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主体的地位,改变了国民党剿共不抗日的现实。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9]在西安事变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倾向,尤其是个别学者,过分强调共产党的客观影响,从而淡化了张学良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主体地位与作用,甚至说捉蒋是张学良受共产党的鼓动而发动的。
学者们对人性问题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马克思则通过对各种人性理论的批判与继承,从人的“自我性”、历史性、总体性和主体性的角度重新界定了人性,但由于马克思的界定散见于不同时期的论著之中,并没有集中系统地阐述,因而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人性观理解上的困难与分歧。如果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是在人的需求、社会关系和人的实践三者的相互作用中建构自己的人性理论体系的,三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一科学的揭示,不但有助于我们对各种人性观的认识,更有助于对人性的正确理解;不但消除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探讨人性问题的种种顾虑,更为我们如何从人性的视角研究历史人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三、人性取向研究的切入点:“心灵考古”
马克思认为人性是通过人的需求、社会关系和实践三者互相作用中体现出来的。就一个具体的人来讲,他常常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为了满足自己种种的需求而努力地奋斗着(即实践着),这种奋斗既受社会关系制约,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与社会的关系,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调整着自己的需求,为了满足调整后的需求也不断地在调整着自己的实践活动,而支配实践活动的力量是藏在心灵里的思想。人性既是人与人之所以具有相同性的谜底,也是人与人之所以不同的谜底。理解具体的人性必须从马克思所说的三者互相作用中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的考察,而从人物心灵入手探究人性是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因为人性虽然通过行为可以体现出来,但它的核心部分毕竟植根于心灵之内。“因此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的中心概念就是行为这一概念,亦即思想本身把自己表现为外部的行为这一概念。”历史学家可以从描述行为出发,“但是历史学家必须做的,就是要从外部事件深入到构成这一事件的思想里面去,并且重新思想那种思想” 。历史“既有内部也有外部,历史学家所确切涉及的,则是它的内部”[2]51。研究西安事变可以从“外部”开始,先搞清“外部”情形,如张学良是如何从拥蒋一步步走向逼蒋、捉蒋,再到放蒋、送蒋的。但历史学家不会以把这件事的“外部”来龙去脉搞清楚为满足,还要把“内部”的,即心理活动的轨迹搞清楚,他心里当时是怎么想的?心理变化过程如何?动机、目的是怎样的?情绪是怎么波动的?激情是怎么燃烧起来的?等等。
一般来说,“外部”的来龙去脉,不管怎么复杂,都可以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挖掘、整理、考证来理清;而要理清“内部”的来龙去脉就没那么容易了。人的行为是受心灵支配着的,而“内部”心灵里的来龙去脉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又常常被厚厚的表象所掩盖着,本来的无形又包裹着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扭曲,这就给探究带来了难度。因此,笔者借用考古界的名词提出对张学良进行“心灵考古”的概念。“心灵考古”是考古学家以发现的遗迹、文物作为“心灵化石”,并通过“化石”反推人们的心灵。对历史人物“内部”心灵的考察,与考古界“心灵考古”有共同之处,都是通过对“外部”的行为表现来考证、还原深藏着的心灵。对张学良的心灵考古与考古界的心灵考古不同的是,我们手里多了一份他自我解剖心灵的史料,即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的最后10年里留下的100多万字的口述,口述中记录了他大量的心理活动,这为我们走进他的心灵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
探讨人的心灵和探讨人的其他方面一样离不开史料,那我们在运用张学良口述历史及其他文献史料对其进行“心灵考古”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在运用张学良口述资料时要注意对其口述时的心理过程进行考察与考证。因为人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对一个人外部行为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进行心理分析时,就必须注意在张学良的口述、日记、书信和其他文献材料的比对中发掘反映其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素材,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心理分析。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心理过程是极其曲折的,他的口述史前后共进行了10个春秋,在这10个春秋里,他的心理变化是复杂的。如果不把他在什么背景下说的,不把他说话当时的前后语境搞清楚,不把他一直强调的“我说话从来前后不矛盾”等因素考虑进去,寻章摘句式地引用,复原出来的照样不是真实的张学良。他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写了不少回忆的文字,他在口述时,有多少话是照顾到了这些回忆文字,有多少是为了不前后矛盾而讲的,必须对其下一番“考古”的功夫。
其次,要从张学良所处的地位、他身上所肩负的政治责任中去探求其心理特征。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心理习惯和个人愿望也就有所不同,“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或观念,另一套习惯和道德准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10]。如分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理过程,就离不开他的社会地位、政治责任及社会关系,至少应该考虑:对九一八的反思是他内心的火种;对南京政府是一帮乌合之众的认识,对蒋介石“用奴才不用人才”的用人之道的洞穿,对蒋介石将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认识上的觉醒,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同意由蒋介石领导抗日的感召,东北军要打回老家去的压力,对东北阵亡将士得不到抚恤的悲情等是火种升温的条件;向蒋介石屡次劝谏屡次失败,屡谏屡败带来的郁闷,“一二·九”运动期间,蒋介石说用机关枪打学生带给他的惊讶,同一天蒋介石召集军事将领会议,没有让张、杨参加带给他的惊恐,是火种迸燃的引信。包括西安事变是怎么和平解决的,他为什么送蒋回宁,如果不是从他所处的地位、肩负的政治责任上去考察他的心理活动、心态变化、情绪波动、人格特性,就很难理解张学良。
第三,要根据张学良所处的文化背景、个人生活经历把握其人格特性。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6]72-73张学良的情感世界极其丰富,他的父子情、母子情、兄弟情、朋友情、夫妻情、女人情、故乡情、儿女情、军旅情和长官情,情情都夹杂着中西文化碰撞的痕迹,都与他个人的家庭、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敬佩他的父亲,说他父亲有雄才,和日本人周旋“什么手段都能来”,他没有他父亲的能耐,所以他才找个靠山----南京政府,想依靠中央来解决对日外交纠纷。他感谢赵一荻,却说“赵四是对我最好的,却不是我最爱的”[11]1155。他为蒋介石写的挽联也有人感到不解:“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11]994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或者按照现代的道德标准、按照民族英雄的标准去解读这些,根本无法理解张学良的心灵世界,只有从人性的角度,也只有从人性的角度才有可能走近张学良,直抵他的内心深层。
恩格斯曾把人的心灵誉为地球上最美的花朵,研究张学良,我们不可能不关注这朵最美的花朵,因为从心灵里绽放出来的花朵最能体现他的人性。研究它,至少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具有学术意义:首先,把握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人格特点,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支配他行为的无形动因;其次,通过心理考察和分析可以揭示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天性、本性的一面,进而避免“简单化”的叙述和“脸谱化”的评价;第三,可以淡化加在他身上的政治色彩和贴在他头上的“虚高”,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作为普通人的平凡和平凡基础上的崇高,使人们能够看到英雄在更多的时间里和普通人是相近的甚至是相同的,至少他在走向英雄的路途中也有常人的心理起伏和喜、怒、哀、乐、爱、恶、欲。
当然,本文所论述的人性取向,并不是张学良研究唯一的取向,它只是诸多取向中的一种,但它是以往关注不够的取向。尽管本文的论述是粗浅的,但笔者相信,随着思想的解放,社会的不断进步,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人性的角度关注张学良,解读张学良。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
[2] 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M]. 何兆武,张文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 李中华. 中国人学思想史[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6.
[4] 利昂·庞帕. 维柯著作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124.
[5] 张学良. 坦言好色诗(1992)[M]∥毕万闻. 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6部.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132.
[6] 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7]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69.
[8] 恩格斯.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9] 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4.
[10]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410.
[11] 王海晨,胡玉海. 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下[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