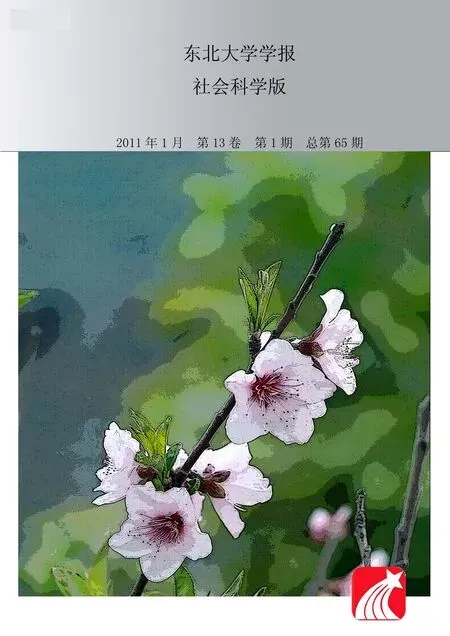论魔幻现实主义在《保留区蓝调》中的成功运用
邓建华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魔幻现实主义曾被用来描述20世纪20年代欧洲后表现主义的绘画并一直与拉丁美洲文学联系在一起。最近,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又被用来指代被边缘化的群体、族群或国家所使用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评论家意识到,加拿大、印度或尼日利亚文学作品中都存在魔幻现实主义。然而,到目前为止,魔幻现实主义作为美国少数民族族裔文学作品表现形式方面的评论十分鲜见[1]。作为美国的原住民的印第安民族和白人殖民者之间的冲突贯穿了几个世纪,历史上的矛盾至今还在对印第安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原住民的民族意识不断加强,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原住民作家。他们致力于宣扬印第安人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揭示长期以来被白人殖民者掩盖的历史。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成为很多作家表现主题的有效手段。
美国著名原住民作家薛曼·亚历斯1966年10月7日出生于华盛顿州东部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区的威皮尼特。母亲是斯波坎人,父亲是柯尔艾伦人。薛曼出生和成长的斯波坎保留区为他提供了无穷的写作资源。《保留区蓝调》(1995)是薛曼·亚历斯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获199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作品中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向读者展现了美国印第安保留区的真实面貌,同时也再现了印第安人悲壮的历史。在这部作品中,薛曼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对揭示作品的主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与特点
德国艺术评论家弗朗茨·罗最早使用魔幻现实主义一词,用来形容一群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德国的画家所使用的被称做“新的客观性”的绘画风格。“那个时候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解还不是现实与虚幻的结合,而是一种发掘隐藏在寻常事物和日常生活中秘密的方法。”[2]弗朗茨·罗认为魔幻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有关,但又有所区别,魔幻现实主义的世界侧重于实物和实际存在的东西,而不是超现实主义所探索的大脑的、心理的和潜意识的现实[3]。
弗朗茨·罗有关魔幻现实主义的理论对拉丁美洲和欧洲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927年,西班牙作家和哲学家奥尔特加把弗朗茨·罗的著作翻译并登载在他创办的《西方评论》上面,此后这个词很快就被拉丁美洲的作家在文学领域广泛应用。
从1940年到1950年,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达到最高峰,涌现了许多著名作家。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认为,“拉丁美洲是两种不同文化碰撞的地方:一个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一个是白人殖民者的文化。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反映了这种文化的二元性。一方面包括了原住民普遍相信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一方面又遵从现实主义作品的传统。除了这些文化因素,魔幻现实主义也反映了拉美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是对南美洲多数政府的独裁政策的一种文学反映,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呼声”[1]。
到了20世纪60年代,虽然拉美评论家仍然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只应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背景下进行讨论,但是魔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的表现形式已经被许多拉丁美洲以外的作家所接受,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有所变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以外的作家开始使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和特点的争论也随之越来越激烈。为方便讨论,本文将魔幻现实主义定义为“一种美学风格或文学叙事模式”[4]。在作品中,魔幻的元素与现实的气氛融合在一起以获得对现实的更深理解。它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包括两种矛盾但又统一的视角。一个是基于对现实的理性的看法,而另一个则接受超自然现象为生活中的一部分。②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超自然的事物不会受到怀疑,……它与叙事者和人物的观念融合在一起。③作者对于事件的真实性和作品中表达的世界观的可信性不作丝毫的评论[5]。简而言之,在作品中魔幻与现实非常自然地并存着,以至于“读者看到超自然现象时并不觉得它与我们传统的现实观念有何矛盾之处”[6]。
在薛曼·亚历斯创作的《保留区蓝调》中,作者非常明显地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借助这样的写法,生动地揭示了白人殖民者欺骗的本质和对印第安人残酷镇压的历史。本文将对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模式在《保留区蓝调》中的运用作细致的分析,重点探讨作者如何运用这个叙事模式体现作品的主题。
二、 一把魔幻吉他揭示了白人殖民者真实的面目
在《保留区蓝调》(以下简称《保》)中,“丛林狼泉水”,一支美国印第安人的摇滚乐队,开始和结束于一把神奇的吉他。吉他是黑人蓝调歌手罗伯特·约翰逊带到印第安斯波坎保留区的。约翰逊是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宣称将灵魂卖给了魔鬼,因而获得了超凡的蓝调音乐演奏技能,但只录了29首歌曲就被人谋杀了。在《保》中,似乎约翰逊并没有如历史记载那样死去,而是他编造了自己的死亡以便逃脱魔鬼的追随。被魔鬼追随了几十年之后,他梦见了一个在山上的女人,把她视为唯一能够救赎他的希望来到了斯波坎。斯波坎部落里说故事的人汤姆斯把他带到了神秘的被称做“大妈妈”的印第安老人那里。约翰逊如释重负地走了,却把这把神奇的吉他留给了汤姆斯。
吉他在小说的第一页就出现了。罗伯特·约翰逊背着它来到斯波坎。它是大部分情节发展的原因,因为它引诱各种类型的人去演奏它。吉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话、移动、心灵感应、变形、流浪、割伤人并回忆自己的过去。约翰逊“埋了吉他,把它扔到河里,把它从高楼上扔下去。但是它仍然能找到他,回到他身边”[7]173。像普通人一样,吉他也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蜷缩成一团,用鼻子擦乐队成员维克多的脖子[7]223。吉他的魔幻行为有时会让小说中的人物迷惑,但从未质疑过什么。汤姆斯与吉他还进行了一场煞有介事的对话[7]29。维克多对他演奏时吉他划伤他的手也一点没有害怕[7]202。观众们可以看到音乐从吉他上跳起来[7]21。这些人对吉他的反应可以使我们确信,当吉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走进了一个魔幻现实的世界,即反常的事物被当做了寻常事物来对待。
薛曼选取吉他是别具了一番良苦用心的。吉他不是印第安人的传统乐器,印第安人的传统乐器是鼓、拨浪鼓、长笛和口哨。吉他是西方的弦乐器,16世纪起源于西班牙,随着殖民者来到了新大陆。吉他的选取旨在用它来影射几百年来对印第安人进行欺骗和迫害的西方白人世界。小说中的人物用它来演奏摇滚乐、说唱音乐,而不是标准的印第安音乐。
在小说中,作者处处都在暗示这个吉他是西方的产物,与白人、西方的文化和殖民主义息息相关。首先,它的力量来自于一个神秘的白人,根据小说中的故事,一个绝望的美国黑人遇到了一位绅士,“潇洒的白人穿着熨烫整洁的黑西装”[7]41。从这位绅士的穿着来看,他的社会阶层和种族已经很清楚了。他提出可以让这个没有任何天分的歌手比任何人弹奏得都要好。而他须要交换的是罗伯特·约翰逊最热爱的东西:自由。约翰逊因此获得了神奇的驾驭吉他的技能,同时失去了驾驭自己的权利。约翰逊想到了父辈们遭到的鞭打和虐待,但是为了获得在舞台上被人喜爱的一瞬间,他出卖了自己的自由。最后,绅士用“指尖碰了一下”吉他,然后带着“约翰逊的灵魂”消失了。
其次,绅士的吉他参与并成为了白人统治者的武器。吉他不断地作出错误和虚假的承诺:暗示乐队能够出现在《滚石》杂志的封面上[7]265。吉他毁灭了演奏者:割伤了罗伯特·约翰逊和一个“印第安老人的手”,使得他们不能再演奏[7]6。吉他侮辱演奏者:在录音棚里突然它从乐队成员维克多的手里跳起来扭动,破坏了对他们的商业成功至关重要的演奏[7]225。
最后,吉他代表着白人殖民主义者编织的金色的陷阱。它使得人们迷失自我,失去方向。它的陷阱就是自我实现。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们很容易被其吸引和利诱。获得这种物质利益的欲望是很难战胜的。在乐队录音失败后,背信弃义的吉他出现在维克多的梦中,继续对他进行利诱,他们之间的对话同多年前约翰逊与白人绅士之间的对话如出一辙。 维克多显然受到了吉他的影响,在从纽约返回的途中竟然把别人的吉他误认为是回来找他的吉他,于是出现了维克多与一个白人争夺一把吉他的场面[7]260。在这里,薛曼暗示了白人拜金主义的可怕危害。如果说最初的“丛林狼泉水”乐队是为了传承印第安文化而唱,那么后来的演出则完全是被金钱的利益所驱动。他们的失败预示着离开了传统文化思想的支撑,印第安文化和精神面临毁灭的危险。
纵观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白人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压迫和欺骗与这把吉他是如此的相似。为了实现向西部扩张的计划,从1778年到1883年美国政府与印第安各部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作出很多虚假的承诺,印第安人离开了自己土地肥沃的家园迁移到贫瘠荒凉的保留地生活。在这期间,先后有超过750块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协议合法地割让出去,而几乎所有协议中对印第安人的承诺都没有被真正履行。最悲惨的一次迁移是1830年签订的“印第安迁移法案”,法案规定所有美国东南部的部落和当时被称做老西北的部落都要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荒原地带。切罗基等部落在长途跋涉的迁移过程中,造成了上千人的死亡,这条路因而被称为“泪水之路”[8]30。
另一个带给美国印第安人历史性灾难的法案是1887年签署的道斯法案,通过把部落的土地分配给各个家庭和个人以结束传统的印第安部落的生活方式。接受了土地分配或同意接受这种“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印第安人被授予公民权。事实上,大多数印第安人直到1924年才享受到这个权利。法案中的一个重要规定允许政府购买“多余”的印第安土地。道斯法案的主要效果是政府有效地从印第安人手中夺走了土地,在道斯法案实施后45年里,政府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走了9000万英亩的土地[8]30。
其他的各项法案仍在继续影响着印第安人的生活,直到现在。在小说中,薛曼反复地提到或暗示政府对印第安保留地的漠视,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保留区人民贫穷的生活状态:商店里出售的廉价的商品,政府“房屋开发与城市开发部”盖到一半的房子,卫生服务机构的缺乏,印第安事务局的冷漠。同时也揭示了困扰着保留区生活的重要问题,如赌博、酗酒、贫困、缺少教育和住房等。透过这把魔幻的吉他,读者看到的是一段真实的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欺骗掠夺的历史和一个真实的印第安保留地的生活现状。
三、 两个死而复生的军官重演了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罪恶
两个来自纽约“骑士唱片公司”的经纪人菲尔·谢里丹和乔治·莱特来到保留区与“丛林狼泉水”乐队签约,邀请他们去纽约录制唱片。谢里丹和莱特也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他们曾率领美国骑兵团在19世纪与奋起反抗的印第安人作战,并且屠杀了几千匹印第安人的马,进而造成大批依赖马匹生存的印第安人的死亡。这就是历史上有记载的1858年的“印第安马匹大屠杀”[9]。在《保》中,谢里丹和莱特同时扮演了两种角色。他们一边是唱片公司的经纪人,另一边则是曾经镇压印第安人的将军。两种角色跨越时空,交替登场,魔幻效果非常明显。
作为经纪人,他们找到“丛林狼泉水”乐队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乐队成员印第安人的身份来吸引观众,赚取商业利益。当乐队录制唱片失败时,他们立即除去虚伪的面具,露出无情的嘴脸,特别是谢里丹,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了乐队。因为对他来说,从他做将军时起,白人殖民者就没有任何错误,所有的错误都是印第安人的。谢里丹代表着历史上对印第安人敌视、虚伪和暴力的主流美国思想。在从乐队录制唱片失败后,谢里丹闯入乐队成员查可的房间欲行不轨。这时这个狡诈的经纪人变回了历史上那个镇压印第安人的将军。他的自白式的宣泄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谢里丹说:“我们给了你们机会。你们所要做的就是搬到保留区去。我们会保护你们。美国军队是印第安人最好的朋友……。但是你们从来不肯呆在我们安置你们的地方。你们从来不听从命令,总是反抗,从来不停止反抗。你知道我是多么厌倦和你们打仗了吗?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弃?”[7]236接着,谢里丹讲述了他残忍地杀害一位怀孕的印第安妇女的故事。他的言语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忏悔,似乎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镇压完全是理所应当的行为。与其相对比,莱特的行为则代表了一部分良心未泯的白人殖民者的心态。莱特从谢里丹手里挽救了查可,并解释他的行为是弥补过去对印第安人犯下的罪行。“莱特看着‘丛林狼泉水’乐队,他看到了上百万印第安人的面孔,被水痘和蚊虫叮咬得千疮百孔,被刺刀和子弹击打得面目全非。他注视着自己的双手,看到了斑斑的血迹。”[7]244在小说的最后,莱特回到了自己家乡的墓地,看到了自己的墓碑,在深深地忏悔自己的行为后得到了妻子的原谅,然后钻进墓地与自己的妻子团聚了。
故事情节虽然荒诞但其中蕴涵的意义却没有丝毫的荒诞。通过莱特,薛曼暗示承认一个国家的野蛮历史可以改变主流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态度。薛曼认为:印第安作家的一个重要的写作目的是重写美国的历史,在过去的历史书中很少承认欧洲殖民者的暴力统治和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因为一旦这样做,将会损害美国的民族形象和骄傲。但是薛曼说:“如果人们能够开始真实地面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和人民,则必须面对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屠杀。为了真实对待我们(印第安人)的文化,他们必须真实对待曾经犯下的罪恶,国家的罪恶,这样,类似的情况才不会再发生。”[10]
在重述历史的同时,薛曼也在提醒印第安人正在面临一场新的战争。诚然,没有莱特和谢里丹,“丛林狼泉水”乐队也许还安安静静地坐在汤姆斯的房子里,无所事事。然而,薛曼暗示对印第安人无情的利用是在商业世界和娱乐业里面正在进行的一场新型的战争。两个行业都是由白人操控着,最大化的商业利益是他们的唯一目的。谢里丹和莱特与他们签约的同时向他们的老板发了一封信,直言物质欲望,称如果将乐队包装成人们心目中定型化的印第安野人的形象,把他们涂上战争的油彩和粘上羽毛,一定会吸引很多的观众。莱特和谢里丹的恶毒意图可以把他们和吉他画上等号。即使在乐队离开后,他们仍然继续着他们的计划。谢里丹找来了乐队中的两个白人女孩,把她们包装成了印第安女人,录制迎合白人的所谓的印第安人的唱片,开始了公开的欺骗。
在这场“战争”中,“丛林狼泉水”乐队被暂时打败了。在录制唱片的最后一刻,吉他背信弃义,不再配合,唱片公司的老板不给他们任何的机会,因为他一贯认为“他们根本就做不了”[7]226。面对来自名誉和金钱的诱惑,忽视自己民族的本质必然会受到白人的利用,而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失败。
四、 传奇人物“大妈妈”的非魔幻事迹揭示了印第安民族振兴
发展的关键
如果说薛曼对于吉他、谢里丹和莱特的魔幻描写成功地揭示了白人殖民者虚伪、凶残和欺骗的本质,那么对于印第安人本身,则没有使用任何魔幻的描写,甚至在有意地强调这种“非魔幻”特征,对“大妈妈”的描写就是如此。“大妈妈”是部落里最具传奇魔幻色彩的人物,她已经184岁,有人看到她在水面上行走 。然而薛曼并没有把她刻画成一个具有非凡魔法的人,相反,着重展现她理性现实的一面。她并非无所不知,也不是无所不能。她没有预见到朱尼尔的自杀,不能阻止马群被大批屠杀 ,不能阻止乐队去纽约签约。她不能飞,也不能突然地出现和隐身。“我不是神”,她曾经说过,“我只是一名音乐教师”[7]209。她的力量表现在她的宽容、博爱、智慧,并非由于其具备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她让维克多原谅曾经猥亵他的白人神父,忘记仇恨,她邀请阿诺德神父参加朱尼尔的葬礼,她对乐队表现深深地忧虑,她是一位深刻了解印第安文化精髓的智慧的长者。
小说设计了一个有趣的情节,在一年一度的印第安保留区居民宴会上,由于来赴宴的人数是炸面包数量的两倍,厨师担心宴会会演变成哄抢面包的骚乱,但是“大妈妈"挽救了局面。就在宴会要演变成大规模骚乱的时候,“大妈妈”走出厨房,将手中的炸面包一掰两半,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化解了危机[7]301。
通过这样幽默的情节,薛曼旨在告诉读者他所描述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现代印第安保留地的真实图景。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保留地人们贫困的生活现实,但这显然并不是作者的唯一意图。他在告诉人们印第安保留地的现实问题只能通过现实的方法来解决,生活中是没有魔法存在的。印第安人力量的源泉不在于超自然的力量而在于人的智慧。“大妈妈”是印第安人传统文化的化身,她的精神必须通过这些保留区的青年人传承下去。在“大妈妈”的梦中,在印第安人传统的庆祝仪式(Powwow)上,汤姆斯等年轻人以及所有斯波坎部落的人围拢在传统的印第安大鼓周围,击打着欢快的鼓点,唱歌跳舞,大妈妈则吹起了印第安人的长笛。在小说的最后,乐队成员汤姆斯、查斯姐妹唱着印第安人的歌曲,带着“大妈妈"的祝福,勇敢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五、 结 语
在《保》中,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薛曼·亚历斯打破了传统的时间观念,让故事中的人物(事物)自由地驰骋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不露痕迹地穿插在故事的讲述当中。作品中历史与现实交织,真实与虚幻交织,印第安人被欺骗、迫害的惨痛历史,印第安保留地青年人面对白人文化的惶恐与迷惑,现代白人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利用和侵略以及印第安民族复兴的根本都得到淋漓尽致地阐释。小说既具备文学欣赏价值又具备社会研究价值,不愧是当代印第安文学作品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Delicka M. American Magic Realism: Crossing the Borders in Literatures of the Margins[J].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of Turkey, 1997(6):25-33.
[2] Spindler W. Magic Realism: A Typology[J]. Forum for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1993(1):75-85.
[3] Bowers M A. Magic(al) Real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24.
[4] Faris W B, Zamora L P. Introduction to Magical Realism: Theory, History, Community[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5.
[5] Schroeder S. Rediscovering Magical Realism in the Americas[M].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4:14.
[6] Chanady A B. Magical Realism and the Fantastic: Resolved Versus Unresolved Antinomy[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5:23-24.
[7] Alexie S. Reservation Blues[M]. New York: Warner Books, Inc., 1995.
[8] Owens L. Other Destinies: Understanding American Indian Novel[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9] Bruce H E. Sherman Alexie in the Classroom[M]. Urbana: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2008:43.
[10] Grassian D. Understanding Sherman Alexie[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