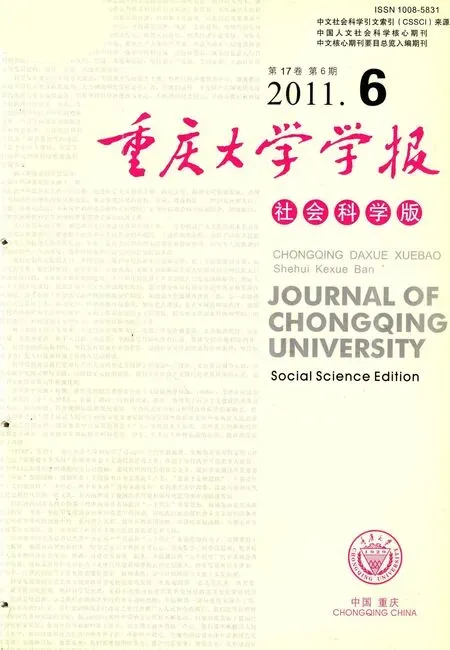抗战时期沦陷区殖民文化建构研究
方艳华
(山东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山东济南 250100)
抗战时期沦陷区殖民文化建构研究
方艳华a,b
(山东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山东济南 250100)
抗战时期的殖民文化是日伪在殖民体制下对沦陷区现存的各种文化资源进行重新认识与整合而形成的。民族文化方面,重点对传统儒家文化及中日关系史进行了创造性“发明”。外来文化方面,激烈排斥资本主义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化,而对宗主国日本的文化则进行了全盘美化。最终,日伪建构起来的殖民文化在民族性上遭到异化扭曲,缺乏自己的独立性与主体性;时代性上打上殖民烙印,被日本自认为优秀的文化所统率和局限。
抗战时期;沦陷区;殖民文化
抗战时期日本殖民者在占领中国沦陷区之后,也取得了文化的占有权,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日伪政权势必要支配沦陷区的文化生产。但问题是,沦陷区社会并非如一张白纸可以信手拈来随意涂抹,而是充斥着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化要素,这些要素大体可以分为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两大部分。日伪要建构新的文化体系,必须要将这些文化资源纳入到殖民体制中,做出必要的选择、解释与定位,并使之组合成为一个符合日伪统治意志的、逻辑性较强的文化整体,而这一过程也正是殖民文化形成的过程。但目前学界对沦陷区殖民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一些具体的文化侵略活动的表象性梳理上,笔者尝试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进行结构性的剖析,重在阐明文化在脱离了原有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的情况下,是如何被操纵其新场景的政治权威所重塑与整合的。
一、对民族文化的建构
民族文化指的是民族共同体所创造的、能够代表该民族共同特点的文化成果的总和,其内容极为丰富和复杂。沦陷区日伪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重新诠释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与民族历史两个方面,前者以儒家文化为最,后者集中在中日关系史领域。
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日本殖民者深知此点,所以在殖民占领时,为了防止对中国固有价值观念过度冲击而危害统治秩序,日伪采取了在恢复和发扬传统儒家文化的幌子下,将殖民理念移植入本土传统的文化谋略。此项谋略的实施,使得儒家文化在沦陷区遭遇了实质性的异化。
王道政治是日本侵华过程中使用颇为频繁的一个口号。对于侵略中国的行径,日本殖民者通常是以提倡王道主义、建设王道乐土来加以解释,他们向民众宣传,“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是源于西洋思想,皆不适合于中国,要想将中国从西洋的文化经济奴役中解脱出来,就必须实行王道主义”[1]。
1932年伪满成立,以逊清君臣为主体的傀儡班底独立打出了“王道政治”的旗帜,将王道政治与日本占领、统治东北的实际结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借用王道政治的天命观,张扬所谓的“顺天安民”,把日本所扶植的傀儡伪满政权说成是中国满蒙地区“三千万民众之意向”,以此证明伪满的合法性。其二,夸饰伪满所实行的正是王道民本主义的“爱民”与“保民”政治。同时为将白山黑水与三江平原从中国神圣的完整版图上分裂出去寻找理论依据,又将“保民”的主体含义歪曲成“保境安民”。其三,鼓吹王道“内圣”之学,强迫伪满统治下的中国民众在“责己而不责人”的基础上,“修养”到能服服帖帖作日伪血腥统治下的顺民而后止。其四,利用王道“外王”之学,侈谈“民族协和”与大同思想,妄图利用儒家以文化划分民族而不是以血统来划分民族的传统民族观念的温和性与模糊性,淡化民族与国家的界线,腐蚀民众的抗日意识,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2]。
华北与伪满壤地相接,华北各伪政权成立之后,日本殖民者也试图将伪满的“王道”阐释模式移植到华北。1938年1月,“头号傀儡操纵人”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在向新闻界评论当时的临时政府时曾说,中国人“讨厌繁琐的规章制度”,所以将来“在实际上也不会搞什么政府规章”。他还强调“中国人很古怪,他们既不需要君主形式的政府也不需要共和形式的政府,因此“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3]。缪斌的新民主义就是这样一套恶意发掘儒家王道学说来迎合日本侵略中国实际需要的反动言论。它打着复兴东方固有文化的幌子,标榜以仁义道德为本,借用儒家经典《尚书·康诰》中的“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和《大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中的“新民”两字,引导老百姓体认日本侵略者灭亡“旧邦”中华民国的“天命所归”,而做日伪政权下的“新民”。同时缪斌又将《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擅加“亲乡”一目,作为培育新民的方法规条,以此最终实现“天下一民,有教无类,泯除种族观念”和“天下一土,有德者有土,泯除国界观念”的所谓“王道平天下”的新民主义的最高理想[4]。
和上述两大伪政权一样,汪伪也在沦陷区的特殊语境下也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的认识。观其大略,一则比附各项内政施策。将《论语·颜渊》中的“子为政,焉用杀”及孟子的“仁者无敌”等主张中有关和平的论说突显出来,刻意强调“孔子之政治思想,中心和平”[5]33,把附敌之“和平建国”论说成是力行孔孟之道;搬出《尚书·大禹谟》中“正德”、“利用”、“厚生”以民为本的为政诉求附会伪政权的殖民统治,称“正德”即是以贤人、哲人有德君子为代表,“人人共任”,“利用”是“尽物之性”,发明致用,“厚生”增加生产,丰富生活,伪政权现在正“奉此遗教,切实发生自己的力量向鹄的进行”[5]43。二则将儒家思想作为日本霸权秩序建设的文化工具,最为典型的表现即是强调历史上儒家文化对东亚诸国的影响,并将其作为“东亚共荣圈”内各方进行“文化沟通”的桥梁,宣称用“孔子学说之涵濡沟通,尤觉深切”[5]35,企图以异化的儒家文化为纽带构建东亚社会的同质性,诱导以日本殖民者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体制下集体认同的形成。可见,此时的儒家思想已与中国传统儒家的根本精神彻底背离。
历史与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休戚相关,在沦陷区特定的场域下,日伪对民族历史建构的重点放在了中日关系史上,但其言说下中日关系史,已不仅仅是对中日交往过程的简单叙述,通过重新发掘、裁剪、编排史实而在各类历史文本中负载上其意识形态因素而将“历史”与“现实”进行对接才是日伪塑造历史的终极目的。
在古代中日关系史叙述方面,日伪有意突出了中日友好交往的一面。建立在暴政而非价值认可之上的殖民统治秩序,自始至终都面临着合法性的问题,日伪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要获得沦陷区民众的认同,而古代中日间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关系在这种认同的产生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无怪乎时任汪伪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澄宇曾直言不讳道“从历史上观察中国之与日本,其渊源甚深,则两国民族稍循前代事实,当有油然而兴亲睦之感者,亦前代所为昭示而不可忽者也”[6]。为此,殖民当局大力呼吁日伪文人要关注中日“亲善”史之研究,沦陷区出版的报章杂志、剧目鼓词中也被强行掺入了大量中日“亲善”史的内容。在一篇名为《中日亲善历史之考证》的文章中,作者就列举了从秦朝至隋朝中日交好之史实,最后得出“中日两大民族,不论血统、地域、文化等,均属一体,两国休戚相关,自应切实合作,共同提携,建设东亚之阵营”[7]的结论。古代中日友好交往的史实成了现实中中国人民应同日本侵略者结好的注脚。
近代中日关系史方面,日伪则将建构的重点放在了对近代以来日本侵华的几次代表性事件的大肆歪曲上。这些事件主要包括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二十一条”、“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例如,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已有大量的史实证明是日本借朝鲜东学党起义蓄意挑衅所为,但沦陷区日伪却有意将开战原因诿过于英、美、俄等西方国家之挑拨,称“然忌者已倡为黄祸之说,以耸国际之观听,不惜施行种种阴谋,以求实现中日鹬蚌之争,于是而有中日甲午之战,此为中日两国间受人拨弄最初之战争”[8]。再如,日俄战争在日伪的笔下被粉饰成日本殖民者为保全中国不惜向强俄开战,受感化之中国与日本联手并肩驱俄,甚至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的“二十一条”也成为日本提携中国,防止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的义举,是“大东亚解放战争”的先声[9]。种种由日伪建构出来的图景与真实的历史相距甚远。
二、对外来异质文化的排斥及对日本文化的推崇
日伪建构殖民文化除了要整合民族文化资源外,还需要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重新诠释定位。在沦陷区特殊的社会关系背景下日伪对于作为“他者”的资本主义文化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文化采取了激烈排斥的态度,与此同时对于宗主国日本的文化则采取了全盘美化的态度。
首先,日伪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拒斥是从否定其核心价值理念个人主义入手的。资本主义文化开始于文艺复兴时代,缘起于不堪中世纪神学独断及教皇压制而适应15、16世纪新世界发现的客观情势而出现的“自我”觉醒。这种“自我”觉醒客观上要求宗教改革、言论自由及发展资本主义,最终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确立了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同时在法律上建立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及契约买卖的自由,由此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得以形成。所以,个人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文化形成的历史起点也是贯穿于其文化各个方面的逻辑起点。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和强化,个人主义日益僵化、走向极端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一战的爆发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之后,西方理论界对于个人主义传统进行批评与反思的同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用集体名义出现的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来试图“拯救”个人主义的危机。沦陷区日伪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否定实际正是承袭和迎合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否定个人主义的理路,最突出的表现即是忽略个人主义的发展历程及阶段性特征,站在道德评判的角度对其进行直接抽象的全面否定。例如,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完全等同起来,称“个人主义主张损人利己和‘强权即公理’,并指斥仁爱互助为奴隶道德,认为只有欺凌弱昧才是君主道德”[10]。“个人主义的发展个性,是自私自利的唯一出处,只求功利,背弃道义,以物质范围精神,造成物质文明的高度矛盾”[11]。顺着对资本主义文化核心价值观否定的逻辑,日伪更进而得出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本质上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甚至称资本主义文化“自古就富于侵略性……违反人类和平本性”,这种侵略性表现于“国家的侵略”和“阶级的侵略”。“国家的侵略”是指“欧洲文化侵略世界造成了国家民族间的不公平现象,因之引起了不休止的国际斗争”,甚至认为“世界上一切的矛盾纠纷,都是欧洲文化侵略的产物”;“阶级的侵略”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从殖民地次殖民地榨取来的物资输回本国,仅仅膨胀了私人的产业金融资本,“使一国的经济操于少数资产者的手里,大众的生活乃日趋低落,由此演成了劳资的冲突”[12]。
日伪上述对资本主义文化本质及危机的言说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但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殖民语境下,围绕反英美的政治目的所做的所谓学术批判很难深入到学理层面而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资本主义文化主要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其内确有极端个人主义、剥削、混乱等糟粕,但不可否认在人类发展史上,它也曾起到过促进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进步作用。而且资本主义文化内涵中也并非仅重物质,同样也重精神。如果不加辨别地将资本主义文化之无限复杂性、多样性嵌入到一个简单的公式中加以抹煞是非常偏狭的。
其次,日伪对共产主义文化的攻击则是围绕马克思主义而展开的。攻击内容上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法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几大方面。在理论依据上或捡拾西方资产阶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牙慧,或取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共言论,或是借用此前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各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旧说,并无新鲜之处。建构手法上较具代表性的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以所谓“严正的态度,展开伟大的思想斗争”[13],而实为故意的胡乱引申,从以下两点可见一斑。
一是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歪曲或者将马克思主义一直反对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后再加以攻讦。例如,对阶级斗争的歪曲上,先从阶级斗争发生的角度将其歪曲为复仇主义、打杀主义进而再行诋毁,称阶级斗争“乃是提倡人类自相残杀,是由文明而重返于退化,是违背合作的原则,复返于兽性的生活……是人类试图毁灭人类的一种‘人类灭亡论’”[14]。再如,对唯物史观的攻击上,把哲学上的物质与具体的物质形态混为一谈,歪曲马克思主义是“物质命定主义”,认为“社会的本质是一种超越个人的客观精神”[15],而这种攻击恰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典型观点,与科学唯物史观有着根本的不同。二是断章取义,不问具体条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一内容从其完整系统中割裂出来而加以强调和歪曲。如抽去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涵,把无产阶级专政混同为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混同为封建君主专制,然后再施以毁谤;将当时苏联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教条主义的错误当作马克思主义不合实践的口实横加挞伐。
以上这些都表明,出于政治上防共灭共的现实需要,沦陷区的日伪根本没有真正搞懂而且也不愿去搞懂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任务只是要骂倒马克思主义,污蔑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化违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已,因此,这些所谓的批判既无理论价值亦无思辨意义。
再次,确立宗主国文化的强势地位,借“文明”之名来合理化殖民统治之实,是殖民者对待日本文化的基本态度。日本在占领中国沦陷区之后,就开始大肆散布与基本史实有出入的“日本文化优越论”,抬高日本固有文化的地位,夸大日本文化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的普遍性价值,甚至将其美化为“神皇一统”的神国文化。
日本固有文化是指距今上限七八千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的渔猎采集时代的原始文化及此后至公元3世纪的以巫术和祭祀为主体的弥生文化。实事求是地讲,日本自身的固有文化并不是十分深厚,如歌舞伎、浮士绘、茶道等很多都是德川幕府中期才出现的。如果从日本文化里,抽去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亚洲大陆文明而追溯他们的原初状态,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是穴居野处的遗迹。当然,每个民族都经历了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一些弱小民族依靠先进民族的熏陶开化而发达独立的并不在少数。但在沦陷区,为了树立日本的文化宗主国地位,殖民者不惜将单薄的日本固有文化美化成程度极高的文明。比如,有人就把“美感的高低”当作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认为“日本的房屋是用木头竹子和纸张造成的,也许被人认为是和南洋土人的住宅相近的文化程度。不过若从造型美的视角来看,拥有简易和素朴外观的日本房屋,却有世界上任何文明国民未有的感觉的洗练性。这是在外国人里面也承认的。从这种见地而论,日本民族的固有文明,不能不说是极高了”[16]。不可否认,日本固有文化确实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范畴与文化特质,在东方乃至世界美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但是如果将日本独有的文化当作是日本文化高于其他文化的论据,显然是非常肤浅的。
抬高日本文化地位的另外一个突出表现便是将日本文化夸张为普世有效的法则。如上所述,日本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融合外来文化才得以形成的。但在沦陷区这种文化特性却被日伪当作是日本文化具有普世有效性的有力证据,日本文化也被夸张地描述为包含中国、印度、西洋三种文化的结晶,“集世界文化之大成”[17],是“建设世界新秩序的先锋,是最优秀的,为世界最珍贵……具有普遍性、有效性,能广布于任何地方,适用于全世界”[18]。此外,他们还将中日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比较,认为日本吸收外来文化非常妥当,但是中国吸收外来文化就导致混乱状态,这是因为日本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可是中国不然,在政治上被外力征服过,因此,对外来文明,不知如何吸收是好,所以吸收之后,容易发生混乱”[19],以此证明日本文化高于中国文化。
沦陷区“日本文化优越论”登峰造极的表达便是将日本文化神化为“神皇一统”的神国文化。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日本的国土,是天神所造,风土之佳,冠乎万国,并且从来未受过异国的征服。(2)日本的天皇即是神,他奉天神的命令来统治日本。(3)日本的皇统万世一系,从未中辍。(4)日本的人民是天皇所传的苗裔,天皇与他们的关系是“义乃君臣,情兼父子”。显然,神国文化鼓吹的神皇合一的神皇谱系相联论,给日本文化涂抹上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此种向壁虚构的引申固然在知识阶层会嗤之以鼻,但对广大民众而言却易被日伪所迷惑。
三、结语
日本侵略中国,是全方位的,他们不仅从器物层面,通过武力震慑等手段迫使被统治民族屈服,而且还从思想文化方面建构一套自己的话语系统左右被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当然,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来看,不仅日伪政权,任何政权为了保持统治的长治久安都必须要依靠其所掌控的政治权力,动用各种文化资源建立一套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且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化体系。但问题的关键是文化建构的操纵主体是谁,建构的目的是什么,最终要把社会意识导向何方。
殖民文化就是日本殖民者在军事征服、武装占领的基础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日本殖民者及其所扶植的傀儡政权所创制出的一套符合殖民者利益的思想体系。它打着恢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幌子,篡改民众的历史意识,排斥资本主义文化与共产主义文化而向日本文化单方面的趋同归附。这种文化在民族性上遭到异化扭曲,在时代性上打上殖民烙印。
首先,从文化的民族性看,日伪所恢复的民族文化是缺乏独立性与主体性的。民族的独立与文化的独立不能分离,如果民族不独立,民族文化也难免要沦为其他民族的附庸。在沦陷区日伪所谓的恢复儒家文化与重视民族历史表面上虽然继承了近代以来各类文化民族主义理论中关于复兴民族文化的只言片语,但在本质上却与文化民族主义根本不同。近代以来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缘起于西方殖民文化侵略所造成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本质上是一种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独立的思潮。但日伪所建构起来的民族文化在民族性方面恰恰是以消解民族独立为目的的,“王道政治”、新民主义诸论的最终发展无不以模糊中华民族的边界意识、国家意识和种族意识为旨归;歪曲历史,建构新的历史意识,也使历史所固有的培育民族国家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凝聚力的功用无从发挥。以文化的主体性而论,日伪所鼓吹的民族文化的复兴并不是文化传统在整合了现代文化价值后所出现的超越传统的高级形态的文化回归,而是根据日本殖民者占领的沦陷区社会的实际,在重新认识、继承民族文化的伪装下,对民族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明”。这种“发明”并非针对现实的文化弊病,而是完全服务于维护殖民统治秩序的需要,沿袭了历代王朝的固有招数。最突出的就是在改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例如,“王道政治”、新民主义对于儒家文化的诠释少有学理上分析和创造,更多的则是建构一套从统治、奴化沦陷区人民的思想入手,训练服服帖帖供日寇摆布的顺民的方法和步骤。
其次,从文化的时代性上来看,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技术、科学、文化的涌入,中西文化的比较论争也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当然,除了早期极端顽固守旧派坚决贬低拒斥西方文化外,从近代思想界的主流来看,人们集中关注的重心并不是要不要接受西方文化的问题,而是如何积极的扬弃民族文化,批判的借鉴西方文化,努力寻求中西文化的切合点,进而探索符合中国文化实际的发展道路,以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与落后状况的问题。当然,新文化的建构并非朝夕之功,但经过近百年来的不断探索,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渊源流变、利弊得失等的认识已经有了比较理性、全面的体认,也有了我们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而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日伪在此时期却以激烈排斥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即便抛去其政治语境不谈,仅从学理上讲,这种对传统固步自封,对外来文化成果不加辨别做简单粗暴的否定也是不可取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殖民当局在对世界文化地图作了一番描绘后,却把宗主国日本的文化,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皇道文化美化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至高无上”的文化,妄图以此确立日本文化的统治地位,将被殖民者的文化纳入到一个以日本帝国为主导的文化一体化的局面中去,实现帝国主义的文化控制。
总之,按照文化学研究中的文化建构概念,新的文化模式的产生是在原有的文化资源和现实的社会关系背景下进行的。建构的过程就是处于强势和领导地位的国家、团体以及组织将外在的信息纳入到已有的文化结构中,引发对原有的文化资源进行重新认识和整合,而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沦陷区殖民文化的建构就是如此。大体而言,其建构的对象是现存的各种文化资源。建构的逻辑有二,一是对原有的本土文化资源进行重新选择裁撤和排列编码;二是引入新的价值观念,排斥屏蔽外来现代价值观念之影响。文化建构的目的是要将沦陷区的文化强行转型成一种缺乏主体性、独立性精神实质的,并以日本文化为依归的依附型的文化形态,而最终沦为中国文化近代化过程中的一股逆流。
[1]黄东.塑造“顺民”——华北日伪对民众历史意识的文化建构[D].首都师范大学,2006:19.
[2]方艳华.论抗战时期儒家思想在沦陷区的异化及原因[J].甘肃社会科学,2007(5):83 -85.
[3]约翰·亨·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册)[M].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18.
[4]缪斌.新民主义讲演集·序[M].北京:新民会中央指导部,1938.
[5]武德报社编.孔子[Z].北京:华北文化书社,1940.
[6]伍澄宇.我的中日亲善之基本理论[J].中日文化,1941,1(6):7.
[7]廖叙畴.中日亲善历史之考证[J].中日文化,1942,2(3):31.
[8]殷同.为中国前途告全国军民[J].新进月刊,1942,1(5):20.
[9]原胜,明之译.二十一条与大东亚解放战争[J].中国公论,1944,10(5):14.
[10]陈贞.东亚文艺复兴的基本问题(上)[J].华文大阪每日,1942,9(1):18.
[11]发动文化革新运动,号召精神建设[J].新进月刊,1942,1(6):18.
[12]沐华.和平文化的指标[J].华文大阪每日,1942,9(11):31-32.
[13]陈宰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批判[J].新民月刊,1942,3(6):84.
[14]旾音.中共理论与策略的根本错误[J].新进月刊,1941,1(1):15.
[15]赵一民.从全体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上)[J].新进月刊,1941,1(3):19 -20.
[16]长谷如是闲.文化性与生存性——日本文化的特质[J].教育时报,1943(10):15.
[17]嘉治隆一述.日本文化情形一瞥[M].东京:国际文化振兴会,1939:2.
[18]李正青.日本文化的特质(上)[J].新民月刊,1943,4(6):58-59.
[19]臼井亨一.东亚新秩序理念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二讲)[J].教育时报,1941(3):9.
Study on the Constructs of Colonial Culture in the Enemy-occupied Areas in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FANG Yan-huaa,b
(a.School of Marxism;b.Post-dovtorate Mobile Station of History,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P.R.China)
In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Japanese invaders and Puppets reinterpreted the existing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 Enemy-occupied Areas,which was lead to formation of colonial culture.In the aspect of national culture,they focused on distorting confucian culture and history of China-Japan relations.In the area of alien culture,they adopted a simple exclusive attitude to Capitalist Culture and Marxism,core of Communist Culture, taken to absorption overall of Japanese Culture.Finally, all of these led colonial culture alienate i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lack of independence and subjectivity, surrendered to Japanese Culture in time's characteristic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enemy-occupied areas;colonial culture
G127
A
1008-5831(2011)06-0134-06
2010-09-0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抗战时期肃奸研究”(20100471508);山东省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日伪对山东沦陷区的文化统制研究”(201003095);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日伪对山东沦陷区的文化统制研究”
方艳华(1981-),山东冠县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