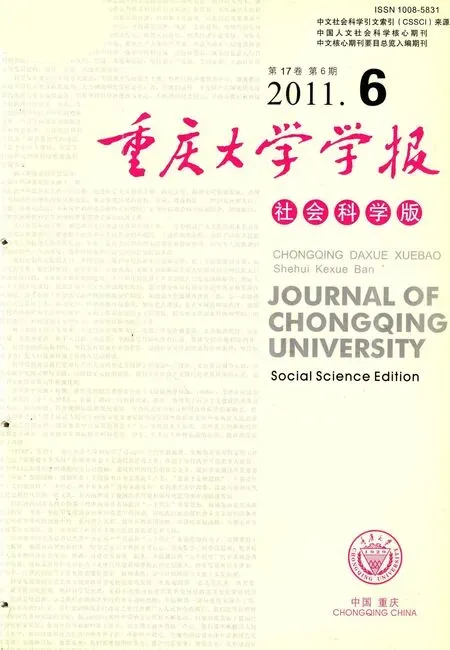北美敌托邦小说的生态书写
谭言红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00050)
北美敌托邦小说的生态书写
谭言红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00050)
敌托邦小说与生态思想有内在的契合。生态主义重视从思想和文化角度对人类驾驭自然进行批判,试图通过挖掘深层次的根源来协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达到平衡。敌托邦文学同样重视思想与文化的批判,它的危机意识涵盖得更广,而这些危机与环境危机叠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末日世界。为了更深入地挖掘这二者的深层联系,文章选取了北美敌托邦小说中的一些经典文本,从对自然精神价值的原初体验,循环时间观中的自我和自然,在倾听中存在的“物我合一”,艺术对自然的回应这几方面来探讨这一亚文类中蕴含的生态思想。
北美;敌托邦小说;生态书写
生态批评重视从思想和文化维度对人类统治自然进行批判,对人类中心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展开深入思考,试图通过分析深层次的根源来调和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重获平衡。敌托邦文学同样重视思想与文化的批判,它的危机意识涵盖更广,不仅是环境的危机,还有政治、经济、个体意识、自由与民主等的危机,而这些危机与环境危机叠加在一起,勾勒出一个末日世界。对于唯理性主义的怀疑,对于唯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各种大众媒介支撑起的晚期资产阶级文化对自然环境的深层次破坏及极权主义与自然精神的尖锐对立,皆普遍地投射在这些文本之中。生态批评家布伊尔·劳伦斯早已指出20世纪末环境敌托邦主义的基础是:对土地过度利用或干预导致不可逆的退化的想象;被变形的自然与人类的对立,以及自然作为被压迫者的报复;(人类)无法找到出路的迷茫[1]。此后,科幻小说与环境问题的联系更直接地体现在2005年出版的《环境批评的未来》中,他不仅分析诗歌和非虚构文学作品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还提到科幻小说作为类型小说,半个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即使没有对生态学产生持久的兴趣,至少也敏锐地感受到地球面临的危机、环境伦理、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2]。乌托邦学者莫兰也认为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已升级,尽管有正义力量的反对。而敌托邦文学最重要的真实在于系统性地反映了造成社会和环境罪恶的根源的能力。他还提到,20世纪50年代敌托邦文学的兴起是由于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它足以担负以下任务: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人性的蹂躏和环境的破坏,同时在现存的社会体系的潜在结构中发掘反抗的种子。敌托邦文学对生态的关注已成为其重要主题。
此类文本在北美不断有佳作涌现。如果说乌托邦作品是“欲望的教育”,那么敌托邦文学就是“欲望的焦虑”,这种寓言式的预言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我、自然等各个方面对未来进行黑色想象,揭示因人类的贪婪欲望而导致自身及其居所的最终毁灭。其中,对科技的负面效应的担忧,对人僭越自然的狂妄的否定,对大自然的报复的细微描写从始至终贯穿着这一文类。从第一部现代敌托邦小说——英国作家福斯特的《机器停转》(1909)开始,在北美大陆上此类佳作就层出不穷。《华氏451》(1950),《迟暮鸟语》(1977),《记忆授予人》(1993),《羚羊与秧鸡》(2003),《丑人》(2005),《无水洪灾》(2009)等皆或多或少地沿着这一脉络向前发展。文本往往蕴含一个共同主题:未来社会地球生态环境受到致命破坏,人类命运陷入无可逃离的困境。而在那些觉醒者与反抗者中,对自然精神价值的原初体验开启了生态意识的闸门,“物我合一”的移情感受在循环时间观中更加强了这种生态意识,这种意识冲出阶层樊篱,与视觉图像时代横扫一切的消费欲望相对立,在对传统文明的历史检索中深入思考存在的方式及内涵。随着当代社会环境意识的加强,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敌托邦文学与生态思想的链接也更频繁的浮现在文本创作及批评话语中,彰显出文学的现实意义。笔者选取了不同时代影响广泛的北美经典敌托邦文本作为分析对象,从对自然精神价值的原初体验,循环时间观中的自我和自然,在倾听中存在的“物我合一”,以及艺术对自然的回应这几方面来探讨这一亚文类中蕴含的生态思想。
一、自然精神价值的原初体验
自然不只是作为人类物质供应的来源而存在,它有其自身的存在意义,对人类还有着精神价值。作为一个完整而自足的体系,万千生命在这个循环的体系中更新换代,生生不已,人类探索其无穷奥秘不应是为了征服,而是在它的多姿多态中感受生命的丰富和活力,吸收其生态智慧,在它的四时更替中激起情感的共鸣,与之和谐相处。对这种精神价值的感受或认知,恰好是对隔离自然,禁止多样性的敌托邦社会的反叛。
布拉德伯里的名篇《华氏451》中的克拉丽丝这个纯真的女孩热爱大自然,从心灵深处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奇,在她身上散发出自然的生命力,而她生命的一部分意义便是探索自然的无穷奥秘。对她来说,连滴滴雨水尝起来都如同美酒。这种热爱被禁锢思想自由、同化大众头脑的极权社会当成了异端。对消费时代异化的人群来说,自然的价值不过是满足欲望的一种物质资源,自然存在的目的不过是为人类服务的商品,仅具有使用价值。如果不如此认为,便归于反叛者一类。她被迫定期看心理医生。而心理医生想打探的是她为什么总喜欢出门,为什么总在森林里到处闲逛,观察鸟儿,收集蝴蝶标本[4]23。这被认为是无意义且有害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影响下,主人公蒙泰戈也对自然产生出亲密之感,当他逃出城市来到山区,“他停下来,大口呼吸着。大地的味道吸得越多,就越是被大地上的万千事物填得满满的。他感到非常充实,这里总有太多东西让他觉得充实”[4]144。当身体贴近大地,他才感受到真实的存在,这种有负担的生命的真实撕下了未来社会轻浮的表面自由的面纱。代表这种空虚的表面自由的典型是生活在视觉图像中的他的妻子米尔德里德,她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参与电视墙播放的庸俗互动节目,清醒时连她也无法容忍这种思想的空虚,试图服药自尽。虚拟的图象与真实的自然之间的张力为蒙泰戈思想的转变提供了可信的动机。
《记忆授予人》的焦点却集中于一个生态智慧被强行压抑的人造社区。文章通过记忆传授人的视角来分析生机盎然,却暗含未知因素的传统社会和现在单调统一却平稳无波的敌托邦世界,“我们放弃阳光,放弃颜色之时,我们也放弃了差异性……我们因此控制了很多事物,但是也失去了很多事物”[5]95。在这个同一化社区里,气候被人为干预,自然界中四季更替的生态循环已被技术操纵,再也没有了雪,“因为雪会妨碍农作物生长,限制耕种时间”。所以,在建立同一化社区的时候,就被废除了。山丘也是同样,由于会给生活造成不便,就永远消失在人们视野中。就连给人们带来温暖的阳光,由于它会造成晒伤,也被硬生生地从生活中划掉,从没感受过阳光的乔纳思才会对这来自天上的暖意感到好奇而愉快。不仅是对气候和地形的控制,动物也从他们的生活中抹去了,同一性成为最重要的生存原则。“没有一个孩子确切地知道那(指动物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不过大家常用这个字眼来形容没有受过教育,笨拙或环境适应能力不良的人”[5]5。这个世界里的一切决策建立在实用的功利主义之上,却忽略了自然本身多样性所蕴含的平衡的智慧,在这样一个单调、孤立,与自然隔离的敌托邦社会中,表面上一切都管理良好,生活无忧,气候被精确控制,但他们的生活如同透明人,人们没有选择权,连家庭这个最能体现血缘关系的单位都是由掌权者理性组合,他们没有自由的概念,也不知自已丧失了自由。没有对于痛苦、战争的记忆,动物、色彩在生活中都已经不复存在,人们不再认识各种鸟类,河马、大象,大自然的变幻多姿,雪的清澈透明,阳光的灿烂温暖都已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只有在记忆传授人的头脑里才保存着自然的原始风貌。自然的生态智慧被极权社会的纯粹理性,完全同一化所覆盖,极权扼杀了象征她智慧的隐藏在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之中的和谐整一和内在平衡,只有记忆授予人能够完成自然的复魅,也因此,作为下一个记忆授予人的乔纳思逃离这个社区,他离开后记忆才会重回社会成员的身上,人们才会在自然中,在对痛苦与幸福的感受中重获自由。乔纳思在对自然精神价值的体验之中,也在历史的断裂处寻到了真实。
而《丑人》却是对大一统的审美标准的讽刺。即将面临美容手术的泰莉(当权者要求年满16岁就必须接受统一的美容手术,不得保留自己的容貌,而美容时借机洗脑)逃出城市来到荒野,眼前的景致远非她所能想象:她一直以为自已居住的城市是庞然大物,整个世界已包括其中,而在这里,一切都比城市更雄伟,更美丽。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在过去人们要住在大自然中,即使没有晚宴塔楼,没有华丽大厦,甚至连宿舍楼都没有[6]152。她渐渐习惯了“烟雾”原始部落般的艰苦生活,对于真实的自然,她放下心头的烦恼:“烟雾”的自然美景也洗涤着她心中的忧虑。山岭、天空,还有四周环绕的山谷每天变幻不已,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着自己的奇妙壮丽。自然,至少是不需要做美容术的,它一如以往[6]230。极权社会之所以隔离自然,其重要原因是他们认识到自然能够予人的精神力量,能唤起人们对于真实,对于更新与变换,对于个性与自我的寻求。而这种自我意识的萌发往往是伴随循环时间观实现的。
二、循环时间观中的自我与自然
生态自我是生态学家提出的概念,强调情境性,不管生态学有何瑕疵,这一观点仍有其现实意义。《无水洪灾》中以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展开的托碧的叙述呈现出女性叙事者在伊甸园的生活过程中,当面对他人、自然与社会时,逐渐发展出的暗合生态伦理与生态价值的自我观念。对于生态自我的这种情境性,薇尔·普鲁姆德有深入的分析。她认为,生态自我是一种关系性自我,它包含了尊重、善意、关爱、友谊和团结。作为一种超越了自我—他者二元论的运动,关系性的自我概念也隐含了对手段—目的二元论的某种颠覆[7]。
对于托碧来说,生态自我的获得是与对自然,对他者的理解,和对女性情谊的理解同时存在的。她生态自我观念的形成与她时间观念的改变同步,缘于她来到伊甸沿并与琵拉和蜜蜂们深入接触后。其时她已不自觉地转换了她原有的线性时间观念。“时间不是逝去的旧物,而是超越自身的永恒存在,是你漂浮其上的汪洋”[8]101。这种时间观早在作家1988年出版的《猫眼》的第一句中就已提到,“时间不是线状而是一种维度,如同空间般的维度”。这种时间观与女性主义倡导的时间观一致。克里斯蒂娃指出,男性的时间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而女性的时间是一种循环往复的永恒的时间。男性的时间概念是有计划有目的,呈线性预期展开、分隔、发展和抵达的时间,也就是历史的时间[9]。女性主义的时间观也与生态主义倡导的时间观一致。文中亚当一号曾说过“须得观察朝阳初升,月相变化,因万事万物皆有其季候”[8]164,这种季节性便是时间的循环性。时间是循环的,而个体只是万物中一个小的部分,在对自然的认同中,将旧有的小的自我与新的大的自我融为一体,在整个生命系统的循环往复中,自我实现其存在意义。这种时间观念与其信奉的万物相依,生命循环相一致,在参与到自然的循环中时,小的自我方体现出生之意义。
生态系统强调“情境性”,生物与环境是相互适应和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范畴,也体现在精神与情感范畴。在与自然的交流中,狭小的自我扩大到自然中去,从而生发出新的自我意识,这是一种生态自我。托碧的生态自我意识是从与伊甸园蜜蜂的情感误置开始。在西方,蜜蜂在很早以前就被认为是一种能启迪智慧的生物,19世纪的迷信认为养蜜蜂的家庭中如有人亡故,蜜蜂必须被告知,否则蜜蜂会离弃这个家庭[10]。琵拉生前把蜜蜂作为有灵魂与感情的生物,是天堂的信使,每天清晨都将日常顼事和讯息告诉它们,尤其嘱咐托碧在其死后一定要告知蜜蜂。在她的感染下,托碧从怀疑、嘲笑到接受,正是在对蜜蜂的诉说中,升华出崭新的自我。这种移情使得自然不再是作为被动的客体存在,对人类不仅有使用价值,它还存在精神价值和行为价值。正如薇尔的分析,“在某些情况下,对特定他者的关爱成为了自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而这种关系就会成为行为和选择的基础”。这也是对机械论的否定,大自然不是机器而是生机勃勃的有情感的循环的有机体,而构成这个有机体的每一部分也有其内在价值。
对道家哲学体会极深的厄秀拉·勒·奎因在《倾述》中同样表现出循环时间观,她(叙述者萨蒂)把阿卡星球的宗教体系定义为佛教或者道教类型的宗教哲学……永生不是终点,而是连贯的[11]94。在这种时间观中,人与自然物我合一,“躯体是世界的躯体,世界的躯体就是我的躯体。所以,如此一来,由一生二”。“这五条树枝孕育出无尽,树叶与花朵枯亡,复又重生,(万物) 皆从此理”[11]86,114。他们的思想体系与生活方式是普世等同的,蔓荼罗既是一棵树,也是一具躯体,一座山,它“一生万象,生生不息,万象往复为一”,动物、人类、植物、岩石、河流,每样分离、聚合,变换成他物,变换成总体,一体中拥有无尽的变化[11]1225-127,在她神秘深邃的宗教话语体系中,自我在循环中得到永生。
而对生态主义者来说,自我必须在参与到整体的循环中才得以体现,这便是二者相悖之处。生态自我是不断在循环中更新的自我,在这样的思想体系中,对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往往在倾听与倾述中完成。
三、倾听与倾述中的物我合一
现代科技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延伸了正常感官所赋予人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使人类感知体验的时空范围大大拓展[12]48。在这个类像化的生存状态中,生命的丰富内涵被转移到对技术的狂热上,符号体系的自我指涉功能使类像连接成整体,自由精神,审美体验,反思与批判都不再是利用符号体系进行艺术创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如同博德里亚所说,“在符号控制中,一切原件都不再存在,存在的只是通过机器,特别是电子媒介的符号产品,这种产品的价值已不再能按照原件来判断,而是来自于符号本身”[12]49。王茜对此观点的见解非常精辟,她指出“类像的本质是事物自身的独立价值和意义被抽空后的符号”,类像化的生存状态是在世界进入图像时代之后的伴生物。
图像时代有哲学和传媒两个层面的含义,这两层含义并非毫无关联。从哲学层面看,海德格尔认为中世纪后的新时代人把自己理解为世界的主体,客观世界被当作图像。世界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这就是说,客观世界是放置在人类主体面前的持存物,它是只具有表象的物体,而作为主体的人类需要观察的就是其表象,这样,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把自然平面化了,使它朝向人自身并为自身而生产自然,自然成为被人控制支配的对象。从媒介角度看,图像时代是指作为媒介的电子图像普遍存在于人们生活中,影响人们思维方式。敌托邦社会中,世界本就是由人们操控的图像,通过电视媒介对被把握成图像的客观世界的进行图像化生产,构成视觉意义上的表象,它朝向的是作为观众的人自身。这种表象同样使世界作为可被征服的客体呈现在人类面前。在图像时代,电子图像符号追求视觉快感,忽略内在精神,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快速变幻的声音画面磨蚀了感知,消解了思维。而这些画面里的自然,是经过意识形态选择之后的第三自然,要么虚假,要么有意突出它的凶险,来激发大众的憎恨与恐惧。如果说,人类的情感表达不需要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语言交流来表现,而是一头埋在更直接、更有吸引力的电子图像里,让变幻闪烁的图像来代替语言和思考,那么,在末世里,这种预言成为了真实。人们对电子图像的喜欢已然超过了对文字语言和口头讲授的喜欢,书面和口传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已被极权政府终结,而完全让位于以电波传送的电影、电视节目。视觉图像时代被忽略的倾听与倾述在初具生态意识的觉醒者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他们通过这一感知方式思索自我、自然及社会的相互关系。
《无水洪灾》中,琵拉作为伊甸园中一个保守的生态主义者,通过倾听来获知蜜蜂传达的信息,并向蜜蜂述说各种顼事、口讯,虽然有将自然神秘化的倾向,但也体现出朴素的物我合一的精神。
《迟暮鸟语》中,亲近大自然的克隆人茱莉,感受着流动的风,低语的树,轻吟的河水,在倾听河流中她找到了自我,她的意识向外延伸,试图捕捉她那部分失落的自我,给她带来宁静的自我。当她在船头上担任警戒,“一个人和这条大河在一起,这条拥有自己的声音和无限智慧的长河。它的声音又轻柔又含混,听不明白字句,但那种节奏是不会听错的,它在演说”[13]94。她似乎随时随地在倾听什么声音,“在岸边听来,河水的声音低极了,轻极了,像在诉说什么秘密”[13]105。离开儿子马克时,她嘱咐道“觉得孤单的时候,就到森林里来,听大树跟你说话”。“城市已经死了,成了废墟,但树是活的,只要你需要,它们就会对你说话”[13]140。副线人物巴里,帮助马克从克隆社会中逃走的医生也隐约听到了森林的声音,感觉到每一片雪花与另一片不同,大自然繁复无比,奥妙无穷。这些人物都在倾听中感受着自然的脉搏,其中有些人又以对艺术的追求来回应自然。
四、以艺术的方式回应自然
有着敏锐艺术感知的人,对自然也不吝挥洒真情。自然不仅与艺术的背景、对象和源泉相关,也反映出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和创作立场。敌托邦时代同样如此。在《羚羊与秧鸡》和《迟暮鸟语》中,两个末世时代对艺术有着自觉意识的人,以被当权者认为是无用和叛逆的艺术来回应着他者身份的自然,与唯科学主义进行着无声的对抗。在《羚羊与秧鸡》的后现代反讽语境下,雪人居住在一个人造的主题公园般的公司大院里,高耸的围墙把公司大院和衰退的城市中心及野性自然隔离开来。他颓废,玩世不恭,由于对自然和艺术还残留一丝热爱,而成为被社会排斥的悲观主义者。尽管他最初是出于对极权的反抗,要成为传统文明和书本的捍卫者和保护者,尽管他嘲笑没落的艺术,没对专业抱多少幻想,他还是认真地投入了人文学科的学习中,苦啃那些“过时”的知识,他记忆了一些古老的语言表达方式,并且词不达意地用在谈话中。“他对这些词渐生出一种奇特的温情,仿佛它们是林中的弃儿,而拯救它们便是他的义务”[14]195。应该销毁的旧书,“他一本也不愿意扔,因此没能保住在图书馆的暑期工作”[14]241。在科技至上的时代,他算是一个异端,他先知般地觉得好像有道最后的界线被越过了,而这被逾越的线会带来想不到的灾难。正是作为异端的他成为了灾难的见证者,存活了下来,虽然他的幸存远谈不上幸运。从他的叙述视角,文本开始和结尾都以末日世界作为背景,自然还是那样美好,而人类的遗迹却那样肮脏,“东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层灰蒙蒙的薄雾,正被一道玫瑰红的幻像似的光芒照亮起来。奇怪的是那色泽看上去仍旧柔和……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世界如何还能这般美丽?因为它一直就是美的。从岸边塔楼那儿传来鸟类的叫喊,这声音同人类毫无相似之处”[14]371。作为叙事者的他亲近自然的思想清楚地表达在语句里。他的朋友秧鸡恰恰相反,是唯科学主义的代言人,但又清醒地预感到有朝一日科技将成为脱缰的野马而为害于世。他生长在一个被围墙围起来的空间中,然后他就成了一个被如此建构起来的人,成为了一个孤立于外界的,封闭的人。他认为“自然之于动物园如同上帝之于教堂”[14]206,这两者对人类来说是危险的,自然应当是封闭的动物园,理该被关闭起来以保护人类。因此,“我不相信自然,或者说不相信带大写字母N的自然”,他相信的是科学打磨出的人造自然。但正是说这番话的他却将最重要的天塘计划(人造人计划)托付给了与之截然不同的雪人,因为他了解,雪人与那些天才科学家不一样的是文学出身的,并无用处的他“富有同情心”。这揭示出秧鸡对自已唯理信仰的矛盾与困惑。
凯特·威廉在《迟暮鸟语》中同样以艺术表达来回应着对自然的深情。克隆人茉莉在随船外出探险时,与其他克隆人一样感受到了离开兄弟姐妹的恐惧和孤独,但在绘画中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方式。“它(自我)在对她诉说,不是用语言,它用的是色彩,是她无法理解的符号,是梦境,是急速掠过的万千幻象”[13]100。她听见“河水跟我说话,还有树,还有云”。对她来说,这些都是生命体,正是这种对自然的诗性感受使她与其他克隆人格格不入,包括她的姐妹。这种强烈的身体感受上升为艺术表达,自然唤醒了她的自我,同时也唤醒了她表达自我的方式——绘画艺术。她的儿子马克,在克隆小孩们中孤独无伴,却在那些小孩和成人畏惧不已的阴森沉寂的森林中自由自在,根据各种大自然的痕迹辨别方向,从不迷路,而他如同他母亲将生命赋予画像一样,他捏的泥塑也是有生命的。与雪人相同,他富有同情心,而这一品性在克隆人中是纯粹的空白。当一批克隆小孩死于辐射线后,他是唯一为他们流泪的,这种同情心是自然人与克隆人的重要分界线。对自然和他人的感情与人物的艺术才能形成一条牢固的链条,通过艺术他们对自然作出回应。
五、结语
这些流传广泛,颇受赞誉的敌托邦文本都体现出对未来社会生态环境的关注以及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探索。敌托邦语境中的生态书写,从哲学层面上来说是对人与其居所的存在关系的思考,从思想层面上来说是探讨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从文化层面上来说是对消费时代的欲望的反拨,是对唯理性主义的功利目的的抗拒。通过对文明秩序的更新,文本创作者浇灌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循环往复的生态价值观。批评者将这种价值观引入到生态批评视野中,不仅是要将这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文明体系推介入社会,批评者也应在社会中身体力行,作其理论的实践者,既引领大众思想又以身作则,这就是生态批评的使命感所在。如同布伊尔所说,更有价值的批评来源于使命感而非专业知识[15]。在使命感的驱动下,敌托邦文本创作者通过对黑暗图景的想象,批评者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分析,在对未来生态作出预警的同时,更重要的目的是启示大众应该把握当下,让社会成为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社会。
[1]LAWRENCE BUELL.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n,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308.
[2]LAWRENCE BUELL.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56.
[3]MOYLAN TOM.Scraps of the untainted sky——science fic-tion,utopia,dystopia[M].Boulder:Westview Press,2000:7.
[4]BRADBURY RAY.Fahrenheit 451[M].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91.
[5]LOWRY LOIS.The giver[M].New York,Random House,1993.
[6]WESTFIELD SCOTT.Uglies[M].New York:Simon Pulse,2005.
[7]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马天杰,李丽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65.
[8]ATWOOD MARGARET.The year of the flood[M].Toronto:McClelland & Stuart,2009.
[9]SHARPE MARTHA.Margaret atwood and julia kristeva:space-time,the dissident woman artist,and the pursuit of female solidarity in cat’s eye[M].Essays on Canadian Writing(Fall 1993):174-189.
[10]BUELL LAWRENCE.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n,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184.
[11]厄休拉·勒奎恩.倾述[M].姚人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2]王茜.生态文化的审美之维[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3]凯特·威廉著.迟暮鸟语[M].李克勤,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14]ATWOOD MARGARET.Oryx and crake[M].Toronto:Mc-Clelland & Stuart,2003.
[15]BUELL LAWRENCE.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97.
Ecological Writing in North-American Dystopian Novels
TAN Yan-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00050,P.R.China)
Dystopian novels are interrelated with ecological thinking which typically criticizes man's control over nature and manages to balance the two sides by exploring the deep roots of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Dystopian literature also puts stress to cultural criticism and its crisis imagination——including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covers many aspects to describe an apocalyptic world.In order to reveal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 dystopian novels and ecological thinking, this paper selects some classical text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from four perspectives.
North-American;dystopian novels;ecological writing
I207.65
A
1008-5831(2011)06-0128-06
2011-09-02
谭言红(1973-),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北美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