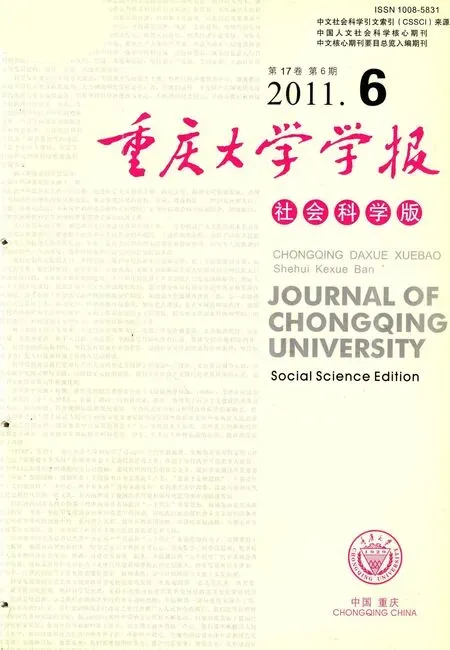从生态法益视觉重新认识犯罪本质
高 飞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4)
从生态法益视觉重新认识犯罪本质
高 飞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4)
用法益取代权利和社会关系,将犯罪界定为侵害法益而不是侵害权利或社会关系的行为,并非简单的词语的变换和更替,而是涉及到对犯罪本质认识的根本进步。法益的提出将价值的评判引入定罪的层面,使得犯罪的范畴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侵害,而是扩展到对社会和公众侵害的范畴。这也为当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根本利益的严重问题,而其他法律又不足以规制和保护时,我们将生态作为一种法益列入刑法的保护对象,将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提供了最大的空间。作为一种新型法益,生态法益的提出引发了我们对犯罪本质的重新思考。随着这种法益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受到或可能受到的侵害或威胁的严重程度,刑法必然作出相应的回应。
法益;权利;生态法益;犯罪;刑法
犯罪本质是刑法学所有理论问题的根基。当每一位刑法学者走进刑法理论的神圣殿堂时,都会见到迎面而来的五个大字“什么是犯罪”。就像游客必须猜中狮身人面神像的谜语才能进入他的领地一样。只有回答了“什么是犯罪”,才能进入下一个问题的探讨,否则一切关于犯罪和刑罚的理论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关于犯罪本质的解读——为什么是法益而不是权利
犯罪的本质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一代又一代的刑法学家都在对犯罪本质进行着解读。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为了否定封建刑法的干涉性、恣意性和身份性,启蒙思想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被奉为近代刑法学鼻祖的费尔巴哈提出了权利侵害说,他认为:刑法的任务就是保护权利,犯罪的本质就是对他人权利的侵害,犯罪就是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费尔巴哈的权利侵害说几乎成为那一时期对犯罪本质解读的通说。但从19世纪20年代起,德国刑法学界展开了对费尔巴哈权利侵害说的批判,其中,毕伦鲍姆(Birnbaum)在1834年提出了财保护理论。毕伦鲍姆(Birnbaum)认为:受到侵害的并不是权利本身,而是权利的对象,是与权利保护有关的财产,因此,犯罪的概念与权利概念无关,而与财产概念有关[1]。毕伦鲍姆(Birnbaum)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法益这一概念,但他的财保护理论却为法益侵害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后,“经过德国黑格尔学派的推动以及维也纳学派的展开”[2],宾丁在1872年的《规范论》中首先明确提出了法益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李斯特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法益理论,最终使其成为刑法学上的基本理论,在德国刑法学上占据了核心和主导地位。
在中国,传统刑法理论中均认定犯罪的本质是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的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为了或主要是为了解决传统刑法理论中社会危害性的空洞性和社会关系的宽泛性,中国刑法学界开始引入法益理论。法益论一出,便以强劲势头影响着刑法学界。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刑法是对法益的保护、犯罪是侵害法益行为的观点已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青睐;虽然众多的刑法教科书在犯罪概念部分都添加了对法益侵害说的介绍;虽然不少学者撰文出书展开了对法益的专题讨论,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刑法学界仅仅是引进了法益这样一个字眼,借用了法益这样一个概念而已。用法益替代社会关系对于中国刑法学的研究尚未起到变革性的作用,对于犯罪本质的认识并没有带来根本性的进展。尤其是对于为什么要用法益取代权利,法益和权利到底有何不同,为什么不能或不应将犯罪界定为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而应当界定为侵害法益的行为,却鲜有分析或者说解读十分混乱。作者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权利与法益的概念。
所谓权利,按照《辞海》的解释,是指“公民依法应享有的权力和利益”①《辞海》,1997年缩印版,辞海编辑委员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252页。;而对于法益,不仅《辞海》搜寻不到,连1984年出版的《法学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也告阙如。顾名思义,法益就是法律上的利益。按照李斯特的说法:“法都是为了人而存在,人的利益,换言之,个人的及全体的利益,都应当通过法的规定得到保护和促进,我们将法所保护的这种利益叫做法益。”[3]而按照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2]比较两位学者的定义,虽然李斯特强调法律对法益的保护,张明楷教授强调犯罪对法益的侵害、强调宪法原则和法益的可侵害性,但在本质上,两位均认可法益是“为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生活利益”。以此定义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础,我们不难看出用法益取代权利、将犯罪理解为侵害法益的行为而不是侵害权利的行为具有其当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权利无法解释所有犯罪,法益给了定义犯罪更大的空间
费尔巴哈的权利侵害说之所以受到质疑,与其“对于许多犯罪不能说明”不无关系。正如张明楷教授指出的“伪证罪在任何时代都被定为犯罪,但很难说伪证罪侵害了谁的权利。此外,费尔巴哈认为虚假宣誓属于诈骗罪、近亲相奸属于对权利的犯罪也是非常牵强的”[2]。以中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罪名为例,也同样如此。盗窃罪、诈骗罪无疑是对他人财产权的侵害;杀人罪、伤害罪自然是对他人人身权的侵害;但受贿罪、渎职罪则难以解释是对什么人的什么权利的侵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已经习惯了权利必然是具体而确定的利益。在谈及权利时,我们不仅要分政治权利、民事权利、道德权利,而且还要冠以具体而明确的名称,诸如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而法益由于没有这样的局限反而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二)权利源于天赋,法益来自法定
虽然权利也被定义为“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力和利益”,但作者认为这里的“依法”更多地针对的是权利的行使而不是权利的来源。权利无须由法律明确地逐一规定或列举,只要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从政治权利到民事权利,从自然权利到道德权利,从来没有哪部法律可以完整地罗列出权利的全部内容。比如中国《民法通则》以前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但并不意味公民不享有隐私权。也许正因如此,《牛津法律大辞典》在解释权利一词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个受到相当不友好对待和被使用过度的词。”②《牛津法律大辞典》,1988年第一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第773页。这里的“不友好对待”是指容易发生歧义而被人利用,正如罗兰夫人对“自由”一词的抨击: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使用过度”是指被泛化而用来作不该由它界定的事物的注脚。而法益则相对严谨,人们无法对它作出任意解释,它只能是法律明确予以确认和保护的利益。正如李斯特所说的:“所有的法益无论是个人利益,或者共同社会的利益,都是生活利益。这些利益的存在不是法秩序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本身。但是,法律的保护把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由此可见,法益虽然本质上是生活利益或者说源于生活利益,但法益并不等同于生活利益,只有受法律确认和保护的生活利益才是法益。就权利而言,也应当如此,只有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才是法益(但并不能由此得出法益包含权利或权利包含法益之类的结论,因为法益并不仅仅是指法律保护的权利,还包括权利以外的其他利益;而权利自然也不仅仅限于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利),公民可以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影响他人权利行使的情况下,享有一切法律明确规定的或尚未明确规定的权利,但并非一切侵害上述权利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尤其是刑罚的处罚。从这个角度讲,为了避免“受到相当不友好对待和被使用过度”,我们在刑法学上用法益取代权利也更具有合理性。
(三)权利呼应主体,法益侧重内容
权利总是对应着特定的主体,正如定义所指出的权利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力和利益。虽然现在权利的主体已经不仅仅限于公民而及于法人和其他组织,但我们可以举出无主的财产,却几乎说不出无主的权利。没有主体的权利形同虚设。而法益则不同,法益是一种生活利益,所谓利益包括对人们现实和未来有好处的事物,这里的“人们”并不要求具体到某个个体。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在民事侵权纠纷中总是会有具体而明确的作为权利主体的被害人(虽然现在民法也在发展,环境公益诉讼也是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但毕竟仅仅是个案或者说例外),但在刑事案件中却完全允许没有具体受害人存在的犯罪,甚至可以说大多数的罪名都不涉及具体被害人,即使是在有具体被害人的案件中,被害人也并非诉讼的主角,被害人的谅解也仅仅是量刑考虑的情节而基本不具有出罪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用法益取代权利也有一定的道理。
(四)权利彰显自由,法益强调价值
权利虽然也被强调要依法行使,也被强调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但毕竟它具有私权性质,最大程度地彰显着自由,也就是说只要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权利人有权自主地行使其权利,例如:自主地转让甚至抛弃他所有的财物;自主地放弃他的债权,而不要求这样的权利行使一定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他自己有益。但法益则不同,所谓益,古汉语中是溢的本字,意为水漫;《说文》称“益,饶也”。所以益应该是能使人增加收益,带来好处的东西,简言之就是给人提供积极的正面效应的利益和好处,是对人们现实和未来有好处的事物。因此,法律尤其是刑法在选择哪些利益需要确认和保护时,必须有相当的慎重,必须是确实对人们现实和未来有好处的利益而不是相反的。而且这些利益之间还有可能存在冲突,法律就会有基于价值的评判而产生的平衡和取舍,法益从某种角度讲正是这种平衡和取舍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利成为民法的宠儿,法益为刑法学者所专注并由刑法学者首先提出,也就绝非偶然。
在回答犯罪本质这一问题时,用法益取代权利、取代社会危害性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词语的变换和更替,而是涉及到对犯罪认识乃至认定的根本进步。它使得犯罪的范畴不再仅局限于对于公民个人(当然也包括费尔巴哈多提出的个人的保护者——国家)的权利的侵害,而是扩展到社会和公众的范畴,并将价值的评判引入定罪的层面,从而扩大了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导致刑法的处罚范围在法定的原则下进行了有限的扩大。
二、关于生态法益的提出——法益的扩张还是应然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曾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要警惕大自然的报复”③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或许人们只有在遭到报复以后才认识到先哲的名言。
早在中国的殷商时期,就有“街上弃灰者斩手”的规定,当然,把它说成“环境立法”未免牵强,但至少说明人们对环境污染有了朦胧的认识。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立法始于欧洲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的轰鸣,城市的拓展,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造成的废气弥漫空间,废渣堆积如山,不仅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无言的生物也默默地承受着灾难。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④八大公害事件是指伦敦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湖烟尘事件、洛杉矶光学烟尘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富士山骨痛事件、九州米糠油事件和日本水俣病事件。,每一次的受害者少则数百多者逾万,伤亡之重完全不亚于一次局部战争。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争论,也不因一个国家政权的兴亡更替而变化,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问题、世界问题。自20世纪中后期起,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饱受环境问题的困扰,人类深刻地感受到漠视大自然所遭到报复的痛苦,也逐渐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热门的话题。在法律层面,生态法益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引发了诸多的讨论。在这些探讨中,作者认为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首先解决。
(一)生态法益的界定
虽然生态法益的提出已有时日,但很遗憾的是对于什么是生态法益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共识。笔者认为要正确地界定生态法益,既要完整地理解法益的概念,同时也必须准确地把握生态的概念。
前面已经提到笔者是在“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的层面定义法益。而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原意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现在通常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包括它们之间以及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以此为出发点,作者认为生态法益应指的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人类基于良好而和谐地生存而产生的共同利益。按照这一定义,生态法益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其一,生态法益是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甚至某个国家的利益;其二,生态法益不是人类保证基本生活的基本利益,而是基于良好而和谐地生存所产生的利益。换言之,生态法益的“益”体现了一种生活的品质,它是也只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三,生态法益与其他法益一样,同样是从一般生活利益中因法律的确认和保护而由法律提升出来的利益。同时,生态法益还应该是可能受到侵害和威胁的利益。
(二)生态法益与传统的三类法益的关系
为了更深刻地探讨法益的价值结构,学者们以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面,对法益进行了分类。如按能否转让、替代为标准,将法益分为专属法益和非专属法益;以是否具备能被实际感知的物质形式为标准,将法益分为有形法益和无形法益。其中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以法益所代表的主体为标准。这种分类方法又有二分法和三分法。二分法将法益分为公法益和私法益。公法益又称“整体法益”,包括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私法益,即个人法益。三分法将法益分为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由此可见,二者并无实质区别,二分法简则简矣,但过于述略,实际上只是在三分法基础上一种整合,意义不大。近来,随着生态法益的提出,有学者提出了法益的四元化即四分法,主张将生态法益与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并立。他们认为:生态法益是传统刑法中的个人法益,是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所不能包容的法益,与传统的这三类法益具有本质的区别,由此提出了“由以往的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三元利益结构向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的四元利益结构演变”的观点[4]。四分法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生态法益的归属。
对此,笔者认为:第一,分类的标准不同。传统的三分法或称三元法益结构是从国家、社会、个人这三个主体的角度加以划分,从而得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类。而生态法益强调的是法益的内容而非法益的主体。四分法虽然强调了生态法益,但将不属于同一个序列的类型并列,具有逻辑上的缺陷。
第二,法益原本就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不同的时代对于利益要求的标准不一样,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利益也就随之不同,这也正是法益的生命力所在。所以生态法益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法益,但它并没有超越法益原有的框架和范畴,将之列在社会法益之下并无任何不妥。
将生态法益纳入社会法益并不意味着与国家法益、个人法益无关。相反,侵害生态法益也可能同时侵害着国家法益和个人法益。台湾学者周治平在评述台湾刑法体例时说“本法采三分制,即第一章至第十章为侵害国家法益之罪;第十一章至第二十一章,为侵害社会法益之罪;第二十二章为侵害个人法益之罪。然三者并非截然对立”。并举诬告罪为例,认为属于同时侵害国家法益和个人法益之罪[5]。生态法益也是如此,对生态法益的侵害不仅侵害每个公民的利益,不仅违背国家的政令、法规,更是对全社会的危害,只有把生态法益纳入社会法益,才能充分体现它主体的广泛性和价值取向上的全民性。当然,由此一来,三分法中关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排序似乎应该变更为“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更为合理。
第三,如前所述,在刑法学上引入法益理论,将犯罪界定为侵害或威胁法益的行为,无疑扩大了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导致了刑法处罚范围在法定的原则下有限地扩大,而这一变革已经为将生态法益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提供了空间。当环境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根本利益的严重问题,而其他法律又不足以规制和保护时,我们将生态作为一种法益列入刑法的保护对象、将严重侵害或威胁生态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实属自然。相反,如果我们将正在试图用法益取代社会关系的法益理论称之为传统刑法,则很可能导致语境的混乱。
由此可见,用法益取代权利和社会关系,用侵害法益来界定犯罪的本质具有合理性,生态法益的提出不是否定而是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三、关于生态法益的保护——罪的调整和刑的变更
既然刑法是对法益的保护、犯罪是侵害法益的行为,那么,刑法自然就应该根据法益本身的重要程度以及其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严重程度来确定罪名以及配置刑罚。我们的刑事立法其实也早已表露出这样的态势:当一种利益需要刑法予以确认和保护时,立法者会随之作出反应,将侵害或威胁这种法益的行为规定为个罪并配置一定的刑罚;随着这种法益的日益重要,以及其受到侵害或威胁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增加,立法者就会将之上升为类罪并配置更为严厉的刑罚。类罪的先后排序也从某种程度彰显出立法者对这种法益的重视程度以及保护力度。
以中国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为例。中国1979年刑法并未将贪污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独立的类罪,而是将其分列,将贪污列入侵犯财产罪中、贿赂列入渎职罪中,但均是个罪罪名;1988年的《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首次在标题中将贪污贿赂罪并列使用,虽然内容上仍属于具体罪名而非类罪罪名,但已经提升了对这些罪名的关注;而到了1997年刑法,贪污贿赂罪则直接作为类罪罪名出现。这一演变过程,与中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日益猖獗,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以及中国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分不开。
虽然作者不赞成将生态法益独立于国家法益、社会法益、个人法益之外,而倾向于将之列入社会法益的范畴,但并不等于不认同生态法益是一种新型而重要的社会法益。随着这一法益的日益重要和面临的危急,作者认为刑法或早或迟应该要作出如下反应。
(一)将生态法益作为类罪客体予以保护
虽然学者们在研究自己涉及领域的犯罪时总是会提出将该类犯罪上升为类罪罪名的立法建议,例如:研究知识产权的学者希望在刑法上设置侵害知识产权的类罪,研究环境犯罪的学者自然建议在刑法上增设破坏环境资源的类罪,这往往给人雷同之感并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是,鉴于生态法益确实是一种非常而且日益重要的法益,现行刑法将之主要放在第六章,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一类犯罪确实不能涵盖和准确地表述这些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内容。因此,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恶化和严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所带来的对良好而和谐的生存态势的日益重视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为大众所接受的趋势,刑法完全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将现在散落在第三章走私罪、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第九章渎职罪中有关侵害生态法益的相关罪名进行聚集和整合,单列一章侵害生态法益罪予以规定,以彰显刑法对生态法益的重视和保护。
(二)细化并增加侵害生态法益的个罪罪名
中国刑法关于侵害生态法益的罪名大概不到20个,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及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等。虽然罪名的规定并非越细越好,虽然有学者提出现行刑法所规定的400多个罪名对于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已经绰绰有余,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来解决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显然应该定罪处罚的行为,但是,由于生态法益作为一种新型的法益,涉及到从动物到植物、从大气到水资源、从噪声到辐射等许多新型的领域和新型的问题,而现行刑法所规定的这不到20个罪名不仅在罪名的排列上给人杂乱无序的感觉,而且确实无法应对侵害生态法益的犯罪行为。因此,刑法有必要借鉴环境法的研究成果,增加诸如噪声污染、水污染等相关罪名并进行整合排序。
(三)修正侵害生态法益个罪的犯罪构成
通览中国现行刑法第六章中所规定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诸罪名,不外乎两类:一类是污染环境类,一类是破坏环境类。而在污染类中大多数罪名均要求“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在破坏类中也多数要求“情节严重”或“造成资源严重破坏或毁坏”。这种在环境犯罪中将只有出现严重实害后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做法,实在显得消极和被动,无法更好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而又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6]。因此,至少应该将部分侵害生态法益的犯罪规定为危险犯罪。
(四)增设刑罚方法或变通执行方式
刑罚是刑法所规定的适用于犯罪人的最严厉的制裁方法,中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方法不外乎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几种。在这样的刑罚体系下,对于侵害生态法益的犯罪,目前也大多是给予管制、拘役、有期徒刑以及附加罚金的处罚,这不仅不足以遏制侵害生态法益的犯罪,更无法直接弥补对生态法益带来的损害。因此,刑法应针对侵害生态法益犯罪的特点,增设刑罚方法或变通执行方式,采取诸如义工、公告、恢复原状等多种途径[4],以期更好地遏制侵害生态法益的犯罪,使生态法益得到最好的保护。
综上所述,生态法益的提出虽然并不是对法益理论的颠覆,而是法益的应有内容,但作为一种新型法益,随着这种法益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严重程度,刑法必然对其作出相应的回应。
[1]杉树藤忠士.刑法中实质的法益概念及其机能[J].青山法学论集,1971(13):173.
[2]张明楷.法益初论[M].修订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5-167.
[3]庄子邦雄.“李斯特”,载木村龟儿编刑法学入门[M].有斐阁,1957:100.
[4]黄锡生,张磊.生态法益与我国传统刑法的现代化[J].河北法学,2009(11):56-58.
[5]周治平.刑法概要[M].台北:三民书局,1963:139.
[6]戚道孟.有关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10-27.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Crime:The Thinking Caused by Ecological Interest
GAO Fei
(College of Law,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P.R.China)
Defining crime as offences against legal interests instead of offences against right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replacing right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legal interest is not just a simple change and replacement of words, but a fundamental progress involv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crime.The putting forward of the concept of“legal interest”introduces the judgment of value into the conviction phase, making the scope of crime not just limited to the offences against the citizens'personal right but expanded to the domain of society and public,which provides large space to include ecology as a legal interest into the a protection object of criminal law and make the activity severely injuring or threatening the ecology a crime when environment problem becomes a severe social problem ,threatening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human being, and other laws can not provide enough regulation and protection.The criminal law will inevitably respon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interest, the newly introduced legal interes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it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severity of the likely injury or threat of injury.
legal interest;right;ecological interest;crime;criminal law
D922.68
A
1008-5831(2011)06-0114-06
2011-09-2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专项人文社会科学类重大项目“集体林权制度创新研究”(CDJSK100192)
高飞(1967-),女,重庆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和环境资源保护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