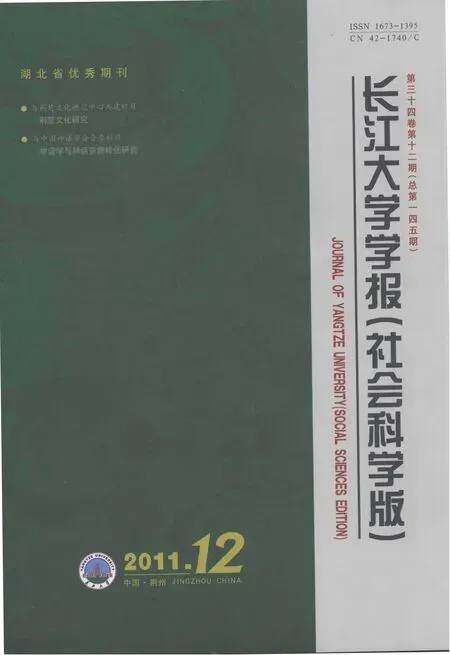旧词新义的认知考察(下)
——流行词“杀手”的语义变化
朱楚宏 毛绪涛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旧词新义的认知考察(下)
——流行词“杀手”的语义变化
朱楚宏 毛绪涛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流行词的词义理解,既要全面把握其内部构成与外部组合,又要深入考察大众习惯与文化语境。“杀手”新义,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汉语词义演变基本规律的体现。当前,“杀手”虽有语义弱化苗头,但由于词汇系统相关词语的影响,“杀手”仍基本维持着语义强势。
流行词;杀手;文化语境;强化;弱化
一、文化与语境
“杀手”新义是一定社会时代的产物。“杀手”新义的理解也就离不开对一定文化与语境的考察。在“名词+杀手”这种组合中,解析名词性定语所蕴含的施受关系,在许多情况下,需要考察大众习惯,需要借助语言环境,否则,就无从下手,也不能确切把握其意义。如,“少女杀手”与“红颜杀手”不同。前者“少女”是修饰性定语(受事),后者“红颜”是同位性定语(施事)。例如:
(1)娜娜长得很漂亮,岁月沧桑,但她依然是那样美,那样高雅,难怪人们称她为棋坛“红颜杀手”。(北大CCL语料库)
(2)一个在大学里人称“少女杀手”的帅哥,毕业来广州之后直摇头,跟我说,广州的女孩真是难泡啊。(《京华时报》2003-5-8第28版)
“红颜”与“少女”都指女性,为什么进入“X+杀手”的结构之后却出现了不同的语义关系?其实,这与汉语群体所赋予给这两个词的特定内涵有关。前者倾向于指“容貌秀美”,后者倾向于指“未婚年少”。虽然“红颜”不一定都是已婚,“少女”不一定都不美,但其意义侧重点却是明显存在的。因此,说到“红颜杀手”,“红颜”是指女性“杀手”的相貌特征;说到“少女杀手”,“少女”是指女性“杀手”的年龄特征。前者是展示“杀手”的秀美容貌,后者是说明被征服女性的年少未婚。这是大致的文化倾向,在具体的运用中还会出现种种变化。例如:
(3)营业小姐介绍说,早在上柜前就有很多顾客订购了这款可爱的KITTY手机,多数都是时尚的年轻女士,当然也有一些男士购买,把这款有“少女杀手”之称的手机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女友。因为是限量供应,现在这款手机已经不多了,要想把可爱的限量版KITTY带回家还要抓紧时间哦。(《江南时报》2005-12-30第17版)
(4)《看我72变》《城堡》《J-Game》让昔日的少女偶像变成了少女杀手。更活泼、更时尚、更新鲜的舞曲,也让蔡依林一下子在华语乐坛新旧曲风的交替时代脱颖而出。(《京华时报》2009-3-8第23版)
例(3)(4)的“少女杀手”与例(2)的用法不同。同样是“少女杀手”,例(2)是指受到女性追捧的男性,例(3)是指受到女性喜爱的事物,例(4)是指受到女性追捧的人(非男性)。这是因为“杀手”的词义有泛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为,在其核心义素〔+制服〕没有改变的前提下,非核心义素〔+施事+受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1]“海洋杀手”与“海浪杀手”的内部关系也不同。例如:
(5)大海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接纳进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流失的地表化肥,会使海域的水体呈富营养化,藻类植物大量生长,耗氧量也成倍增加,致使鱼虾大量死亡,这期间在阳光照射下海水会呈现一片耀眼的红色,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海洋杀手”——赤潮。(北大CCL语料库)
(6)回溯历史,海啸造成了众多耸人听闻的灾难,在几乎所有的海洋中称凶霸道,从来无敌手,从来不留情,海浪杀手,一次又一次袭击人类。海浪本身既致命又神秘,它可以时速达到每小时700公里,发作一次将会引起整个地球的震动。(北大CCL语料库)
在“海洋杀手”中,“海洋”是受事,指破坏海洋生态的现象;在“海浪杀手”中,“海浪”是施事,指威胁人类生存的现象。这是特定语境下人们对两种物象的不同感受造成的:前者是海洋生态话题,“海洋”是整体概念;后者是海啸灾难话题,“海浪”是具体形象,后者更具冲击性的动态特征。
另有一些“名词+杀手”的组合具有临时性与特定性,也很新潮很前卫,有的在慢慢形成专有名词,这种临时性与专门性,也会给词义理解带来一定的困难。如“师奶杀手”、“硬盘杀手”、“生态杀手”、“股市杀手”、“影子杀手”等。有的在理解上比较特别,需要细心体会。例如:
(7)自秋季以来,我国许多省市广泛传着市场上出现假桂圆的消息,一些新闻媒介也相继出现了诸如“桂圆竟是疯人果”、就‘桂圆杀手’告读者等的报道,这给消费者造成很大恐慌,也给一些地方及企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北大CCL语料库)
(8)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党代表达斯林说,该党的各地区组织每3个月组织一次集会,党员们可以对腐败现象畅所欲言。集会中,还经常给青年党员讲述腐败故事,将腐败定性为“牢狱杀手”,充分揭示其危害性。(北大CCL语料库)
例(7)的“桂圆杀手”,与一般的“水果杀手”、“植物杀手”一样,“桂圆、水果、植物”都是受事,受威胁对象,但在具体组合中又有不同。“水果杀手”、“植物杀手”是指严重危害水果、植物生长的事物现象,而“桂圆杀手”,却是指因为以假乱真、严重威胁桂圆正常销售的现象。例(8)的“牢狱杀手”,也不同于“市场杀手”、“马路杀手”等,“市场杀手”是指有掌控市场能力的人,“马路杀手”是指威胁道路安全的人,而“牢狱杀手”却是指有被关进牢狱危险的行为。这些变动不居的多样性意义,完全是由语境提供的。
再如“麻瓜杀手”、“豪门杀手”,其专门性很强,需要借助专门知识索解。据百度上说,“麻瓜杀手”的“麻瓜”,是指世上不会魔法、不相信有魔法的死硬派。英国女作家J.K.罗琳于1998年写的系列儿童小说《哈利·波特》。后来人们把一切不会魔法,不相信魔法的人叫做麻瓜。此外,医学上的麻瓜指的是回避现实生活,关注内心世界的人群。“麻瓜杀手”是指对麻瓜有严重威胁的人。“豪门杀手”的“豪门”,是指足球中通常指一些有过辉煌历史的,或持续较长时间战绩彪炳的球队,“豪门杀手”,顶级球队的足球高手。例如:
(9)布莱克是一个著名的麻瓜杀手,而且很可能准备加入神秘人一伙……当然啦,你连神秘人是谁都不知道!(〔英〕J.K.罗琳〔J.K.Rowling〕著,马爱农、马爱新译《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一名优秀的射手总是能引来豪门的追逐,更何况托雷斯还是专克巴萨这样的豪门杀手,为了对付仇人,皇马当然不会放过托雷斯;而为了避免受害,拉波尔塔肯定也不愿看到他落入皇马之手。于是,西班牙两大豪门开始了疯抢托雷斯的行动。(无缺《天设之敌》,《当代体育》2007年第11期)
二、强化与弱化
“杀手”一词新义的产生,体现了当前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这里主要谈谈词义泛化、词义强化、词义弱化等现象。
有学者指出,“杀手”的词义有泛化的趋势。[1]所谓词义泛化,是指词义从指甲事物演化到指乙事物,或从指个别事物到指一般事物。[2]如当前多用“美女”称呼女性,“美女”出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的引申变化,是典型的词义泛化现象。[3]就核心义素的淡化来说,“杀手”也有泛化的态势:“杀手”一词由“凶杀”题材的传统故事向现代生活的其他领域延伸与扩展。“杀手”的核心义素是“威胁(制服)”,“威胁(制服)”的前提是对峙双方的存在:即一方威胁(制服)另一方,形成对峙状态,“杀”与“被杀”就是一种对峙。推而广之,疾病对于人体、虫害对于植物、污染对于环境、竞赛的胜者对于败者,被崇拜者对于崇拜者,等等,一方对另一方都存在着威胁(制服、折服),也可看成是一种强弱对峙。因而,一些处于优劣高下对峙关系的人或事物中的“强者、优者”,都可以称之为“杀手”。如“采用了超耐磨橡胶的安踏篮球鞋,在市场上号称水泥杀手”一句的“水泥杀手”,处于对峙关系的是鞋底与路面:鞋底是施事,水泥路面(球场)是受事,水泥路面是被“制服”被“威胁”对象。原句是说,安踏篮球鞋质量好,鞋底耐磨,水泥路面难奈它何。
在讨论词义演变时,张志毅、张庆云提到过词义的强化、弱化现象。[4](P254)这里仅从词义变化角度讨论强化与弱化的关系。在词义演变中,强化与弱化相互作用可能形成一个动态过程:用夸张手法造成词义由重变轻,其强化是起因,弱化是结果。如“购”(重金悬赏→购买)、“穷”(极贫→贫)、“病”(重病→病)等。起初用前者(如“购”的“重金悬赏”)来表示后者(如“购买”)的意思,是一种夸张手法,是强化;久而久之,前者(如“购”的原义)被磨损,意义就弱化了。当前,以青少年口语为主的“超级、郁闷、崩溃、疯狂、颠覆”等,都有这种弱化趋势。
由强化到弱化是一个过程,是否进入弱化,弱化程度如何,会呈现出不同状态。如传统汉语中,“有才”(单位比词大,用法与词同)是对人的一种高度评价,“有才”比“有德、有钱、有势、有人缘、有能力”等都更有力度,更能受到人们的尊重、羡慕。当今口头上称赞别人时,无论轻重,一般都用“(太)有才(了)”,而不用一般的褒义词(如善良、聪明、睿智、英明、杰出、优秀、精细、敏锐、能干、熟练等)。“有才”的流行,虽与春晚小品的广泛影响有关,但也有语词表达上原因:用夸张强化语义。“有才”的这种用法可能导致语义的弱化,只是这种弱化当前并未完全到位。
“杀手”一词的泛化,起初,很可能也是一种大词小用。如“残暴杀手”→“癌症杀手”、“生态杀手”、“球场杀手”,前者是基点,后者是喻指。有了前者的比照,后者的意义得以强化;同时,随着词义的稳定与独立,后者(这一组中也有强弱差异)的意义又远不如前者重。
不过“杀手”一词也有其特殊性,“杀手”一词的意义并不弱(也与语素意义有关)。在“杀手”词义初露弱化苗头的时候,又有一种补救机制出现了——用叠加予以强化。这主要是指汉语词汇系统中其他有关的词对“杀手”的影响。在我们的大脑中,词汇不是杂乱地堆积,而是成系统的。当用某一个词进行造句时,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词语的信息可能会相伴相随,以致牵引与带动词义的微调。汉语词汇中,与“杀手”有关的词还有“下手、动手、毒手、杀手锏”等,这些词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首先是它们具有共同语素“手”,其次是意义都可以有这样的含义:表示对象与对象之间强弱对峙下的一种处置状态。请看这组相关词的释义:
[毒手]名杀人或伤害人的狠毒手段:下~|险遭~。(《现汉》2005)
[撒手锏]名旧小说中指厮杀时出其不意地用锏投掷敌手的招数,比喻最关键时刻使出的最拿手的本领。也说杀手锏。(《现汉》2005)
[下手]动动手;着手:先~为强|无从~|我们还没到,人家就下了手了。(《现汉》2005)
[动手]动①开始做;做:早点儿~早点儿完|大家一齐~。②用手接触:展览品请勿~。③指打人:两人说着说着就动起手来了。(《现汉》2005)
这一组词与“杀手”一样,都可以表示“给对手以打击”的含义。名词“杀手”具有“威胁、制服”等潜在的动词义素;动词“下手”与“动手”都有开始做的意思,如果这种开始的动作是针对竞争对手与处置对象,且出手动作很重很猛、于对方不利时,这就与“杀手”的威胁性意义重合、叠加了。这突出地表现在“下……手”这一类动宾结构中。例如:
常昊此时下得很顽强,宋泰坤也没能乘胜追击,痛下杀手。(北大CCL语料库)
陆小凤道:“可是你对我下的是杀手。”(古龙《陆小凤传奇》)
李铁这家伙有肉不吃豆腐,估计是准备暗下杀手。(柳建伟《突出重围》)
关键时刻,马晓春趁白棋点角后未站稳脚跟,猛下杀手锏,使白角成劫杀,并最终以半目取胜。(北大CCL语料库)
而最难解决的是长年积累下来的地方政府一些“政绩工程”的欠款,在这方面政府必须下“杀手锏”,否则将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北大CCL语料库)
以巴实力悬殊,真要动杀手,以军称2小时就能重新占领巴区,而阿拉法特不会活过下一分钟,驱赶他易如反掌。(陈克勤《阿拉法特:巴以和谈能否离得开你》,《人民文摘》2002年第三期)
话说回来,这一类用法,其实都可以看成动宾式离合词“下手”(动手)的扩展用法,而不是“杀手”的正宗用法。不过,由于在词形上与“杀手”部分相同,因而不能不正视“杀手”的这种用法。如果按词切分,“杀手”作为词的身份当无可怀疑。如例,可切分为:“他∕对∕我∕下∕的∕是∕杀手”。在我们搜寻到的语料中,“痛下杀手”出现频率较高,其中“痛”可用“连、暗、滥、猛、狠、突、忽、就、便、要、竟、不、未”等替换。在这些组合中,“X下杀手”还只是一种松散型结构。有时,“杀手”并非处于“下杀手”的格式中,但却仍与“毒手”“杀手锏”意思相当,确有“最厉害的一手”的意思。例如:
宝树“啊”的一声,右手一扬,一串铁念珠激飞而出。念珠初掷出似是一串,其实串著铁珠的丝线早被他捏断,数十颗铁珠忽然上下左右,分打胡苗二人的要害。这是他苦练十馀年的绝技,恃以保身救命,临敌之时从未用过,此时陡逢大敌,事势紧迫,立施杀手。(金庸《雪山飞狐》)
从教学实际考虑,尤其是从对外汉语教学实际考虑,对这类组合中的“杀手”的意义应该有单独的解释。其意义可概括为:具有威胁性的、强有力的手段。“杀手”与“毒手”“杀手锏”可成为一组具有相关、相近、相同意义的词。[5]“毒手”与“杀手锏”都是一种很厉害的“手段”,而“手”可用来表示“手段、手法”等也使“杀手”的意义向“毒手”、“杀手锏”的意义靠拢提供了可能。这也可作为“杀手”词义变异中以“手”的多义关联为理据的一个例证。事实上,人们在运用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将“杀手”与“痛下杀手”的“杀手”联系起来理解。下边是百度对一足球运动术语的解释:“影子杀手,作为球队最隐蔽的进攻手段,影子杀手通常隐身于前锋身后,或组织进攻、制造杀机,或亲自出马、痛下杀手;往往成为本队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对手现实中的梦魇。”
三、小结
“杀手”除了表示“刺杀人的人”这个传统意义之外,其新型用法非常活跃,如何将这新出现的隐性词义与用法完全发掘出来,还需要有一个沉淀与思考的过程。我们围绕“杀手”一词的旧词新义主要讨论了以下六个问题。
第一,词典滞后于语言实际,“杀手”新义已经出现,但还没有一个全面综合的现成解说。
第二,在汉语中,“杀手”的两个语素都是自由语素。作为单字,它们都被分别列入常用汉字表;作为单词,它们也都被分别列入常用词表。因为常用,所以意义广为人知;因为广为人知,所以一些临时用法易于被人们接受。
第三,在具体的运用中,“杀手”的字面意义常常受到特别关注:有时侧重“杀”的意义,有时会侧重“手”的意义,有时又可能兼顾“杀+手”的双重意义。
第四,根据名词性定语与中心语之间的施受关系,可将“名词+杀手”这一典型组合分为限定性定语与同位性定语两种。
第五,在许多情况下,区分“名词+杀手”的内部语义关系,需要考察大众习惯,需要借助语言环境,否则,就不能确切理解其意义。
第六,“杀手”新义,是词义演变中因强化手段而带来的语义弱化现象。同时,汉语词汇单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又使“杀手”的一部分用法能够维持语义强势。
这里仅对流行词“杀手”的运用现状及语义生成原理做了一点粗略的探讨与论证,对于认知流行词及流行文化,可能会有一定参考意义。至于“杀手”的引申系统,我们基本没有涉及。笔者的想法是对于一个正处于活跃状态中的流行词,不必给它过早地下全面性的结论。
[1]胡丽珍,宋肖娜.“杀手”释义商榷[J].汉字文化,2009(3).
[2]吴登堂.词义的泛化[J].辽宁师专学报,2004(2).
[3]邢建丽.“美女”称呼语的泛化及其语言学分析[J].语文学刊,2011(1).
[4]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王国锋.投“杀手锏”一票[J].咬文嚼字,2004(5).
The Cognitive Study on New Meanings of Old Words——The Semantic Change of Popular Words“Killer”
ZHU Chu-hong,MAO Xu-tao (School of Literature,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Hubei 434023)
We ne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combination of popular words,and have a deep investigation on people’s reading habits and cultural context.The new understanding on the word“killer”not only reflects the modern life,but also embodie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hinese semantic change.Currently,“killer”has the weakening tendency,but because of the relevant influence in word system,this word still maintains the strong impact on modern language.
popular word;killer;cultural context;strengthen;weaken
H146.3
A
1673-1395(2011)12-0071-04
2011 10 08
朱楚宏(1953-),男,湖北仙桃人,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语义与语用研究。
责任编辑 袁丽华 E-mail:yuanlh@yangtze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