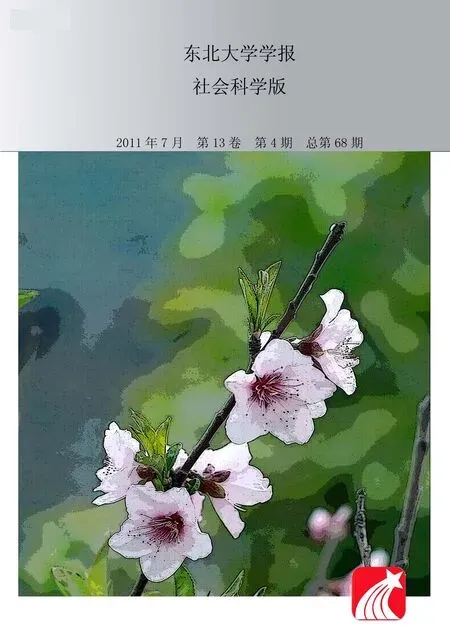关键期假说及其对我国英语教学初始年龄的启示
王勃然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一、 关键期假说简介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关键期并非语言学家首创,而是源于生物学,指有机个体对某类外部刺激最为敏感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这种刺激早于或迟于该时期,产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Lorenz观察到小鸭或小鹅在孵化出生8~9个小时之内将第一眼看到的移动对象认作自己的母亲,并对其产生依恋。这种印刻(imprinting)现象只在出生后一天内发生,超过30小时之后即自行消失[1]。Gould等对白冠雀的研究也表明,成年雄雀的叫声中包含某些能自动触发雄雏雀脑内收录装置的特定音符,而雄雏雀只有在出生后的40~50天内听到成年雄雀的叫声,日后才会鸣叫[2]。
作为创立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简称CPH)的先驱,Penfield & Roberts基于对失语症患者的临床观察,从神经语言学角度提出了大脑的可塑性假说(Brain Plasticity Hypothesis)。在他们看来,人类的语言能力与大脑发育密切相关,习得的最佳年龄应该在10岁以内。在此期间,人们可以在自然环境里,无须外界干预、无须教授,轻松快捷地掌握一门语言。而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大脑左右半球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出现了所谓的侧化(lateralization)现象[3]。1967年,Lenneberg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关键期假说。他把儿童习得语言的优势归因于生理因素,认为语言是大脑的产物,必定受到生物机制的约束。儿童从2岁至青春期(10~12岁)到来之前,左右脑半球都参与语言学习,对语言输入格外敏感,能够最轻松、最快捷地调动内部的生理机制,实现语言习得的自然发展[4]。青春期到来之后,大脑发育趋近成熟,并发生了侧化,失去了处理语言输入的独特能力,取而代之的是通用的认知模块和信息处理系统,语言学习的效率因而急速下降。
二、一语习得框架下关键期假说的正反理据
1. 一语习得框架下关键期假说的正理据
关键期假说创立之初,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是一语(即母语),而非二语或外语。支持此理论的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理据,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①大脑神经的可塑性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消退;②语言习得所依赖的内在机制和普遍语法随着生理成熟将不再适用;③如果关键期内语言能力没有得到发展,这种能力就会丧失。
Penfield & Roberts认为:婴儿出生时大脑皮层的某些区域具有固定的功能,但有一块出生时功能未定的皮层最终将用于语言和感觉。儿童在开始说话和感知之前,这一功能未定的皮层就像一块空白的石板,上面没有任何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白板上印刻了许多内容,而且无法拭去。在4~8岁期间,儿童运用这片空白区域可以轻易地同时习得几种语言,而到了10岁或12岁之后,语言中心的总体功能得以确定和固定,从此不能再迁移到大脑皮层已被知觉占领的另外一侧。Lenneberg发现婴儿从出生到2岁之间,神经元迅速生长,从2岁到青春期,神经元生长变缓,到青春期之后就基本停止了。更为重要的是,2岁之前和2岁到青春期这两个阶段与大脑侧化的两个阶段恰好吻合。青春期前左大脑受损的儿童,术后其语言不会发生紊乱,原因在于任一脑半球受伤导致的语言障碍都可以由未受损的另一半球代行其职,语言习得的损失相对较小,能很快恢复总体的语言控制功能。而成年人如果左脑受损,即便做过手术之后还会表现出持久的语言障碍,并发展成不可逆的语言功能丧失,这是因为青春期之后,神经系统不再具有以往的弹性,失去顺应性(compliance)及重组能力,语言的自然习得机制开始失效,处理语言的能力开始弱化,语言学习也就越来越困难。
有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系统与生俱来,所有的儿童都可以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段里习得母语——“儿童能在出生后的短短几年内掌握那么抽象和复杂的语言规则,是因为天生就有一种语言习得的心理倾向,能使他们系统地感知自然环境中的语言,并最后学会使用它”[5]。在Chomsky看来,人类的语言看似一个心理客体,实则是一个生物客体。语言机能就像身体中的每个器官一样,具有生物属性,其基本特征取决于遗传基因。这种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遵循所有语言的共同规则,即普遍语法,而普遍语法在不同的语言中以各异的参数呈现。正是由于这种专有机制的存在,儿童只要置身于某种语言环境之中,就能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形成语言能力;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语言相关的内在机制逐渐丧失或无法激活,所以习得语言的最佳年龄应该在发育期之前[6]。在语言生物性这一点上,Chomsky的语言习得机制和关键期假说可谓不谋而合。
有的语言学家跟踪研究一些地方发现的“狼孩”、“猴孩”、“猪孩”之后发现,无论人们采取何种方式教导这些回归社会的孩子,他们的语言能力都达不到正常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儿童的水准。美国加州“都市野孩”Genie出生后即被父亲当做智障儿加以隔离,在1~13岁之间被剥夺了接触社会和接受语言输入的全部机会。1970年,数位语言学家开始采用各种方法教授Genie语言,却无法帮助她达到同龄儿童应有的母语水平。通过探究一个19岁墨西哥籍先天失聪男孩E.M.的语言学习情况,Grimshaw等发现在借助助听器学习语言34个月之后,他无法解决语音方面的很多问题,不能顺利掌握时态、词序、介词及代词的用法,而且此结果与使用助听器8个月后的测验成绩相比,无显著性差异[7]。这表明,先天性听力丧失的儿童之所以在青春期后学习语言存在困难,很可能是错过了语言习得的关键期。
2. 一语习得框架下关键期假说的反理据
一语习得框架下的关键期假说,由于很难找到完全不接触语言的孩子,无法进行验证,因而一直备受争议。就关键期的终止年龄而言,Krashen在分析了用来证实关键期假说的诸多数据之后,认定大脑的侧化年龄大约为5岁,比Lenneberg提出的12岁要早很多。因此,即便所谓的关键期存在,它与大脑的侧化也是不同步的。后来,Witelson细化了大脑对言语刺激的敏感度与个体发育成熟之间的关系,认为对语言习得起关键作用的两个生理临界点分别为5岁与青春期。Pinker则在他的著作《语言的本能》一书里谈到:“一个正常人的语言学习在6岁达到顶峰,随后这种能力逐渐减弱到青春期或稍迟一点,在此之后就很少有人能够掌握这门语言了。”[8]就语言习得的层面而言,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坚信人在青春期之后并非完全不能习得语言,而是学习某些语言的核心部分会遇到一定的困难。Scovel认为在语言的各个模块中,唯有发音存在关键期。生词、句法的学习与语音学习是完全不同的过程,前者无须牵连肌肉神经,也没有“生理上的物理运动”[9]。针对语音习得,Oyama特别提出了敏感期或最佳期的概念,指出语言习得的能力或敏感度是逐渐而非突然终结的[10]。
总之,由于研究对象的匮乏,对关键期假说的实验和论证逐渐转向二语习得,大量的有关二语习得关键期和年龄因素的研究及争论得以开展,而支持和反对的理据似乎各占半数。
三、二语习得框架下关键期假说的正反理据
二语习得是否存在关键期,是语言学习的一个核心问题。赞成派以实证研究为依据,坚信关键期假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被推翻,反对派则提出非生物基础的解释,认为认知发展、学习机会、语言环境等才是导致最终水平出现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1. 二语习得框架下关键期假说的正理据
Lenneberg不否认关键期之后个体有习得语言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在关键期外的二语学习不同于关键期的学习。语言功能的神经表征和不同层面由于开始学习二语的时间早晚有别,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青春期之后,二语学习者使用不同于一语习得的路径,语言习得的自然性快速消退,语言学习变成一个特意而为之的费力过程。
信奉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人最喜欢引用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12岁才移民到美国的他,说英语一直带着浓重的德语口音,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讲起英语来却不带一点德语口音,这被称为“基辛格效应”。在众多研究者看来,二语习得的关键期与语音习得息息相关。Asher & Garcia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发音最为本土化的移民到达年龄为1~6岁,其次是7~13岁的人,而13~19岁的人发音最差,似乎有一个生物变量决定着学习者发音的标准度[11]。Long通过实验发现,6岁之前开始学习二语的孩子,其语音一般都不带外国腔;6~12岁之间开始学习的孩子,有的有外国腔,有的则没有;而12岁之后才开始的学习者,一般都有外国腔[12]。
Johnson & Newport测试了46名在不同年龄移民到美国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的英语语法判断能力,结果表明年龄成为被试能否胜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即青春期前移民的被试的语法判断能力较强,且与到美国时的年龄成负相关,而青春期后移民美国的被试的语法判断能力较差,且与年龄因素不相关[13]。Patkwosky通过实证研究证实,15岁以下的学习者在句法方面能达到的二语水平比15岁以后才开始接触这门语言的学习者要高,年龄对二语学习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 二语习得框架下关键期假说的反理据
Hakuta认为,证明二语习得关键期的存在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首先,关键期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应该明确。其次,关键期结束后的二语习得水平应该和关键期内有着显著的差异,存在清晰的断层。再次,关键期内和关键期前后的语言行为应有质的差别。最后,关键期内的二语习得不应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14]。
对于第一个条件,研究者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与Lenneberg设定的2岁到青春期区间不同的是,Krashen认为儿童在5岁已完成了大脑的侧化,这意味着大脑侧化与青春期之后很难掌握二语的论点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Long认为二语习得的关键期发生在6岁之前;Johnson与Newport认为语言学习的衰退期始于7岁,大概到15岁结束。在Birdsong看来,青春期并非二语学习成功的临界点,对二语习得真正起作用的是“机遇窗口”(Window of Opportunity,简称WOP),它从出生一直延续到27.5岁,比人的生理成熟期延长了十几年的时间[15]。看来,即便关键期存在,始于何时、终于何时还尚无定论。
就第二个条件,Bialystok & Hakuta发现英语水平随着移民年龄的增长持续降低,在青春期之后并未出现断层现象。语言学习的生理机制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减弱,但这种变化是循序渐进的[16],不会像某些动物行为那样突然减少或消失。一方面,语音水平虽然与初次接触二语的年龄高度相关,但其关系还是一种渐进的线性关系,并没有出现在某个年龄明显转折、语言学习能力急剧下降的那种结果,这与关键期假说的观点显然相左。另一方面,成人在关键期后学习二语仍可达到本族语者的语言水平,普遍语法继续发挥作用,年龄因素不会对语法的学习有所影响。诸多研究发现,过了青春期之后才移居到美国的被试,他们的句法判断能力和当地人的水平相当,其英语水平有可能和母语为英语的人一样好。这也与关键期假说的第二个条件相违背,使得二语习得的关键期假说再次遭受挑战。
第三个条件是儿童与成人的二语习得应有质的差异问题。根据关键期假说,青春期过后,自然语言的学习机制被关闭,二语学习只好借助于其他的机制,因此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然而,各种研究表明,无论是从最终语言水平还是学习过程来看,儿童和成人的语言学习机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二语发展的过程中,儿童和成人既拥有普遍的习得启发机制,也使用相同的操作程序。语言学习能力在各个年龄段都会衰减,并不仅仅局限于青春期之后,其原因应归结为认知能力的改变,而不是与年龄相关的语言模块的变化。
至于第四个条件,许多学者都认为环境因素对二语习得至关重要,是决定语言发展最为关键的变量之一。儿童与成人语言方面的差异并不是语言习得机制本身造成的,而是语言机制的外部因素造成的。在进行早期二语教育的实验中不乏成功的例子,但据统计,这其中90%都与移民的二语学习有关,与双语制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这种成功与其说是早期教育的成果,还不如说是环境优势的产物。事实上,对二语和外语的区分正是建立在二语习得环境的基础之上的,而Krashen的习得与学习之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语言环境的划分。
四、关键期假说对于我国英语教学初始年龄的启示
Larsen-Freeman和Long曾经说过:“年龄问题对于二语习得研究理论的建立、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语言的教学法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能够证明年龄大的学习者与年龄小的学习者有所不同,那么成人继续获得普遍语法的说法将受到质疑。如果能够证明年龄小的学习者比年龄大的学习者学得好,那么早期外语教育就要大力提倡。”[17]Stern也提出:“在学习因素中,与外语学习相关的年龄问题一直是语言教学理论中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不管答案是什么,其对于学校体系中语言教学的组织都有深远的意义。”[18]
近年来,我国很多地区的外语教学呈低龄化趋势,小学一年级甚至幼儿园就开始设置英语课程,一些社会办学机构更是极力夸大早期学习英语的种种好处。受到如此大环境的影响,家长们纷纷听从外语学习越早越好的片面宣传,害怕自己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显然,这种外语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基础之上的,而实际上,当前低龄外语教学的理论依据不足、教学实践经验薄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存在此类关键期,它也只是影响外语学习的诸多因素之一,不应盲目夸大其作用。只有个体因素、语言因素和文化因素等共同作用时,才能决定外语学习的速度、效率和最终水准。
从个体因素看,外语学习的起点应放在母语习得基本完成之后,学习外语不能以牺牲或削弱母语为代价。一个人能达到的外语水平,基本上就是他的母语底线。对于一个学习者来说,如果没有母语,就无所谓外语;如果没有在母语环境中形成的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就不可能真正学好一门外语。杨雄里院士曾经指出:一般人的逻辑思维形成是通过母语学习,过早学习外语,极可能造成干扰,导致逻辑思维能力缺陷。在Piaget看来,处于前运算阶段(2~7岁)的儿童比较倾向于使用一种语言,如果此时再学习另外一种语言,他们往往会混淆这两种语言,无法正确表达思想,发生母语负迁移现象,这不仅会对儿童产生一定的挫败感,还会对他们未来的学习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这个时期的儿童如果不是生活在双语制的社会环境中或有绝对优良的师资及完备的教学设施作保障,最好使用一种语言。
就语言因素而言,二语习得与外语学习在语言环境、语言输入、语言学习目标和语言水平方面都有着明显的质与量的差别。所谓二语,一般是指在本国与母语享有同等地位甚至更高地位的一种语言,在学习所在地发挥除母语之外的通用语的社会作用,而外语一般是指在本国之外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在自己国家中学习的某种非本族语言。如此看来,英语在中国是一门纯粹的外语而非二语。正如Ellis所述,关键期假说对良好语言环境下的二语习得是非常适用的[19]。毫无疑问,移民美国的孩子在关键期内开始学习英语的话,他们所讲的英语会比成人好。这些儿童是在二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平日里可以随时随地与英语零距离接触;而反观我们中国的孩子,虽然学习英语的软硬件条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但他们毕竟不是身处目的语国家,欠缺一个真实、自然的语言学习环境,无法获取保质保量的语言输入。同时,外语教师的语言水平总体上无法与二语教师相提并论,同伴之间的语言输出更是少得可怜,严重阻碍了英语在学生头脑中的内化进程。此外,由于汉语和英语分属不同的语系,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困难要远远超过欧美学生。研究发现,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学习者学习英语时所犯的错误只有3%来自母语的干扰,而母语为汉语的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所犯的错误51%都来自母语的干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键期假说对我国的英语教学是否适用,还是一个未知数。
语言学习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习得的过程,没有合适的文化环境是不可能真正掌握一门外语的。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的差异是构成中国学生学好英语的另一大障碍,如果让一个孩子早早开始学习一门外语,很容易造成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混淆的状况。众所周知,语言是民族的标志和文化的载体,母语学习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儿童也在学习一种看待世界和适应社会的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会不知不觉地渗入到他们的思想之中,故而不用母语进行启蒙教育是荒唐可笑的。对此,Malmberg有着极为深刻的论述:“母语对于个人的文化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在早期教育中,个人首先被引入本民族的文化之中,然后被引入国际文化中,再后来被引入抽象世界中,所有这些教育活动必须在母语环境中进行……”[20]。应该说儿童过早学习英语会影响汉语的学习,不利于我国文化的传承。
我国教育部2001年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基本目标是:2001年秋季始,全国市、县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从2002年秋季起,乡镇所在地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起始年级一般为三年级。针对这一政策,国内众多学者进行了理论评述和实证研究,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刘润清等人认为,我国儿童学习英语的最佳年龄在9岁左右[21],因为这个时期的大脑仍保留着关键期的灵活性,并且认知能力已趋于成熟,同时对使用所学语言也不会感到拘束。然而,小学英语课程开设至今,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师资队伍良莠不齐、教材五花八门、教法流于形式等等。董燕萍针对1200名小学英语骨干教师开展的问卷调查表明,要在小学全面开设英语课程,师资培训是当务之急;不顾具体的师资条件,在小学盲目开课,不仅会造成巨大的教育浪费,而且还会挫伤相当一部分孩子今后学习英语的积极性[22]。胡明扬认为:“如果小学外语教学的师资问题解决不了,让一些自己的英语都没学好,发音全是中国腔的老师去教小学生,一旦养成习惯,将来再改就比登天还难,还不如不学。”[23]赵世开更是觉得“与其滥竽充数,还不如不开设这样误人子弟的课程”[24]。
在笔者看来,我国开展英语教学的初始年龄应该定在9~12岁,即在条件成熟的发达地区,可以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而对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依实际情况可以推迟到小学四五年级或六年级。根据关键期假说,这四年均处于外语学习的最佳年龄段,在生理、认知、情感、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且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或许,有人会质疑10岁以后再学外语,是否为时过晚。在桂诗春看来,11岁及之后的儿童的认知能力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元语言意识较为敏感,模仿力和长期记忆能力增强,而母语系统已经建立,不会受到很多干扰。认知能力的发展为语言能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内容”,语言能力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认知能力的发展[25]。而束定芳在综合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之后指出:“如果在12岁开始学习外语,这样的学习者只要在良好的语言环境和科学的教学方法下,最终也能达到或接近说母语的水平。”[26]可以这么说,9~12岁开始学习英语的儿童,无论语音水平还是最终水平都可以达到相当的高度,而且语言能力比低龄儿童更耐磨蚀。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一语习得框架下的关键期假说,得到的肯定似乎超过了否定的声音,但苦于研究对象的匮乏,无法获取有说服力的充分理据,而传统二语习得框架下的年龄研究往往拘泥于关键期生物机制的束缚,忽视了认知、情感、心理、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在笔者看来,学习二语的初始年龄只是决定语言习得成功与否的因素之一,把不同年龄阶段二语习得能力的差异简单地归因于神经生物机制有失公允,势必会影响我们对于外语习得本质的认识。
我国的英语教学已经出现了“越早越好”的发展态势,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绝不能因为低龄儿童在习得外语语音方面的相对优势,而忽视了过早学习外语对儿童母语习得和逻辑思维发展方面的负面作用。在我国当前小学外语师资和教育经费相对紧缺的情况下,从哪个年级开设英语课程一定要将必要性和可行性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关键期假说对于英语教学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Lorenz K Z. The Companion in the Bird's World[J]. The Auk, 1937(3):245-273.
[2] Gould J L, Marler P. Learning by Instinct[J]. Scientific American, 1987,256(1):156-181.
[3] Penfield W, Roberts L. Speech and Brain Mechanism[M]. New York: Atheneum Press, 1959:1.
[4] Lenneberg 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M]. New York: Wiley and Sons, 1967:12-13.
[5] 王初明. 应用心理语言学[M]. 长沙:湖南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134.
[6] 胡壮麟. Linguistics: A Course Book[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87.
[7] Grimshaw G M, Adelstein A, Bryden M P, et al.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Adolescence: Evidence for a Critical Period for Verbal Language Development[J]. Brain and Language, 1998(3):237-255.
[8] Pinker S. The Language Instinct[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4:133.
[9] Scovel T. A Time to Speak a Psycho-linguistic Inquiry into the Critical Period for Human Speech[M].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88:56.
[10] Oyama S. A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 Nonnative Phonological System[J]. Journal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1976(3):261-283.
[11] Asher J J, Garcia R. The Optimal Age 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J]. Modern Language, 1969,53(5):334-41.
[12] Long M H. Maturational Constraints on Language Development[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0(12):251-285.
[13] Johnson J, Newport E. Critical Period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Maturational State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89,21(1):21-45.
[14] Hakuta K. A Critical Period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9:212.
[15] Birdsong D. Ag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A Selective Overview[J]. Language Learning, 2006,56(S1):9-49.
[16] Bialystok E, Hakuta K. Confounded Age: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Factors in Age Differences fo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Birdsong 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9:79.
[17] 埃利斯. 第二语言习得概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485.
[18] Stern H H.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367.
[19] Ellis R.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295.
[20] Malmberg G. Extreme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Between Related Individuals of Gyrodactylus Pungitii[J]. Systematic Parasitology, 1970,32(3):137-140.
[21] 刘润清,吴一安. 中国英语教育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21.
[22] 董燕萍. 从广东省小学英语教育现状看“外语要从小学起”的问题[J]. 现代外语, 2003(1):40-47.
[23] 胡明扬. 外语学习和教学往事谈[J]. 外国语, 2002(5):2-9.
[24] 赵世开. 学习外语的漫长道路[J]. 外国语, 2002(5):10-15.
[25] 桂诗春. 心理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178.
[26] 束定芳. 我看外语教学改革[J]. 国外外语教学, 2001(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