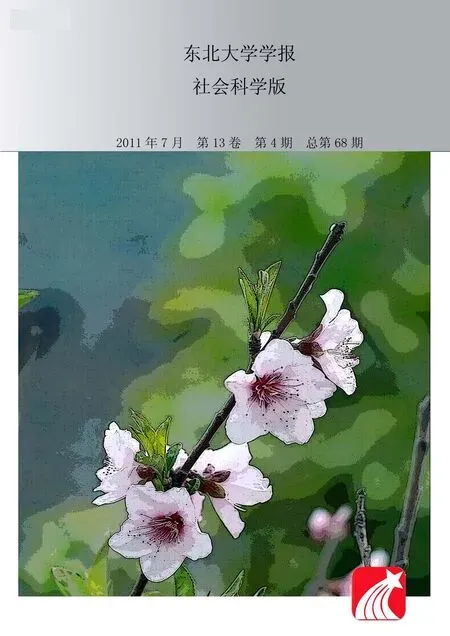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的“不辩”之辩
沈宗艳,胡玉海
(1.“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辽宁沈阳 110044;2.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沈阳 110036)
在张学良不长的政治生涯中,经历数次重大历史转折,而且每一次转折都与近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作为历史经历者和创造者,张学良在这些转折中都扮演主要角色。作为主角他曾收获人生辉煌——人们赞美他是千古功臣;他也遭受奇耻大辱——人们辱骂他是“不抵抗”将军。对前者,张学良平静接受;对后者,他也曾说:“用不着跟他辩,毁誉由人,说骂由你,我不在乎”[1]344。
但我们在他的口述历史中发现,在诸多历史大事件中,他说的最多的是九一八事变,而且重点都是讲有关“不抵抗”的问题。
一、 反省自我与为己辩护
九一八事变,对张学良身心的影响巨大而又久远,这是他永远的痛,是他人生中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这种永远的痛和奇耻大辱,当然是日本侵略造成的,也是他张学良个人造成的。因为是他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在事变爆发的次日,他对《大公报》记者明言:“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1931年9月19日下午和20日晚,张学良两次对外报记者谈话称:“昨夜接沈电,惊悉事变,已电饬沈绝对不抵抗”。“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即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
当时,张学良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实行力避冲突的不抵抗政策,一方面符合中央“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同时也适合中日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张学良强调中国军民不准备抵抗和没有抵抗,既是事发当时的事实,也是说给国际社会听的,以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希望国际社会干预,希望国联出面制裁。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用电话向参谋长荣臻发出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后来张学良在回忆这一问题时说:“除对日本判断错误外,同时迷信条约神圣,错估国联的制裁力量。——当时我是认为国际可以解决争端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的警告。”[2]125
而事实并非如此,经国联行政院常任理事和非常任理事14名代表投票表决,13票赞成,只有日本1票反对,决议未能通过。1931年11月16日,国联还在开会的同时,日本继续进兵,并占领了齐齐哈尔。直到这时,张学良开始怀疑国联“是否自认其无能”[3]。在认识到国联和国际社会不能阻止日军侵略的同时,张学良也认识到当初不抵抗命令铸成的大错。12月15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请褫副司令职务电”,“良守土无状,适构斯变,诚万死不足以蔽辜”。“学良缪绾军符,遭逢国难。”[4]324
热河抗战失败后,张学良再次向国民政府请辞。从缪绾军符,遭逢国难,到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说明张学良已开始反省自我,承认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仅是错的,而且于国家和民族是有罪的。
当时,张学良虽然承认九一八事变时,缪绾军符致使国难,同时也认为这一责任不能完全由他一人承担。他不能不为自己辩解,以解精神上的压力。在与外报记者谈到热河抗战时说:“救国非一人之力所能为,热事亦然。”1933年2月4日,胡汉民致函张学良称:“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云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张学良所说该为不抵抗“负最终之责任者”另有其人。不久,张学良被迫下野准备出洋,胡汉民复去函劝慰:“兄典军东北,久历岁时,今为人所乘,有怀莫白……。是非所在,天下不乏同情”。矛头所及,不言而喻。
此后数年间,张氏透过各种渠道,屡番在私下或公开场合为自己、为东北军曲加辩解。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告诉杨虎城:“蒋在九一八事变时把我害得好苦,我当了替罪的羔羊,这是有证据的,终有一日我会将此事表白于天下”。杨则安慰说:“大家不光原谅你挨了暗砖(意即张学良受了蒋介石的暗算),还会一致拥护你哩。”[5]张学良多次对部下将士讲过:“东北的失陷有着复杂原因,其责任不能完全由东北军担负;政府也犯了‘依赖国联’、‘希求事态不扩大’的两个大错误”[6],甚至公开对群众说过:“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7]。
说政府有“两大错误”和“上级不许我打”,这是事实还是张学良在为自己辩解?两者兼具,从事实上讲,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于1931年7月23日在江西“剿共”前线发表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宣言,事变后,有依赖国联解决中日争端的指示。9月23日,在《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中,明确提出,“深信此次事件,苟经一公平之调查,国联本其应有之职责,必能与我以充分之公道,乃合理之援救”。要求国人“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8]。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员大会上演说也强调:“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判断”[9]。张学良以这些事实为自己的“不抵抗”政策进行辩解,也能自圆其说,因为一位边疆大吏岂能不按中央大政方针行事。从另一方面看,张学良本人也必须承担责任。
张学良作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兼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当时是负责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又是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具有很大的自主权限,何况蒋介石曾于热河抗战前也明确提出:“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请吾兄负其全责”[4]481。如张学良能以东北之力抵抗日本之侵略,国民党中央及蒋介石是乐观其成的。总之,作为北方最高军政长官对东北沦陷,他也是难辞其咎。国民政府免其职,实际上就是对张学良丢失东北的惩处。
在国人痛斥“不抵抗”政策时,特别是在张学良下野后,也有人认为他是在替蒋介石背了黑锅,帮他进行辩解。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均曾言及,“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和“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所阻”等,隐含张蒙受莫白之冤。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政论家王芸生,在《国闻周报》上也发表一篇言论,张学良到晚年还记得这段话:“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但是如今我们,一提到不抵抗主义,可就会联想到张学良,张学良是这个主义的实行者。……等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觉着‘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那时候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就是换作他人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样不抵抗。以过去的济南事件为证,凡是对日本武装挑衅行为,不都是退让吗”。张学良说:“他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2]123
由此我们看到,张学良在日本拒绝执行国联决议案后,一面开始反省自我缪绾军符致使国难;一面也在为己进行辩护,认为自己当了替罪的羔羊。
二、 辩驳细节与还原历史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既强烈而又深远。正因如此,这一事件也成了近代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关于九一八不抵抗问题的原委,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
能够说明张学良当了替罪羊的最有力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所谓的“铣电”。“铣电”是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主要证据之一。据张学良机要秘书洪钫1960年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10]。此后,这段资料就成为张学良执行不抵抗命令的主要依据。“铣电”属于个人回忆史料,其真实性、可靠性历来受人质疑。海峡两岸及旅美等多位学者曾对此考证并提出质疑,胡志伟和李永中更撰文细加考辨,认定始终无法证实“铣电”的存在,当属无中生有、以讹传讹。而与此相反,窦应泰在《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中,却详细记述了1996年10月21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荻书斋”开馆典礼上,展柜上赫然便有“铣电”原件,内容与洪钫所述一字不差,这说明,这是仍须进一步考证的问题。
二是石家庄密谈。石家庄密谈是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主要证据之二。据何柱国回忆称:“张学良于1931年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约张于1931年9月12日在石家庄与蒋会晤。”何柱国说:“那时我驻防在石家庄,便担任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张学良下的不准抵抗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11]
三是张氏夫妇秘藏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有很多材料说,张学良曾长期贴身带着个小皮包,里面收藏着蒋介石不准抵抗的电报。还有的说张学良将蒋介石不抵抗的手谕交由于凤至收藏在美国的保险箱里,讲得神乎其神。
上述这三条史料如若属实,可以证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上述资料均出自于个人回忆或传说,因此关于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问题,学界仍是争议纷纭。张学良恢复讲话自由后,人们都想从他口中得到有关重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有关九一八不抵抗的原委。
在张子丙、张子宇访问张学良时,问及是否有“铣电”,张学良只是含糊地说:“大概,我记不住了,我想也许有这个电报,因为那时候要冲突了,知道日本要出事”。张学良晚年,当多位记者在不同场合问及“铣电”及九一八不抵抗命令问题时,他的回答前后一致,综合张学良前后的说法,确可以得出“铣电”不存在的结论。1990年8月,当日本NHK记者问道:“当时中央,即蒋介石或国民政府对您有指示,命令您不要进行无谓的抵抗呢?还是您自己决定的呢”。张回答说:“这件事情,现在有好多人替我辨别,说是当时中央怎么样。当时中央还没有那么厉害,……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不能将责任推到中央去。”[12]1991年5月28日,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东方新闻》主编李勇等走访张学良时,问及蒋介石是否下手谕令张不抵抗,张学良立刻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13]。张学良对唐德刚、郭冠英也讲过这一观点:“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不是的,不是的!这个绝对不是的,不是事实。”[1]274一连四个“不是”,由此可见,他对此事不容争辩的认定。
关于石家庄密谈之事,也只有何柱国一人的回忆资料,究竟有无,人们当然期待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证实。在张子宇姊妹对此进行询问时,似乎没有引起张学良的任何记忆。这样,考证张学良和蒋介石两人当日行踪,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依据张友坤等人编著的《张学良年谱》,有石家庄会晤记载;而根据胡志伟《澄清铣电真伪,促进两岸统一》和李永中《由“不抵抗命令”谈“铣电”及“石家庄会谈”真伪之说》两文的考证,蒋介石在1931年9月12日全天的行止、作为,并无石家庄之行,何氏回忆显然纯属杜撰。由此表明,石家庄会晤有无仍须进一步考证。
关于张氏夫妇秘藏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一事,张学良明确地否定。他说:“有人说蒋公打电报给我,我还拿一个皮包,把电报每天带在身上?瞎说、瞎说!没有这个事情,瞎说,外头瞎说!”[1]279
这样,关于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的三点重要依据,基本上均被张学良否定。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始终强调“不抵抗”的命令是他下达的,与中央无关,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上述三点是否存在的价值。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反复强调,九一八时期,对中央和蒋公凡有请示,则皆答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这说明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是奉了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而不是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命令。这些细节的澄清,对还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三、 “不抵抗”与“判断错误”之关系
在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中,我们看到他一面肯定地说,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是他下的,与中央和蒋介石无关;一面又坚决否认自己是不抵抗,而只承认是“判断错误”。这看似绝对矛盾的理论,就是张学良的“不辩”之辩,这种“不辩”之辩,对张学良来说十分重要,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从一般意义上讲,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就是不抵抗,这是必然的逻辑关系。张学良试图用“判断错误”的罪名来替换“不抵抗”的罪名,那么是否成立呢?
一是没有把日本的事情看明白。张学良不止一次地谈到,“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首先,日本的军人想这样做,日本政府会控制,因为他这样做违犯了国际条约,惹起了国际问题。其次,这样做于他本身也是不利的,所以他不会这样做”[2]77-78。对日本不可能这样做的判断,与其事变前的主张不相一致,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事既北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4]124。前后矛盾的说法,显然是在为判断错误寻求理论背景。
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错误。张学良认为日本的军事行动只是挑衅行为。为了支撑这一观点,他对访者说:“咱们过去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2]276。这一说法,如按当时中日关系的现状讲,实行这一原则是正确的;而他已看到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又如何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
三是对“条约神圣”和国联制裁能力的错估。事变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从蒋介石到张学良形成了共识,那就是依靠国联和国际社会解决中日争端。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说,在对日本方面错误判断的同时,也“迷信条约神圣,错估国联的制裁力量”。“当时我是认为国际可以解决争端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的警告。”[2]125这一错误判断,导致九一八时下达不抵抗命令。但当日本拒绝执行国联决议案后,应及时调整不抵抗政策。这正如《国闻周报》所批评的那样,张学良的“罪过不在九一八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2]124。
张学良用以上三个层面的“错误判断”,来替换“不抵抗”是不能成立的。从这两个词语关系上看是前后的逻辑关系,而不是平列的对等关系。一般规律是先有对客观事物的判断,才有最后的决策。是张学良对当时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导致他实行“不抵抗”的政策。
以上这三方面的错误判断,对张学良实行不抵抗具有重要关联,但导致张学良实行不抵抗的原因,有更重要的三点,这是他实行不抵抗的根本原因,其中有的也隐含于张学良口述历史之中。
一是敌强我弱的判断。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不止一次地谈到日本军队,认为日军很强。他说:“那人家训练好,装备好。”“日本厉害,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就算剩一个人也打,这是数量上不能比的。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工兵去破坏俄军的铁丝网,他们身上带着炸药,每个兵躺到铁丝网那,这样把铁丝网炸开了,他们真有军人的精神。”张学良在事变当天夜间,曾对将领们分析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14]。
二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影响。蒋介石于1931年7月,在南昌行营发表一个通电,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声称:“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5]。这个通电是作为国策发表的,张学良的对日主张不能不按这一方针去做。事变发生后,张请示南京政府,答复均是“相机处理”等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这让张学良“触目伤心,心灰意冷”。
三是中东路事件的影响。中东路战争是由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支持促成的。可战争打起来后,既未得到军事、资金的支援,也未得到外交上的支持。所以王芸生在评论中说:“在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张学良认为王芸生的评论,说到了他“内心的隐情”[2]123-125。
综上所述,从张学良的“不辩”之辩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下达不抵抗命令和主观上不想抵抗是不同的,所以张学良只承认“判断错误”,而不承认“不抵抗”;三点“判断错误”虽然不能完全成立,但综合当事人当时所处环境及个人身心状况的判断,与其不抵抗尤其是继续不抵抗,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后三点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但他在口述历史中只是隐隐谈及,而不与“不抵抗”政策相联系,这正是张学良的高明之处。一方面这既符合历史事实,同时又保护了两个重要的当事人。这为后人如何看待和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一个永久性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唐德刚. 张学良口述历史[M].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2] 张学良. 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M]. 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3] 张学良. 关于国联的宣言[N]. 大公报, 1931-11-24.
[4] 毕万闻. 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4部[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5] 政协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回忆杨虎城将军[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196.
[6] 张主任委员讲演“中国出路唯有抗日”[N]. 解放日报, 1937-01-05.
[7] 张德良,周毅. 东北军史[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210.
[8] 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N]. 世界日报, 1931-09-24.
[9] 蒋介石在南京市党员大会之演说[N]. 华北日报, 1931-09-23.
[10] 洪钫. 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北京:中华书局, 1960:24.
[11] 何柱国. 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 北京:中华书局, 1981:66.
[12] 管宁,张友坤. 张学良开口说话[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78.
[13] 李明扬.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N]. 香港信报, 2001-10-16.
[14] 周毅,张友坤,张忠发. 张学良文集:上卷[M]. 香港: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6.
[15] 张其昀.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卷[M]. 台北: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4:3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