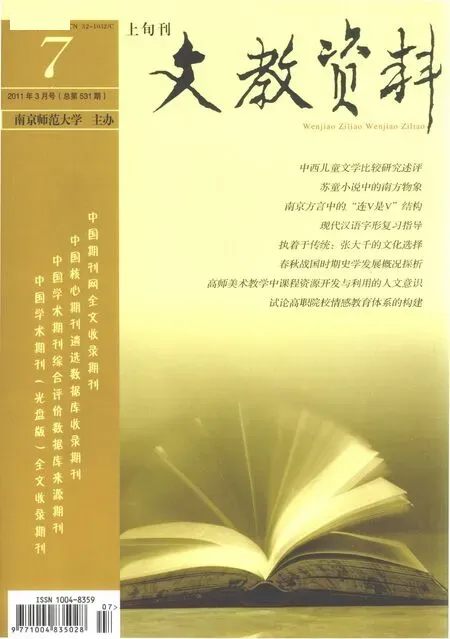论伽氏解释学对翻译的影响
龙珣
(合肥师范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1.引言
传统翻译理论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其语言基础的,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与客观世界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在此理论的指导下的翻译研究是以一种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以认识论哲学为哲学基础,以工具理性为理性基础的译学范式 (吕俊,2007:61)。在这种译学范式下,作者用语言来揭示客观世界,这是编码的过程,而译者要想了解作者在原文中反映的客观世界,就必须通过文本的阅读“忠实”地对作者在语言中所使用的一系列符号进行解析,也就是所谓的解码。语言成了一种纯粹的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镜像工具。人们追求语言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和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唯一性和精确性。只要分析方法得当,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作者想要表达的“唯一正确”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人们也强调作者的原意。好像谁发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谁就功德圆满。这实际上是作者的独白话语(吕俊,2001:115)。这一思维方式实际上过于强调作者是创造的主体,是主宰文本意义的最高权威,从而把译者置于一种极端被动、从属的地位,译者必须紧紧跟在文本和作者的后面,不能违背作者的任何意思。17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德莱顿曾经把译者比作“奴隶”,就是这一思想的形象反映。许钧说:“以原作者为中心,文本决定一切,把语言当作纯粹的表达工具,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作者是主人,译者只能是仆人,只能是一个隐形人,他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不被承认,也不被鼓励的。消隐自己的个性,保持纯粹的客观,忠实地传达一切,这些近乎金科玉律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阻隔译者主体性的一道观念屏障。”(许钧,2003:10)
总之,译者在传统译论中的地位毫无疑问是卑微的。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论转向将认识论的主体哲学转向了语言论的解释哲学,从传统的被动媒介式的语言工具论转向了本体论存在论的语言论。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阐释学使人文科学摆脱了科学主义的长期统治;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被消解,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从而促成了由文本中心论转向读者中心论。伽氏解释学通过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及自然科学方法局限性的批判,指出哲学的使命就在于挽救现代人的精神及艺术精神危机,重新探讨人文科学的方法论 (董务刚,2002:115)。正是在这些方面,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找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但哈贝马斯认为,伽氏解释学过于强调传统的重要性,却缺乏对传统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哈贝马斯认为,解释学意识即是自我反思的过程及意义,批判和反思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步骤和前提。因此,哈贝马斯在接受伽达默尔一些正确的解释学观点的同时,也对伽达默尔展开了批判。本文从他们两人思想的不同之处对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加以讨论。
2.伽氏解释学中的“视域融合”和“效果史”
2.1 关于“视域融合”下的译者地位彰显。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解释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盛行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是一种探求意义理解和揭示的理论。伽达默尔在继承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深化了对理解的认识。他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但在伽达默尔眼里,这种偏见是“合法的”。他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解的意义,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并声称:“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实际上,我的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Gadamer,1975:262)
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因此两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域(Horizon)。视域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中总含有作者原作的视域,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域。两种视域之间存在着差距,而这种差距是任何理解者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域交融在一起,从而达到“视域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域,达到一个全新的视域(王岳川,1999:210)。伽达默尔把“视域融合”视作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中介,视域融合后产生的新视域一方面包括了现在视域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历史视域的注入与更新。所以伽达默尔认为视域融合是“对话的充分实现”,在这种对话中表达出来的东西不仅是属于解释者的,也不仅是属于被解释的对象的,而是一种共有(吕俊,2007:67)。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即在翻译中,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域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谢天振,2000:55)。我们可以看出,在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概念下,文本的意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动态生成物,是多元的、无限的、不断更新的。正是这种“多元的、无限的和不断更新”的文本意义,使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只能是一个逐步接近其审美本质的过程。译者作为一个阐释者,只能尽最大可能地接近原著,但是他们不可能提供一个和原著完全对等的译本,因为译者不可能像传统翻译理论要求的那样,完全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异己的视域。就文学翻译而言,译者的主体性在“视域融合”的概念下显得尤为突出。许渊冲说,科学研究是1+1=2;3-2=1;艺术研究的是1+1=3;3-2=2;因为文学翻译不单是译词,还要译意、译味。所以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过程,也不会是一种简单的文本间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的叛逆”不可避免。
视域融合的过程不会是一种平缓的过程,而是两种视域激烈碰撞、冲突和排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熟悉的世界带入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所以译者视域和作者视域也不可避免地会相互碰撞和排斥,而这种碰撞和排斥的结果就是译者必然要对原文文化进行一定的过滤,在这个过滤的过程中,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策略,还是取决于译者的定夺。而这种定夺的过程,同样是译者主体性地位彰显的明证。如Auther Cooper用“Shy the Nymph”来替代《诗经》“关雎”中的“窈窕淑女”。Nymph是古希腊神话里的“仙女”,它使《关雎》蒙上了一层西方美丽的外衣。一位“君子好逑”的中国古代少女,一下变成了西方的仙女。而在近代翻译中,在文学形式融合过程中出现的中西视域相碰撞、相过滤的现象也十分普通。如拜伦的《致雅典少女》,经苏曼殊转译,就成了中国式的“桑间濮上”之情。而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Edward Fitzgerald翻译的中古波斯诗人海亚姆的《鲁拜集》更是文化过滤的产物(Lefevere,1992:32),其译文把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波斯诗人脱胎换骨地过滤成了一个厌世的英国天才。
总之,在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概念下,译者跳出了传统译论为自己设置的桎梏,他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和自己的视域,来进行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这与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完全抛弃自己固有的世界、客观被动地探求作者本意和文本意义的做法完全不同。作者不再是原文意义的唯一操纵者,而译者也不用再亦步亦趋如“奴隶”般紧跟在作者身后。在“视域融合”思想的指引下,文本意义是由译者与作者对话产生的,从而消解了传统译论中作者的“绝对中心”地位,由此,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彰显无疑。
2.2 伽氏解释学中的“效果史”。
从上面对“视域融合”概念的阐述上,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注意到伽达默尔不仅强调主体间的对话性,而且把时间(历史)”的概念引入意义的形成之中。他认为人置身于历史之中,这本身就包括了对历史的理解,理解是离不开历史的,正当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出历史的有效性来,伽达默尔把这种历史称为“效果史”(吕俊,2007:67)。在效果历史中理解作品,这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艺术作品是包含其效果历史的作品。”(Gadamer,1975:264)在伽达默尔看来,文本是开放性的,它的意义也是永远不可穷尽的,因此它是超越它所产生于的那个年代的,这就为不同时代的人们理解它提供了可能性。艺术作品如果只是作为一种绝对存在时,那它也就不可能被任何理解方式所接受。效果历史原则强调从艺术作品的效果历史中理解作品,这就把历史与现在密切相连,从而充分肯定了古代文本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伽达默尔关于“效果史”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认识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世纪中期的西方文艺批评曾经热衷于“理想范本”的追求,要求批评家在文本面前忘却自己,排除主观感受,把回归到作家的原始意图看作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其实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抛弃自己固有的主观感受,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作者那个陌生的世界。而且,由于理解的历史性,文本的意义也永远不可能在某一点上被固定住,事实上,它是永远处于向未来生成的无限可能性之中。文本是一种开放性结构,对其真正意义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文本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中的。
2.3 从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思想批判地继承看伽氏解释学的不足之处。
伽达默尔继承并深化了海德格尔关于理解的 “前结构”思想,认为:“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洪汉鼎,1999:355)这是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处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而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社会环境则让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自己合法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时代的烙印,是任何人无法消除的。哈贝马斯并不否认传统和成见在理解和解释过程中所承担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他认为伽达默尔过于倚重传统。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用传统来证明成见的权利的这种成见,否定了反思的力量,然而,后者在能拒绝传统的主张中证明了自己……”(王岳川,1999:272)
根据解释学的理论,译者都是带着一种合法的偏见——“前理解”而进入理解的过程,而这种“前理解”是受历史文化传统制约的,因此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也必然有着自身所接受的文化传统的色彩,而这种色彩也必然会反映在他的译文中,也因此形成他特有的翻译风格。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哲学解释学的理解固然离不开传统背景,主体离不开前理解,但作为理解者本身,他是可以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的,通过这种反思和批判,从而使被歪曲的交往关系得到改善,趋于合理。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可能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很可能来源于无效交往或伪交往。”(徐友渔、周国平、陈嘉映、尚杰,1996:193)那么以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去反观翻译,我们会认识到,当译者带着“前理解”去进行文本翻译活动时,由于在翻译之前没有对自身所接受的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而将由传统作用而形成的特有风格带入到译文中,从而导致译文在艺术特征、情趣甚至内容方面都会与原文产生一定的偏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译者曲解了原文。这样的话,译者与作者之间的交往,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对话,就是不平等的,而这样的交往活动,按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是无效的、不真实的。
3.结语
伽氏解释学提出的“视域融合”概念对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否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规则设定意义的原则,他把效果史引入到对文本的理解,也挑战了人们仅关注共时性而悬置了历时性的倾向。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会有这样的体会:无论译者多努力忘却自身,进入原文文本,力求去领会原文作者的意图,但是还是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所熟悉的价值观点带入源语世界。但是这并不代表作者的原意是不可认知的。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创作文本,必然会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好恶情感和审美情趣反映到文本中,这是确定的,但是随着历史性的演变,文本的意义会发生变化,有些意义会被遮蔽,而有些意义则得到彰显,所以,在艺术的文本中作者的本意有可认知的一面,也有难以全部认知的一面 (董务刚,2002:117)。因此,我们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应将源语作者主体视为可认知的对象,从文本了解作者,认识作者,甚至变成作者,达成与作者的共识,就像演员深入角色内心深处去体验任务内心的思想感受,力求准确生动地再现角色的精神风貌一样。
[1]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2]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3]许均.“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4]董务刚.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研究——兼谈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J].四川外国语学报,2002,(6).
[5]Gadamer,H.G.Truth and Method[M].New York:The ContinumPublishingCo.,1975.
[6]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7]谢天振.作者本意与文本本意[J].外国语,2000,(3).
[8]L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Source Book[C].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2.
[9]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0]徐友渔,周国平,陈嘉映,尚杰.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