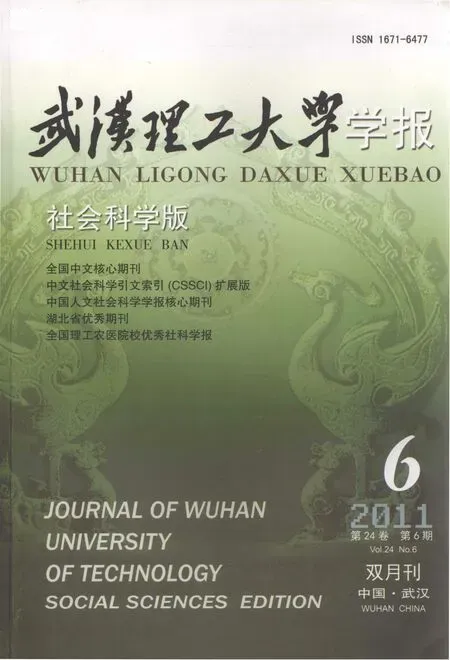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
汪树东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当代文学发生发展于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浪潮中,对现代文明的憧憬一直是不言自明的正面主题,但当现代文明的负面因素渐渐显露,批判也就接踵而至。当然,现代文明的负面因素是多重的,例如对传统文明的破坏,对道德伦理的摧毁,对大自然全面的摧残等等,因此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立场也颇不一样,在生态意识、生态文明立场上来考察现代文明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全面破坏,以及对人性和文明发展方向的颇成问题的设定,具有根本的意义。本文要考察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的发展状况,批判的内容和特点,以及意义和局限。
一、中国当代文学生态批判发展阶段
对生态意识的认识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都是渐进的过程,虽然到了21世纪初,部分作家已经确立了鲜明的生态意识,以之为根据的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意识也渐趋成熟,但发展过程艰难曲折。
(一)沉寂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主宰了中国大陆。这种意识形态对发展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方向提出了严厉批判,但它对发展现代文明本身,尤其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以全面征服与改造大自然以及极大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为主旨的现代文明的基本方向,非但不反对,反而推崇备至。因此,此阶段的中国文学对现代化没有反思批判意识,作家理所当然地把现代文明作为正面的理想追寻,把现代文明作为不加反思的价值标准贯彻至作品中。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都是写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著名篇章,它们尽情展示了农村对现代文明的无限向往之情。《创业史》中代表现代文明的韩技术员给梁生宝互助组送来技术支持,而《山乡巨变》的结尾处,是城市工人给清溪乡高级社送来各种现代化农具和化肥。他们需要改造生活的资本,就会毫不犹豫地像梁生宝那样到终南山去割竹子,大自然是人民生活予取予夺的资源库。摆脱贫困才是头等大事,运用现代文明方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就是最高律令。当人民从宿命论中摆脱出来,发现了可以征服与改造大自然的现代文明,强力意志也就极度膨胀起来。此时的新民歌《我来了》就写道:“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1]159大自然的神性被彻底剥夺,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声也成空谷足音,被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人自视为神,堪天役地,为所欲为。即使现代文明的某些负面因素已经开始呈现,但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负面的,而是由此听到现代文明的凯歌高奏。此时期四川开县新民歌《青烟直上九重霄》唱道:“炼铁炉,高又高,/青烟直上九重霄,/玉皇高叫受不住,/众神熏得眼泪抛。”[1]234空气污染在一心一意想着在钢产量上赶英超美的人民心中并不是空气污染,而是一种审美对象!天上众神被青烟熏得受不了,那只是人民力量的强大。这种感受中,生态意识无法呈现,生态批判亦无可能。
(二)萌发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
虽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主潮还是追求现代化,而且大部分作家还是把现代化当作不言自明的价值理想,例如,就像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中那样,把乡村小姑娘对山外城市文明的向往当作人性中最动人的情愫,但对现代文明的复杂态度也偶有流露。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轰动当年,高加林在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的两难抉择,就是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两难抉择,这种两难之所以会形成,就是因为作者看到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流风所及,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的人家》、《小月前本》、《腊月正月》等都展示出对传统道德和现代文明的两难选择。虽说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还无法上升到理性层次,但是作家对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复杂性的感受和体验本身就蕴含着对现代文明批判的可能性。生态批判首先在那些知青作家笔下展开了,如孔捷生的小说《大林莽》就对那些肆意征服与改造大自然的现代观念提出挑战;阿城的《树王》也从民间朴素的生态意识立场上批判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极度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从而对现代文明取一种怀疑态度;至于李杭育的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则批判了现代人对自然生命的竭泽而渔式的掠夺,表达了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疑惧之情。
(三)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现代化浪潮突飞猛进,而文学界却出现了文化寻根浪潮,对现代化的态度渐显暧昧。尤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人与大自然较为亲和的关系全面断裂,敏感的作家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终于全面开始。高行健的实验话剧《野人》演出于1985年,其中对牺牲大自然以追求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尖锐批判。更为振聋发聩的声音来自报告文学,如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对中国的土地危机、水危机、森林危机等大加关注,批判锋芒直指现代文明引发的人口爆炸及欲望泛滥等病症。此外,张炜的小说《三想》通过人、老白果树、母狼三者的随想而拼接出现代文明泛滥、自然生命丧亡的恐怖场景,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对城市文明的鄙弃和对自然野性的崇尚,老鬼的小说《血色黄昏》对当年下放内蒙古的知青在草原上垦荒造成的可怕生态后果的反思,贾平凹的小说《废都》对现代城市文明堕落的描述和对山野生活的向往,等等,都表明了部分作家已经具备对现代文明进行生态批判的理性意识。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发展至此,生态文学的蔚成大观也就不再遥远了。
(四)高潮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1992年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现代化发展驶入全球化快车道,发展至今,虽说中国经济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但付出的代价,尤其是生态代价,也极其高昂。作家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也就是随之全面展开,趋于高潮。笔者以为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陈桂棣的生态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发表于1995年,此文对淮河水污染的全面报告促人警醒,让国人全面了解到发展现代文明的惨重代价。另一个是1999年10月由国内外的许多知名学者和作家参加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召开,随后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由李少君执笔的座谈会纪要《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该文对我国乃至全球完全不顾生态问题奉行的发展主义方向提出了批判,措辞激烈,思辨深入,感情充沛,影响深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进入高潮期,参与的作家多,作品亦多。韩少功、徐刚、张炜、哲夫、于坚、迟子建、蒋子丹、叶广芩、贾平凹、姜戎、雪漠、陈应松、胡发云、张抗抗等作家都开始自觉地以生态意识为皈依,对现代文明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彻底告别了曾经想当然地把现代文明作为价值理想的幼稚时期,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获得了深化,尤其是对生态意识的追寻和建立,使他们的文学具有面向未来的启示意义。像韩少功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张炜的散文《融入野地》、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陈应松的小说《豹子最后的舞蹈》、姜戎的小说《狼图腾》等堪称生态批判高潮期的代表作。
二、中国当代文学生态批判的主要内容
按照未来学家托夫勒的概括,现代文明有六种基本特点: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2]。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批判
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文明的顽固内核,它总是不证自明地把人类视为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存在,把其他自然生命仅作为工具对待。毕飞宇在散文《人类的动物园》中曾说:“我读过几本关于动物的书。在许多这样的科学读物里,都有动物‘作用’的介绍。而这样的‘作用’又是以人的需求为前提的。比如说,一提起犀牛,便是:肉可食,皮可制革,角坚硬,可以入药,有强心、清热、解毒、止血之功效。……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每一员对动物世界的习惯心态都是帝王式的。为我所领、为我所用。”[3]作者言语中对现代人的自以为是的嘲讽之意显而易见。许多作家通过展示别种自然生命的内在灵性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叶广芩的小说《黑鱼千岁》中,那条黑鱼为了给同伴报仇先是装死,最后不惜牺牲生命。郭雪波的小说《大漠狼孩》中的母狼对狼孩的情义也非常人所能比。对动物生命内在灵性的揭示自然使人类中心主义不攻自破。其次,许多作家通过展示人与自然生命之间的生态关联来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贾平凹小说《怀念狼》中狼被猎杀后,人也疾病缠身。雪漠小说《狼祸》中,当人猎杀了狐狸、狼,土地的沙漠化就急剧恶化,人也就丧失了立身之基;此时,人类中心主义的幻想也就不攻自破。
(二)对现代文明的欲望化的生态批判
在人类所有的古典文明中,对待人的物质欲望全都是采取节制甚至摒弃的谨慎态度,从来没有哪类古典文明会论证人的物质欲望的合法性。然而,现代文明是例外,它不但论证了人的世俗欲望满足的合法性,而且把欲望视为文明的发展动力,更是让人的情感、意志和精神都为人的欲望服务,让所有科学技术、工商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乃至学术研究等都为了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而转动。但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无限的欲望指向有限的大自然时,大自然的溃败无法逃避。因此,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欲望化的生态批判也就如火如荼。李存葆在散文《鲸殇》中说:“现代工业文明使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扩张了人的各种欲望。人类的欲望无边和地球的资源有限互为抵牾,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构成永恒的差距。”[4]雪漠小说《狼祸》中,那些放牧者在生态条件本就极为脆弱的沙漠边缘无限制地增加载畜量,也是被获取财富的欲望逼得疯狂的表现,作者的批判自然严厉。
(三)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生态批判
助长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欲望化倾向的根本动力无疑是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采取的是机械论世界观,在它眼中,世界是可以无限分析、任意重组的同质化世界。它并不重视大自然的生态整体性,当然也就不承认自然生命的内在灵性和内在价值。当没有宏伟超越的目标来引导现代科学技术时,它就很容易蜕变为人类手中的暴力,后果便堪忧。李存葆认识到,“科学能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和便捷,却也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科学能使人类变得无比强大,却未能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原子战、化学战、细菌战的阴影,常使人类惴惴不安;科学能使人类去广泛地认识物质世界,却未能使人变得更加善良和高尚……”[4]27。在生态意识视野中,现代科学技术显示了其两面神的特征。姜戎小说《狼图腾》中,当人驾驶着吉普车用步枪猎狼时,狼的所有威严便荡然无存,而现代人的骄狂与自得就愈发高涨。现代科学技术使人有可能暂时地局部地战胜大自然,把人高高地置放于大自然之上,若人仍缺乏自我反省意识,缺乏与大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意识,最终就会使人自食恶果。
(四)对现代文明的标准化的生态批判
绿色和平运动曾提出生态学三大原则之一就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取决于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条原则不但是自然界的生态真理之一,而且也是人类生活的文化生态真理之一。但是现代文明以效率为唯一原则,倡导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理性化笼罩一切,直接导致现代世界的标准化、机械化、单一化、同质化的简化倾向。韩少功在散文《阳台上的遗憾》中曾说:“这种高楼大厦正在显现着新的社会结构,展拓着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在统一着每一个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在不分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以反过来侵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产生同样的流行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同样的恋爱经历,以及同样的怀旧情结?……这些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5]当人与大自然被标准化世界隔开,甚至身心体验也被标准化后,那么人又如何展开丰富的心魂呢?
(五)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态批判
现代文明的种种特征无疑是最集中表现于城市文明中,而城市文明尤其是反生态的典型。所有反生态的观念、言论和行为几乎都可以溯源至现代城市文明中。因此,作家对现代城市文明可以采取道德批判、审美批判,但更彻底的还是生态批判,例如韩少功、张炜、海子、苇岸、徐刚、郭雪波、于坚、迟子建等。韩少功在《山居心情》中写道:“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但城市越来越陌生了,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现代钢铁鼠疫,还有高墙上长满空调机疙瘩的现代钢铁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6]城市的反生命和反生态的本质在此被描绘得极为形象。对大自然的禁锢和镇压竟然就是现代城市的追求,被人视为享受!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迷误!
三、中国当代文学生态批判的特点
生态意识的呈现,使中国当代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获得了稳固的批判立场,而且将会真正拓宽批判视野,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有可能对现代文明的浪潮中发出真正有价值的声音。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代文学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从批判路向上看,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批判关注的核心
相对于世界各地的古典文明而言,现代文明的异质性显而易见。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也就看到现代文明不同的负面因素。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而言,现代文明是破坏传统文化的罪魁祸首;对于后现代主义者而言,现代文明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铁笼;对于以批判为宗旨的审美现代性而言,世俗现代文明是资产阶级的庸俗本性。中国当代文学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也同样具有不同的价值立场。像汪曾祺等作家,在对传统文化和乡村礼俗的精心描摹中,品味着传统生活的细致情韵,对现代文明有着幽微超脱的淡然批判。像20世纪80年代的路遥、贾平凹等作家,展示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两难抉择,便暗含着对现代文明的些微疑惧。像陈忠实、张宇、李佩甫等作家则在相关小说中通过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复活,来对现代文明的道德沦落表达迂回批判。而20世纪90年代后的张承志据守伊斯兰信仰对现代文明的信仰缺失、功利主义泛滥表示愤怒,张炜则常常展开对现代文明的道德理想主义批判。像朱文等晚生代作家则常常退入肉身快感层面来对现代文明进行声嘶力竭的批判。与这些现代文明批判相比,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则直逼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基本关系,具有更为宏阔深入的视角,从而保证了批判的准确和力度。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毕竟是人之存在最为根本的关系之一,现代文明也正是从对大自然的机械化设定基础上发展起来,最严重的后果也就表现于大自然的败坏;因此,生态批判超出其他批判视角,具有罕见的现实性和整体性。
(二)从批判资源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更注意汲取传统文化、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边远地区乃至农村地区的民间文化资源
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的根基是生态意识,西方生态文学的生态意识一般更多地来自现代科学研究,尤其是生态学,例如利奥波德的《沙郡纪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莫厄特的《鹿之民》等;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则更多地取自于传统文化、少数民族宗教文化、边远地区乃至农村地区的民间文化资源。阿城的《树王》、贾平凹的《废都》等就更多地向强调天人合一的传统道家思想遥致敬意。郭雪波的《沙葬》、《银狐》,李传锋的《红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小说则是向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寻求生态意识资源。李存葆的散文《净土上的狼毒花》也对藏族传统宗教的自然生态保护意识详加申述,引为同调。姜戎的《狼图腾》更是通过塑造蒙古族毕利格老人来传达蒙古族的草原生态保护意识。许多生态批判的作家都是来自边远地区或有农村成长经历,诗人于坚曾说是云南少数民族对天地的敬畏之情唤醒了他的心灵,周涛散文的生态意识是受到新疆广袤大地神奇大自然的影响;而迟子建之于黑龙江大兴安岭农村,张炜之于胶东半岛野地,韩少功之于湖南农村,陈应松之于湖北神农架等,都可见出边远山区农村的影响对作家生态意识的确立至关重要。这种生态批判资源的多源性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更多姿多彩。
(三)从批判程度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是全面而深刻的
就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的全面性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生态危机都有所涉及,例如作家徐刚的系列报告文学,哲夫的系列报告文学等。而许多小说和散文对现代文明的内在性质,如人类中心主义、标准化和同质化等,也都曾进行全面的批判。就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的深刻性而言,许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能够深入现代文明的内在肌理,展示出人与大自然的复杂关系,达成对现代文明和生态保护的独特理解。例如雪漠的长篇小说《狼祸》并没有简单地大肆抨击现代人对自然生命的掠夺,而是充分地展现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怎样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四、中国当代文学生态批判的意义和局限
无论从文学史还是就现实时代来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赓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文明批判传统
中国发展现代文明本来就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逼迫下不得不采取的生死存亡之计,对现代文明往往既羡慕又怨恨,更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界对现代文明的大肆批判,更助长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意识。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对现代文明一直都存在着鲜明的反思批判意识,例如鲁迅的《文化偏至论》中对西方现代文明偏至的洞幽烛微式批判,沈从文依据理想化的湘西世界对现代文明的功利化和世俗化的批判,张爱玲对现代文明导致的人伦失序和人心颓败的批判。这种批判传统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深邃认识。但到了1949年后,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传统顿然丧失,变成了政治意识形态之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渐兴起的生态批判接续上了这个良好传统,拓宽了中国文学的视野,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
(二)通过生态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恢复了对现实的直接感受,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少有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生态观照,而现代文明对人的最大威胁却首先在于对大自然的摧残。德国当代作家君特·格拉斯在接受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弗尔特里内利文学奖时曾说:“人类可以停止只顾想到他们自己吗?他们——这些神一样的创造性的生命,拥有理性,成为越来越多的发明的创造者——敢于对他们的发明说不吗?他们准备弃绝可能的人性并对残存的自然表示一定程度的谦逊吗?最后,我们还想不想做我们想做的——也即互相喂饱,直到饥饿消失,变成奇谈怪论,变成一个很久以前的食尸鬼的故事?”[7]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作家还只能津津乐道于人类历史的风云变幻,都市人的悲欢离合等,那就是一种可悲的盲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态批判,是对现实的最大关注。像徐刚、哲夫、陈桂棣、韩少功、郭雪波、张炜等作家那样的生态批判,使中国当代文学的立意更为高远,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变得更复杂,更全面。
(三)通过生态批判,中国当代文学确立了生态意识
现代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地球和人类的生存问题,整体的生态意识才显得如此迫不及待。李存葆曾语重心长地说:“人类真正的不幸,在于不懂得在珍惜自身的同时,也应珍惜身外的一切生灵;不懂得自身生命的彩练原本与身外生命的虹霓连成一片。人之外的任何生命的毁灭,不仅是兽的悲哀,更是人的悲剧。”[4]25人的生命的繁盛和丰富必然要求着自然生命的繁盛和丰富,当自然生命不可能避免地凋零殆尽时,人性也将日趋单薄,人心也将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中渐渐枯竭。现代文明必须放弃对大自然的无限制征服和改造,更不能为所欲为地利用大自然来满足人永无餍足的欲望,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尊重生态规律,承认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
当然,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尚存在种种局限。首先,许多作家作品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时,存在把它简单化、概念化的弊病。例如贾平凹的《废都》《怀念狼》等小说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态批判就是如此,仿佛都市为罪恶之源,现代文明乃堕落之根,返回山野就能获救。这就遮蔽了现代文明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从而也就无法真正到位地批判现代文明。其次,许多作家作品对生态意识的理解存在着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例如对于许多作家而言,似乎只要人类抛弃现代文明,回到自然状态,就可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无疑是对生态意识的误解。人是不可能抛弃文明的,也不可能抛弃现代文明,即使现代文明比前现代文明对大自然的破坏再厉害十倍,人也不可能返回前现代文明。人不可能像现代工业文明一样为所欲为地为大自然立法,但也不可能抛弃文明任由大自然为自己立法,而只能是重新使文明与大自然和解,这才是生态意识的核心内涵。因此,像叶广芩小说《山鬼木客》那样主张人抛弃文明回到自然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再次,许多作家作品批判现代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时,往往单就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着眼,这样就限制着作家作品的眼界。马克思曾说:“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8]因此,必须充分地考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相互制约的。若能注意这些以克服局限,中国当代作家的生态批判也许能够更为深刻,更富有启发意义,为世界提供更有价值的文学佳作。
[1] 郭沫若,周 扬.红旗歌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59.
[2]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82.
[3] 宗 思.与生灵共舞[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235.
[4] 李存葆.大河遗梦[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7.
[5] 韩少功.鞋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243.
[6] 韩少功.山居心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86.
[7] 格拉斯.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J].黄灿然,译.天涯,2000(1):111-120.
[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