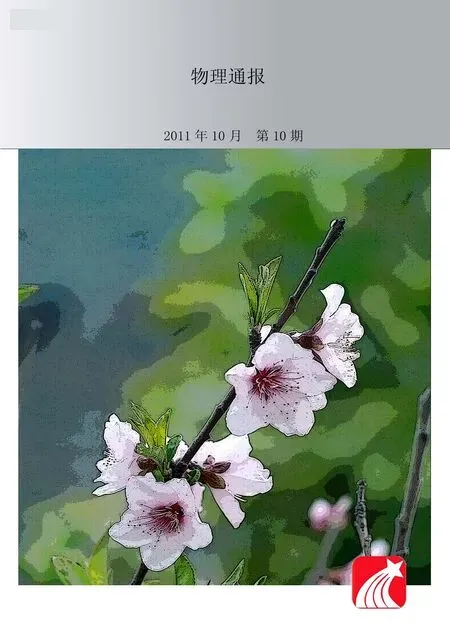发现星空秩序的路线简图
朱崇军
(灌云县教育局教研室 江苏 灌云 222200)
康德有一句影响极广的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是持久和深沉地思考着,就越有新奇和强烈的赞叹与敬畏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康德那里,星空与道德有了联系,那是因为秩序.人类为了寻找星空的秩序,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展望这条历史道路上熠熠生辉的里程碑,不禁让笔者想到了皮埃尔·迪昂的一段深刻论述:任何物理学理论都是通过一系列润色进行的,它使体系从无定型的第一批草图逐渐达至比较精致完美的状态[1].了解发现星空秩序的历史即使是一条路线简图,对于我们也是有益的,因为弗兰西斯·培根说过,对于那些想发现人类理性本质和真正用途的人来说,学习历史是有实用意义的[2].
1 “两球宇宙”模型
所谓“两球宇宙”模型包括一个为人而设置的内球(地球)和一个为恒星设置的外球(天球).到“两球宇宙”模型的形成,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已走过漫长的道路,因此“两球宇宙”模型虽也源自人类的直觉和想象,但它更经得起推敲,也能解释许多天文现象,所以它能容纳自公元前4世纪到哥白尼时代 1 900年间大量不同且有争议的天文学和宇宙论方案[3].
2 托勒密体系
在托勒密体系中,地球静止且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与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的地位一样,也是行星之一.太阳除做向西的周日运动,还沿着黄道向东做缓慢的周年运动.五大行星各自都在一个较小的“本轮”上做匀速圆周运动,但本轮的中心又在一个庞大的“均轮”上绕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太阳和月亮没有本轮,直接在均轮上运动,地球又稍稍偏离所有均轮中心.起初是单本轮、单均轮体系,但它所预言的运动和观察到的行星的运动相比较时,行星并不总是出现在预测的位置,所以它并不是行星问题的最终答案,而只是一个有希望的开始.在从希伯克斯到哥白尼(1473~1543年)的17个世纪中,所有最富有创造性的技术天文学的研究者都致力于发明一些新的细微的几何修正,以使基本的单本轮、单均轮技术更精确的符合观测到的行星运动.在这些努力中最伟大的要算是托勒密(约90~168年)在公元150年前后所做的工作,他取代了前人,结出了《至大论》这一丰硕成果.《至大论》浓缩了古代天文学最伟大的成就,是第一部为所有天体运动提供完整、详细和定量解释的系统的数理论著,以至他的所有继承者包括哥白尼在内都要模仿他来开展工作[3].这里要注意的是“托勒密体系”是指解决行星问题的一种传统方法,而不是指任何个人的一种特殊的解答.
托勒密体系的所有版本,都只有5个大本轮,而用以解释量上的细微偏差的小本轮,只取决于在预测精度方面对体系的要求.因此,托勒密天文学的不同版本之间小本轮的数目相差很大.使用6~12个小本轮的体系在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并不少见,因为通过对小本轮尺寸、速度和倾斜角度的适当选择,几乎所有微小的不规则性都可以得到解释.在托勒密体系中还用偏心匀速点这个装置,以帮助调和本轮理论与实际观察结果.均轮的转速保持恒定,但不是相对于它的几何中心,而是相对于偏离中心的某点保持恒定,该点即是偏心匀速点.从均轮的几何中心观察,行星似乎是以不规则的速率运动或摇摆不定[3].
均轮、偏心圆、偏心匀速点和本轮,这些数理装置并非一下子发展起来的,但是托勒密的贡献是杰出的.解决行星问题的这全套技巧以他的名字而流传,是因为托勒密首先将一组特别的组合圆放在一起,解释在行星的视运动中观测到的定量的规则性与不规则性.其效果如此之好、方法如此之有力,以致为了提高行星理论的准确性,托勒密的后继者们在本轮上添加本轮,在偏心圆上添加偏心圆,以充分开发托勒密的基本技术中多种多样的功能,并最终导致整个定量体系在数学上过于复杂和深奥.引发哥白尼去探索行星问题新的解决途径的那些问题,正是在这种深奥的量化理论内部.
3 哥白尼革命
托勒密之后的众多天文学家在不断批评和修正托勒密体系,导致托勒密体系已不再是一个,而变成了一大堆.天文学传统已经变得散乱,再也不能完全规定一个天文学家在计算行星位置时应该用什么方法,从而也无法确定从他的计算中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像这样的模棱两可,是使得天文学传统丧失其内在力量的主要源泉.一个理论的变形骤增,正是危机的通常迹象.危机的意义在于,它指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4].散乱并且错误不断,这是被哥白尼喻为“怪物”的迅速增长的传统天文学的两大特征[3].对于哥白尼革命所依赖的天文学传统自身的明显变化来讲,这是两个主要根源,但不是唯一的,哥白尼已经发现,古代人在这件事上已有分歧[5],另外“革命”还跟时代潮流有关.时代潮流表现在多个方面:航海业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视界,却降低了托勒密的权威;历法改革要求有新的天文理论的指导;人文主义带来了新的信念(自然中存在简单的算术和几何规则)和新的观点(太阳是宇宙中一切活力原则和力量的来源,它的辐射给予宇宙以光芒、温暖和丰饶);柏拉图主义的复活:数学在地上世界的不完善和变动不居的现象之中示范了永恒与真实.哥白尼生活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核心时期,由于老套的东西很容易在普遍骚乱的时期被抛弃,所以动荡本身就有利于哥白尼的天文学革新.哥白尼革命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是人的宇宙概念以及人与宇宙之关系的一次转型.在文艺复兴思想史上的这一幕,被一再地宣称为西方人思想发展的划时代转向.
1543年哥白尼《天球运行论》的出版[3],揭开了天文学和宇宙论思想上一场巨变的序幕.《天球运行论》是一个有多方面问题的文本,但它又是转变科学思想的发展方向的文本,具有双重特性;它既是古代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保守的又是激进的.
哥白尼是为数不多的一群最早复兴整个希腊化技术性的数理天文学传统的欧洲人之一.这一传统在古代由托勒密的著作推至顶峰.《天球运行论》也正是为解决在哥白尼看来托勒密及其继承者尚未解决的那些行星问题而著.在哥白尼的著作中,地球运动的革命性观念最初只不过是这位熟练而又忠实的天文学家试图改良计算行星位置的技巧时一个反常的副产品.哥白尼说,对当时天文学的坦率评价表明,靠地心说解决行星问题希望渺茫.旧有传统的方法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相反还产生了一个怪物.他断定,在传统行星天文学的基本思想中,一定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是首次有一位在技术上胜任的天文学家处于其研究的内在理由而拒绝历史悠久的科学传统,而且促使哥白尼推动地球的只是对数理天文学的改革.哥白尼革命本质上不是在计算行星位置的数学技巧方面的一场革命,但它的起点却是如此.在认识到需要新技巧和发展新技巧方面,哥白尼为这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革命做出了唯一的原创性贡献[3].
哥白尼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地动说的人;前无古人的只是哥白尼在地球运动基础上建立了数学体系.如果地球能够像绕自身的轴旋转一样也围绕中心做轨道转动,那么逆行运动以及行星在黄道上相继的两次运行所需时间的不同,就不需要使用本轮也能解释,至少可以得到定性的解释.在哥白尼体系中,行星运动主要的不规则性都只是表面上的.从运动的地球上看,实际上规则的行星运动就显得不规则了.
逆行运动和绕黄道运行所需时间不固定这两大不规则性,在古代导致天文学家使用本轮和均轮来解决行星问题.哥白尼的体系解释了这两大不规则性,而且没有使用大本轮.而为了对行星运动做出哪怕只是近似的和定性的解释,托勒密用了12个轮.哥白尼对行星的视运动完成了同样定性的解释,却只用了7个轮[3].他只需给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各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轮,再给月球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轮.对于只考虑行星运动的定性解释的天文学家而言,哥白尼体系肯定经济得多.但哥白尼又并没有解决行星问题.从纯粹的实践的角度来看,哥白尼的新行星体系是一个失败,它并不比其托勒密派的前辈更精确,也没有显著的简化.正如哥白尼认识到的,日心天文学真正的吸引力是审美方面的而不是实用方面的.只有那些把定性的简洁性看得比定量的精确性重要得多的天文学家才会把这当作令人信服的论证,而不顾《天球运行论》中精致的本轮和偏心圆的复杂体系.
所以,被哥白尼说服而接受地动观念的人们又从哥白尼止步的地方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地球的运动,而他们所致力的问题已不再是哥白尼所从事的旧的天文学中的问题,而是他们在《天球运行论》中发现的新的日心天文学中的问题.哥白尼给他们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前辈都无需面对.在对这些问题的追究过程中,哥白尼革命得以完成.
任何个人能够做出的革新范围必定有限,因为每个个人在研究中都必定要使用在传统的教育中学来的工具,而他穷其一生也不可能把这些工具全部换掉.后来的相关著作越来越多地从《天球运行论》中借用数据、计算和图表,至少是从它的某些与地球运动无关的部分借用.在16世纪后半叶,这本书成了所有天文研究中对高深问题感兴趣者的标准参考书[3].天文学家已经离不开《天球运行论》,也离不开基于它的星表.哥白尼的方案缓慢但显然不可动摇地赢得了地位.
4 第谷的调和
如果说哥白尼是16世纪上半叶欧洲最伟大的天文学家,那么第谷(1546~1601年)就是后半叶杰出的天文学权威.他设计和制造了许多比过去更大、更稳定、校正得更准的新仪器.凭借无比的天才,他检查并纠正了在这些仪器的使用中发生的许多错误,建立起一整套关于搜集行星和恒星位置的精确信息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他开始对行星实行定期观测;只要行星穿过天际,而不只是在某些特别有利的位置才观测.现代的望远镜观测表明,当第谷极为仔细地测定恒星的位置时,他的数据精度可以达1′,对行星位置的观测精度通常可靠至4′,甚至更好;这是肉眼观测的非凡成就[3].不过比第谷的个人观测的精度更重要的,是他所积累的数据整体的可信度和广度.在他的一生中,他和他训练的观测者,把欧洲天文学从对古代数据的依赖中解放了出来,并且消除了一系列由于错误数据产生的表面的天文学问题.可信的、广泛的、最新的数据是第谷对解决行星问题做出的主要贡献.除此之外,他还发明了既不同于托勒密又不同于哥白尼的第三种体系,即第谷体系——月亮和太阳的圆圈以地球为中心,而其余5颗行星的轨道的中心又是太阳.在第谷体系中,小本轮、偏心圆和偏心匀速圆也是必需的.
第谷体系最显著、最有历史意义的特征就是,它适合于作为对《天球运行论》导致的问题的折中解决,它使几乎所有博学的17世纪托勒密天文学家都转向第谷体系,它就像是《天球运行论》的一个直接的副产品.第谷对哥白尼的批评和对行星问题的折中解决表明,他跟当时大多数天文学家一样无法突破传统的思想模式.不过,第谷高超的观测在引领同代人走向新的宇宙论方面比他的体系更为重要.第谷在临终前,还喃喃地说:“我多希望我这一生没有虚度啊!”1602年,开普勒编辑出版了第谷遗留下来的观测资料[6],并从中探讨行星的运动规律.开普勒的伟大工作真正使第谷的一生没有虚度.
5 开普勒立法
开普勒(1571~1630年),终其一生,以狂想曲般的情调,将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特有的思想运用于太阳中心体系.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宇宙的神秘》(1596年出版),首次展示了为新天文学所作的数学论证的充分力量.[3]开普勒在努力使数学技巧适应以太阳为主宰的宇宙图景,正是因为坚持这种努力,开普勒最终解决了行星问题,把哥白尼笨重的体系转变成一项极其简单和精确的计算行星位置的技术.得到这个结果的过程是异常艰苦的(研究火星运动大约用了10年时间)[3],开普勒一丝不苟地尝试修改他的轨道以适应第谷的观测数据.一长串不成功的试验迫使开普勒做出结论,没有任何基于组合圆的体现能够解决问题.他设想肯定有某种别的几何图形包含了问题的答案.他试了各种不同的卵圆形,但都不能消除他的试验性理论和观测之间的偏差.然后,他偶然注意到偏差本身以一种熟悉的数学方式变化;他研究了这种规律性,发现若行星以变化的速率沿椭圆轨道运行,就可以使理论与观测相符合.
行星沿单纯的椭圆轨道运行,太阳占据椭圆轨道的两个焦点之一;这就是开普勒第一定律.紧接着是开普勒的第二定律,完善了第一定律所表达的描述,即每颗行星的轨道速率以这样的方式变化,使得行星到太阳的连线在相等的时间间隔内扫过相等的椭圆面积.开普勒使偏心圆、本轮、偏心匀速圆以及其他特设性装置,都不再需要了.单独一种非复合的几何曲线和单独一个速率定律就足以预测行星的位置,这还是第一次;而且预测结果跟观测一样精确,这也是第一次.开普勒的6椭圆体系使日心天文学生效了,把哥白尼的革新中隐含的经济性和丰富性同时显现出来[3].
开普勒第三定律是一种新型的天文学定律.第一、第二定律跟古代和中世纪的一样,只决定单个行星在自己的轨道上的运动.相反,第三定律建立了不同轨道上的行星速率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条迷人的定律,因为它指出了一种过去从未在行星体系中觉察到的规律性.尽管它几乎没有直接的实际作用,但第三定律正是在开普勒的毕生事业中最令他着迷的.他是数学上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相信整个自然都是简单的数学规律性的例证;而发现这些规律正是科学家的任务.对于开普勒和别的具有他这种性情的人来说,一条简单的数学规律本身就是一个解释[3].单就开普勒在数学中的成就而论,他就足以赢得永恒的声誉.当然他是一位数学方法的坚决拥护者,但他与早期的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相比是有差别的,这差别在于他强调要把理论严格地应用到观测到的事实.哥白尼革命和第谷对星体资料的整理,对于提供一个有待于发展和证实新的、重要的数学理论来说是必要的,对于提供一套完整的资料也是必要的,而那种证实就必须在这套资料中找到.正是使用这一方法,而且也是为此目的,开普勒达到了对其三大定律的划时代的发现[5].因其三定律,开普勒被誉为为天空立法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开普勒虽然取得那么多伟大成就,但却一生贫困.在格拉茨大学做讲师时,薪水很少,他不得不靠编制占星历书而养家糊口.他自我解嘲地说:“如果女儿占星术不挣来两份面包,那么天文学母亲准会饿死”.后来,虽说身为宫廷天文学家,但薪水常常拖欠,以致1630年11月15日,在他去索要拖欠20余年的薪水时,染伤寒死于途中[6].
6 伽利略的望远镜
1609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1564~1642年)首次通过望远镜观看天空,整个星空充满了无以数计的新成员.某些哥白尼派预设的宇宙极大的扩张甚至是它的无限性,突然变得不那么荒唐了.望远镜使得支持哥白尼主义的论证倍增.1609年以后,对天文学只有一知半解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望远镜亲眼看到,宇宙跟常识的幼稚告诫并不相符.望远镜成为一种流行的玩具,对天文学或任何科学此前从未表现出兴趣的人,也买来或借来这种新仪器,在晴朗的夜晚热切地搜索天空.一种新的文学也随之诞生了.科普读物和科幻小说的萌芽都可以在17世纪发现,一开始望远镜和它的发现是最显著的主题.这就是伽利略的天文学工作最重要的地方:它普及了天文学,而且普及的是哥白尼天文学[3].
不同的体系被人们相信是出于相同的原因,那就是它们都为看起来重要的问题提供了似乎合理的回答.发现始于意识到反常,即始于认识到自然界总是以某种方法违反支配常规科学的范式所做的预测.于是,人们继续对反常领域进行或多或少扩展性的探索.这种探索直到调整范式理论使反常变成与预测相符为止[4].从发现星空秩序的路线简图中,我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启示:不同体系是不同时代的科学理论,科学也总是在新理论取代旧理论中进步的.
1 (法)皮埃尔·迪昂著,李醒民译.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247
2 (美)托马斯·库恩著.范岱年,等译.必要的张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7
3 (美)托马斯·库恩著.吴国盛,等译.哥白尼革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64,69,138,126,128,165,181,196,205,207,208,212,219
4 (美)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0,49
5 (美)爱德文·阿瑟·伯特著.徐向东译.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43
6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3,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