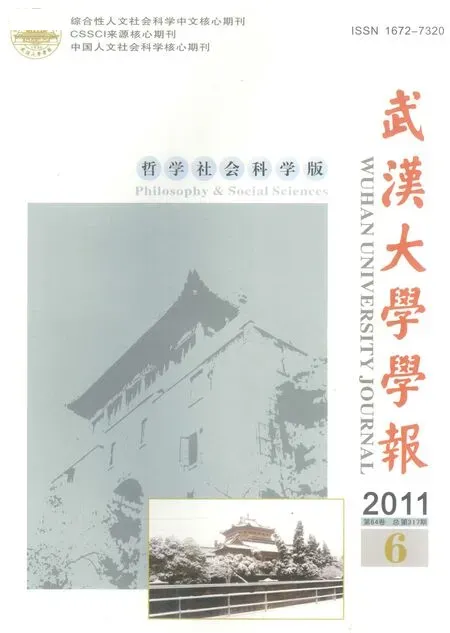论意思自治在侵权冲突法中的现代发展——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之相关规定
贺琼琼
一、意思自治在侵权冲突法中产生与存在的理论依据
(一)侵权行为法的价值取向转变与其私法的本质属性
传统侵权冲突法理论通常认为,侵权法的功能主要在于制裁和惩罚,侵权法通过对侵权行为人进行惩罚以保障社会安定、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和实现社会公平。例如,德国学者萨维尼认为侵权法是强行法①赵相林:《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3页。、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认为当地利益的保护和法律所体现的政策的实现要比受害人利益的保护重要得多,即使是卡弗斯的“结果选择方法”也是更多关注对侵害人的惩罚,而非受害人的救济。侵权法被赋予了过多的强制性和公共政策属性,所以,出于维护侵权行为地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一些国家在制定侵权冲突法时总是竭力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在侵权冲突法中很难找到容身之所。但是,随着侵权行为类型的多样化,传统的侵权形式从过错责任发展到过错推定,甚至是无过错责任。侵权行为法维护侵权行为地的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功能不断减弱,“保护公民权利和补偿受害人损害的功能日渐突出”②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其通过“私人的合意安排而加以减损的私法性质不断增强”③宋 晓:《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9页。,作为权利人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法律手段,侵权行为法的私法属性日益明显。私法首先是保护私人利益的,只有在最大限度内承认私人对私法行为的自主性,通过私人自己的意志和行为才能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当代意思自治原则向侵权法律适用领域渗透的一个重要基础。
(二)现代侵权行为的复杂化与侵权行为地法原则的内在缺陷
“法律一方面需要满足确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另一方面也需要实现灵活性和个案的公正性,这对矛盾和法律本身一样历史悠久。”①S.C.Symeonnides(ed).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Progress or Regres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p.44.确定性和灵活性向来都是法律追求的目标,冲突法制度中尤其如此。侵权行为地法原则以空间连结点为指引寻找侵权行为准据法,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冲突正义的实现,有利于实现法律选择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但是,由于各国冲突规则不统一,当事人选择在不同国家起诉将很难保证判决结果的一致性。此外,由于当事人无法预见调整其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准据法,难以对交易作出具体的安排,也会带来交易成本的增加。而且,随着侵权行为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任何一个客观的连结因素都难以经常性地体现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②Friedrich K.Juenger.Choice of Law and Multistate Justic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3,p.48.。在跨国侵权案件中,一个侵权行为的行为实施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分跨数国的情况屡见不鲜。诚然,如果侵权之诉的所有事实发生在一国境内,侵权行为地自然在该国境内,根据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时的法律适用是明确的;但是,如果构成侵权之诉的所有事实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境内时,根据侵权行为地法原则,这些国家都可以成为侵权行为地,此时的侵权行为地法原则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仍然不加区别地运用侵权行为地法原则判定行为人的责任,则往往不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从而带来不公正的结果。因此,在侵权冲突法中引入意思自治,可以大大降低侵权行为地法原则的机械和僵固,而给当今复杂多变的侵权诉讼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
(三)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与美国冲突法革命的理论铺垫
为了改变传统侵权冲突规范的僵化和机械,美国率先在侵权领域掀起了冲突法革命的浪潮。在这场革命中,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学说,特别是“结果选择说”。该说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侵权领域可以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但它对僵硬的传统冲突规范进行软化处理,要求法律选择从判决结果入手,既要对当事人公正,又要符合一定的社会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为意思自治原则在侵权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此外,随着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日益增强,各国冲突法立法在追求法律的确定性、判决结果的一致性的同时,也开始更多地考虑到法律的灵活性与个案的公正性。意思自治原则通过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可以保证法律选择既满足对当事人的公正又能实现社会公正,因而自然会在国际私法的诸多领域得以适用。
(四)冲突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完美结合与意思自治原则的自身优势
无论是从“冲突效率”与“实体效率”③See,J.P.Trachtman,Economic Analysis of 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Virginia Journal o International Law,Vol.42,2001,p.42.,还是从“冲突正义”与“实体正义”层面的价值取向考察,在侵权法律适用中,比起侵权行为地法这类传统的硬性冲突“规则”和最密切联系这类现代灵活的“方法”,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均为最优的冲突法律制度的安排④徐崇利:《我国冲突法立法应拓展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2期,第131~135页。。侵权行为地法原则虽可保证一定程度的冲突正义,但其以空间连结点为指引机械地寻找法律,根本无法保证所选法律必将公正地处理案件。最密切联系原则虽可以实现法律适用的简便性,但其以追求实体正义为价值取向,由于实体正义的标准本身充满了争议,因此又有可能破坏法律选择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正如一位法官所言:“如果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即使是法官也很难判断哪一个才是真正满足抽象意义上的公正的法律。”⑤S.C.Symeonnides(ed).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Progress or Regres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既然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在侵权领域中广泛地适用,可以将这种判定侵权行为地的自由裁量权赋予法官,为什么就不能赋予当事人以这种选择权呢?在司法实践中,作为第三方,法官在判断一国法律适用的结果对双方是否公正或是否存在实体效率时,通常容易视本国法律为实体正义的最佳体现,从而过多倾向于法院地法的适用。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一方面,他们更为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因而更有能力选择更为适合调整彼此之间侵权法律适用的实体法;另一方面,选择的实体法由于经过了双方意思的协调,因而更能有效地解决争议,从而真正实现国际私法所追求的实体正义的目标。所以,尽管兼顾国际私法上的“冲突正义”与“实体正义”是一种两难的境地,但当事人意思自治无疑可以被视为是这两者在侵权领域法律适用中的最佳结合。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引入及其在侵权冲突法中的国际实践
(一)以瑞士为代表的法院地法限定模式
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率先将意思自治原则引入侵权领域,根据该法,法律选择的时间是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纠纷解决之前。该法赋予了当事人选法的权利,但将这种选择限制在法院地法的范围之内。在瑞士的影响下,许多国家也规定了类似的立法,如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71条、《俄罗斯民法典》第1219条第3款、《乌克兰国际私法》第49条以及我国《民法典》(草案)。对于瑞士的这种规定,有学者认为,其实质是在于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①何其生、卢熙:《论侵权行为自体法的发展》,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12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7页。。也有学者认为,是因为瑞士国际私法担心全面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会把惩罚性赔偿等其不愿接受的法律政策引入瑞士法院②宋 晓:《侵权冲突法一般规则之确立——基于罗马与中国侵权冲突法的对比分析》,载《法学家》2010年第3期,第165页。。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将当事人的选法范围局限于法院地法的做法不仅保守,而且不太合理。一方面,侵权行为法属于私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私法领域的重要原则。另一方面,立法之所以将选择法律的范围限制在法院地法,无非是为了维护法院的公共秩序和防止当事人滥用法律选择权,而防止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损害国家利益完全可以通过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来实现,这种限制当事人选择的做法既是多余,同时也有违内外国法律地位平等原则。
(二)以德国为代表的“无限”的受害人选择模式
德国1999年《民法施行法》对侵权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进行了规定。根据该法第40条,在侵权事实发生之后,如果没有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任何法律。双方当事人不能预先约定行为的准据法,即使双方可以预见侵权法律关系的产生。与《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相比,该法虽仍将选法时间限定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不允许事前选择,但其进一步扩大了意思自治的范围,取消了法院地法的选法限制,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此外,德国《民法施行法》在侵权冲突法立法中还特别强调对受害者利益的保护,并将受害人选择涉外侵权关系的法律适用视为最好的做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原告有权选择法律适用,其前提是侵权行为实施地和损害结果发生地位于不同的国家,且侵权行为实施地国的法律给予受害人的保护不及损害结果发生地国。此外,该法还对受害人的选择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受害人只能选择损害结果发生地国的法律,而且,如果当事双方拥有该条规定的共同惯常居所,受害人选择的法律将会被排除适用。
(三)以欧盟为代表的“有限”的事前选择模式
2007年欧盟《关于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的第864/2007号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4条对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进行了规定。根据该条,双方当事人通过损害发生前可自由转让的协议来选择法律适用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均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该法律选择是以明示的或以某种确定的方式得出的,且不妨碍第三人的权利。如果案件的全部因素均与一个欧盟成员国以外的国家有关,则即使该国的法律未被当事人选择为准据法,该国法律中的强行法也必须得到遵守;如果案件的全部因素均与欧盟成员国有关,只是分布在不同的成员国内,则双方当事人对第三国法律的选择,不得妨碍共同体法中强行法规定的适用,如果强行法规定当事人协议排除适用某成员国法律的适用无效时,则相关成员国的法律仍应得以适用。《条例》区分侵权行为发生前和侵权行为发生后两种情形,既允许事后选择,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事前选择。《条例》没有将选法范围局限于法院地法,而是赋予其类似于合同法律适用中意思自治的自由度,体现了对传统侵权冲突法律适用规则的突破,这一方面有助于降低传统侵权冲突法律适用规则的僵固性所带来的弊端,同时也给侵权冲突的法律适用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如此,《条例》有关意思自治的规定仍然是不够的,《条例》虽然设置了强制性规则条款来保护弱方当事人的利益和防止当事人规避第三国和欧共体的强行法,但由于这些条款的可操作性不强,导致限制无法真正地发挥作用。比如,关于商事活动如何进行解释?商事活动中弱方当事人的利益如何保护?都显得模糊不清①贺琼琼:《欧盟侵权冲突法一般规则的新发展》,载《法国研究》2010年第4期,第98页。。
三、我国侵权冲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在侵权法律适用中规定意思自治原则。2000年,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率先在侵权领域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200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以下简称《民法典》(草案))第九编第八章第81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虽然表明了我国学者和负责起草的立法部门对侵权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的接纳和认可,但我国在侵权法律适用中明确规定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正式立法则主要是指《法律适用法》中的相关条款。如上文所述,《法律适用法》已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并于2011年4月1日起施行。该法结束了中国没有统一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它不仅对中国自身有重要意义,而且对那些与中国有密切民事交往的其他国家也将产生深远影响。该法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制度进行了创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扩大适用就是其创新的表现之一。
(一)《法律适用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解读
从《法律适用法》的相关条款来看,直接规定意思自治原则的条款是总则第3条和分则第44条。除此之外,《法律适用法》还在总则第2条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根据该条,只有在《法律适用法》没有对涉外侵权关系的法律适用进行规定的情况下,才能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所以,结合总则第2条与分则第44条,可以看出,《法律适用法》是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一般侵权法律适用中的首要原则的,即在处理一般侵权关系的法律适用时,应首先考虑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其次是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原则,如果以上原则都不能适用,最后采用侵权行为地法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兜底条款”,只能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时候方能适用。
比之《民法典》(草案)第81条,《法律适用法》的一大创新就是扩大了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该法不仅对其适用范围进行扩大,而且将意思自治原则放在总则中,赋予其非常重要和突出的地位。第44条不再将当事人选法的范围局限于法院地法,而是直接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任意选择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对于当事人选法的时间,第44条作了限定,即当事人只能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进行选择,《法律适用法》不允许事前选择。而且,总则第3条也对当事人的选择施加了两条限制,其一,当事人必须“依照法律规定”选择;其二,当事人的选择必须以“明示”方式做出,《法律适用法》不承认默示选择。除此之外,《法律适用法》还从不同方面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构成了限制。这些限制包括:(1)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不能违背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2)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的适用不得损害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3)当事人选择的外国法律只能是外国的实体法。由此可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除了必须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依照法律规定明示选择之外,还受到我国的强行法、公共秩序保留以及反致等制度的制约。《法律适用法》虽然在《民法典》(草案)的基础上扩大了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但显然没有成为完全的无限意思自治。
(二)《法律适用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评析
首先,关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地位。《法律适用法》赋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侵权法律适用中以首要位置,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当事人私权的尊重,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而且,也体现了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如上文所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把选择法律的权利赋予当事人,既可以克服侵权行为地法原则带来的机械和僵化,又可以避免最密切联系原则因对实体正义理解差异而导致的结果的不确定。在侵权法律冲突规范中,无论是从冲突正义,还是从实体正义的价值取向分析,当事人意思自治都优于其他规范。《法律适用法》将意思自治原则作为首要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在涉外侵权纠纷处理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可以实现案件结果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而且还可以提高案件审判的效率,减少成本,从而最有效地实现我国涉外侵权关系法律适用中的冲突正义与实体正义。
其次,关于当事人选择的范围。在《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无论是我国的《民法典》(草案),还是学者们起草的《示范法》都一致将当事人的选择限制在法院地法的范围之内,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到《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担心涉外侵权关系的法律适用可能损害到我国的国家利益。从世界各国国际私法近年的发展来看,意思自治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如果说瑞士当初将当事人的选择限定在法院地法是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不自信的话,如今,当事人意思自治在侵权冲突法中的地位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无论是德国的《民法施行法》还是欧盟的《条例》都已跨越了早先存在的思想障碍,对当事人的选择范围不加限定。《法律适用法》取消法院地法的限制,通过强行法、公共秩序保留和反致条款对当事人的选择予以限制的做法,不仅可以防止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而且符合意思自治原则的最新发展趋势,同时更有利于侵权之债的双方当事人对其利益进行协商以有效地解决争议。
再次,关于当事人选法的时间。我国《法律适用法》第44条只承认事后选择,不承认事前选择。如上述分析,虽然事后选择从逻辑上看对双方当事人都是公平的,也是各国国际私法立法广泛认同的做法,但由于侵权事件发生后,加害人与受害人通常会形成利益冲突,当事人达成一致进行事后选择的可能性很小,事后选择的适用空间并不大,该条款并不能充分发挥意思自治原则在侵权领域中的作用。如果只规定当事人的事后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致使侵权冲突法中的意思自治条款无异于“空中楼阁”。在这个问题上,欧盟《罗马条例II》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即既允许事后选择,又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允许事前选择,同时设置一定的条款以避免合同强势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使对方不利。这种做法无疑更能反映涉外侵权法律适用原则多样化、灵活化的发展趋势,同时真正显示出意思自治原则内在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意思自治在侵权冲突法中的作用。我国未来的法律修改可以考虑借鉴。当然,由于双方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并没有产生,当事人往往难以预料侵权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事前选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仍需予以一定的限制。
四、结 语
比起合同领域,侵权冲突法中意思自治的发展还与之存在一定的距离。而且,国际实践对其在侵权冲突法中的运用程度也有一定的差别。尽管如此,意思自治原则在侵权领域具有其存在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其总体的发展趋势是,意思自治在侵权领域的发展程度越来越高,各国赋予意思自治的自由程度也在逐渐扩大。我国《法律适用法》不仅在侵权冲突法中引入意思自治原则,而且赋予其首要地位。这种做法一方面表明了我国侵权冲突法的立法更加先进和科学,符合国际私法立法更加尊重当事人的私权,更加注重冲突正义与实体正义价值融合的最新发展趋势,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在涉外民商事交往中更加开放的态度。虽然有些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毕竟这一革新为推动我国涉外民商事关系更加健康和协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