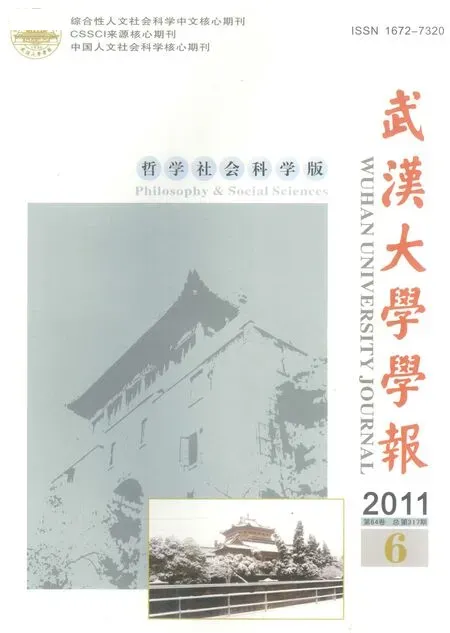法人投资者功能性国籍的确定——以ICSID仲裁制度及实践为中心
杨卫东 郭 堃
法人投资者功能性国籍的确定
——以ICSID仲裁制度及实践为中心
杨卫东 郭 堃
选择ICSID仲裁已经成为通行的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式。ICSID公约第25条(2)(b)为扩大公约的属人效力范围,赋予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东道国法人投资者以另一缔约国国籍,但公约本身对法人东道国国籍的认定、外国控制的形式和程度,以及功能性国籍协议的具体表现形式等付之阙如,学者学说和ICSID仲裁实践歧异纷呈。法人投资者的东道国国籍应当依据东道国国内法及相关国际条约予以认定,而其功能性国籍则需满足ICSID公约的客观标准,功能性国籍协议并不限于明示的书面形式。
法人投资者;功能性国籍;ICSID仲裁
ICSID仲裁已经成为解决东道国和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的普遍趋势。东道国为了便于对外国投资进行监管和基于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考虑,往往要求外国投资者以根据本国法律成立的公司作为投资工具。同时,由于法人投资者组织体系和股权结构的复杂性,因而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东道国公司殊为常见,此类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不具涉外性,原则上应由东道国国内途径予以解决,不能诉诸国际仲裁;但是,倘若将东道国与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该国公司排除在受案范围以外,无疑会大大削弱ICSID仲裁机制的作用。因而,ICSID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5条(2)(b)在对人效力范围问题上虽然仍然坚持法人投资者须为非东道国公司的基本原则,但同时规定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东道国法人,经争议双方同意,可视为另一缔约国的国民,此种为公约目的而赋予东道国公司以另一缔约国国民资格的国籍称为从属性(subsidiary)或功能性(functional)的国籍①R.Rayfuse,ICSID Reports:Reports of cases decided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5.。一些包含有中心条款的国家国内外国投资法也将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本国公司视为外国投资者,不少双边、多边国际投资条约则在投资者定义条款中将缔约一方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缔约对方公司视为前者的法人投资者。鉴于此,笔者拟以公约及其仲裁实践为中心,对法人投资者功能性国籍问题进行一些梳理和探讨。
一、法人投资者东道国国籍的确定
(一)东道国国籍认定标准及准据法
可能被赋予功能性国籍的法人投资者必须首先是作为公约缔约国的东道国的法人,必须指出的是,公约第42条关于争议法律适用规定解决的是中心管辖权确定之后实质性争议的准据法问题,争议双方通过协议只能赋予已然拥有东道国国籍的法人投资者以另一公约缔约国国籍①Christoph H.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A Commenta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67,281.。因此,公约第42条不能作为认定法人投资者东道国国籍的准据法,争议双方亦不能在法人投资者东道国国籍事项上意思自治。
公约专为解决东道国与他国国民之间的投资争议所设,每一缔约国均可能同时是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不可能采用双重标准认定东道国法人国籍和缔约方法人国籍,在公约起草过程中是否规定法人国籍的客观标准颇具争议,曾经试图采用注册登记地、住所地和控制性利益标准,但均遭到反对,因此公约最终文本本身并未就法人投资者的国籍标准作出任何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心公约第41条虽然确定地表示仲裁庭是其自身权限的“法官”,有权将当事方有关中心管辖权的异议作为先决问题或实质争议予以考虑。但是,中心仲裁实践在认定法人国籍问题上并未任意行使这种自裁特权,脱离有关国家国内法而意图为公约发展认定法人国籍的所谓自治标准,上述认定法人投资者东道国国籍的标准仍然源于各该国国内法的规定;因此,如同自然人投资者国籍的认定,是否具有东道国国籍仍然须以该国国内法为准据法,而不论该国国内法采用何种法人国籍标准,超越国内法讨论法人国籍标准毫无意义。同时,上述案例中东道国和功能性国籍国均未缔结或参加国际投资协定,因而认定东道国国籍的准据法只能是该国国内法,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法人投资者的定义可能不同于缔约各方国内法上的标准,倘若存在此类国际投资协定,根据国际条约优先国内法适用的原则,法人投资者的东道国国籍应当依据国际投资协定予以认定。
(二)东道国国籍的保有
就中心管辖权而言,一国是否具有中心公约缔约国地位的关键日期不是争议双方同意中心仲裁之日而是仲裁程序启动即一方申请仲裁之日,该日期同时适用于东道国和投资者国籍国②Christoph H.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A Commenta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63.。与公约对自然人投资者适格性所需满足的时间条件不同,公约并不要求法人投资者在同意仲裁之日和仲裁申请登记之日均拥有公约缔约国国籍。因此,无论东道国是仅在中心程序启动之日获得缔约国地位抑或在同意中心仲裁之日即丧失原有的公约缔约国资格,均不影响中心管辖权。
法人投资者可因两种原因而丧失原东道国国籍而取得非公约缔约国国籍,其一是前述认定东道国国籍的准据法发生改变;其二是前述准据法未改变而该法人投资者自主进行变更。公约第25条(2)(b)第二段的目的是将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东道国法人与该国之间的投资争议纳入公约管辖范围,东道国在同意中心仲裁之后改变准据法,致使该法人丧失主体适格性,有违诚实信用和禁止反言原则,应不发生导致该法人丧失主体适格性的法律效力,尤其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原东道国在双方同意中心仲裁之日意欲成为公约缔约国,则更为确定无疑。鉴于公约第25条(2)(b)第二段是法人不得具有争议当事国国籍基本原则的例外,实质上构成东道国主权的限制以及此类法人投资者因此而享有利用中心仲裁机制而直接向东道国求偿的特权。因此,如果此类法人自行变更东道国国籍而取得非公约缔约国国籍,当然丧失中心仲裁程序的主体适格性。
二、法人投资者功能性国籍的确定
(一)外国控制的形式和程度
公约虽然在一般意义的缔约国法人国籍标准问题上保持缄默,但对争议双方通过协议将东道国公司视为另一缔约国公司规定了“外国控制”的客观标准。学者们普遍认为外国控制须由仲裁庭独立于功能性国籍协议单独予以认定③Gaillard,E.,Some Notes on the Drafting of ICSID Arbitration Clauses,3 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 136,1988,p.140;also see Moshe Hirsch,The Arbitration Mechanism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1993,p.102.,中心仲裁庭多次重申,根据第25条(2)(b)后半段规定,投资争议双方在东道国公司视为外国国民事项上仅享有有限的意思自治,双方不能通过功能性国籍协议将任何东道国公司视为另一缔约国投资者,功能性国籍协议或同意中心仲裁的协议只是中心享有管辖权的可反驳的事实推定(presumption),仲裁庭必须依职权主动审查有关事实,确定东道国公司在双方同意中心仲裁之日是否满足外国控制的客观标准,如果中心对未满足外国控制标准的东道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行使管辖权,将违背公约的目的①在Vacuum Salt公司诉加纳案中,原告为一家依据加纳公司法成立并具有加纳国籍的公司,公约缔约国希腊国民Gerassirnos A-lexis Panagiotopulos先生在双方同意中心管辖时拥有20%的股份,争议双方1988年签订的租赁协议中含有中心条款,原告是否因此而被认为是希腊公司对中心管辖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该案仲裁庭将此案与此前的Amco诉印度尼西亚、Klöckner诉喀麦隆、LETCO诉利比里亚,认为前述三案仲裁庭并非简单地依据原告东道国公司于被告东道国之间的中心管辖协议而认为主动满足了第25条(2)(b)后半段的条件,而是因为原告东道国公司中的外国控制的因素非常明显(Amco、LETCO全部所有权为外国控制,Klöckner51%的所有权为外国控制),因此,仲裁庭并未采纳原告公司的意见,简单地依据投资协议中的中心条款而认定中心对此案享有管辖权,而是通过审查有关事实,发现原告公司缺少外国控制因素,拒绝行使管辖权。See 4 ICSID Report,pp.342~343,344.。
投资者控制公司的形式多种多样,资本参与或股权比例是判断外国控制的重要依据,但并非总是可靠,管理和技术优势、决策影响力等也能对公司产生控制,公约并未明确规定外国控制的形式和程度,中心仲裁庭在不同案件中采取的路径也不尽相同。因此,提出的认定外国控制的三条基本思路较具方法论价值:第一,无论采用何种标准,如果外国投资者拥有100%股权则可以肯定地被认定为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第二,外国投资者完全不拥有股权亦当然排除外国控制因素的存在;第三,作为认定外国控制的股权比例很难抽象地确定,但外国投资者拥有的股权越小,中心仲裁庭就应该考察其他因素,如管理权、表决权、决策程序等任何其他合理标准。该案仲裁庭据此认为原告公司为希腊公民控制的依据不足,该公司仍为东道国公司,仲裁庭不享有对该案的管辖权。
(二)非公约标准与功能性国籍的确定
一些含有中心条款的国内外国投资法和IITs将具有外国控制或某些涉外因素的本国或缔约一方公司视为外国或缔约另一方公司,这些非公约标准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重述型和自治型,前者基本照搬公约规定,仅规定东道国公司因为外国控制得被视为外国或另一缔约方投资者②如荷兰和瑞士BIT范本,see Rudolf Dolzer & Margret Stevens,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pp.214,224/5.,因而中心仲裁庭可依前述方法认定功能性国籍;后者则规定了东道国公司功能性国籍的标准、形式及程度,与公约相比,进而可分为非特定型和特定型,其在中心仲裁庭认定功能性国籍中的作用有所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非公约制度除上述积极性外国控制标准之外,有些IIAs还确立了消极性的外国控制标准,即规定虽然缔约一方公司具有某种被缔约另一方投资者控制的因素,但不得将其视为缔约另一方公司,典型适例如中-瑞士BIT(1987)第1条2(2)规定投资者包括“依照缔约任何一方法律设立并且住所地在其领土内的所有经济实体或法人,或者由缔约任何一方国民或依照缔约任何一方法律设立并且住所地在其领土内的法人或经济实体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有经济实体或法人。”但议定书第一条明确该定义不适用于瑞士(中国)投资者依照中国(瑞士)法律在中国(瑞士)领土内设立的经济实体或法人。缔约方之所以将此类公司排除在外,表明如果将其视为缔约另一方国籍(功能性国籍)投资者而适用该IIA有违东道国重大经济利益,不愿赋予其中心仲裁程序主体的资格,中心秘书长和仲裁庭对此消极标准理应予以承认和尊重。
(三)功能性国籍的保有
公约第25条(2)(b)后半段要求作为争议当事一方且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公司必须在同意中心管辖之日具有东道国国籍,也就是说,东道国公司受外国控制的事实在争议双方同意中心管辖之日即已存在,从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关于公约报告第30段关于该条的解释对此给予了进一步印证。此类公司的东道国国籍自争议双方同意中心管辖时即较为固定和明确,而中心仲裁规则第2条并不要求双方在同意中心管辖协议及功能性国籍协议中就对功能性国籍予以特定化,而只是要求申请仲裁一方在中心秘书长登记之前确定功能性国籍国,因此外国控制者国籍在争议双方同意中心仲裁之后和仲裁程序启动之前可能发生变化,即使争议双方在同意中心管辖之日已经确定了功能性国籍国,随后由于外国控制权的转移导致非原功能性国籍国的公约缔约国投资者单独或联合控制,自然并不影响中心仲裁管辖权③Christoph H.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A Commenta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331.。然而,当东道国公司在争议一方申请仲裁时转为东道国或非公约缔约方投资者控制,其对中心管辖权的影响引起了学者和中心仲裁庭的关注。
笔者以为,应当区分东道国公司外国控制在争议双方同意中心仲裁之日后发生转移的不同原因而决定各自对中心仲裁管辖权的效力。东道国公司控制权发生移转的原因不外两类:自愿转让和强制转让,前者因东道国外国控制股东与东道国或非公约缔约方投资者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而导致控制权转移,交易各方理应知晓并承担丧失诉请中心裁决投资争议的法律后果,因而中心仲裁庭不再享有管辖权。后者最为典型的是由于东道国逐步本地化(progressively localization)策略的实施或征收而为东道国投资者控制,如果东道国在逐步本地化既定的情况下仍同意将其此类公司的争议交由中心仲裁或者嗣后颁布逐步本地化策略或实施征收行为,依据诚实信用和正当期望原则,当不发生由于缺乏外国控制因素而否定中心仲裁管辖权的效果。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一些IIAs明确规定为了公约第25条(2)(b)后半段的目的,缔约另一方投资者须在“争议发生前”或“产生争议的事件发生前”控制缔约一方公司①如英国BIT范本(2005)第8条(优先)(2)、荷兰BIT范本第9条、ECT(能源宪章条约)第26条(7)规定该时间是“争议发生之前”,see Campbell Mc Lachlan QC,Laurence Shore,Matthew Weinige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Substantive Principl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82,425;34 ILM 1995,pp.248/9;美国BIT范本第6条(8)规定该时间为“产生争议的事件发生前”,Christoph H.Schreuer,The ICSID Convention:A Commenta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330.,可被视为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因此判断东道国公司是否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关键时间是投资争议或者导致投资争议的事件发生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存在四个时间:争议双方同意中心仲裁之日、产生争议的事件发生之日、投资争议发生之日和申请仲裁之日②在中心仲裁实践中,Maffezini诉西班牙、Lucehetti诉秘鲁等案仲裁庭注意区分了产生争议的事件(event/events)发生时间与争议产生时间之间的区别。前案被告国依据阿根廷-西班牙BIT适用于条约生效之后的投资争议的规定,主张其与原告之间的投资争议(实际上是产生实质争议的event/events,而非争议本身)发生在阿根廷-西班牙BIT生效之前,从而提出管辖权异议,该案仲裁庭注意到了导致双方发生争议的事件产生于该BIT生效之前,但并不意味着那时已经发生了争议,“事件导致争端是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而争议则产生于当事方分歧的表达和不同观点的陈述,即使产生争议的事件发生在前,其只有通过法律请求权的形式才能获得精确的法律含义,此时方能产生当事方法律观点及利益的冲突”,导致双方争议的事件虽然发生在阿根廷-西班牙BIT之前,但争议却在该BIT生效之后才发生,因此驳回了被告国的管辖权异议;后案涉及的BIT规定不适用于条约生效之间产生的争议,该案仲裁庭认为双方之间的投资争议实际上早在该BIT生效之前就已产生,因而裁定仲裁庭并无管辖权。See Rudolf Dolzer,Christoph Schreuer.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41~44.,显然,在争议双方关于同意中心仲裁的协议与功能性国籍协议成立于不同时间时,此类IIA中所谓产生争议的事件发生时间和投资争议发生的时间均早于仲裁申请之日;而当争议任何一方直接根据此类IIA中的中心条款(相当于以法律条款形式体现的standing/general offer)提起仲裁申请(相当于acceptance)时,同意仲裁之日即为判断是否存在外国控制之日。质言之,如果东道国公司在争议双方同意中心仲裁之日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控制,即为满足公约第25条(2)(b)规定的属人管辖条件。
三、功能性国籍协议的形式要求
公约第25条(2)(b)后半段并未明确规定功能性国籍协议的形式要件,因此,与争议双方关于中心仲裁的同意一样,功能性国籍书面协议或条款、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东道国公司根据东道国国内立法以及国际条约中的相关条款(相当于东道国的standing/general offer)提起仲裁申请(相当于acceptance)足为满足功能性国籍的形式要件,当然并无疑义;然而,在争议双方并不存在前述书面和独立的明示(explicit)功能性国籍协议情形下,同意中心仲裁的协议是否可被同时视为争议双方在功能性国籍上隐含(implicit)的共同意思表示,学者学说和中心仲裁实践分歧较大。
中心仲裁实践越来越倾向接受隐含的功能性国籍协议。在假日饭店诉摩洛哥案中,原被告之间并无明示的功能性国籍协议,被告坚持“清晰和明确的共识是必要的”,原告则认为其是为了被告的利益且是应被告的要求而设立的,被告国也承认其完全为外国控制并一直将其作为外国控制公司,表明被告已经同意将其视为另一缔约国国民。仲裁庭讨论了功能性国籍协议究竟应该为明示还是可为隐含的问题,认为功能性国籍构成公约确定的一般原则的例外,当事双方应该清晰和明确地予以表达,只有在存在某些排除对当事方意图作任何其他解释的特殊情形时,隐含的功能性国籍协议方可接受,否则此种协议通常应当是明示的①Cable TV v.St.Kitts Nevis,Award,13 January 1997,13 ICSID Review-Foreign Investment Law Journal,1998,pp.328~370.。本案原被告并无此种意图,因而仲裁庭认为原告非中心程序的适格主体,同时还引用了示范条款,表明仲裁庭认为如果东道国将其本国公司视为另一缔约国国民的意愿一般应当表现为“附属协议”的形式②Tupman,W.M.,Case Studies 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35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1986,p.813.。
因此,中心仲裁实践在功能性国籍协议形式要件的要求极其宽松,当事方同意中心仲裁的协议即为功能性国籍协议,但是招致了坚持功能性国籍协议为独立于同意中心仲裁协议学者们的批评。比如Amerasinghe就认为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当事方之间的同意中心仲裁协议都可解释为东道国承认了本国公司的外国国籍,惟有在当事方有直接接触和签订直接协定的情况下,方可作此推断,如果同意中心管辖权是基于东道国立法或有关条约,则并不存在功能性国籍协议。
此外,中心仲裁庭关于外国控制因素的追溯实践也表明并不以专门和独立的功能性国籍协议为必要条件,中心仲裁庭基于外国控制的客观标准而追溯东道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此种实际控制人在很多时候并非同意中心仲裁条款的当事方,但并未影响中心仲裁庭的管辖权。
从以上中心仲裁实践可以看出,中心仲裁庭在同意形式上经历了由明示同意为主有条件采用默示同意到两种同意方式的并行使用。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心公约第25条第2款第2项所要求的同意可以采取默示方式,但是仲裁庭不能仅仅根据东道国知道当地公司受到外来控制这一事实,或者仅仅根据投资协议双方订立的中心仲裁条款这一事实,就推断当事人双方同意将在东道国设立的当地公司视为中心公约意义上的外国公司,而是应该根据投资协议在实施过程中双方的履约行为或其他相关的实际行为加以推断,而不应该根据投资协议本身加以推断③陈 安:《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5页。。
杨卫东,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102206。
郭 堃,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法学硕士。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10YJA820121)
车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