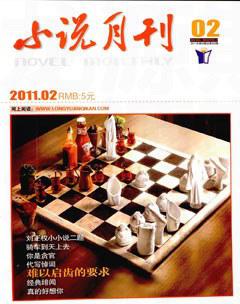沈传生
宋以柱
沈传生是从小水村跑到镇上开饭店的。
那时,土地包产到户刚几年,看着一大片地,沈传生愁的差点把自己的脑袋摁进地里去。到了玉米及膝的时候,土地松软,水份足,该套种豆子了。沈传生到了地头,左看右看,找块平整的石板,扛到地头树荫下,抱着镢头,倒头就睡。睡足了,掀起石板,把豆种往下一倒,回家了。到除草的时候,沈传生又找上了那块石板,一头高,一头底,正好靠着睡觉,一靠,平着就倒下去了,掀起来一看,压烂了一窝豆苗。
娘哭爹骂,骂急了,他跑到镇上不回来了。
大凡懒人,都得先解决饿肚子的问题,谁知道沈传生哪来的本事,在镇上开了第一家饭店,还娶了镇驻地村书记的女儿。一改革,一开放,镇上的生意人就多了,开油坊的、开商店的、理发的、修理自行车的,一夜之间就冒出来,也有买了拖拉机、汽车,搞货运的,一条街热闹起来了。沈传生捏着粗瓷茶壶,坐在树荫下,冷眼打量来来往往的车辆人流,来了收货的、送货的,都得进饭店招待,都得给我送钱。还真让他揣摩准了。
沈传生掌厨,大个子妻子配菜、管账,找个帮手送菜、迎来送往、打扫卫生,饭店的生意好起来了。第一次回小水村,沈传生骑铮亮的永久牌自行车,上身雪白的衬衣,袖管高高挽起,一块手表就在腕子上耀眼,村里人就说,这世道要变。
外镇的来了,外县的来了,外省的来了,操着各种口音,穿了各色衣服,要求菜的口味就更不一样。儿子长发,白脸,贼眼,正在读初三,给沈传生一鞭子赶到济南学厨师去。学了半年跑回来,带回来一个济南的媳妇,还不到结婚年龄,就先在饭店帮忙。儿子倒也争气,干得很带劲,菜的花色品种一多,客人就多起来。街上的生意人、客户都来。看看这阵势,沈传生跑村上要地皮,崴过年去,一憋气盖起带地下室的三层楼,客人来了可吃可住。爷娘年龄大了,干不动了,沈传生安排爹娘到镇上来晒太阳。爷抽商品烟,云门牌或者大鸡牌,一天三顿辣酒,露着黑牙红牙龈,没事直嘿嘿,或者到桥上看一会儿玩水的,钓鱼的,回来坐树荫下,点烟,烫酒。爹疼烟酒,沈传生喜茶。
迎来送往的,到了九十年代尾巴梢上。
相熟的客,有钱的主,沈传生就抱了一瓶好酒,攥两盒讲究一点的烟,坐下手,敬几杯,说一番客套话,再让厨房加两个菜。熟人遍地是,人也就活泛,算是镇上的一个角了。镇上经济靠水果种植、贩卖,南来的,北去的,多了去了。来饭店的水果贩子都拿眼瞅柜台上的儿媳妇,送菜的小服务员,醉了的就说话不中听。沈传生看在眼里,晚上,跟儿子一合计,把地下室倒腾出来。看出来儿子兴致很高,亲自租辆车跑到济南附近的一个县,领回来三个短装黄毛的丫头。外地的客人多了,呆的时间也长了。本镇的客户却来的少了,想来的怕人家指指戳戳,年龄大一点的,干脆就在街上骂。沈传生的爹不太习惯,骂了几句,沈传生拾起爹的南泥壶往红水河里一扔。老头的声音就小了。
沈传生长就的一副青皮楞头相。
儿子跑了,还有一个地下室里的黄毛丫头,还有一摞数目不小的存折。沈传生已经掂不动大勺了,但没事一样,找来一个厨师,干了不久,老婆不让来了,加钱也不干了。再找一个,半路上撂挑子,受不了沈传生老子有钱的熊样。折腾了几次,来光顾的就少了,黄毛丫头也留不住南来北往客,和客人一块不见了。半年时间,沈传生的贵宾楼就空了。沈传生开始坐在楼下的闲地上喝茶抽烟骂人。要不到这份上,他会把房子租给沈玉生,他几时拿眼皮夹过沈玉生这号人?
儿子是一年后和警察一块回来的。不足一米六的儿子成了大盗。回来一趟,看看爹娘媳妇儿子,又走了,去的那个地方不近,不可能有饭店,在济南学的手艺八成要荒废了。饭店没法开了,就找人说合着,包出去,一家老少住到地下室去。很晚了的时候,喝一口苦茶,听楼上各种口音吵吵闹闹。或者到洪水河边,听蛙鸣,听鱼跃起的水声。
学校门前突然就多了一副车,两轮,有一个大棚子,双层,上面左边一个锅子,锅里是油,冒着热气,右边几个不锈钢盘子,摆放着待炸的鸡腿、小鱼、火腿肠、蘑菇等,下面一层是一个液化气罐,塑料管连着锅子下面的气灶。旁边站立的正是沈传生。正是深秋,风冷且硬,沈传生蜷缩在大衣里,只露出一只手往嘴角递烟。出来一个校警撵他走,不让在学校门口摆摊卖三无食品。沈传生梗着脖子不让:老子天天吃这个。你是谁老子?校警很年轻,上前猛推了一下沈传生的肩头。沈传生的拳头攥了两攥,又慢慢舒展开来。
我等等就走,我等我孙子,他在里面上学。
说完,沈传生努力地把目光投向学校校园。
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张家坡镇教委 256113 13583349148
——站在树荫下也能减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