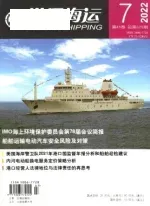中国航海历史的形成时期——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文/ 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孙光圻
中国航海历史的形成时期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文/ 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 孙光圻
西周末年,奴隶制度历盛而衰,出现崩溃趋势。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继位,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史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中国古代航海事业基本形成。
一、春秋战国的航海活动
(一)海上强国的出现与海上战斗的频繁发生
春秋战国,各诸侯大国十分重视建立海上武装力量,如齐、吴、越都是有着庞大舰队的海上强国。
1.“海王之国”——齐国
春秋前期,齐国向东方通往大海的途径仍被由莱夷族、东夷族等组成的莱国所阻断。公元前7世纪中期,齐桓公成为东方霸主,并将势力影响扩展到山东半岛东部,“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公元前567年,齐国征服莱国,辖地扩达,成为能直接控制环山东半岛以及渤海航行的海上强国。据《孟子·梁惠王下》称: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至公元前5世纪初的齐景公即曾对晏子说:“吾欲观于转附、朝舞(今山东半岛东北端成山),遵海而南,放于琅邪(今山东省胶南县琅琊台西北)。”由此可见,从山东半岛北部出渤海海峡,再循黄海沿岸南下至胶州湾一带的航路已被打通。这条黄渤海航路还可以延伸直达东海钱塘江口。关于齐景公的航海活动,《说苑·正谏篇》中说他曾“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此时,齐国已掌握了山东半岛沿海的航行权,海船也已相当可靠和舒适,沿海航行相当活跃,舟来船往,习以为常。
2.“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吴国
吴国地处今长江下游的沿海地区,定都于吴 (今江苏省苏州市吴县),是一个“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江南海上强国。史料中曾记载楚人伍子胥投吴后,与吴王阖闾谈论如何训练“舡军”(即水军) 时说:“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今舡军之教比陵军 (指陆军) 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由此可见,吴国水师的兵力、阵法、法度等已颇为齐备,充分反映了其航海实力之强盛。
3.“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越国
越人与吴人一样自古习于航海,有文身断发习俗。东汉人应劭解释说,由于“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越王勾践曾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由此不难看出越人相对发达的造船业与相对高超的航海术(见图1)。

为了与邻近的宿敌吴国争霸,越国也建立了强大的水师。《吴越春秋》中说,越有“楼船之卒三千人”。《史记》中说,勾践有“习流二千”,“所谓‘习流’,是即习水战之兵”。公元前494年夫椒之战,越与吴“战于五湖 (今太湖),不胜,栖于会稽”。勾践遭此惨败,仍不忘霸业,他卧薪尝胆,又建立了一支精锐的水军。公元前482年,越王勾践乘吴王夫差率大军北上黄池 (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与晋争做霸主之机,指挥越军攻入吴都,并“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泜淮,以绝吴路”。吴王闻讯,由黄池返回驰救,双方舟师在淮水中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干遂之战”,结果吴国大败,从此一蹶不振。越王勾践取夫差而代之,成为一代霸主。
(二)沿海航路与大规模的海上运输
春秋战国时期,海上强国之间的争霸斗争对沿海各区域以及通海江河各水段的航路通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渤海与渤海海峡横渡的航路,环绕山东半岛的航路,由浙江沿海至山东半岛的航路,江浙闽粤之间的沿海航路以及江水、河水、济水、淮水、泗水各大川的航路和人工运河,太湖等航路都成为当时舟船频相出没的交通干道。“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说明一个江海交叉的综合航行网络已开始形成。
在航路通达的同时,各濒海沿江的诸侯国大力发展水上航运,利用船舶作为运送物资、人员的交通工具,即使偏隅内地的国家也尽力凭借江河而为之。如秦国司马错攻楚时,即动用了“大船舶万艘”,运送“巴蜀众十万”和“米六百万斛”。《史记》记载,秦国船队中,“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
为有效地推动并控制水上运输,有的诸侯大国已着手航运管理。如在1957年出土于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的“鄂君启金节”,即为战国时期楚怀王赐给鄂地封君启的行路符节。其一为“车节”,其二为“舟节”。“舟节”即特许的水上航运优惠通过凭证,上面规定了船队规模,“屯三舟为一舿,五十舿”;航行区域“自鄂往”湖北、湖南、江西的水路范围;征税办法“见其金节则毋政 (征)”,“不见其金节则政”。这不但反映了春秋战国水上航运之发展,而且开拓了其后千余年唐宋市舶管理制度之先河。
在海上运输方面,越国两迁其都的海上航行,规模最为显赫。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充分利用擅长航海的国家优势,在联系山东半岛与三江五湖的战略要地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并从会稽“徙都琅邪”。这是第一次江海航运迁都。第二次迁都是在越王翳三十三年 (公元前379年)。其时已值战国,越国传至五世越王翳时,国威大为下降。在强敌压境、内治衰微之下,越国在山东半岛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复去琅邪,迁都于吴。越国两迁首都,人员之多,军辎之重,物资之巨,舟船之众,自不待言。史籍上说,越首次迁都时,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还曾使楼船士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为桴”,其海上航运规模之盛由此可窥一斑。
(三)越海航行、远洋探索与海外贸易
在沿海航行活跃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的越海航行与远洋探索有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4方面:
1.越人横渡台湾海峡的航行已呈现出主动的迹象
《越绝书》载,“勾践徙治山北,引属东海内外越”。在春秋时期,越国曾盛极一时,领有大越、内越与外越之地。外越,当指东海之外勾践所领有的海外越地。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兵讨伐闽越时,闽越王弟余善曾图谋举国“亡入海”,迁居海岛。这些越人的海外领地,据《汉书·朱买臣传》称,“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这个 “大泽”,正是“自泉晋江东出海间,舟行三日抵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的“巨浸”,亦即勾践领有“外越”之一的澎湖列岛。澎湖之地,密迩台湾。越人既能至澎湖,那么东临台湾就易如反掌了。《临海风土志》载,“夷州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石也”,越王射石即为越王统治之象征。
2.寻找海上“三神山”的探索活动
春秋战国,人们的地理视野早已越出黄河、长江流域而展向海外,但由于航海实践能力有限,对海洋充满着许多神秘的遐想,盛传着在燕齐东面的海洋中有神山仙岛的神话。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作过形象的描述:“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 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行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自在焉……其物禽尽白,而黄金为宫阙。未至,望之为云,及到三神山,又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
从司马迁这段文字可揣测当时远洋探险的几点特色:其一,远洋探险航行并非凤毛麟角,而是时有活动,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曾多次派遣船队出海远航;其二,既由一国君主所遣,航行规模及航具设施当具有相当之水准;其三,三神山在渤海中,且曾有人到过;其四,当时远航已用风帆,然因不能掉戗驶风,而被风引来引去,终莫能至。显然,寻找三神山的航行,实质是人们前赴后继,向深海大洋探险活动的曲折写照。
3.远航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
我国山东半岛与黄、渤海地区居民对朝鲜半岛的航海地理位置的认识,到战国时已见诸古文献。《山海经》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东海”指今之黄海,“北海”,其时则指今之渤海。当时人们已知道朝鲜在今黄海水域,与渤海相距不远。这样,沿着渤海海峡中的庙岛群岛与辽宁南岸,海船就不难驶达该域了。同时,随着朝鲜半岛沿岸航迹的延伸,当时中国人已航至半岛的南部与东南部了。朝鲜半岛南部多次发现具有中国战国时代文物特色的铜铎、铜剑等,说明了当时的航海者已来往于黄海两岸。
随着中国海船到达朝鲜半岛南岸和东南岸,那么跨海去日本列岛就顺理成章了。《山海经》中说:“倭属燕”,“巨燕在东北陬”。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已知道倭在朝鲜半岛南面,有些苦于战乱兵祸的北方沿海居民纷纷以朝鲜半岛为中介,渡海至日本列岛,并带去先进的金属文化与水稻种植技术,使处于石器时代并过着原始渔猎生活的日本开始从绳文式文化的长期缓慢发展中摆脱出来,向着使用金属工具和进行水稻种植的弥生式文化飞跃转变。
4. 南海的海上贸易
在南海的航海活动方面,散布在我国东南沿海的越人是主角。越国的主要根据地在今浙江省境内,但越族人的分布很广,往南自今福建、广东以至越南的北部,其沿海地区及附近岛屿皆为越族居住地。越国为开展政治、外交活动,常利用越人在南海活动并与海外进行贸易的方便条件,以奇珍异宝来拉拢同盟或者缓解敌对者。楚国称霸时,百越朝贡,楚王竟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楚王之珠玑、犀象,无疑是来自百越朝贡。至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楚王趁越内乱而灭越国,把江东建设为郡。越虽“朝服于楚”,但“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仍控制着南海的航海贸易,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大军50万经略岭南,其目的还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海外传统商品。在春秋战国时期。越人主要通过珠江口的番禺 (今广东省广州市) 进行航海贸易。“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在南海之上舟船往来、互通有无的航海贸易景况。
二、 航海知识与技术的奠基
(一)航海地理知识
春秋战国之前,由于航海活动与能力所限,人们常把海看做世界的边际。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察目光开始伸向海外。邹衍的“大九州”说,海上“三神山”的传说,充满神奇色彩的《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解》,以及较为真实的《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等问世,反映了航海地理知识在大胆和迷惘的追求中得到空前的发展,已经开始懂得海洋并非世界边际,在海洋中还有很多已知和未知的陆地与岛屿。同时,也开始将中国大陆外侧的水域划分为几个不同向名称的古代海区。如将今天的渤海称为“北海”,今天的黄海称为“东海”,今天的东海称为“南海”。
(二)海洋气象知识
春秋战国的海洋气象知识主要体现在对风的认识上。《吕氏春秋》提出八风的概念。“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飓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周礼·春官》又说:“保章氏……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所谓“十有二风”,即“从子至亥”的十二辰(十二支) 之风。即:子是正月,风向来自北;丑是二月,风向来自东北偏北;寅是三月,风向来自东北偏东;卯是四月,风向来自东;辰是五月,风向来自东南偏东;巳是六月,风向来自东南偏南;午是七月,风向来自南;未是八月,风向来自西南偏南;申是九月,风向来自西南偏西;酉是十月,风向来自西;戌是十一月,风向来自西北偏西;亥是十二月,风向来自西北偏北。
在认识风的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气象预测知识也比前代有了进展,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三)海洋水文与天文知识
春秋战国时,人们对潮汐的认识日趋明确。 “朝宗于海”,开始懂得了潮汐与海洋的关系。《禹贡》中也说:“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这段文字说明当时的航海者已能利用潮流进行航行了。
这一时期,天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沿黄、赤道带将临近天区划分成28个区域的28宿体系已经齐备,为度量日、月运动的空间位置提供了参照坐标。对夜间航行定向价值最大的北极星已有所记载。古文献中有“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说,据考,“璇玑玉衡”可能即为观测北斗七星位置的天文仪器。《周髀算经》中也对此曾有描述。另外,《韩非子·有度篇》中已有“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记载,这种碟匙式的测向仪器虽然主要用于陆上,但在海上应用的可能性也不能说绝对没有。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从此,中国航海事业走上发展和繁荣的道路。